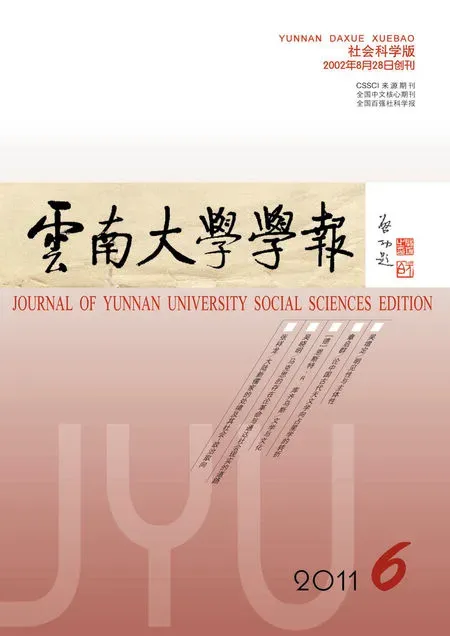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论哲学及人文学的分科
2011-12-08唐文明
唐文明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论哲学及人文学的分科
唐文明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哲学;教化;科学;人文学;经学;王国维
1898年到1907年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其时他认为哲学是出于人的精神的内在需要,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并强调哲学是人文教育的根本。针对清政府于1902年、1904年分别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大学人文学分科方案。这一方案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哲学来代替经学的地位,其背后隐含的是以哲学代替宗教的思想。1907年,王国维宣布放弃哲学研究。后人常常根据他“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自述,认为他是出于情感和兴趣上的原因而放弃了哲学,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科学的认同使他无法再相信他原本就喜欢的形而上学。而这也是他转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的方法可以充分运用于史学,且史学也是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一种方式。他写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实质上就是为可以充分运用科学方法的史学张目。1912年,王国维在日本以烧毁《静庵文集》的激烈行为明志,从此明确走上了以史学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道路。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滥觞于西学东渐以后。以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概念、命题、思想以及体系框架为基础,整理、分析、阐述、评断中国传统思想,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常常只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其实这是不够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对于应被恰当地理解为诠释学的人文学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科学方法的问题,而在于精神真理的问题,因为人文学的宗旨乃是教化。这就提示我们,在反思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时除了要留意于方法的问题之外,还要留意于真理和教化的问题。就此而言,方法论上的改变自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哲学就其合理的目的而言乃是企图以哲学的进路接引古典教化传统,是对古典教化思想的现代诠释。在前几年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真理与方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澄清,从而产生了一些混乱。这种反思性的讨论也促使我们将目光转向近代以来经学解体而代之以文学、史学、哲学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王国维显然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王国维对于哲学、文学和史学的研究都有所尝试,而他的这些尝试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建构都具有典范意义。本文论及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对哲学及人文学分科的看法,并理出王国维从哲学转向史学的思想线索,进而反思中国现代人文学接引中国古典教化传统的努力和不足。
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大约是从1898年他入东文学社开始。在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等日籍教师那里,他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生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1](P119)1901年夏,王国维结束了在日本不到半年的留学生涯回国,此后便决定从事于哲学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究人生问题:“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复往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1](P119)此后一直到 1907 年,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①1906年6月,王国维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第129期上刊登了自己的一张半身照片,所附说明是“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他撰写的与哲学有关的文章及其翻译的哲学著作,大都写作于这个时期,且大都发表于这一时期他负责编辑的《教育世界》杂志。1907年是王国维告别哲学的时间,但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哲学撰述以及以哲学为指导的文学撰述 (即美学研究,如《红楼梦评论》)颇为自信:“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苻曩则,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1](P120~121)而且,他对于哲学和文学的深切情怀在他对哲学和文学倍感绝望之际仍得以保留:“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2](P122~123)
综观王国维这一时期所写的与哲学有关的文章,可以概括出他关于哲学的一些基本看法。首先,王国维指出,追求真理是哲学的要务:“苟研究哲学,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是从。”[3](P7)王国维此处所谓真理,当然是指与人生观、宇宙观有关的精神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真、善、美是与人生问题有关的三种价值,而“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3](P8)王国维认为,哲学所追求的有关真善美的原理是跨越时空的永恒真理,而哲学之所以神圣,正在于此:“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 (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 (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4](P131)
其次,王国维在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下提出哲学思考的冲动来自于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在精神上特有的形而上需要:“饮食男女,人与禽兽之所同,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则岂不以理性乎哉!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日夜相迫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释者,不得其解,则心不宁叔本华谓人为‘形而上学之动物’,洵不诬也哲学实对此要求而与吾人以解释。”②参见王国维:《哲学辨惑》,见《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7页。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对人与禽兽之别的说法稍异,除了提到与理性对应的知识之外,还提到了情感,而这又和他以哲学与美术皆志在真理的看法相一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见《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31页。以理性为人之所异于禽兽者,这一看法自然来自于西方哲学传统,其思路不同于中国思想传统。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对于宇宙、人事之解释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乃至核心的主题,但关于这一点并不从人与禽兽之别的思路上立论。比如孟子的著名看法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乃在仁义
第三,既然哲学源于人在精神上的根本需要,那么,哲学就具有其内在的价值。王国维顺此推论,认为以哲学为无用之学而非难、拒斥哲学的做法错失了对哲学之意义的真正理解“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5](P34)既然形而上的需要是人在精神上的根本需要,而哲学恰能满足人的这种需要,那么,即使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哲学仍然是有益之学。在这里王国维主要强调的是哲学之于教育的价值:“况哲学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辞其为无用之学;而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5](P35)“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3](P8)因此, “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3](P9)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在王国维那里,说哲学具有独立的乃至神圣的价值与说哲学的功用乃在教育这二者并不矛盾。①虽然有时他在为纠偏而进行的辩驳中所使用的表述容易引起误解,比如他在强调哲学以及美术的独立价值时说:“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见《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33页。在写作于191年的《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则说:“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又说:“事物无小大,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见《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132页。他的意思统而言之是说,哲学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中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中的精神需要,而这种精神需要恰恰能够表达出人类生活的内在旨趣,恰恰意味着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王国维将哲学的功用定位于教育无疑受到了西方哲学——更具体地说是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的巨大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他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的使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至于教育的宗旨,从社会功能上说,乃在于“增进现代之文明”;从具体内容上说,正如上述引文所说,乃在于人格的成就与完善。王国维曾专门撰文讨论教育的宗旨:“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 育 (意 志)、美 育 (情 育)是也。”[6](P9~10)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关于美育的看法。在《去毒篇》中分析“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时,王国维将中国人沉溺于鸦片的原因归结为情感上的无希望、无慰藉,并以此为由明确反对以国民资格之劣、国民知识之缺乏或国民道德之腐败来解释其原因的看法: “今试问中国之国民,曷为而独为鸦片的国民乎?夫中国之衰弱极矣,然就国民之资格言之,固无以劣于他国民。谓知识之缺乏欤?则受新教育而罹此癖者吾见亦多矣;谓道德之腐败欤?则有此癖者不尽恶人,而他国民之道德,亦未必大胜于我国也。要之,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于感情上而已。”[7](P63~64)在此思路上,王国维甚至肯定了鸦片对于中国人生活的积极意义,即能够使人在不断交替的苦痛与空虚中得到暂时的慰藉:“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欲望之将达也,有希望之快乐;不得达,则有失望之苦痛。然欲望之能达者一,而不能达者什佰,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若胸中偶然无一欲望,则又有空虚之感乘之。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无非欲祛此感而已。彼鸦片者,固遣日之一方法,而我国民幸而于数百年前发见之,则其鹜而趋之固不足怪。”[7](P64)最后,王国维提出,去鸦片之毒的根本方法在于政治之修明与教育之普及,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即是情感教育,具体来说则在宗教与美术:“故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合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7](P64~65)
王国维对宗教和美术的肯定是从其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的,即二者都能够给人以情感上的希望或慰藉。将宗教和美术紧密关联于国民的情感教育,王国维的这个看法与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蔡元培是一致的。就思想资源而言,二者都深受启蒙时代以来德国哲学的影响,这也是很清楚的。①在启蒙以来的德国哲学传统中,康德企图在纯粹理性的限度内重构宗教,于是提出了理性宗教或道德宗教的概念;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看法,又以哲学为宗教的扬弃。将宗教信仰与情感直接挂钩的则是施莱尔马赫。至于将审美与人的情感能力直接挂钩的,以康德为典型。表面上看来,王国维认为宗教和美术二者皆不可废,这是他与蔡元培持论不同的地方。但实际上,他也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宗教的。王国维已经明确地将宗教与鸦片相提并论,他的看法实际上和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相差无几:“今夫蚩蚩之氓,终岁勤动,与牛马均劳逸,以其血汗易其衣食,犹不免于冻馁。人世之快乐,终其身无斯须之分,百年之后,奄归土壤。自彼观之,则彼之生活果有何意义乎?而幸而有宗教家者,教之以上帝之存在、灵魂之不灭,使知暗黑局促之生活外,尚有文明永久之生活;而在此生活中,无论知愚贫富,王公编氓,一切平等,而皆处同一之地位,享同一之快乐;今世之事业,不过求其足以当此生活而不愧而已。……彼于是偿现世之失望以来世之希望,慰此岸之苦痛以彼岸之快乐。宗教之所以不可废者,以此故也。人苟无此希望,无此慰藉,则于劳苦之暇,厌倦之余,不归于鸦片而又奚归乎?”[7](P65)如果说有关美育的原理最终仍然要靠能够满足人的形而上需要的哲学来解答的话,那么,隐含在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看法其实是以哲学代替宗教。②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论亦当从此解。“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是仅就情感教育而言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宗教主要是在教育的意义上来说的,美育的背后其实是理性,正如宗教的背后是信仰一样。
王国维对哲学的这些基本看法,最后都归结在一个重要的主题上,即如何看待、理解、诠释、接引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问题,大概也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王国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约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他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今姑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及宋儒之学言之。夫六经与宋儒之说,非著于功令而当世所奉为正学者乎!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 《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3](P8)取六经、诸子及宋儒之学而以哲学论之,意味着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中,至少在经、子和集中都有不少属于哲学的部分。③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亦具有学科分类的意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其次,他认为中国固有的哲学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其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3](P8~9)对此,王国维亦有更为具体的论述和进一步的发挥: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8](P127)由中国固有之哲学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这一看法,王国维引申出了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3](P9)王国维对中国固有思想的批评以及他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主张,明显是从西方哲学的眼光中而来的“他者的镜像”这与他受日本近代学术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这一思路也正是后来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路。1918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在蔡元培所写的序言中也曾明确提到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一个难处正在于“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9](P1)后来,冯友兰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看法,认为中国古代思想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却有实质上的系统,并以此为要点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哲学史的方法,是黄宗羲《宋元学案》的方法。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哲学史家的工作,首先是要把某一哲学家的思想的实质系统整理出一个形式的系统,黄宗羲的学案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基本上仍然是一种编排史料的工作。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确实是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实质系统加上了一个形式的系统。虽然其所加的未必全对,但在中国学术界,则是别开生面的。”[10](P70)如果考虑到王国维还写了 《论性》《释理》、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孔子之美育主义》、《周秦诸子之名学》、《墨子之学说》、 《原命》、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等很多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那么,很显然,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无论是从诠释方案还是从具体实行来看,王国维都是更早的先驱。
第三,直面“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之大势,王国维还以能动与受动的往复循环立论,提出了中国思想开展之诸期说: “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造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绎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11](P121)王国维以西洋思想为第二佛教的看法,值得留意,其背后隐含着的信念是:中国思想正在经受又一个受动时代,欲图能动则必走调和中国思想与西洋思想之路,正如宋儒调和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一样。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对于中国固有思想的发展前景并未因西方思想的强势进入而有所动摇,反而充满了自信,他认为西方思想要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安顿,须力图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11](P125)
第四,顺着上面的思路,王国维也评论了当时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改造中国古代学说的一些做法,具体来说主要针对的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其有蒙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于吾国思想界上占一时之势力者,则有南海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浏阳谭嗣同之《仁学》。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然康氏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以为禽犊’者也。谭氏之说则出于上海教会中所译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学之‘以太说,半唯物论,半神秘论也。人之读此书者其兴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学,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见。”[11](P122~123)
王国维的这一评论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其一是他的人文主义立场,即以宗教为迷信以泛神论来理解康有为的以元统天说;其二是他对当时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敏锐观察,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皆以学术为政治之手段。第二点尚有可说者。教化与政治的关系颇为复杂可合而言之,可分而言之。从精神层面上说教化精神高于政治精神并规范着政治精神,就是说,政治赖以成立的基本理念来自于某个人群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而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往往依存于教化;从制度层面上说,政治制度高于教化制度并约束着教化制度,就是说教化制度既然设立于国家这一最高的政治制度之内,就必须接受其统治。在此分疏之下,如果分开考虑人文学与教化、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王国维的敏锐观察其实表明,为政治服务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而且,相比于为教化张目的使命而言,为政治服务的使命更属当务之急。王国维之后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文学史也能证明这一点。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检讨近百年来侧重于为政治服务的中国人文学的得失,有必要重提人文学应当为教化服务的宗旨。
另外,在以哲学的进路接引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上,王国维还就当时关于人文学的分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了哲学在人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其中大学堂分科为“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12](P236~237)1904 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其中大学堂分科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经学科又分为十一门:一、周易学门,二、尚书学门,三、毛诗学门,四、春秋左传学门,五、春秋三传学门,六、周礼学门,七、仪礼学门,八、礼记学门,九、论语学门,十、孟子学门,十一、理学门;文学科又分为九门:一、中国史学门,二、万国史学门,三、中外地理学门,四、中国文学门,五、英国文学门,六、法国文学门,七、俄国文学门,八、德国文学门,九、日本国文学门。[12](P340,341,349)这两个学堂章程都是 “略仿日本例”,但与当时日本大学的分科相比,这两个学制有其特殊之处。就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而言,其特殊之处至少有二。其一,两个学制皆非常重视经学。在壬寅学制中,经学被放在文学科之下,列为文学科第一门;在癸卯学制中,经学的地位更得以加强,成为与文学平列的一科,而将理学放在了经学科之下。至于这么做的理由,自然是出于尊经之意。其二,在两个学制中皆无哲学一门,无论是在两个学制的文学科分科中还是在后一个学制的经学科分科中。这么做的理由,按照张百熙的陈述是为了“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因为在他看来“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鹜广志荒之弊”。[13](P66)
1903年,王国维专门针对壬寅学制写了《哲学辨惑》一文,为哲学正名,其要点已见于上文。1906年,他又针对癸卯学制写了《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再次陈述了哲学的重要性,并基于对哲学之于尊经的意义、哲学之于文学的意义等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他对文学科的分科建议。
对于张之洞在大学章程中力图体现其尊经的苦心,王国维首先表示了肯定,指出张之洞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惧邪说之横流、国粹之丧失”,“其抉翼世道人心之处”不能不令人“再三倾倒”。之后,王国维笔锋一转,对张之洞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关于哲学的重要性以及哲学在文学科大学分科中应有的地位王国维除了重申《哲学辨惑》一文中的看法之外,还以欧洲和日本大学的分科情况为例进一步说明: “夫欧洲各国大学,无不以神、哲医、法四学为分科之基本。日本大学虽易哲学科以文科之名,然其文科之九科中,则哲学科褎然居首,而余八科无不以哲学概论、哲学史为其基本学科者。”[3](P33)之后,王国维重点分析了哲学之于尊经的意义和哲学之于文学的意义
王国维认定他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研究自由的时代,而非教权专制的时代,并以诸子哲学与儒教哲学的关系来类比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指出哲学不惟不妨碍尊经,还能促成经中所包含思想的发扬光大,当然前提是经中所包含的思想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至周、秦诸子之说,虽若时与儒家相反对,然欲知儒家之价值,亦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况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哉!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3](P36)至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王国维认为, “其密切亦不下于经学”。王国维兼论中西文学以申说此义:周、秦乃至后来宋、明“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西洋之文学亦然。柏拉图之《问答篇》、鲁克来谑斯之《物性赋》,皆具哲学、文学二者之资格。特如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且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学之一分科之美学中求之”。[3](P37)
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王国维对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的设置及分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他反对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更加强化经学而将经学科与文学科平列为二的做法,建议“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即以经学科为文学科大学中的一科。在提出这个建议时,王国维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立场,反驳了一个为经学科大学辩护的意见,即以西洋大学有神学科来论证中国大学宜有经学科:“为尚书辩者曰:西洋大学之神学科,皆为独立之分科,则经学之为一独立之分科,何所不可?曰:西洋大学之神学科,为识者所诟病久矣。何则?宗教者信仰之事,而非研究之事,研究宗教是失宗教之信仰也;若为信仰之故而研究,则又失研究之本义。西洋之神学,所谓为信仰之故而研究者也,故与为研究之故而研究之哲学不能并立于一科中。若我孔孟之说,则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以自外于学问者哉!”[3](P38)
其次,王国维申说“群经之不可分科”。对此,王国维援引了来自古人的一个看起来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即强调治一经须通诸经:“夫‘不通诸经,不能解一经’,此古人至精之言也。……夫我国自西汉博士既废以后,所谓经师,无不博综群经者。国朝诸老亦然。”[3](P38~39)王国维亦以体贴入微的口吻推测了癸卯学制分经学为十一科的缘由:“而顾分经学为十一科者,则以既别经学于文学,则经学科大学中之各科,未免较他科大学相形见少故也。”[3](P39)这种看似保守的论调其实非常激进。经学内部的分科所根据的是古代六艺之说,是与经学所对应的教化实践直接相关的。《礼记·经解》记载孔子之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章学诚曰:“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14](P951)就是说,在“学在官府”的时代,六艺的分科与当时的政教制度直接相关;而在孔子那里,六艺的分类则对应于教化实践的不同方面。质言之,经学内部的分科关乎经学所承载的教化思想的实质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其来源而言还与古代政教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并不是一种形式化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王国维表面上诉诸经学内部的统一性来论证群经之不可分科,其实是欲以来自西方的形式化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来重新规划重新安置古代教化中的经典系统。这种做法的革命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其所标榜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经典这一点而言,自然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形式化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来重新规划、重新安置古代教化中的经典系统,极有可能招致对经典的粗暴肢解,从而使得对经典的研究难免于支离破碎,最终背离经典研究为教化服务的根本目的。
王国维对这一可能的问题并非没有察觉他其实是将哲学作为人文学内部的一个基础性的因而能够起到整合作用的学科来看待的。这显著地反映在他关于人文学具体科目设置的建议中:“由余之意,则可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而定各科所当授之科目如左:一、经学科科目:1.哲学概论;2.中国哲学史;3.西洋哲学史;4.心理学;5.伦理学;6.名学;7.美学;8.社会学;9.教育学;10.外国文。二、理学科科目:1.哲学概论;2.中国哲学史;3.印度哲学史;4.西洋哲学史;5.心理学;6.伦理学;7.名学;8.美学;9.社会学;10.教育学;11.外国文三、史学科科目:1.中国史;2.东洋史;3.西洋史;4.哲学概论;5.历史哲学;6.年代学;7.比较言语学;8.比较神话学;9.社会学;10.人类学;11.教育学;12.外国文四、中国文学科科目:1.哲学概论;2.中国哲学史;3.西洋哲学史;4.中国文学史;5.西洋文学史;6.心理学;7.名学;8.美学;9.中国史;10.教育学;11.外国文。五、外国文学科科目:1.哲学概论;2.中国哲学史;3.西洋哲学史;4.中国文学史;5.西洋文学史6.□国文学史;7.心理学;8.名学;9.美学10.教育学;11.外国文。”[3](P39~40)从这个分科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国维的建议中,经学科虽然被保留下来作为文学科大学中的一科但经学科的科目几乎全部被哲学或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科目所占据,而在文学科大学的其他各科中,哲学不仅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而且也占据了基础性、主导性的地位。实际上,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王国维的建议隐含着有以哲学代替宗教的意思,而这一点表现在学科设置上就是以哲学代替经学。
仅仅在写作《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的第二年,即1907年,王国维自述其兴趣“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从此他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放弃了对哲学的专门研究和努力探索。王国维放弃哲学的原因经常被归于个人情感和兴趣,即著名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的论调。这个论调来自于王国维的自述,但仅仅从个人情感和兴趣的角度来理解他放弃哲学这一事件是非常肤浅的。实际上,理解这一事件的一个重要线索是科学对他的影响。王国维在决定专攻哲学之前的时期正是他大量学习科学的时期:从1898年到1900年,他在东文学社的两年半的学习期间所学的内容除了外语之外,主要就是数、理、化;1900年,他帮助罗振玉编辑《农学报》时曾有《农事会要》的译作;1901年,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不到半年的留学生涯中专攻的是数学和物理学;1901年,他在武昌任职农务学堂译授时的工作内容是协助外籍教员讲授农学课程,并在此期间翻译了来自日语和英语世界的一些农学书刊和其他科学书刊。①王国维:《自序》,见《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另外,王国维有数学方面的译著《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收入《王国维全集》第十六卷,原书为日本藤利喜太郎著,王国维的译文曾连载于《教育世界》第十五~十八号,旋收入教育丛书初集,由教育世界出版所于1901年出版;王国维亦有物理学方面的译著《势力不灭论》,收入《王国维全集》第十七卷,原书为德国赫尔姆霍茨 (Hermann von Helmholtz,王国维译为海尔莫壑尔兹)著,王国维据英译本译,原载于科学丛书第二集,由教育世界出版所于1903年出版。科学注重的是经验,其核心的研究方法是实证,而科学的权威亦由此而产生。王国维既然兼以理性和人的形而上需要申说哲学之意义,在他那里就必然存在着如何理性地看待形而上学的问题。其实,在他关于“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的著名自述中,这一点表露得很清楚:“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2](P121)也就是说,正是来自实证论、快乐论、经验论等与科学观念密切相关的这些思想,才导致了他觉得本来可爱的形而上学变得不可信了。如果我们能够断言其时科学的权威在王国维的心目中已经坚定地确立起来了的话,那么,王国维的烦闷其实是由科学与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可能冲突所引起的如果联系1923年张君劢发表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而引发的论战的话,这是发生在王国维的精神内部的科玄论战。
在写作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很少谈到哲学,而是将学问分为科学、史学和文学三大类,并强调三者之间的关联:“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荡,得以此三者括之焉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德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15](P129~130)如果哲学只能被归入 “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范围的话,那么,王国维这里是将哲学划归于科学。如果仍以宇宙人生之真相为哲学探究之对象的话,那么,王国维似乎论及哲学与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之间的相互关联:“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15](P132)这种理解的问题在于,如果科学的权威已然确立无疑,那么,对于宇宙人生之真相的解释权是否还继续留给哲学?一个更为大胆的猜测则是,既然王国维将一切学问分为科学、史学和文学,那么他是否有将哲学剔除出学问行列的意思?这个猜测无疑是错误的,但在某种意义上离王国维的真实想法却也不算太远,特别是如果坚持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话。王国维自然是将哲学划归在科学之下,但这恰恰意味着,在他的这个分类中,对于哲学的取舍是以科学为基准的。换言之,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样被划归为科学的哲学里,王国维早年对其有可爱之感的那些形而上学思想,自然是被视为谬误而排除在外的,只有那些他认为可信的思想——实证论、快乐论、经验论——才符合他的作为科学的哲学概念。
实际上,在这篇序文中,王国维只有一处明确地谈到哲学,是在论及科学之历史时将哲学之历史与物理学之历史、制度风俗之历史相提并论。与他专攻哲学时期强调哲学的重要性等看法相比,这篇序文的最大变化在于对史学之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史学研究中应用科学方法之重要性的强调。我们知道,王国维在这篇序文中主要申说了三个命题: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其中,他关于学无新旧的申说明里是为了调停科学与史学之争,实际上是在科学的权威已然确立无疑的处境下为史学张目:“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15](P131)他关于学无中西的申说明里是为了阐证“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实际上是为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科学方法正名:“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邝、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15](P131)而他关于学无有用无用的申说则意在强调包括科学、史学和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对于政治、教育和民生的功用和价值:“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汽、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鲜。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15](P132)
王国维后来主要是以史学研究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并在晚年明确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前后思想的转变很值得注意这种转变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古典教化精神越来越深刻的体认和越来越笃实的信服。王国维提出的问题毋宁是:在科学的权威已然确立无疑的新时代里以何种方式接引中国古典教化传统?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学术关怀下王国维弃哲学而从史学。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再一次东渡日本的王国维毅然决然地烧毁了《静庵文集》。这当然是他非常郑重其事的明志之举,但这既不表示他早期的哲学探索对于他的学术事业完全失去了意义,更不意味着哲学的进路对于接引中国古典教化思想毫无价值王国维对史学的重视,以及对史学研究中科学方法的强调,其实是被人文学与教化的关联方式所决定了的。当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权威,教化就沦为传统。于是,若以科学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文学来接引教化传统,史学就成了基础性的学科,换言之,在此处境中,一切人文学首先都是史学,史学在人文学中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如果说以哲学代替经学必须依赖于本质主义,那么,以史学代替经学则必须依赖于传统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从以哲学代替经学的方案转变为以史学代替经学的方案只不过意味着在本质主义遭到科学的猛烈打击后转而乞灵于传统主义。因此,一个问题始终悬在我们头上:站在重振教化的立场上看,经学是否还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对于这个问题最为深思熟虑的答案或许已经展现出来了:如果经学所对应的教化体系仍然值得肯定,而无论哲学还是史学都无法真正承担过去经学所承担的理论功能那么,恢复经学就是重振教化的必然选择。
[1]王国维.自序[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2]王国维.自序二[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3]王国维.哲学辨惑[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4]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A].王国维全集(第一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5]王国维.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6]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7]王国维.去毒篇[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8]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A].王国维全集 (第一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1]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A].王国维全集 (第一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12]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4]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A].文史通义校注 (下[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A].王国维全集 (第十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B259.9
A
1671-7511(2011)06-0058-10
2011-01-10
唐文明,男,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卢云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