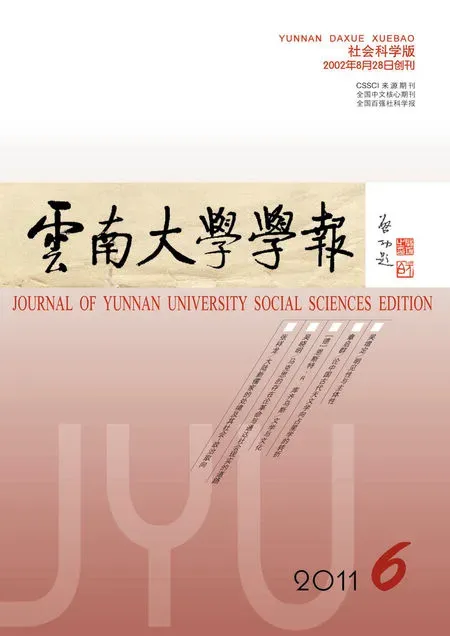近代基督教信仰在认识论上的转向
2011-12-08王爱菊
王爱菊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基督教认为,人生活在此岸世界,却不属于此岸世界,而应该不断超越此岸世界,并努力趋向彼岸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基督教哲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张力。从本体论上看,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是一切真理的来源,故而真理必然被上帝自上而下地启示出来。否则,有限的人便无法获得关于无限的上帝的真理。因此,要认识上帝,必定先要有上帝赐予的信仰。可是,从认识论上来看,为了认识上帝的道,人类必然是从自己出发,以个体的体验和思考为起点,自下而上地认识上帝以及上帝的启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才能确定上帝的存在,理解上帝的属性,了解圣经的内容,体验人与上帝的沟通。
从基督教历史来看,集经院哲学之大成的托马斯·阿奎那肯定人的认识能力,建立了人从感性事物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五种证明,同时也强调上帝的启示对于人的理性能力的优越性和超越性,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了平衡。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却认为,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受到罪的玷污,故而人无法凭借理性认识上帝,只能依靠上帝白白赐予的信心和恩典。然而到了17世纪,西方人逐渐相信只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便能认识上帝的道,对上帝的信仰悄悄被替换为对上帝的认识。英国圣公会主教斯第林福利特 (Edward Stillingfleet,1635~1699)曾经说过:“我们所说的信仰,就是心灵的理性和推理的行为。既然信仰就是同意那些足以让心灵同意的证据或理由,那么它必定是一个理性和推理的行为。”[1]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成为认识上帝的道的方法和标准,基督教成为理性主义的宗教。由此不难看出,基督教在近代强调信仰的认识论意义,经历了认识论的转向。近代基督教信仰在认识论上的转向与理性时代对人的理性能力的高扬有一定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转向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出现,它是从宗教内部开始的。不过,在讨论这个转向如何发生和为何发生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信仰。
一般而言,信仰 (faith)可以被区分为两个方面:[2]其一,作为主观行为的信仰 (faith),即个人的信任或者相信;其二,作为客观对象的信仰 (the faith),即作为被相信对象的客观事物或命题。日常意义上的信仰必然涉及某个可以信赖的对象,如某个人所说的话或一本书的存在。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则通常会涉及被相信的某个宗教命题或者教义,如宇宙是上帝创造的,等等。基督教作为一套丰富的信仰体系,则包括本体论 (如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上帝与人的关系等等)、认识论 (即上帝如何显明自我,并如何让人类了解他的属性和意志),还包括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 (如耶稣的生平故事),最后还包括伦理学 (例如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训导等)。
作为个人主观相信的信仰,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相信或同意 (belief,assent)和拯救意义上的信靠 (trust)。认识论意义上的信仰,通常指人类对基督教教义或者命题的认识和相信,其对象是人所获得的对上帝的知识,即前面所提到的宗教命题或者教义体系。拯救意义上的信仰,通常指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任和委身。认识论上的信仰要求人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去相信,拯救意义上的信仰却是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相信某事物的真实性。结合信仰的这两个方面,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宗教改革以来近代基督教信仰的微妙变化。
一、信仰的客观对象:从圣经到信经
宗教改革时期,信仰的客观对象逐渐由惟独信仰圣经转向相信圣经和信经 (creed)。宗教改革家们无不强调“圣经原则”,将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来源和终极标准。路德提出“惟独圣经”的口号,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传统和人类一切权威。他反对教会和神职人员垄断诠释圣经的权力,坚持每个教徒都有解释圣经的自由权利,所以教徒能够通过直接阅读圣经与上帝交往。路德强调圣经是规范原则 (Normative Princip le),也就是说,凡是圣经没有禁止的,只要人感到合适和有裨益的,就可以兼收并蓄。后来,加尔文甚至比路德更加重视圣经的无上权威,以圣经为规管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认为一切都应该按圣经办事。[3]在加尔文看来,《圣经》是“永恒的真理准则”,是一切完美信仰和对上帝正确认识的源泉,是教会组织和纪律的依据,而人在圣灵的感动和光照之下可以从圣经中得到关于神的真知识。
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天主教和新教在圣经诠释上的分裂。他们各自以权威自居,独断地宣称唯有本教派的理解才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并且在维护一己之标准的同时攻击对方的判断标准。在路德看来,如果按照天主教的标准,只会造成道德上和宗教上的灾难。天主教则批判路德派以良心为标准,并指出如果没有教会的引导,教徒便无法真正理解圣经的含义。由此,天主教和新教各个派别都声称,只有相信本派关于圣经的理解才能得救,否则便会受到永罚。
关于圣经的分歧同时还发生在新教内部。虽然新教各派都强烈诉求于圣经的权威,都认为圣灵的光照一定能够让人理解经文的意思,可是一旦摆脱了外在的权威,否认了集体的公会议的决定,这种内在的自由很容易会导致信仰上的混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马太福音》一处经文的理解。这句经文描述的是最后的晚餐: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送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26:26)。路德从字面意思把“这是我的身体”理解为“饼是我的身体”,认为主餐是基督真实的临在。茨温利却认为,“这是我的身体”应当被视为隐喻,意思是“饼象征着我的身体”。在他看来,基督的身体并没有真实临到圣餐的饼和酒里面,而作为圣礼的主餐只是象征性的,并非真的是在吃基督的身体。加尔文的观点和他们的也有不同,因为加尔文既反对路德,认为基督的身体在天上,并没有真实临在于主餐中,同时也反对茨温利,希望像路德一样在圣餐的时候吃到基督的身体。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圣灵奥秘地透过主餐之饼与酒的象征,把基督的身体和忠心的信徒结合在一起。[4]
为了统一对圣经的不同解释,规范信徒对圣经的理解,也为了避免信徒在诠释圣经上的混乱以及走向异端,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正确的参考框架,以便他们能够更容易把握圣经,新教领导人采取了三种措施。[5]第一,编写旨在教育新教信徒并向他们灌输基督宗教的实质的“教义问答” (catechism),对教徒阅读圣经进行指导。针对普通信徒,路德编写了《基督教大教义问答》和《基督教小教义问答》,就基督教所必需掌握的知识,例如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以及圣餐礼,给予了清楚明晰的阐释。加尔文对路德的《教义小问答》推崇备至,以之为典范,而他自己的《基督教要义》内容清晰,在对圣经的引用上非常娴熟而且富于说服力,使得读者感到只要有了它和圣经这两本书就能了解基督教和改革宗教义的全貌。第二,通过召开会议达成有关圣经的解释和教义的决议。新教运动开始之际,并不主张以会议决议的方式来处理圣经的问题,可是由于圣经诠释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人们不得不召开会议来解决圣经诠释上的争端。1523年,苏黎世市议会举行公开的辩论会,讨论茨温利的“六十七条结论”。此次会议开了新教通过会议决议的方式来决定某种对圣经的解释是否符合圣经的先河。第三,对教徒阅读圣经和解释圣经的范围加以限制。由于担心文化程度低的人在解释圣经时会出现偏差,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所以新教领袖主张,一般的教徒甚至无需阅读圣经,只需看看教义问答之类的书籍便可,即便要阅读圣经,也要以教义问答为指导。
新教的这三大措施其实是又回到了天主教的传统。本来是以圣经的权威反对天主教大公会议的教义,现在也通过召开会议制定教义。本来主张以对上帝的直接信仰来反对教士解释圣经的垄断权力,现在也编写解释圣经的指导手册。天主教以托马斯的《神学大全》为圣经解释的规范读本,新教的路德派便以路德的《教义问答》为指导,加尔文派则以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为根据。这样一来, “惟独圣经”的口号变成了惟独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从而堕入了新教所反对的天主教的独断,走向了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个人自由诠释圣经的反面。
值得注意的是,马丁·路德虽然提出了“惟独信仰”,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像德尔图良那样主张信仰主义,反对对信仰进行解释。路德所谓的惟独信仰,针对的是信徒的得救问题,是他对保罗的“因信称义”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说,信徒要在上帝面前称义,必须依靠内心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不是依靠罗马天主教会所指出的购买赎罪券等外在事功。实际上,路德本人撰写了大小教义问答以及《施马加登信条》等材料阐释他的信仰,以规范信徒的信仰。
与路德相类似,新教各派的教会为了阐明本教派的信仰主张,与其他教派划清界限,纷纷制定了属于本派别的信经。信经就是阐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的条文。新教运动中产生了很多信经,如路德派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1530),英国圣公会在伊丽莎白一世临朝之时规定的《三十九条信纲》(1563),加尔文派在英国内战期间制定的《威斯敏斯特信条》(1647)。宗教改革时期大量信经的出现有诸多原因。一方面,新教教派回应天主教的挑战,证明新教信仰并不只是内心的虔敬,也能够以命题的形式阐释出来并可以被论证推理。另一方面,新教各派教会都成为国家教会,有必要为本国信徒明确信仰标准,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本教会在教义上的一致性,更有利于与其他派别区分开来。
除此以外,信经的大量出现和加尔文有很大关系。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批判了中世纪的“隐性信仰” (Implicit Faith,即默信),主张“显性信仰”(Exp licit Faith)。在他看来,中世纪的神职人员认为三一论的教义过于复杂和神秘,无法为所有的教徒所理解,便鼓励在智识上存在局限的信众去相信教父关于教义的阐释,所以中世纪的“隐性信仰”在本质上是指对教父教义的信仰,即对神学家的信仰的信仰。加尔文否认了这种对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的教会的信仰,主张真正的信仰就是信上帝和基督。然而,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这种对上帝和基督的“显性信仰”却渐渐蜕变为对某种信经或告白的信仰,而得救与对这些信纲中的教义的相信密切相关。这些教义问答和信经的出现表明,基督教信仰的对象逐渐被客观化。人们在相信圣经的同时,还把他们的信仰对象固化为一套教义体系。
二、主观意义上的信仰:从信靠到相信
除了信仰的客观对象发生变化之外,信仰在主观意义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重视正确的信仰,并从强调拯救意义上的信靠转向强调认识论意义上的相信。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对信仰的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他曾经用坐船过海的比喻加以说明。他说:“一切在乎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如同一个必须过海的人,但心中胆怯不肯乘船,因为不相信舟船。这样的人只得留在岸上永不得过海,因为他不肯上船。”[6]认识论意义上的信仰是在有充足证据的基础上确切地相信一条船的存在,而拯救意义上的信仰则不仅如此,而且更是信任这条船可以安全地载人过海。如果船是否存在可以得到证实或证伪,那么该船能否安全地载人过海则在过海之前难以确定。如果人只是相信船的存在,而不肯信任它可以安全地载他过海,那么他会不愿意上船,从而永远过不了海。所以,拯救意义上的信仰,不仅是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存在,更是信靠他的应许,信任耶稣有能力把人从罪恶之中救赎出来,从而将自己委身相托,与耶稣联合为一。[7]
和路德一样,加尔文认为信仰是坚定的信念,能够使人得救。然而,和路德不同的是,加尔文明确提出信仰应该寻求理解,并鼓励教徒对上帝的意志和良善有明白确定的认识,而不是盲目地默信自己不了解和不研究的事情。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的第二章中,加尔文专门对信仰的含义和性质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信仰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知识,不仅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也是对神圣意志的知识”。“信仰和理解联系在一起”。“信仰是对神的仁爱的一种不变而确实的知识,这知识是以基督那白白应许的真实为根据,并藉着圣灵向我们的思想所启示,在我们心中所证实的。”[8]
加尔文强调信仰是对上帝和基督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依然是拯救意义的,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也并不意味着信仰是人的理性认识的对象。虽然在当时的宗教信仰实践中,由于上文所提及的种种原因,这种知识已经逐渐转化为对信经的信仰,信经所规定的正确信仰却不是独立无援的理性认识的客观对象。首先,作为知识的信仰是关于上帝的意志的知识,而上帝的意志是人无法揣度的,所以人需要在上帝白白赐予的礼物的援助之下,才能获得得救的知识和确信。其次,按照加尔文主义的全然败坏说,人的理性能力已经遭到玷污,有所亏欠,所以无法认识上帝的意志。这一点在新教的信经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三十九条信纲》第十八条中说: “若有人胆敢说:无论人信甚么理,奉甚么教,只要他能按着所信的理,和自然之光奋勉而行,就可以得救;那么说这话便该受谴责,因为圣经上明白指示,人惟靠耶稣基督之名,才可以得救。”[9]所以,加尔文所说的信仰即知识,并不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更不是指接受某套信仰定则就能使人自动被拣选从而得救。
不过,加尔文神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以及阿明里乌对加尔文的观点的批判和纠正,促使信仰成为客观的认识,而不再停留于主观的体验。[10]随着阿明里乌派对于加尔文的败坏说和预定论的反驳,这些“得救的知识”不再只是上帝采取主动并早已预定的那些被拣选之人所能获得的知识,而是进入了人的理解范围。[10]阿明里乌指出,加尔文主义中的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和有限救赎 (Limited atonement),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上帝事先已经预定了谁将得救,谁将下地狱,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就在人的得救过程中毫无用处。这也意味着人自身的道德责任被勾销了,而上帝将承担所有的道德罪恶的沉重责任。这样一来,上帝的预定与上帝的良善和正义之间便发生了矛盾。加尔文还强调有限救赎,认为耶稣只为被拣选之人而死。然而《新约》中很清楚地写着,耶稣为众人而死,这与有限救赎说也有着明显的矛盾。此外,加尔文强调神恩独作论,认为人的得救完全属于上帝的恩典,为了使救恩完全归于恩典,救恩就不是人可以自由选择或接受的恩赐。可是,“按照加尔文的思维模式,惟有罪人接受救恩的方式并非自由和积极的选择,而是无条件与不可抗拒的授予,才是真正借着恩典得到的救恩。并且,惟有事先预定并在永恒里命定的,才是真正的救恩。”[4]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积极地表现而获得救赎,这在加尔文看来便是剥夺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使得上帝对世人的救赎取决于人的自由行动。针对于此,阿明里乌提出了“有条件的预定”和“先行的恩典”两个重要概念,既让人在得救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又避免了完全靠事功得救的佩拉纠主义。“有条件的预定”是指上帝的永恒目的就是拯救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正如“阿明里乌信经”第一条所言:“上帝用那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永恒不变的旨意,在创立世界以前,便已在基督里面,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借着基督,从堕落和有罪的人类中,决定拯救那些因圣灵的恩赐,而相信他儿子耶稣,并在这个信和信的顺服中恒忍到底的人”。[9]“先行的恩典”是指神提供给所有人的恩典,也是罪人获得救赎所不可或缺的恩典。但是因为是先行的恩典,所以又是可以抗拒的。但只要人不抗拒,借着信心让它在生命中运行,这个恩典才能使人称义。这里的“不抗拒”不是道德上的善行,而是单纯地接受,是人对某些教义表示同意和接受。[10]有了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同意和接受,上帝就被免除了让人遭受永罚的尴尬,人也不需要为了得救而不得不在道德实践上采取一定的行动。由此,阿明里乌使得获救不再完全依靠不可理解的上帝,而是部分取决于人的客观认识和同意,不再是加尔文严苛的神恩独作论,而是“神人合作说”。
质言之,阿明里乌的“神人合作说”导致得救的真理不是上帝和选民之间不可言说的神秘交往,而是成为了可以谈论、可以承认也可以否认的命题,而且只要同意和接受这些命题,便可以得救。正如哈里森所言,“信仰从此不再是“同意” (assensus)和“信靠” (fiducia)之间不可捉摸的平衡: “同意”战胜了“信靠”。[10]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7世纪出现的不绝如缕的对信仰命题或者定则的讨论中明显看出。自然神论者赫伯特提出了五大宗教“共同观念”,并且认为这五大观念才是信徒得救的信仰原则。1658年,托马斯·罗杰斯的《英国信条》(British Creed)的第二版出版。在这本关于《三十九条信纲》的评注中,作者把英国的信仰、教义和宗教解释为“以命题形式分析出来”的信条。同一年,加尔文派的著作者理查德·扬出版了《通往恩典和救赎的简短确定之路》,旨在简化和澄清宗教问题。他列举了三条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则,认为这就是信徒必须相信的核心教义,通过它也可以让成百万的人逃脱地狱。最合适的例子应该是洛克。他对于各种神学教义和体系深为不满,于是亲自仔细阅读圣经,以便弄清楚什么才是得救所必须相信的基本命题。1695年,洛克发表了《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明确提出,从圣经的福音书来看,同意和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惟一的命题原则是成为基督徒所必需的,如果再加上实践方面的忏悔,便可以得到永生。到了洛克这里,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宗教信仰准则的数目已经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当宗教信仰不仅是内心的虔诚或宗教的神秘体验,而是体现为对一套确定的知识体系的认识和同意的时候,宗教上的认识论转向就算最终完成了。
路德和加尔文都将圣经奉为权威,主张信徒直接阅读圣经以获得信仰,极力推崇拯救意义上的信仰。他们的这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唤醒了个人探索宗教真理的自我意识和自信,但是信仰却不能只是停留于个人的宗教体验,而是仍然要寻求被表达和客观化。所以,信仰的认识论意义仍然不可避免地在实际信仰生活中显现出来,信仰的对象逐渐成为某种客观的信仰命题或定则,信仰则变成对该命题的认识和同意。
经历了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基督教信仰比较重视人的理性认识,却漠视人的心灵所体验到的种种痛苦和挣扎,剥离了宗教中的灵性和情感,因此在18世纪后半叶遭到了休谟的批判。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宗教信仰的所有证据——包括从奇迹和预言出发的证明和理性论证——逐一进行了辨析和归谬,否认信仰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如果说休谟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破坏了信仰的客观性基础,那么康德则彻底地将信仰从认识论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了现象和本体、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认为宗教信仰属于本体界,不再是经验知识的范围,不是以思辨理性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由此,近代信仰在认识论上的转向宣告破产,而以人心道德为基础重新确立起了自己的地盘。
[1] Gerard Reedy.The Bible and Reason[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
[2] Paul Helm.Introduction[A].Faith and Reas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7.
[3]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路德文集·序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4]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吴瑞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张庆熊.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克尔.路德神学类编 [M].王敬轩译.香港:道声出版社,1961.
[7]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 John Calvin.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M].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5.
[9]历代基督教信条[M].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9.
[10] Peter Harrison“Religion”and the“Religions”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