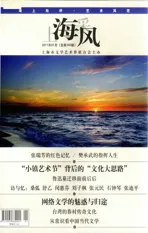当摄影师遇上了“白毛女”
2011-11-30文/信芳
文/信 芳
当摄影师遇上了“白毛女”
文/信 芳

张元民与石钟琴
在摄影家的眼里,舞蹈无疑是一门最能表现人的情调、最直接有力地展现人的生命力的艺术, 摄影家用镜头抓住的虽只是其“美丽的瞬间”,但常常会因之而享乐无限,甚至一生。当一个摄影家遇上了美丽的舞蹈家,且能够碰撞出火花,这不能不说是“人间添美眷”的大喜事。
张元民,电影摄影家、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石钟琴,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芭蕾舞剧《白毛女》第一代“白毛女”的饰演者,两人的完美结合,在沪上文艺界传为佳话。然而,张元民向来低调,以工作忙而几次谢绝了我的采访。他说工作忙倒是实话,虽已退休,却依然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这完全是“尽义务”,故有人笑称他是文艺界的“志愿者”。那天,我在上海影城从原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先生那里得知,张元民石钟琴夫妇1992年就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模范夫妻”后,就更信心十足,紧追不放了。终于,张元民答应择日接受采访。虽然后来还是“一波三折”,但有今天这篇访问记真还得感谢他和夫人的支持。
张元民:拍电影有点“阴差阳错”
张元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海金陵中学度过的。现在已是摄影专家的他,直言当初他还没碰过照相机,也未爱好;对美术倒有点兴趣,但画得也一般;倒是“工科”方面有专长。那时每周一次劳动,为丰华圆珠笔厂生产的笔芯加工:为防笔油倒流,要在它的尾部装上一小“活塞”。一把150支,支支要用手工安装,繁复的手工使张元民想到了“技术革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与另一个同学合作竟把用机器装配的“革新”搞成了,这项创造发明在市里还得了奖。
张元民告诉我,其实当时他最有兴趣的是搞“新闻”。1960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招生,内有一个“新闻摄影”专业吸引了他。虽只有30个名额,且内招15名,却引来800多名考生。经初试、复试,他竟真考上了。后来他从一位教授那里得知,原来录取他,还有他在中学期间那个小发明的因素。因为当时学校很想在电影机械方面培养专门人才,所以看上了他。

张元民正在拍摄影片《江姐》(1979年)
三年的专业学习,临到分配,一心想干新闻的张元民十分指望能被分配去拍新闻纪录片的“科影厂”,但事与愿违,他偏偏被分到了拍故事片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张元民知道,按电影厂的老规矩,从进厂到成为一个电影摄影师起码也得15年,其中5年机械员,5年助理,5年副摄影,然后才有资格提升为“摄影”。此时,正好赶上拍摄由赵丹、祝希娟主演的《青山恋》,于是在5人摄影组中他当起了“机械员”。别看它级别最低,任务却最艰巨,每天给摄影机清洁保养,给师傅装片,拉皮尺测距等,不能有丝毫差错。因为这是“遗憾的艺术”,机器出故障,一切就得重来,用电影界的行话说,他得给众人“骂死”。张元民深得其理,所以,小心翼翼,一丝不苟。一部电影下来,得到摄影和剧组的满意。当拍摄第二部电影时,除当机械员外,还奖励他当上了“小助理”,其主要工作是“跟对焦距”。当然这同样十分重要,对焦不准,或晃或虚,都是废片,均得重拍。当然,一贯对工作认真的他,除了圆满完成任务外,还从老师和师傅那里偷学了不少技术。
此时文革就将开始,想不到的是,远在山西当总工程师的父亲因责任事故而被处理。张元民自此被划入“成分有问题”一类而下放到安亭汽车厂劳动。但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不久,正在嘉定试制的“上海牌轿车”需要拍摄有关纪录片,有人想到了正在劳动的张元民。张元民欣然接受了任务,自扛摄像机开始拍摄。最危险的是在“飞车”上拍摄轿车以120码时速超越火车的镜头,但张元民没有畏惧,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自此,他足足拍了5年的纪录片达60多部(集)。特别在艺术性纪录片上大有收获,不论是《黄山风景》,还是《上海工艺美术》,都获得了前辈摄影家的肯定。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局摄影总技师、摄影家吴蔚云,吴大师高兴地收他为“关门弟子”。
1979年,“于无声处听惊雷”,工人作家宗福先编剧的话剧被搬上银幕,张元民与计鸿生一起参加拍摄。同年,又参加了由吴蔚云担当摄影顾问,由空政文工团出演的歌剧《江姐》的拍摄。
从此一发不可收,在其后10年中,张元民在故事片领域与著名导演鲁韧、宋崇、杨延晋等多次合作,以一年一部、甚至两部的速度拍摄了《飞吧!足球》《车水马龙》《闪光的彩球》《快乐的单身汉》《最后的选择》《滴水观音》《绞索下的交易》《T省的八四、八五年》《笑出来的眼泪》以及戏曲片《两张发票》等。
此后,张元民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上海电影厂总工程师、党委书记、上影集团党委书记、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副书记,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视家协会副主席。
石钟琴:“芭蕾”是我的终身事业
打开国家文化部“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名册,芭蕾舞剧《白毛女》赫然在目。作为芭蕾舞第一代“白毛女”,与此剧共同成长的石钟琴,以她精湛的“足尖艺术”跳进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而且名扬四海。
其实石钟琴早在上海市舞蹈学校当学生时就跳起了“白毛女”。1966年,毕业后来到上海芭蕾舞团担任起主要演员。在芭蕾舞台上她还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奥杰塔、黑天鹅奥杰丽雅;《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机智、勇敢的马尔塔娜;《魂》中饱经风霜的祥林嫂和《雷雨》中阴沉忧郁的繁漪等。然而“白毛女”的光环太亮丽了,致使淹没了她以后塑造的众多角色。
提起“白毛女”的家喻户晓,石钟琴今日依然说,这是我们前辈艺术家精心创造和我们一大批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石钟琴回忆道,当时,胡蓉蓉、严金萱、傅艾棣及后加入的林泱泱等老师创编了这个舞剧后,又邀请黄佐临先生担任艺术指导。佐临先生不愧是个大师,他提议将原歌剧中杨百劳喝盐卤自尽改为黄世仁上门逼债,杨白劳和喜儿在与黄世仁、穆仁智的抗争中,杨白劳被打死。这一改突出了贫下中农的反抗精神,而且他还建议增加一场“荒山野林”的戏,喜儿逃亡荒山野林中,受尽艰辛,喜儿由黑发变成了灰发,又由灰白变成了白发,同时调动舞台上布景、灯光、化妆等手段,把喜儿成长过程,完全在舞台上尽显出来。
这样,当年一场《白毛女》中的“喜儿”由两个演员来完成。茅蕙芳先出场,饰演天真纯朴的“黑发喜儿”,而后她出场,饰演苦大仇深的“白发喜儿”。石钟琴说,要演好“白毛女”还真不容易。因为她长在红旗下,没有白毛女那种苦难生活的经历。比如第六场奶奶庙,白毛女在雷电交加的夜晚,下山来到奶奶庙拿供果充饥,正巧碰上来此避雨的黄世仁、穆仁智。此时演员的眼神要表现出仇人相见,怒火中烧的表情,可她就是恨不起来。因为饰演反派角色的都是同学,他们的动作设计又都接近戏曲丑角的造型,看着看着有时还会发笑。正是在胡蓉蓉等老师的耐心启发和示范下,才慢慢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找到了角色的脉络。第七场山洞中,为更好地表现白毛女和大春相逢时的喜悦心情,提高了舞蹈技巧的难度系数,为完成“单腿转带转身”的技巧,石钟琴说,每天练习不下300次,那时真是累得连走路、上楼梯脚都抬不起。

石钟琴在芭蕾舞《白毛女》中饰演“白毛女”
当舞剧《白毛女》被搬上银幕时,石钟琴仍然饰演白毛女。她记得开拍第一个镜头是白毛女进奶奶庙偷食。她依然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用夸张的形体动作表达探望心情,结果失败了。桑弧导演为她帮助分析,她才知舞蹈是块面结构,电影是分切镜头,因而需要演员多运用延伸和不过于夸张的脸部表情来传情达意。《白毛女》拍了整整一年,辛苦可想而知。由于拍电影常常反复,穿的脚尖鞋长时间由缎带绑着,至今在脚背上还留下未退的深痕。石钟琴笑着说,这也算这部影片给我们留下的记忆。
“周恩来总理看了17遍《白毛女》。”关于周总理对《白毛女》的关爱,石钟琴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最最难忘的是总理在各种场合看《白毛女》后,却是以观众身份提建议。比如,刚开始对于戏服的处理完全“写实”,做得破破烂烂的。总理建议:“舞台上不能只讲自然主义,也要有点浪漫主义。”结果,改动后的服装既有了时代特征,也符合芭蕾要求。当年,在《白毛女》中加写歌曲的尝试曾引起争议。总理认为,中国芭蕾应该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人有“载歌载舞”传统,不妨加唱。结果,序幕及喜儿与大春相认的高潮,都配上了唱。这些精美旋律,传唱至今。舞剧伴奏采用管弦乐与民族乐器相结合的形式,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感,一直深深吸引着广大观众。

石钟琴近影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石钟琴一直演到四十岁以后才离开心爱的舞台,在芭蕾演员中算是艺术生命最长的一位。石钟琴痴迷芭蕾,更视芭蕾为终身事业,所以退休后她没有闲着,当北京的一位舞蹈家与上海闸北区教育局合作创办远东芭蕾艺术学校后,她欣然接受邀请担当该校领导和艺术指导,她没有一点特殊,与师生一样同坐班车往返学校。石钟琴认为,芭蕾舞优秀人才对于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来说,至今依然稀缺,仅靠我国现有的几所学校培养,难以补上缺口,所以国家同时鼓励民间办学,对于这个有资质的业余学校,她理当支持,自己还有余热,可继续发光。
苦恋10年,抱得美人归
“她对芭蕾艺术岂止追求,简直是痴迷。”谈到爱人,张元民话语不多,但喜形于色,看得出,称赞的同时,还有点佩服的意味。40多年了,他对她太了解了,原来他们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
“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与石钟琴的哥哥是很要好的朋友。就是这种关系,我们1965年就认识了。”张元民如是说。当张元民毕业后在电影厂当机械员时,石钟琴还是舞蹈学校的学生。他们最初的接触只是偶然出去玩玩,或拍拍照。他们的恋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张元民回忆说,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现在小青年的浪漫,可能是两人的为人和性格上的同一所致。但有一点张元民十分清楚,如要与石钟琴结合,那至少要等10年。1966年,石钟琴毕业后进了芭蕾舞团,按当时规定,男女演员在30岁以前是不能结婚的,而后来《白毛女》成“样板戏”后,这规定更是严格执行。
“不过,当一个人对其对象萌生爱意后,会有信心,更有动力。”张元民笑了。
有一段时间,石钟琴天天在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府大礼堂(当时叫市革会大礼堂)演出。当时,张元民住在虹口,石钟琴住在静安。张元民穿着流行的军大衣,天天骑着自行车在剧场门口等候。石钟琴的“白毛女”下妆最晚,一般要到10时后。他将石钟琴骑带着送到家,然后再返回虹口,第二天清早又赶去电影厂上班。石钟琴心痛地不要他送,但这又怎能劝说热恋中的男人。时间一长,门口收票的已认识了这位张朋友,偶尔有空位时,叫他进去避避风,可张元民不想麻烦人家,甘愿在礼堂对马路的屋檐下等候,虽然北风呼啸,但心里却是热的,且丝毫没有悔意。
1974年,苦恋了10年的张元民,终于等到了石钟琴的“而立之年”,他们结婚了。尽管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恋爱,但婚礼仍十分简单,只是双方家庭吃了顿比较丰盛的饭。
1978年年底,话剧《于无声处》进京献演。不久接到上级通知,要尽快将此剧搬上银幕。就在这不久,一个后来取名张晶磊的孩子来到世上,这可把张元民急坏了:因为《于无声处》已开拍,作为第一次挂名“摄影”,张元民自知责任重大。白天他紧张地拍摄,下班后回家开始值班——孩子半夜喂奶、换洗尿布等一应由他一人负责。空时合眼睡一会,第二天一早又赶去“拼命”。就这样,一个月里他没有换过衣服。不过,电影如期完成,且得到较高的评价。吴蔚云对自己的徒弟疼爱地说:“好啊,儿子也有了,戏也拍完了!”
被誉为“足尖下的茉莉花香”,石钟琴的“白毛女”已经红遍天。就在有人“表忠心”写效忠信时,张元民却对石钟琴说,胜利时我们脑子一定要清醒,这事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做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搞艺术,虚的一套毫无意义。石钟琴十分赞同丈夫的意见,所以文革中从没有“不妥”行为,在领导和群众中赢得了口碑。后来,石钟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这一切依然没有增大她的“架子”,反而更多地想到大家,为大家服务。曾拍摄过《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从奴隶到将军》等影片的著名摄影师沈西林,1972年在桑弧导演下又拍摄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就此与石钟琴认识。文革后,当石钟琴了解到沈西林住房困难,只住十几个平方时,为他奔走并向有关部门呼吁,后来有关政策得到了落实,沈西林对此至今感谢不尽。
上海摄影的明天将更灿烂
2008年4月,上海市摄影家协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张元民当选为主席。同年7月,他被增补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张元民笑着告诉我说,其实电影摄影是他的专业,而“拍照”是业余的。张元民深感上海现在的摄影水平与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上任后,他与协会其他领导和专家们对上海现行的“摄影”进行了一番梳理,提出了努力方向。他认为,要使上海的摄影水平再上台阶,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以促进日益提高的摄影艺术的新发展。其次是专业队伍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缺乏文化修养的摄影者很难想象会有很高的建树。在这方面,张元民深有体会地说,不少前辈艺术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如经典电影《林则徐》,它之所以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成就,相当程度归功于导演郑君里和摄影。这部影片的摄影是前辈摄影艺术家、上海摄影家协会的老主席黄绍芬先生。在“送别”一场,邓廷桢被清廷派往福建,这对林则徐来说是失去一臂。影片选用江边码头、逆水行舟、群山孤帆、青松白云来烘托举杯告别,情景交融。黄绍芬说,李白有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林则徐急步奔上城垣、登山远眺、白帆远去,他一步一望,沉重心情已融汇在画面中。又如“秉烛夜读”和“打太极拳”的细节,看来是一幅山水画上的“闲笔“,是不经意的笔墨点缀,但不能没有这几笔。正是这几个无言的镜头,表现了林则徐这个人物的心理过程和情绪转换。所以我认为,黄绍芬先生在影片中这种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是他深得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结果,太值得我们汲取和学习了。
不过,张元民说,我们上海摄影队伍基础深厚,如今除专业队伍外,业余摄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我们的业余团体会员已达十几个。我们与国际交流和交往正进一步展开。同时,我们的新生代正在茁壮成长。所以他很有信心,上海摄影艺术的明天将更灿烂。

张元民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