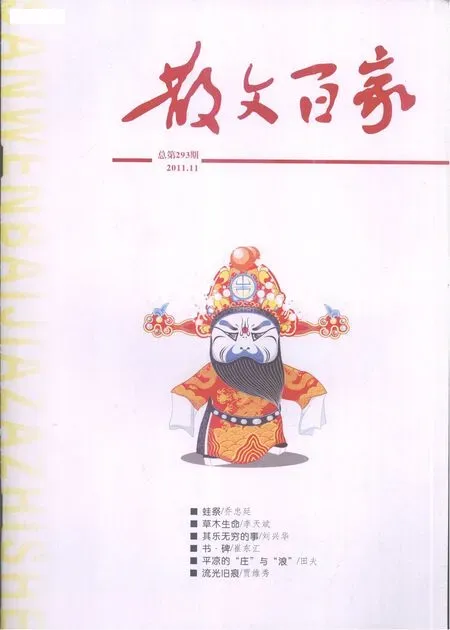其乐无穷的事(外二篇)
2011-11-21刘兴华
刘兴华
曾经有三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天高高在上,看得见,摸不着,想与其斗,有劲使不上。虽然那时有句口号:人定胜天。但具体到事上,好像也没对天怎么样。
别的村我不知道,但我们村却与地斗得最不遗余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砍树,老村的坟场很大,坟场里种满了白毛杨,人们总说树大招风,无论有风,还是没风,离很远就能听到那一片树发出低沉的轰隆声。
我没看到人们砍伐这些树,等我注意到这些时,这里只剩下一片高低不同的土丘,土丘前面以前有很多石碑,现在也大多砸烂了。那石碑高、厚、宽都以九为最大,取之久远之意,还暗含九泉之下,九天之上的祈福。
那么厚的石碑,要用多大的劲才能砸烂呀?当时因为人们常吃不饱,所以常用吃饱与吃不饱说事,最常听的一句话是:吃饱了撑的呀!听父亲说,没事做时就尽量少活动,还要把腿放到高处,躺着不动,这样能减少胃的消化,都饿成这样了,怎么还有劲砸这些不相关的东西?那天,正好有一家把坟里的棺材起走了,我曾跳进坟坑去,坐在里面想这事,想了半天也没想通。
坟场的附近是一片片枣树,还有梨树,也全都砍了。树砍了,可人们还想吃枣子和梨子呀,就趁月黑时去邻村偷,邻村恨透了我村那些偷梨的人,捉住会吊到树上打。我没去偷过,但等人家收完了梨子和枣子,我会拿一根长长的竹竿去那里找对方遗漏在树上的梨子和枣子,我们把遗漏的梨叫风梨,好似大风刮来的一样。把枣叫落红枣,也是对方落下的红枣之意。低下头瞅瞅树下走动的那些腿,大都是从我村里走来的。
还有就是挖地道,白天挖地道,晚上就放电影《地道战》,老村已经没有一户人家了,先去那里挖。老村宅基地高,那地道挖得也大,最长的有二三十米吧,说鬼子来了,就藏到那里去。
过了没多久,又要求家家户户挖地道,当时我一家人还商量了把地道挖在什么地方,挖在什么地方才不容易被发现。
因为紧挨河边,又没垫地基,水层特浅,挖了还不到两米,就出水了,只好重新填上。屋里总不能整天守着一口水井吧。
与人斗的事见过一些,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个人戴上用白纸糊的高帽子,那帽子比人还高,下面是一个圆口,戴到头上去,上面是个尖,然后让那人站到条凳上去,等那人在条凳上站好了,就有人诉苦,说到激愤时,就有人踹那凳子,把凳子踹倒,站在上面的人就会摔到地上。从对面踹,人会摔个四肢朝天,从后面踹,那人就会趴在地上,地上有时弄很厚的尘土,人落在上面,尘土就会溅起很高,弄得那人身上,脸上,甚至嘴里都是土,人们就大声笑,那帽子会摔出去更远。有时地上会铺一层炉渣,那东西硬硬的,摔在上面会把身上弄破,站在凳子上的人会穿得厚厚的,天热也不敢穿薄衣服。
也见过让一个女的在街上走,那个女的和我家是邻居,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孩,头上扎着一对羊角辫,经常跑到我家来找我玩,我也曾去她家玩。她家有一只大公鸡,有一次我去她家,手里拿着一块高粱面饼,那公鸡见了就上我手里抢吃,我把那饼举过头顶,那鸡跳起来去吃,那鸡落下来时,喙在我肚子上划过,当时就划破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去过她家。
我没见过她的男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让她在街上走,还让她的脖子里挂着许多只鞋,她低着头,走得很慢,她的身后跟着很多人。人们像不认识她似的,或者说想要重新认识她似的,总有人冲她大声说,抬起头来。
她始终没抬头,那天她从街上回家就服了毒,那毒叫信,据说外表和冰糖的结晶体差不多。
她的两个孩子围着她哭,闻讯赶来的人就死死捺住她,往她的嘴里灌大便,她就不停地呕吐,方法虽然很恶心,但总算把她救了过来。
自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大高帽子,但听说有人背地里做这东西,夜深了带上它去地里偷庄稼。那时,还有看庄稼的人,叫看青,庄稼没成熟前,叫青,如青玉米,青高粱,统称青棵。不过这名字不如青草叫得普遍。
看青的人听到田里有声音,就会大嚷一声,那偷庄稼的人就会戴上白帽子,猛地从地里站起来,看青的人以为遇到鬼了,掉头就往家跑,有的回到家还会病好多天。
最后一次与人斗是分地,分集体的财产,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谁家分的地比自己的好,谁家分的农具比自己的好,也要争吵半天,村干部没办法,让人抓阄,好坏全凭运气,外面不争吵了,就回家争吵去了。
过 继
在农村,有的夫妻因为自己不能生育,就去兄弟姐妹家要孩子,喜欢谁要谁。如果那孩子还小,就会专门买些好吃的,哄那孩子,然后问那孩子,叔叔好吗,或者姑姑好吗,或者姨好吗,或舅舅好吗?大都是这样的话,那孩子过年也吃不到这么多好的东西呀,满嘴是油,满手是油,一边吃一边说,好!
小孩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父母可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呢,心里就暗骂,你这个傻精吃,一会就把你送了出去。
想要孩子的人就会接着说,我家好吃的可多了,好玩的可多了,跟我去吧。
那孩子只顾得吃了,哪会想对方什么用意呀,嘴不地停咀嚼着,眼还看着摊在纸上的食物,头也不抬就说,好!
孩子都说好了,做父母的怎么好说不同意呀,好在家里孩子多,要走一个,还有好几个呢,便转过身去抹下眼泪,说,那你就带他走吧!
要孩子的,一般上午去,吃过中午饭,再说会话就该回去了,带孩子走时,一般也不会直接告诉孩子,只说让孩子过去玩些天,一玩就玩不回来了。也有聪明的孩子,被带走时,突然明白自己要被送人了,就哭喊着不肯走,要人的亲戚已经打定了主意,那肯改变,把那孩子抱到自行车上,一只手捺住了,骑车就走。孩子在车上使劲踢使劲闹,那车子就不停的来回晃,走老远了,还听那孩子喊,“爹呀,娘呀,为什么把我送人呀?你们再也不要我了呀?”
过继一般选男孩,如果是兄弟,大多在一个村住着,孩子两边跑,也不用改姓,父母经常能见到,孩子好像也和住在自己家没多大区别。如果男孩年龄大些的,父母会直接开导他,说,你看你叔,或者你大伯家日子多好,过去受不了罪,往后你也大了,也快说媳妇了,有他们操办,也省了父母的心。如果你不过去,你看看,上面还有好几个哥呢,什么时候轮到你,你想打一辈子光棍呀。
农村把找不到老婆的男人叫光棍,三十大几的人,在村里走过来走过去的,让人瞧不起。光棍汉子在一起,也没什么正话说,专讲一些传奇故事,不是这家地主小姐看上这个光棍了,就是那个地主小姐看上那个光棍了,一天天地做白日梦。如果村里来个女讨饭的,那光棍们就像乱了窝一样,四处打听去哪里了,恨不能领到自己家来。又是扫院子,又是收拾屋子,还把多日不洗的脸擦干净,别人家怕要饭的上门,院门都关上,只有光棍汉的院门屋门都敞着。
过继的孩子听父母这样说,也知道父母是对自己好,尽管心里不高兴,但并不恨父母。父母这时还会说,你看你叔或者大伯家,日子比咱家里好,等他们老了,那家里的东西全是你的了。
话说到这里,那男孩不仅不恨父母了,还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恐怕其他兄弟过来要和自己抢一样,以前是天天住在父母家里,只是名义上过继,后来,便去叔叔或者大伯家多了,渐渐就不回来住了,和父母的感情也一天天淡下去。
如果是姐妹来要,麻烦就多一些,姐妹嫁在一个村的少,大多在外村,甚至外县,外省,孩子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一次,去了还要改名换姓,孩子虽说是自己亲生的,但一送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养儿才知道父母恩,要孩子的人自己没生育过,不知道养大个孩子有多难,加之这孩子又不是自己亲生的,也没什么感情,家里添个孩子,就像添了头猪狗一样,也不管孩子冷暖,自己身上一天天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孩子却成天穿得没个人样,天热了还没单衣换,或者天冷了还没棉袄穿。
来之前许下的好吃的好玩的都没有了,一天天就知道让孩子干活,天不亮就往地里撵,不是砍草就是拾柴去,回来还要挑水做饭,而那两口子还躺在炕上呼呼大睡呢,就是醒了,也不起来,在被窝里翻个身,说,去,把鸡窝打开去,去,把院子扫扫。
孩子干的活越多,就越恨自己的父母。我记得有个叫树立的,五岁时就给了他姑姑家,等他要结婚时,他父亲说,如果他再叫他一次爹,他愿意给他买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位列“四大件”之首,另外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树立别说叫爹了,看都没看他爹一眼,扭头走了。
过继后的孩子,也有再接回来的,这种情况一般是要孩子的家庭发生了变故,或自己生了孩子,或者两口子有一方过世了,另一方又重新组成了家庭。
接回来的孩子性格也变了很多,半夜里总是哭,父母说什么,总是不听,用农村的话说,你让他打狗,他骂鸡,你让他上东,他上西。反正就是和父母对着来。有的父母气得就打自己,那孩子冷冷地看着,像个外人一样。这感情有的过几年就好了,有的一辈子再也没好过。
摆话蛋
站在东家往西看,一家一个摆话蛋。
农村人把说话叫摆话,摆话蛋也是一个级别,相当于家庭说话冠军。
摆话蛋是男人的专称。
我仔细想了一下,摆话蛋都是瘦人,因为一天天摆话,可能也会耗费很多精力,有的早晨一出家门,就伸懒腰,打哈欠,睡了一夜了也没休息过来。
人都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摆话蛋只有遇到另一个摆话蛋才会兴奋得两眼放光,嘴唇也像刚抹了润滑油一般红润起来,揣在袖子里的手也像抽芽的树枝,在风里不停地摆动着,嗓子也不由自主地咳嗽几声,就像戏台上那唱戏的,先啊啊几声。
摆话蛋摆话的内容和闲话老婆不太一样,张家长,李家短的,有的和现实生活不太搭界,有的类似幽默小品,有的类似于民间传奇,有的则是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各有所长,各有所好,也各有各的听众。
摆话蛋一个人守着几个听众,有点像单口相声,说得人也没多少精神,语调也低,如果再有另一个摆话蛋加入,就有如多了一个捧哏的,你来我往,气氛就热闹了许多,如果再来一个摆话蛋,就有点像演小品了,各亮各的绝活,听众里也会笑声不断。
我村有个叫柱子的,就是有名的摆话蛋,长脸,眼睛向外凸着,爱眨眼,牙齿也长在嘴唇之外,永远装不进嘴里去,因为爱摆话,队长让他在外面跑业务,当时我们村有个明胶厂,有一天他到县城跑销路,他一个人骑着车子这个没劲呀,车子左摇右晃的,连骑车的劲也没有了,正在他打算坐下休息一会的工夫,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车从他身边路过,他马上来了精神,说:“大哥去哪里呀?”
那人回头看了一眼柱子,说,“回家!”
柱子说,“正好,咱一块走吧!”
柱子紧蹬几下车子,追上那人,扯东拉西的就和人家摆话起来,说谁家生的孩子没有屁眼,光吃不拉,那肚子憋得鼓鼓的,孩子光哭,没办法就去医院人工开了一个,人工开的口没弹性,不敢吃主食,只吃流食,怕便秘。后又说有一个男人三条腿,两条腿走路用,走路走累了,就把另一条腿从裤子里搬出来,像放凳子一样,放到地上,能坐在上面休息。
那人只是听着笑,并不接话,柱子摆话得就更上劲了,说有一个人会气功,一天摆场子表演刀枪不入,等他运好气,有人把刀抡圆了向他的肚子砍去。
那气功师脱了上衣,露出鼓鼓的肚子,又使劲束紧黑布条的腰带,来个骑马蹲裆式,两手使劲向前伸,开始运气,不一会,那气功师的脸就憋得黑红黑红的了,眼珠子也憋得鼓鼓的,那抡刀的看他运得气够足了,抡刀就砍了过去,就在那刀将要砍到气功师的刹那,气功师的脑盖骨“嘭”的一声飞上了天,气功师倒地身亡,原来他把该运到肚子上的气运到头上去了。
“还有,还有……”柱子那个兴奋呀,因为他从来没摆话过这么痛快,那人下了车子,笑呵呵的说,“还有什么呀,我到家了,你去哪里呀?”
柱子说:“我去县城跑业务呀,这是到哪里了呀?”
那人就说,现在到市里了,县城都过了一百多里地了。当时已经中午了,那人看柱子除了爱摆话也没什么坏毛病,就留他在家里吃饭。
那人有个妹妹,二十三四岁了,圆脸,五官都不少,就是眼有点向下凹,有点像长在深坑里一样。皮肤挺白,就是雀斑大点,像在脸上贴了部分雀蛋皮。
柱子本来也不好看,再加上又是个摆话蛋,游手好闲的,没人肯把闺女嫁给他,快三十了,还是个光棍,那人就问柱子愿意娶他妹妹吗,柱子一个农村人,一下子娶了个市里的,虽说是个菜农,也好比老鼠找了一个蝙蝠,人家怎么也算是个“空姐”呀!哪有不愿意的道理。
柱子娶亲的前几天,我村的另一个摆话蛋,主动跑到柱子家去,问柱子他娘,说:“婶子。俺柱子哥以后还回来吗?”
柱子他娘说,不回来了,市里多好,听柱子说,市里的房子有的叫楼房,比村口那棵百年老树还高呢,茅厕也在屋子里,在屋里吃,在屋里拉,特别方便!
摆话蛋听了,就去找队长,也要当业务员,队长说,说说你会摆话什么,这个摆话蛋就像面试一样,摆话起来,什么四大软,什么四大硬,什么四大痛快,都是荤素搭配,没一个是能摆到桌面上的。队长就说,咱俩拉拉手吧。
拉手是农村买卖人之间谈价的动作,队长先摸了摆话蛋两个手指头,又攥了一下他的手,意思对方是二百五,说,你是这个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