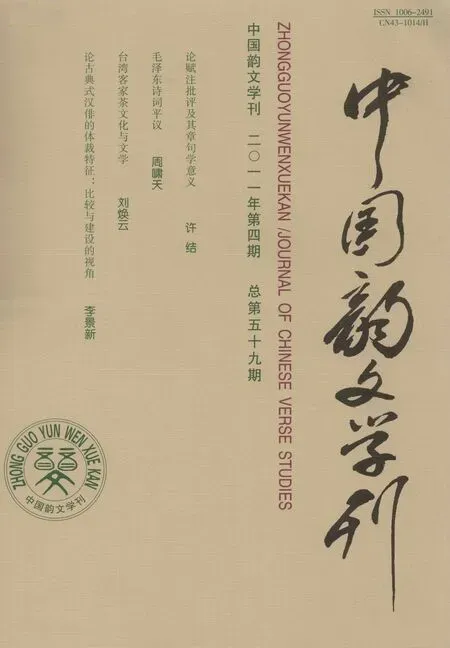论赋注批评及其章句学意义
2011-11-20许结
许 结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赋注兴起于晋、宋时期,有同时人注与后人注之分,及自注与他注之别,对此,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注例》辨云“古赋不注,世传张平子自注《思元赋》,李善已辨之矣。盖两汉魏晋四朝皆无自注之例。赋之自注者,始于宋谢灵运《山居赋》”;又云“有同时人而为之注者,如刘逵之注《吴都》、《蜀都》,张载之注《魏都》是也。有后代人而为之注者,如郭璞之注《子虚》,薛综之注《二京》是也”。至于赋注之用,李善《上文选注表》所言“弋钓书部,愿言注缉”,说明其缉录注解之义。然而赋注何以兴起于晋、宋,盛行于唐、宋以后,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赋学批评形态的意义,则无专论,本文试为辟发,聊作引端。
一 赋注与经学传注传统
在文学史上,赋注实缘于“文集”之兴①按:古代文章初指辞赋,刘歆《七略》设“诗赋”(以辞赋为主)一略,至王俭《七志》始改称“文翰”,已兼“杂文”,阮孝绪《七录》则立“文集”,以明当时作者专集之兴。,且开作者“文注”之先声;而作为“注”例的传承,则显然又缘自“经注”,即汉代兴起的经学章句之传注之学。对此,倘作宏观思考,则与学术大势之变移有关。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论《文集》云“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又如吴汝纶《天演论序》论晚周诸子后之学术则“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虽视阈不同,但有一点是相近的,那就是专家之学的衰退,解释性学问的兴起,注疏之学则与此学术大势纲维相系。落实到具体,由经注到赋注,则在于汉人传注之学的兴盛。刘知几在《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中解释传注云:“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1](P131)②按:浦起龙释:“首原训诂之体,名殊义一。”传注一体,均“训诂”经义,然所言“转授”与“流通”,又明两用,而有关赋注(训诂)的产生及意义,亦当于此经学渊源予以体认。试作三层辨析:
其一,经传与赋的关系。“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2],而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就其本质而言,是“传”经的时代,如四家(鲁、齐、韩、毛)传《诗》等,以明经学“转授”之意义,然“赋”与经“传”共时而兴,其间关系,值得一辨。首先,赋之本字与“传”通用,如《汉书·淮南王传》“安入朝,上使为《离骚传》”,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读之,若《毛诗传》”,取“传”解“经”义,清人王念孙则谓:“传当作傅,傅与赋古字通。注曰:《皋陶谟》‘敷纳以言’,《文纪》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3](P296)此取“传”(傅)即“赋”义,绝非孤证,如近人啸咸《读汉赋》认为王褒《四子讲德传》据《汉志》宜为“赋”,《文选》改题为“论”,是“传亦谓之赋”的例证[4]。1993年尹湾汉墓出土汉简《神乌傅》,也是“傅”、“赋”字义相通又一证据[5]。其次,汉赋作为一种新文体,无论在词章、义理上的用“经”,还是对如《诗经》创作的拟效,都具有一定以“文”传“经”的意义,这与班固《两都赋序》所言“赋者,古诗之流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就赋用“经”而言,或取其辞,如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取辞于《诗·召南·殷其雷》“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或取其义,如王粲《登楼赋》“冀王道之一平兮”,取义于《尚书·洪范》“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表达处乱世而对太平的期盼。由此于“经”的引述与推阐,所以宋人龚鼎臣《东原录》有谓:“赋亦文章,虽号巧丽,苟适其理,则与传注何异!”至于拟效,赋与《诗》的关系最为密切,如主题描写:论宫室,则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之仿《鲁颂·閟宫》;写都邑,则有班固《东都赋》之仿《商颂·殷武》;述游猎,则有扬雄《长杨赋》之仿《大雅·皇矣》等,诚如晋人孙绰谓“《三都》、《二京》,五经鼓吹”[6](P260)。由赋本义到其用经与拟效,无不表现出对经义解释、推扬的特征,这与经之“传注”异质同构,也因此可见从经注到赋注的历史渊源。
其二,经注与赋注的关系。赋注是文学注疏的最早样本,也是继经注后出现的文学注疏体,其与经注不仅有一贯之义,如赋注在经义上可谓对经注的再阐,而且其注例亦拟效经注,形成内在的关联。汉代经学传注,如文帝时立《鲁诗》、《韩诗》,景帝时立《齐诗》,三家已备,武帝时《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书》立欧阳(生),《礼》立学官,迨至宣帝,《礼》分大、小戴(德、圣),《春秋》立“公羊”博士,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等,其如欧阳氏、平氏传《欧阳尚书》、夏侯氏传大、小《夏侯尚书》、韦氏传《鲁诗》、伏氏传《齐诗》、尹氏传《谷梁春秋》,皆训举大义,研习章句,所谓“汉人最重家学,世世转相传授,盖欲其益明耳”[7]。这种经注家数,如三家注《诗》,均单注一家,赋注拟效,则如刘逵之注《吴都》、《蜀都》,张载之注《魏都》,郭璞之注《子虚》,薛琮之注《二京》;而由家数入于会通,亦汉代经注史实,如郑玄汇注《三礼》,笺注《毛诗》,尝以《礼》注《诗》,以《诗》笺《礼》,赋注拟效,则如六臣注《文选》,其中赋作十五类,皆汇注性质。然考察赋注的出现,则缘于赋集(选)之兴,而其前因,又是经学读(注)本在东汉以后的盛行,这与章句之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三,章句与经注、赋注。从广义而言,经注、赋注都是章句之学,赋注对赋作章句的解释,也是缘自汉代经学章句的。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可见章句学不仅在字句篇章之解,还在通明大义,这是注例之要则。据《隋书·经籍志》载,汉代经学章句著目甚多,其中如《诗》之薛氏章句、《春秋》之贾逵章句,皆为当世显学,而王逸《楚辞》章句正秉承“依经立义”①王逸《离骚经章句》有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后世赋学章句的榜样,至于晋以后大量赋集的出现,如谢灵运《赋集》92卷、崔浩《赋集》86卷、梁武帝《历代赋》10卷等17种,既为赋创作提供范本,也表明其赋学章句的兴盛②如《隋志》著录之梁武帝编《五都赋》6卷,即汇集张衡《二京》与左思《三都》而成,为京都赋提供范本,《文选》赋首“京都”当与此有关。。而由“谢注”到“《选》注”,其对赋语言学、词章学、名物学、典故学、鉴赏学的批评贡献,已成为辞赋笺注学的历史性范本。
二 以“谢注”与“《选》注”为例
魏晋以后,文章大显,既有名“作”,也多名“注”,其时除“经部”群注外,有如“史部”之郦道元注《水经》、裴松之注《三国志》、“子部”之刘孝标注《世说》,成就“三大名注”美誉,且与原著相得益彰。而“集部”之注,据《隋志》所载,首标王逸注《楚辞》12卷、郭璞注《楚辞》3卷,而诗、文则有蔡邕《典引》注、刘和《杂诗》注、沈约、王纶、陆缅诸家《梁武连珠》注、何承天《连珠》(陆机)注等,而“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8](P1089),故赋注尤盛。如《隋志》有“《杂赋注本》三卷”下著录:
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
薛琮注张衡《二京赋》二卷;
晁矫注《二京赋》一卷;
傅巽注《二京赋》二卷;
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
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
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
徐爰注《射雉赋》一卷。
他如“孙壑注《洛神赋》一卷”等,惜多亡佚。因此,探讨赋注义例,现仅存较早的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与《文选》赋注,堪称范式。
“谢注”开赋作自注之先河,成为读解赋文本意的第一手资料,故具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思想意义。试观其中注例一则:
《山居赋》:“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妍。年与疾而偕来,出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自注:“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之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9](P1576—1577)①按:《山居赋》载录《宋书·谢灵运传》,又见《艺文类聚》卷六十四。严可均《全宋文》卷三十一收录。
其注以训诂解义理,以释典明赋意,其中尤以阐明文意出处,最有价值。如释“今事”,赋中云“远南则松箴、栖鸡、唐嵫、漫石”一段,作者自注:“栖鸡,在保口之上……松箴在栖鸡之上……唐嵫入太平水路……漫石在唐嵫下……下有良田,王敬弘经始精舍。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注明当时地理,兼及人文事相。而释“古典”,解释章句,则又兼及“四部”(经、史、子、集)。如引“经”者:
《山居赋》:“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祛弊;宫室以瑶琁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自注:“《易》云,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盖取诸《大壮》。琁堂自是素,故曰白贲最是上爻也。”[9](P1755)此取《易》义,隐括古典,故以自注说明。又如引“集”(文)者,其赋文云:
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应璩作书,邙阜洛川。势有偏侧,地阙周员。铜陵之奥,卓氏充釽摫之端;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
再观其自注:
仲长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广泽,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后。”应璩与程文信书云:“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谓二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扬雄《蜀都赋》云:“铜陵衍。”卓王孙采山铸铜,故《汉书·货殖传》云:“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金谷,石季伦之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镇下邳时,过游赋诗,一代盛集。谓二地虽珍丽,然制作非栖盘之意也。凤台,秦穆公时秦女所居,以致箫史。丛台,赵之崇馆。……楚之云梦,大中□居《长饮赋》②按:诸本皆缺一字,或作“山”字,据有关学者考证,此处有脱误,引赋文当出自边让《章华台赋》。:楚灵王游云梦之中……遂造章华之台。……淮南青丘,齐之海外,皆猎所。司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园,卫之竹园,在淇水之澳,《诗》人所载。橘林,蜀之园林,扬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长洲,吴之苑囿,左(思)亦谓长洲之茂苑。[9](P1755—1756)
其中广引仲长统《乐志论》、扬雄《蜀都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左思《三都赋》、应璩《与程文信书》等集部文献,兼及史部,且隐述《诗·卫风·淇奥》诗意,以释解赋文的名物、典故,尤其是赋家对前人创作的拟效,通过自注加以钩沉与阐发,于文献、学术,均有直接意义。例如赋中引述“子部”文献,则多属《老》、《庄》,如赋写江海,则注引《老子》“海为百谷王”,《庄子》之“海若”;赋写“有贷以善成”注引《老子》“善贷且善成”、赋写“糟粕犹在”注引《庄子》“轮扁语齐桓公”寓言等,如果合观其引“经”多《易》义,正构成“三玄”之学以印合当世学术思潮,构成赋作的“嘉遁”主题。
“自注”最能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由谢氏开创的这一注例,亦为后世赋家承继,如宋初吴淑撰《事类赋》并自注,即为又一典范。而与“自注”不同,继“谢注”后之“《选》注”则属“他注”,其注本又分两种形态,一是“单注”,即“李善注”;一是“汇注”,即“五臣注”(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又合“李善注”为“六臣注”①按:据近年由日本引回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选》注除“六臣注”,尚有公孙罗、陆善经注等残文,可资参考。。相对而言,“他注”与“自注”比较,更多文献的征引与意义的阐发。例如《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所言“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李善注引《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子曰:东里子产润色之”,以及扬雄《剧秦美新》“制成六经,鸿业也”等文献以证其文意之渊承。又如赋序谓“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李善注:“言周道既衰,雅、颂并废也。《史记》曰:‘周武王太子诵立,是为成王;成王太子钊立,是为康王。’《毛诗序》曰:‘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乐(纬)·稽耀嘉》曰:‘仁义所生为王。’《毛诗序》曰:‘止乎礼仪’、‘先王之泽也。’然则作诗秉乎先王之泽,故王泽竭而诗不作。作,兴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10](P21)如此广征文献,复叠引述,充分显示了“他注”对原文意旨的发覆与再阐。当然,“《选》注”与“谢注”之不同,还在于“汇注”的特征。
试以班固《东都赋》为例,来看“李善注”与“五臣注”的互参与济补:
赋文:“乃动大辂,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李善注:“《东观汉纪》曰……《周易》曰……《逸礼》曰……《尚书》曰……。”李周翰注:“大辂,天子法驾。言动法驾,遵天子之衢。衢,道也。省方,观四方也。巡狩,循行守牧之人,谓察四方之士,观诸侯之政。穷,尽也。览尽万国土物之所有无。被,及也。烛,照也。考声教所及幽远之处,则以皇明照之。
赋文:“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李善注:“《左传》臧僖伯曰……《礼记》曰……《王制》曰……。”刘良注:“言因蒐狩之时简兵讲武,则依《王制》、风雅之节。《王制》,礼篇名也;风雅,《诗·小雅》章。”
赋文:“焱焱炎炎,扬光飞文。”李善注:“《说文》曰……《字林》曰……。”吕延济注:“焱焱炎炎,旌旗貌,飞扬光彩成其文。”
赋文:“举烽伐鼓,申令三驱。”李善注:“《毛诗》曰……《尚书传》曰……《周易》曰……。”吕向注:“伐,击也。言举烽击鼓以申令三驱。驱,逐也。三驱之法,背己及左右驰者皆逐之,向己舍之,故曰三驱。”
赋文:“由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睇禽,辔不诡遇。”李善注:“《左氏传》曰……孟子曰……刘熙曰……。”张铣注:“由基,善射者;范氏,善御者。睇,迎视也;诡,异也。言射者不迎视其禽,御者不诡异以随物。言车骑轻捷,鸟兽不暇翔去而至杀,不必尽杀去也。”[11](P26-27)
上列五臣注各一例,可见李善注(略)多征引文献,而五臣注则多释文阐义,可为互补。例如第三例李善注引《说文》、《字林》释“焱焱”为“火华”,“炎”为“火光”,而吕延济注谓“旌旗”飞扬之状,两说虽异,自可并存。
从“《选》注”赋例,可见较“谢注”尤密,其中通训诂、考名物、释章句、明义理,基本成为后世赋注拟效的法则,然其中也内涵了“赋注”的特色与意义。
三 作为批评形态的赋注
赋注依附于赋作,所以作为一种批评形态,势必落实于赋体,也就是由赋体看赋注,则能区别于其它文体之“注”,并可从其独特风貌观觇赋注的赋学价值。
如前所述,赋注中无论是自注还是他注,也无论是单注还是汇注,作为“注”体的基本特征,如注音、诠字、训诂、释义等,是为通例,并无特异。因此,赋注的特色,更多体现于赋体的特色,尤其是大赋体的宏衍博丽,其中的丰富内涵,非赋注难以彰明,而赋注的批评形态,则因赋体之内涵而呈现。再以“《选》注”汉赋为例,胪举其特色:
一曰“经义拟效”,这根源于“赋者,古诗之流”的创作意识,汉赋从某种意义上成为承载经义的特殊形态,而后世创作,特别是唐宋诗赋取士,常常用经题而明经义,形成一大创作传统②清人阮亨《律赋经畬集·凡例》(道光己亥新镌扬州二酉堂藏板)云:“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元仆射《镇圭赋》、白尚书《性习相近远赋》、蒋防《不宝金》五赋、王起《庭燎赋》、《蛰虫始振赋》、陈仲师《鹊始巢赋》、张仲素《反舌无声赋》、李处仁《虹藏不见赋》、韦充《东风解冻赋》、许敬宗《麦秋赋》,其他不可枚举。我朝经学昌明,星使抡材,悉取经语以觇古学,故是编专采五经,若《论》《孟》《学》《庸》《周官》《尔雅》凡在《十三经》之目者,间亦采焉。”按:此选考试律赋专用经题者。。对汉赋用经,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有所言及:“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及扬雄《六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述于纪传,渐渐综采矣。到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而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于中如张衡诸赋,引述经义百余处,仅《思玄赋》一篇,引《诗》《书》词义,竟有数十例。试摘录赋中数语及《文选》李善注如次①按:衡赋有旧注,《文选·思玄赋》李善注:“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李说甚是。:
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穷而介立。(李善注:《毛诗》曰:“独行茕茕。”《楚辞》曰:“既惸独而不群。”)感鸾鷖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李善注:鸾鷖,喻君子也。《毛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彼无合而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旦获讟于群弟兮,启金縢而后信。(李善注:《尚书》曰:“武王既丧,管叔乃流言于国曰:‘公将弗利于孺子。’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王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说……”)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旧注:《毛诗》曰:“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李善注:毛苌《传》曰:“辟,法也。民之行多为邪辟,此言无遣为法也。”《尚书》曰:“蒸民乃立。”)[10](P214)
按:李善注分别引述《诗》之《唐风·杕杜》、《曹风·鸤鸠》、《大雅·板》,《尚书》之《金縢》、《益稷》(古书合于《皋陶谟》)诸篇词语,以明张衡描写之出处,于注释赋文的同时,也彰明经义。正因赋家好为用典,故经语经义融织赋作描写之广与密,其它诗文诸体无与伦比,这一赋体特色,也为注家留下使才骋学空间,形成赋注既依经立义,又广征博采的特色。
二曰“名物之类”,标明的是赋之“体物”特征,亦即“赋者,言事类之所附”(曹丕《答卞兰教》)的创作原则,因而赋注在极大意义上成为赋的“名物”解释,并由此构成特有的批评体系。缘此,晋人左思摹拟汉人而作《三都赋》,立意就在“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三都赋序》)[10](P74);清人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其“按部考辞,分题辨类”的编排意识即着眼于所谓“上稽乾度,笼星辰雨露于毫端;俯验坤舆,聚都邑山川于纸上。大之兵农礼乐,动合王章;小之服食舟车,咸关日用。……虫鱼草木多识,乃格物之资;刀剑琴书游艺,亦怡神之助”(《上历代赋汇表》)[12]的“物态”与“事类”。元人陈绎曾论《汉赋法》,认为:“汉赋之法以事物为实,以理辅之,先将题目中合说事物一一依次铺陈,时默在心,便立间架,构意绪,收材料,措文辞。……写景物如良画史,制器物如巧工,说军阵如良将,论政事如老吏,说道理通神圣,言鬼神极幽明之故,事事物物,必须造极。”[13]基于这样“穷形尽相”的“物态”描写,以致有谓“《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作志书、类书读”(袁枚《历代赋话序》)[14],即“赋代类书”说。回到赋体创作,诚然如此,而赋注围绕赋家描述内涵的解释,亦自然以名物为中心而展开。如司马相如《上林赋》继上林之“水”所谓“八川分流”的精彩描绘之后,转而叙写水中之物及注家辨类分解云:
于是乎蛟龙赤螭,“鱼亘”“鱼瞢”渐离,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李善注:文颖曰:“龙子为螭。”张揖曰:“赤螭,雌龙也。”李奇曰:“周洛曰鲔,蜀曰“鱼亘”“鱼瞢”,出鞏山穴中。”司马彪曰:“渐离,鱼名也。”张揖曰“未闻。”郭璞曰:“鰅,鱼有文彩,鰫,似鲢而黑,鰬似鱓,魠,鱤,一名黄颊。鱓音善;鱤音感。禺禺,鱼皮有毛,黄地黑文。魼,比目鱼,状似牛脾,细鳞,紫色,两相得乃行。鰨,鯢鱼也,似鲇,有四足,声如婴儿。”又,吕延济注:并龙鱼名。)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李善注:郭璞曰:“揵,举也。鳍,背上鬣也。”《高唐赋》曰:“振鳞奋翼。”郭璞曰:“处,隐岸底也。”又,张诜注:深岩窊曲处也。言龙鱼之徒皆举掉鬣尾奋振鳞翼于窊曲之处。)鱼鳖欢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李善注:《小雅》曰:“夥,多也。”应劭曰:“靡,边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边也。张揖曰:“靡,厓也。”《说文》曰:“玓皪,月珠光也。”玓皪与的皪音义同。又,吕向注:欢,鸣也,谓鱼鳖戏跃声也。万物非一类也。明月珠子,水宝也。的皪,光明貌。靡,江边也。)蜀石黄碝,水玉磊砢。(李善注:张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碝石,黄色。水玉,水精也。磊砢,魁礨貌也。”《山海经》曰:“重庭之山,其上多水玉。”又,吕向注:磊砢,相委积貌。)磷磷烂烂,采色澔汗,丛积乎其中。(李善注: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辉也。”又,李周翰注:言宝玉符采映辉之貌。丛积,谓丛积于水中也。)[11](P179)
李善注以引述旧说为主,五臣则或自为说解,然均释名物,通训诂,显然一致。当然,赋家体物,义出多端。其与当代都市文明、商业贸易、外交活动、礼仪行为等关系密切,故有“物以赋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赋取穷物之变”(刘熙载《艺概·赋概》)之说[15]。而其“体物”方式,又有横向罗列如前引《上林赋》之“水族”等,或为纵向叙写如张衡《西京赋》中“百戏表演”等,赋家描写尝尽心于此,所以注家同样用力于此,使赋注成为形象生动的名物词典。
三曰“宏博之象”,这是赋的体势与景观,同样包含了赋兼才学与词章意义,而赋注围绕赋家笔势的展开,也具有宏衍博丽的特征。至于赋家宏博,祝尧《古赋辩体》卷三《两汉体上》对《子虚赋》有段形象的描述:“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綵缯之之父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16]针对这种创作现象,近人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曾论西汉辞赋云:“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沈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17]这里既倡赋家湛深之学,又重视赋作笺注的学问,绾合二者关系,是有意义的。如班固《西都赋》描写西京制度,先述三辅之胜境,极尽描绘四方景象之能事,试举其“阳”(南)、“阴”(北)数语为例:
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李善注:《上林赋》曰:“崇山嵸巃崔嵬。”扬雄《蜀都赋》曰:“苍山隐天。”《韩诗》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汉书》东方朔曰:“汉兴,去三河之地,止灞浐以西,都泾渭之南,北谓天下陆海之地。”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又,吕延济注:海者,富有如海,故言陆海珍藏。谓美玉出蓝田。)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李善注:《汉书》:“弘农郡有商县、上雒县,扶风有鄠县、杜陵县。”《说文》曰:“隈,水曲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滨,涯也。”又曰:“泽鄣曰陂,停水曰池。”又,吕延济注:商洛,山名。)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注:言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汉书》曰:秦地“南有巴蜀广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尔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又,李周翰注:言水物杂出与蜀相类,故曰近蜀。)
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李善注:《汉书》:“谷口县九嵕山在西。”《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大王之国,比有甘泉、谷口。”《汉书》:“公孙卿曰: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甘泉作延寿馆、通天台。”《汉宫阙疏》曰:“甘泉林光宫,秦二世造。”《汉书》曰:“王子渊作《甘泉颂》。”又曰:“扬子云奏《甘泉赋》。”又,张铣注:九嵕,山名。上有九峰冠,犹戴也。甘泉,山名。汉置宫于上,以祈祀,故言灵宫。又,刘良注:秦汉之君皆于此游观。)[11]
由此一例,可见注家对赋之宏博之象的认知与解读,既具体而微,也视野开阔。当然,注家所及赋中博物之象,又源于赋家的创作特征,于此相关者如前所述有二:一是赋兼才学,如周雷《历朝赋衡裁序》所言“平子赋都,给笔札者数年;太冲研京,搜故实者十稔。故能牢笼百态,摇劈群言。既徵博以逞奇,亦积迟而造险”[18],赋家的艰辛也带来了注家的艰难,赋作的才学也必然影响着赋注的博采。二是赋重修辞,如方逢辰《林上舍体物赋料序》所说“赋难于体物,而体物者莫难于工,尤莫难于化无而为有。一日长驱千奇万态于笔下,其模绘造化也,大而包乎天地;其形状禽鱼草木也,细而不遗乎纤介”[19],体物之工,在修辞之妙,赋注着力于此,其中详尽的解释,乃于赋体词章学之构建作出不可忽略的贡献。
唐宋以后,赋体进入程试,为适应士子科举文战竞技之需要,诸多赋选与赋注已为教学与传播之需要,古典的“时文”化,也使赋注具有了更为普遍的工具化的功能。例如大量类书的出现与为提供士子文试津筏相关,而宋初吴淑撰赋体“类书”之《事类赋》,且加详注,所谓“遽奉训辞,俾加注释……庶令学者知其所自”(《进注事类赋状》)[20](P2),即彰显其功用。也正因为科举考赋之风的兴起,赋注又逐渐脱离单纯的赋学笺注意义而与赋的解题、评点等手段结合,进一步汇融于赋体章句学。
四 赋学章句:注释与评点
赋注重在明训诂,释章句,而赋评同样是对章句的解释,自唐宋以后科举考赋,特别是清代围绕翰苑试赋制度出现的大量赋选,往往注、评合璧,形成较完备的赋学章句体系。对因科举试文而兴的章句评点,学界或有轻诋,而吕思勉《章句论》则于其中“圈点”之法颇有正面评价:“圈点之用,所以抉出书中紧要之处,俾人一望而知,足补章句所不备,实亦可为章句之一种。”[21](P52)如果说早期赋注与评更多地是对赋作进行整体性的阐释,那么自科举考赋以后,此类注与评则更着重于“擒题”,以为类型之示范。清人顾南雅《律赋必以集·例言》云:“每一题即有一题应用之典,且分出数层,即有每层中应用之典,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往往有绝不相涉,引来适成奇妙者,此又在组织之工,心思之巧也。”[22]也正因为这种“奇”、“巧”在技艺上的讲求,赋的批评在工具化的同时,也变得细密化。例如赋之“体物”一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倡“体物写志”说,而至元人陈绎曾《文筌》撰《楚赋制》、《汉赋制》时,则引申出“实体”、“虚体”、“象体”、“化体”、“量体”、“连体”、“影体”七类,至于他法,亦可谓达到“穷形尽相”的境地。
由此赋学批评背景的变化,再看赋注与赋评,其于章句的研讨,最突出地是体现在“句法”之意义。早在唐代围绕科举试赋而编纂的《赋谱》[23],就是以句法为中心的,所谓“凡赋句有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而其中“隔句”又有六法,即轻、重、疏、密、平、杂,这决定了赋的长短与体势,也成为论者传授赋法的关键所在。南宋郑起潜编写士子范本,于《声律关键》论律赋句法谓“何谓琢句?前辈一联两句,便见器识。……造句不一,四六为工,八字句尤典雅。前辈云:长不如短,缓不如切,轻不如重。……每韵起句、接句、缴句、散句、联句,贵有精神,有力量”等[24],也可见对考赋之句法的重视。由于珍重“句法”,后世评注结合,多由句解展开,用于教学。例如清人叶祺昌编《律赋标准》[25],于《序》中言评注体例云:“先解题,以示作法揭宗旨;次句解,讲明用意,俱切题诠发,反正离合,虚实浅深,或顺或逆,要不使一语蒙混,一字含糊;段后分疏每段大意,条分缕析,以见篇法;篇后又总评通篇佳处,务将作者布局命意运笔遣词之苦心,抉发靡遗……又恐初学见闻未广,腹笥未充,因特详为注释,以便翻阅。”据此序所言,形成了由“题解”、“行批”(句解)、“疏义”(段意)、“总评”(篇法)与“注释”组成的宏整的阐释批评系统,其中“注释”似乎退居于“初学”解蒙的次要地位,但如果对读其中“注释”与“行批”,同样可见以句法为中心的批评特征。比如书中评解盛观潮的八韵律体《隔千里兮共明月赋》(以题为韵)“行批”与“注释”一例:
于是(行批:此二字是从上段顺笔接说。)客邸身羁,故园目纵。愁重于张,[注释:张平子有《四愁诗》]秋悲似宋。[注释: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行批:是隔千里之心绪。)帛传飞雁,[注释:《汉书·苏武传》:“后汉使复至匈奴,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在某泽中。”]报来两字平安;塞远卢龙,[注释:高适诗:“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寄道一声珍重。(行批:是别后不能共的情怀。)试问露零地白,秋思谁多;[注释:王建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愁思在谁家。”]料知烛灭光寒,[注释:张九龄诗:“灭烛怜光满。”]夜吟应共。(行批:人隔千里,不能共处一堂;月虽一个,可以两地同看。)①有关叶著对清代律赋之注评与介绍,详参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至148页。
其中注释仍延用前此注式的解释名词,训诂词义及申明文意出处,然旧注对句意的阐释则由评点(如行批)取代,形成了注、评结合的批评方式。
由于赋选、赋格的大量出现,赋注也呈示了多种形式。如余丙照的《赋学指南》是一部兼赋格、赋选的编撰,为示士子津筏,就有“总注”与“分注”的区别。比如余编论述赋家“诠题”中之“点醒”一例,引述清人陆润章《小楼一夜听春雨》、齐召南《壁中闻丝竹》等八篇赋题(有简略引文)为范式,其如陆、齐二赋之“总注”云:
《小楼(一夜)听春雨》,陆游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苏轼诗:“宛然学舍小如舟。”杜牧之《秋夕》诗:“天街小雨凉如水。”
《壁中闻丝竹》,《汉书》:“鲁恭王壤(坏)孔子宅,欲以为宫,闻壁中琴瑟丝竹声,得古文《尚书》,悉以还孔子。”《礼》:“王言如丝。”《尔雅》:“疏简,竹简也。”古未有纸,载于简。
余氏所谓“总注”,实际上是采用李善注《选》赋之法以为“题解”之用,其中承变,值得关注。而其编之“分注”,如书中“炼局类”五卷,编者选录自汉迄清赋作(全帙)计54篇(其中当朝即清代28篇),又采用“题解”(或缺)、“注释”(即“分注”)与“评点”三者合成之法,进行阐释。试举两赋为例:
庾信《华林园马射赋》,题解:“《庾子山集注》:华林园在长安城西别苑。”注释一例:“元鸟司历”四句(原赋:于是玄鸟司历,苍龙驭行,羔献冰开,桐花萍合。):“仲春之月元鸟至,天子驾苍龙,献羔开冰,先荐寝庙。季春之月,桐始华,萍始见。皆见《礼记》。”评点引陈念吾语:“琢句端凝,吐词风雅。”(《赋学指南》卷十一)
安苓《燕雁代飞赋》,题解:“《淮南子注》:燕春分来,雁春分去,诣汉中也;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诣彭蠡也。故曰代飞。”注释一例:“燕候社,《广雅》:‘春社来,秋社去。’故谓之‘社以南飞’。雁随阳,杜诗:‘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原赋:燕候社以南飞,雁随阳而北翥。)评点(按:无人名,宜为余氏本人):“凡题有正意宜醒者,泛衍题面,则呆矣。从燕雁取材,从代字落想,使正意轩豁呈露,此老手看题最清处。”(同上卷十五)[26]
此一论古赋,一论时赋(清代),注评均多句解,点醒主旨,授人以渔。然而这种以注评之法融汇古今赋体,又与明清时代“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相关,这不仅使注评“时赋”之法转向“古赋”,更重要的是以“古赋”章句为“时赋”创作示范。再举清人鲍桂星《赋则》评点班固《西都赋》一例,分别有“眉批”与“尾评”。先观“眉批”数则: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眉批:发端简逸,先提东都,逆入最紧。)
“左据函谷二崤之阻”一段(眉批:瑰玮。)
“故穷泰而极侈。”(眉批:穷泰极侈,是西都一篇主意。)
“隆上都而观万国。”(眉批:顿挫。)
“昭承特盛”一段(眉批:昭阳、未央,提出分写。)
“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眉批:随手发出正论。)
“尔乃正殿崔巍”一段(眉批:摹写入神,佳在参差变化无斧凿痕。)
“百兽骇殚”一段(眉批:看似毫不着力,盖意用也。古人不可及处在此。)
“钜石隤,松柏仆,丛林摧。”(眉批:三句参差得妙,古人无板对也。)
再观其“尾评”之语:
是赋超逸不如长卿,瑰奇未逮平子,沉博终让子云,典核且逊太冲,要其措意高,修辞简,布局紧,结体完,兼作者之长而无末流之失,且成之也不需岁月之久,允堪矜式艺林。[27]
鲍氏《赋则》是为正清代翰苑赋体而编,兼及童蒙课赋之用,故而融会古今,以“古”意衡“时”文,借“时”法评“古”体,其尾评“不需岁月之久”之赞语,已透露科场用赋的信息。倘若我们将鲍评《西都赋》与“古注”(如《选》注)并观,则不难可看到赋学章句之承变及完备过程,而其中注评的结合显然是其极为重要的特征。
[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王芑孙.读赋卮言[M].清嘉庆渊雅堂刊本.
[3]王念孙.读书杂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4]啸咸.读汉赋[J],上海:学艺,1936 年第15 卷(2).
[5]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J].北京:文物,1986(8);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J].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陈乔枞.齐诗遗说考[M].清光绪十四年刊本.
[8]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2]陈元龙.历代赋汇[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陈绎曾.文筌[M],清李士棻家抄本。
[14]浦铣.历代赋话[M].清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15]许结.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J].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8(5).
[16]祝尧.古赋辩体[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刘师培.左盦集[M].《刘申叔遗书》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8]周雷.历朝赋衡裁[M].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19]方逢辰.蛟峰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吴淑.事类赋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吕思勉.文字学四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22]顾南雅.律赋必以集[M].清道光壬午重刊本.
[23]佚名.赋谱[M].今有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4]郑起潜.声律关键[M].清阮元辑《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5]叶祺昌.律赋标准[M].清光绪七年重刻本.
[26]余丙照.增注赋学指南[M].清光绪二十三醉经堂本.
[27]鲍桂星.赋则[M].清道光二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