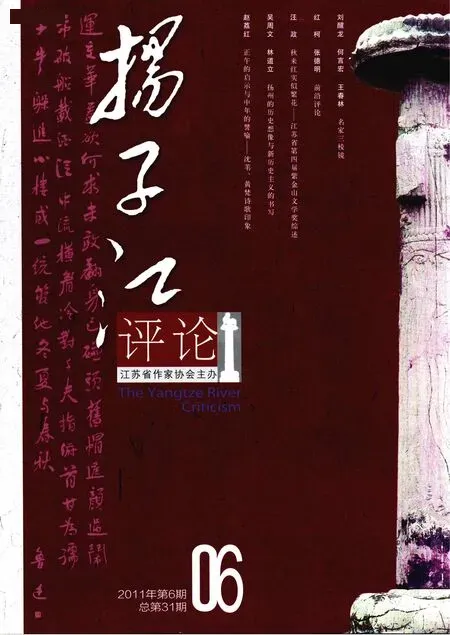从“打工妹”到“知识分子”——试论郑小琼诗歌创作的转型
2011-11-19罗执廷
罗执廷
1980年出生的郑小琼无疑是这几年来中国诗坛最受瞩目的一颗新星。她有着旺盛的创作力,十年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题材包括怀乡诗、打工诗、社会批判诗、女性诗歌等。但她最受关注也最获好评的还是反映打工生活的诗,人们将其纳入“底层写作”的潮流之中并作了高度的评价。正如人们常常谈到的,她这类诗歌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她是以一个打工妹的身份,以亲历的打工体验为基础,对艰辛、屈辱的打工生活,对打工人群的苦难命运进行了深切的描绘,从而引发人们对这种底层命运背后的社会不公进行质疑与反思。2001—2007年间,郑小琼在广东东莞经历着真正的打工生活,从最初辗转于黑工厂和收入极微薄的几家小厂,再到终于在一家五金厂安身,其间打工的真实体验构成了她诗歌创作的基本动力和主要内容。就像评论者余旸所说:“打工生活中特有的经验,比如对铁器、机械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也使其诗歌具备了其他领域的诗人难以具备的经验优势与感受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震撼的感受。”①五金厂的机台操作工,这种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的岗位给了她最底层的真实体验,这也正是郑小琼能够写出那些质朴、粗粝甚至是具有暴戾风格的打工诗歌的重要原因。可以说,长期身处打工生活第一线让郑小琼的打工题材诗歌具有真实感人的细节和生命的痛感,这比那些“前打工诗人”们的追忆性的打工诗更具现场感和冲击力,更是那些“底层关怀”诗歌对打工生活的想象性书写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问题也来了,约自2005年起,《人民文学》、《诗刊》、《诗歌月刊》、《天涯》、《诗选刊》等重要文学刊物纷纷发表郑小琼的诗歌、散文作品,她也频频获得各种诗歌奖项,频频接受媒体的采访,还被推举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成为明星式的公众人物。在她迅速获得了文学声誉和社会声誉,生存环境陡然改变之后,她还能葆有一个打工妹的身份与心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她逐渐脱离了打工第一线,2008年起又成为广东省作协的专职作家兼一个省级文学杂志的编辑。从打工妹到文化人,这种身份的转换及其后果当然也反映到了她的诗歌创作中。最近出版的诗集《纯种植物》(花城出版社2011年6月版)就明显呈现了她这两三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诗歌的书写对象、内容方面,也表现于写法和技巧方面。
在以前的诗歌中,郑小琼常常以一个在场者、亲历者的身份,如实地叙述或描绘着自己以及自己周遭人们的遭遇;而她近两三年所写的诗中则很少有那种亲历的场景,诗人逐渐由诗中的主人公变成了旁观者,由“写自己”转向更多地审视社会、历史,从主要取材于自身经历变为更多地依赖于第二手材料,即使写到自己也多采用第三人称,将自己化作一个被观察者和被审视者。在前一部诗集《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中,总共77首诗(包括长诗)中就有54首明确出现了主人公“我”,约占全书篇目的70%。这种人称使用明显体现出郑小琼对自身经验的重视和表现自我的热情与坦荡。而在《纯种植物》这部新诗集中,只有63首诗出现“我”这一人称,占全书篇目的42%。作为自我叙述、抒情的主人公的“我”的减少表明诗人开始有意地减少自我的出场,或者是在取材上疏离自身经历。我们也很容易感到《纯种植物》中许多诗篇都取材于诗人的阅读经验,比如《灯》、《黑暗》、《读友人私印书籍》、《内脏》、《鹅》、《诗歌》、《转弯》、《木偶》、《深夜诗句》、《霜迹》、《雪山》、《阅读》、《古典》、《流放》、《幻象》、《面孔》、《在冬日》等诗中的“报纸”、“史书”、“书籍”、“书页”、“典籍”之类的语词都明显指向了一种阅读行为。转入职业写作与编辑工作,这让她有了更多的阅读机会,阅读所获得的信息、感想、联想等内容就逐渐取代个人亲身经历,成为近期诗作主要的取材对象和灵感来源。
与书写身份、书写对象的转变相应,她的诗歌表现手法也发生变化,由叙事、场景描绘更多地转向抽象的议论或抒情。在先前的诗歌中,诗人偏好通过叙述事件与经历来表情达意,或者通过具体的场景与细节的描绘来蕴蓄情感与主题,议论、抒情都比较节制。比如写一个叫田建英的城市拾荒者:“1991年她来这里”,“1996年,她回乡/带来了辍学的老大与老二。1999年再回去”,“2001年老大在深圳吸毒贩毒进了监狱”,“这些年,她一直没有变……”(《风中》)通过叙述,诗人勾勒了这个底层妇女的人生轨迹与悲哀命运,其中的同情与悲怆隐而不发,耐人咀嚼。郑小琼运用得更多更成功的还是细节和场景的描绘,且看《碎石场》这首诗:
……我正面对的
是无名山区的黄昏 有炊烟
有朦胧中的光明……
拐弯的碎石场上 三个农妇弯腰拾着
石头 夕阳在背后闪耀 原始的金黄
涂在她们佝偻的身上 啊 这无言的
沉默的金黄 在碎石场的河滩
它们有着神话或者史诗的辉煌
啊 时光经过 它不停地将我磨损
在打开车窗的瞬间 有风正吹送
这山区古老而昏暗的贫穷
又如《在医院》一诗:
……落日照着这个疾病缠身的穷人
我认识他们,来自矮墩墩的山头
他们蹲着
坐着,在医院的门口
他们蛇皮袋子皱褶的衣裳跟长满茧子的手中
带着体温的钞票,他们木讷的眼神
盯着白色的墙壁
……
他们相扶着,走出红十字的医院
落日照着她的眼神,他的疾病
在贫穷中,他躺在低矮的木床上
等待疾病吞食他落日般的生命
在这些诗中,具体而又生动形象的场景描绘本身就内蓄着力量,诗人即使抒发情感也是自然流露,绝无夸张做作。而最近两三年的诗则写法大变,多以直接的议论与抒情取代了场景描写,显得抽象、空洞。例如《裂纹》这首诗:“从地图寻找时间的纹理/风移动发炎的咽喉 盐骨上/搁浅着厌倦 雨水从北方/迁徙到南方 过去像蜥蜴/在墙上爬行 细碎 飘忽/残忍 针表散漫又执拗/充满着寓意 马匹去了象征的森林 成为隐喻/在阴影间 时间有了裂纹/光移开黑暗 屋顶的大海/涨潮水中的树木落叶/石头冒烟 祈祷来自内心”。这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颇觉抽象难解。其实,仅仅从诗题的变化中我们即可看出她近来诗歌的抽象化与不及物性趋势。她先前的诗《碎石场》、《黄麻岭》、《五金厂》、《铁》、《黄斛村》、《银湖公园》、《机台》、《村庄》、《火车》、《深夜三点》、《人行天桥》、《在医院》、《小镇》等,多以具体事物名词为题目,而近两三年则多以“喑哑”、“黑暗”、“关系”、“事物”、“囚”、“交谈”、“橙色年代”、“莫名的力量”等这类抽象名词为诗题。在前一部《郑小琼诗选》中,只有《非自由》、《善恶》、《相》、《所有》、《语言》、《完整的黑暗》、《幻觉者的面具》等十来首诗的诗题较抽象,只占整部诗集的极小比重。而到了诗集《纯种植物》中,148首诗中几乎有四五成的诗都采用了较抽象的诗题。
从上述诗写的变化里,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心态、姿态和诗学取向的变化。概言之,这种变化即是从打工妹“在场”的呈现与“嚎叫”转变为知识分子式的旁观与评说。自然,这种变化并不是这两三年才开始,而是早就有根苗。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郑小琼就声称她最喜欢的其实不是自己打工题材的诗或乡村风格的诗,而是《在医院》、《进化论》、《人行天桥》这一类,“因为这种风格更多的是将我自己置身于一种大的环境的感受……而打工题材与乡村题材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部分感受。前者我想追求一种自由的庞大的,自由性的写作,它们更多的呈现了个体对世界完整的感受”②。郑小琼的意思是她更热衷于那种超越了个人打工体验的,体现了较宏阔的社会视野,具有社会批判性的诗歌写作。从最初的乡愁抒发和个人打工生活书写,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审视,她的视野逐渐开拓,笔触更加深刻、尖锐。然而,从个人经历书写到观察评说整个社会与时代并为底层代言,书写者的身份也在逐渐演变。就像余旸在评论中指出的,随着视野的拓展,诗人的书写也在“越界”,“诗歌中那一拘囿于自己个人经验的独立个体,被一个充满悲悯、俯视人间、拥抱现实(但‘现实’是值得怀疑的)的苦难英雄的形象所代替”,诗人俨然像是“一个坠落在工厂车间的‘普罗米修斯’”③。这也许是受了某些批评家的引诱。从2005年起,关于郑小琼的诗歌评论开始涌现,但这些评论大同小异,都是在强调郑小琼诗歌为底层代言的性质,强调其社会政治意义。这就难免诱导诗人,让她的书写姿态越来越公共化、非个人化,“代言”的意味越来越浓。最近两三年,郑小琼“普罗米修斯”式的书写姿态又进一步发展为知识分子式的姿态与立场。这当然显示着诗人视野的扩大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但也伴随着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好抽象玄思、好用大词、好雕琢诗句,从而失去了原本明晰与自然的诗写优点。
有人曾将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与王家新、西川等人的“知识分子写作”作比较,认为:“知识分子”诗人们关注的是形而上的层面,而郑小琼关注的是底层的现实,而“在此时代境遇中,也许关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更比关注一个宏大的概念显得更可贵”;而且,“知识分子写作是追求以文本为主体的写作,他们在诗歌形式上变换着各种技巧,‘诗就是诗’,诗是对‘语言可能性的无穷探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诗歌牺牲了许多读者。”④这种比较肯定了郑小琼前期诗歌的具体性与现实性,批评了知识分子型诗人偏爱宏大概念偏重形而上之思的毛病,颇有道理。但郑小琼这两三年的诗作偏偏就走上了自我否定、邯郸学步的险径,颇有滑入“知识分子”写作陷阱的迹象,她的爱用大词,爱抽象议论和抒情就是明证。且以《喑哑》一诗为例:
我以为流逝的时间会让真相逐渐呈现
历史越积越厚的淤泥让我沮丧 喑哑的
嗓音间有沉默的结晶:灼热的词与句
溶化了政治的积冰 夜行的火车
又怎能追上月亮 从秋风中抽出
绸质的诗句 柔软的艺术饱含着厄运
他们的名字依然是被禁止的冰川
被挤压的词语带着盐的使命
良民被挤得热血汹涌 躯体的愤怒
升起 而我常感到莫名的悲伤
那些不可摧毁的声音中 他们痛切地
触摸到自身 积蓄的 分散的……
它在淤泥的深处成为照亮的真相的烛光
因为没有描绘出具体的时空情境,这首诗里的“真相”、“历史”、“政治”、“厄运”、“良民”、“淤泥”、“使命”等词究竟何所指,实在难以破译!如果说作者因有某些顾忌和不便,只能用这种朦胧的暗示、象征手法,那也应在诗中留下些蛛丝马迹。但我们从《喑哑》这首诗中找不到这样的暗示或可资联想的东西。像这类不知所指让人迷茫的概念或词语在郑小琼近年的诗歌中并非少数。比如“我们从泥泞的历史抠出腐败的真相……在镜中/遇见宫殿与黑色的苍穹 变形的面孔/黑暗 脆弱的月亮成为唯一的信仰/它温柔伸出水袖 划出了黑暗帝国的伤口”(《黑暗》),这里的“黑暗”、“历史”、“宫殿”、“黑暗帝国”之类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除了作者自己,很少有人能够猜透。此外,《囚》一诗中的“艺术弯腰穿过外语的狭门 物理对/政治保持敬意”,《橙色年代》中的“教条式的革命”,《舌头》中的“我们用身体/涂改着政治的错误”,《疾病》中的“政治武装者喊着虚幻的祖国”,《深渊》中的“孤立的/自由沿着马的嘴唇饮水”,《怀疑》中的“真理压弯了草茎”,《火焰》中“柔软的火焰压低了钢铁的枝条”,《结晶》中“真理像豆荚一样爆裂”,《鸟》中的“黑暗的灌木林中真理似的雨滴”,等等,都是没有提供具体语境或给出暗示的让人费解的句子。近两三年来,郑小琼变得越来越喜欢用大词了,“祖国”、“人民”、“历史”、“真相”等等,充斥于她的新诗集《纯种植物》之中,其中“黑暗”一词用了70多次,“历史”一词用了37次,“暴力”用了27次,“思想”26次,“真相”23 次,“自由”23 次,“信仰”22 次,“真理”19 次。这些词用到诗中多显得大而无当,不明所以。
张清华在为诗集《纯种植物》所写的序里赞扬了郑小琼的“大词癖”,宣称:“在这颠覆和戏谑一切的时代,我惊异于这个‘80后’的青年,居然在她的诗中一直固执地与‘历史’、‘英雄’、‘思想’、‘人民’、‘悲剧’……这些大词站在一起,而作为使用者,她和它们之间,居然是这样地对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让我相信,词语本身的意义和力量是不会匮乏的,容易匮乏的是主体自身,当主体显示出真正的担当意志与能力的时候,死去的词语便会重新活转过来,并且被擦拭得闪闪发亮。从这个意义上,她就不只是值得肯定,而且还值得赞美了——因为我们时代的诗人们已经放弃、甚至作践这些词语很久了。”⑤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在我看来,郑小琼的诗并没有因为使用这些大词而变得更好,她也无力让这些大词重新焕发光彩。诗毕竟是诗而不是政治,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大词的使用是否有助于提升诗歌的思想内涵或艺术质量,是否产生了真正的打动人的好诗。显然,这些大词的使用除了使诗具有了“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壳,却未能提升诗的内在质地,反而使诗写得抽象、晦涩甚至是生硬、干瘪。
在十余年前诗坛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中,“民间”派曾大力抨击“知识分子”的技术主义趣味。而在我看来,郑小琼的诗歌写作在语言和诗艺上也有一种从“民间”向“知识分子”转变的迹象。郑小琼先前诗歌中那种口语化风格,那种质朴甚至是粗野的措辞(长诗《人行天桥》中就比较明显)如今是很少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更文雅、更精致、更书面化的语词和更刻意的诗句雕琢。我们试以两首同题诗《小镇》来做个对照:
市镇的河流悠长苦闷,树枝挂满碎布
白塑料袋,屠牛铺的案板迸发江南暮春气息
喝浑浊的水,唱清脆的歌,百感交集的心灵
失去光辉的远山,多少卑怯在暮色中抒散
临街的破旧的杂货店,笨拙的红漆招牌
雨水滴着石板街,低矮而清苦的旅馆
在星辰的幽光里辨析这浸透岁月清苦的晦暗
万物压抑而憔悴,活着的人积满了不幸
摇晃着,那张张堆满铁锈的脸
黑暗中淤积往事的旧灰
它的轻
有如时间在瘦弱的针尖上颤动
(选自《郑小琼诗选》)
喉间卡着陡峭而寒冷的冬天 小镇石街上
传来小贩们的嗓音 像白色的药片溶解水中
从阴暗的旅馆辨认石头 它们克制而镇定地
漂浮 暮晚在窗外一闪便折进黑暗间
轻如从台阶上走过的野猫 爱 吞咽着
孤独而悠长的小巷 码头翻阅异乡的船篷
桥在青苔砖上做着飞翔的梦 槐树将翅膀
伸进大地中 河水淹没陈旧的煤灰场
黑夜分娩出灯火 在平原上闪烁
在小镇的命里 我辨认着自己微寒的面孔
(选自《纯种植物》)
前一首《小镇》写于2008年之前,后一首《小镇》则写于近期,前者基本是写实的风格,语词使用简单、朴素;而后一首则特别注重修辞和词语使用的陌生化,“喉间卡着……冬天”,“嗓音像白色的药片溶解水中”,“石头……克制而镇定地漂浮”,“桥……做着飞翔的梦”,“黑夜分娩出灯火”……都是极怪异或极重修辞技巧的语句。近期的郑小琼尤其偏爱使用特殊、怪异的意象和修辞,诸如:“马匹去了/象征的森林 成为隐喻”(《裂纹》);“她用思想的石头/取暖 石头是她白色的信仰/也是她黑色的钢铁她却不幸/成为风暴中悲悯的水银”(《石头》);“肺部滚烫的星辰”(《立场》);“时间与水银的深涧”、“在沉睡的水银中寻找朴素的认识”(《烙铁》);“孤独像块黑陨石在胸腔里飞行”(《陨石》);“黑夜像一匹黑马低下头颅/在它黝黑的响鼻中/黎明正在洗澡”(《黑》)。这些诗句中,“马匹”、“石头”、“水银”、“陨石”、“星辰”等意象都十分奇崛,“马匹成为隐喻”、“肺部滚烫的星辰”、“时间与水银的深涧”也是颇为怪异的修辞。这些超出人们日常经验的怪异意象和修辞运用,固然显示了郑小琼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和对诗艺的追求,却不能说是很成功。随着创作的日益自觉,郑小琼必然不满意于自己早前诗歌语言和技艺的粗糙,因此尝试着有所提升。但她的这种尝试明显走过了头,走到了片面讲究技巧的误区,与曾经广受抨击的那种“知识分子”或学院派诗人的“技术主义”趣味同流了。
综上可见,随着生活背景的变化和职业身份的转变,郑小琼的诗歌越来越脱离底层生活经验,越来越染上了知识分子的某些趣味。事实上,她的诗歌(包括打工题材的诗歌)的读者并非底层群体或打工群体而是知识阶层,只为文学界、知识界所关注或激赏。这大概很自然地就诱导她的写作越来越有意识地靠近知识阶层的趣味。就像余旸所指出的,“她就放弃了自己诗歌从中诞生的真实感受的底层经验,而俯就那些虽然边缘化但是精妙的少数人,诗歌中提供的判断自动脱离了来自底层的经验之地,而迅速地接受了来自思想文化上的抽象判断”⑥。但我还是更欣赏她早期诗歌的那种粗粝与发自底层的偏激(比如《人行天桥》中粗野的诅咒),此乃郑小琼诗歌中最具震撼力,最能打动人心并逼人深思的地方。来自底层的鲜活经验、朴素的情感和自然情绪,汪洋恣肆的宣泄或嚎叫,不厌其烦的铺叙或描绘……这些正是她的诗的美学价值所在。对于郑小琼写作身份的转换,诗评家张清华持肯定的态度,称之为“身份的升华”。他说:“‘见证性’曾是郑小琼诗歌的力量来源,而今当她在脱离了‘女工身份’之后,我们无疑可以欣悦于她身份的持续获得——这是一个精神求索者的身份,一个化身为与‘灯’和‘火焰’同在的追逐光明的扑火者,一个思考更多真理与命运的主体。因此她也变成了一个有丰富人格内涵和可靠力量的‘抒情主人公’。”⑦对于这种看法我却不愿苟同。在我看来,以抽象表达代替具体呈现和描绘,以空洞的大词代替具体事物和情境,以怪异的语象和技术化的修辞代替朴素流畅的口语,这绝非进步。诗人当然不能始终重复自己,总得求新求变,然而盲目地知识分子化,甚至不自觉之中习染上“知识分子写作”的陋习,这恰恰可能是歧途。当然,郑小琼的诗歌转型还在试验的阶段,我们应该鼓励她勇于尝试,此路不通走彼路。她应该如何转型,我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建议,这也没有必要。我唯愿她少走弯路,早日脱去浮华进入返璞归真的成熟境界。
【注释】
①③⑥余旸:《“疼痛”的象征与越界——论郑小琼诗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②郑小琼、何言宏:《访谈: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诗选刊》2008年第1期。
④赵春丰:《犀利而精粹的底层诗歌写作——论郑小琼的诗》,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2011年提交,未刊,引自中国期刊网。
⑤⑦张清华:《代序:语词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纯种植物〉》,见郑小琼《纯种植物》,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