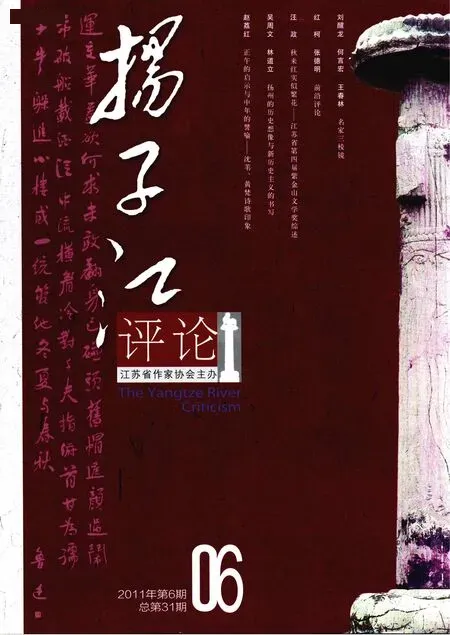秋来红实似繁花——江苏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综述
2011-11-19汪政
汪 政
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今年三月份启动,经过申报、评审,结果已经于11月初公布,并将于近日颁奖。
本届紫金山文学奖覆盖面广,获奖作者层次多样,既有国内外知名作家,又有刚走上文坛的新人,既有专业作家,又有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本届评奖增加了影视文学剧本奖和网络文学奖。影视艺术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强的艺术样式,但成功的影视作品是建立在优秀的文学剧本基础上的,为了鼓励影视剧本创作,发挥文学在影视艺术创作中的作用,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增设影视文学剧本奖,体现了这个奖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在网络文学奖的设置上。网络文学是新兴的文学类型,相比传统纸质文学,它在主题、题材、表现方法与传播手段上有许多新的特点。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家文学奖也试图将网络文学纳入评奖范围,但都没有评出,其原因与未能明确标准,未能协调好传统文学与新兴文学的关系有关。但紫金山文学奖第一次设立网络文学奖时就评出了该奖,这不但表明了江苏网络文学的水平,也表明紫金山文学奖在如何对待新兴文学上的气度与胸襟,表现了一个文学奖在审美理念上的创新。在奖项设置上,文学编辑奖与文学翻译奖的意义也需要提及。前者是对文学“后台”工作者的尊敬,说到这次获奖的梁晴、冯光辉和胡翰霖,多少具有影响的作品从他们手上出去,许多作家的成长都与他们相关,对他们心存感激。而后者事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这次获奖的两部作品都是广获好评的译作,引进好的译作不仅给读者带来享受,更为作家提供借鉴。也许,从交流的意义上讲,未来的翻译奖不仅关注“进口”,还将对“出口”进行鼓励。
作为连续性的区域性的综合文学奖,本届紫金山文学奖全面反映了三年来江苏文学的发展与现状,成为考察近年来江苏文学的一个有效平台。具体地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进一步彰显了江苏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络化的叙事模式,这里有都市文化人的叙事线索,有留守式农村的叙述,有城市农民工的描写,还有旧式人物的传奇穿插其间。这正是中国当下社会生存样态的具体而微,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相对稳定与变动游离等等,凭此,赵本夫的思考具有了全景式的生态背景,而思考的主要方向则是以现代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的质疑与批判。鲁敏的长篇小说《此情无法投递》借助于一桩强奸案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作了编年史式的叙述。在这个长时段的叙述中,不仅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世界的变化得到了观照,而且社会风俗的变迁也得到呈现。实际上,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分析的对象已由单个的个体扩大到了社会主体,其笔法与思想轨迹已相当接近于心理分析的社会描述,在社会世相的描述与思想的勘探上都有所突破。而夏坚勇的报告文学《江堤下的那座小屋》将一位栖身江堤小屋的乡土草民推到了前台,为了救援无亲无故、落水遇难的外省船夫,竟然无怨无悔、不计后果地倾囊奉献,甚至将其面临高考的一双儿女接到身边,视若己出。作品彰显出平凡中的伟大,将赞美给予这个社会日渐稀缺因而越发可贵的纯厚而圣洁的慈悲情怀。肖静的报告文学《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一个村庄的命运》虽然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题材,但作品从人与村的关系入手,将人物的性格与村庄的变迁融为一体,并且从深层次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确实如此,江苏的作家们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中越来越显示出思想的深度。王尧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以个人记忆的形式重新梳理八十年代经验。个人思想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变迁熔于一炉。朱辉的短篇小说《止痒》借助一个网恋的故事,探讨了当代文化人的现实境遇与困顿。罗望子的中篇小说《我们这些苏北人》对中国乡土社会有真切而独特的体认,家族、土地、乡村文化生态等层面在作品中都被仔细地打探与考量。而肖元生的《松坡寺》的思考显然得益于作者在题材上的选择,他借助于寺庙这一特定的空间,不仅试图反映中国数十年的风云变幻,而且通过俗世与宗教的文化间的张力对人性与欲望进行叩问。邓海南的获奖电视剧本《上海上海》容量深阔,它通过主人公刘恭正和众多人物的刻画,展现了形形式式的人物不同的命运,他们的创业、搏斗、生存与挣扎同时是上海这个纷繁复杂的东方都市的生动写照。其他如胡继风的《想去天堂的孩子》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记述,王巨成《震动》对地震中儿童生活的叙述,王旭《光明》对有“缺陷”的描写,以及凌鼎年微型小说集《天下第一桩》对社会现实的广泛关注等在反映时代、思考现实上也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二是文学队伍生机勃勃,文学新人势头强健。江苏文学历来以代有才人著称,老作家们笔耕不辍,而中青年一直是江苏创作的中坚,这样的文学格局因为一些更为年轻的面孔的加入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这几年来,江苏又出现了不少在省内外产生影响的文学新人,余一鸣是近年来江苏小说创作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入流》、《放下》、《剪不断,理还乱》、《把你扁成一张画》、《江入大荒流》都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次他参评的作品是中篇小说《不二》。有评论家这样认为,余一鸣洞穿世事的目光没有丝毫的迟疑,坚定、决绝。他有着“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诚恳,面对人性深处的溃败、社会精神和道德底线的洞穿,余一鸣‘不二’的批判或棒喝,如惊雷裂天响遏行云”。格格是上届的新人奖得主,这次她以长篇小说《骚江》摘得长篇小说奖,评委们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它构思宏阔,叙述从容,显示出作者驾驭长篇的能力,这部小说是作者《大江边》中的一部,评委们对作家如此年轻,却在观察社会,体验人生上表现得如此成熟老道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样是上届新人奖得主,黄孝阳的《人间世》虽然没有得奖,但同样得到评委的认可。他继续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传统,将对社会的观察与批判和形而上的哲学沉思结合起来,思考精深,想象丰富,表现出作者不俗的才情。苏宁也是近年创作成绩显著的青年作家,这次她以《平民之城》获得散文奖,作品以自己居住的苏北小城为书写对象,在对身边街闻巷议、家长里短的细细诉说中,描绘出一方水土独特的生存状态和蕴含在其中的独特的美,温婉从容,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生活和不生活于此中的人们。丁捷近年的创作呈井喷之势,这次他以《亢奋》成为紫金山文学奖网络文学奖获奖第一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方式具有鲜明的网络文学的特征,小说通过某城市电视台长的改革成败和命运沉浮,反映了时代快速发展中的种种精神症候,表现了新世纪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复杂而生动的图景。作品在网络上曾经拥有极高的点击量。这次获得新人奖的是叶炜、葛芳和梁弓,叶炜在高校工作,已经表现出学院作家的一些特征,他既从事创作,又兼攻理论批评,他的小说创作善于在中国现代性的多元矿藏中发掘独特的叙述价值,而他的理论批评体现出宽广的视野和思考的勇气。葛芳在小说与散文写作上都有令人称道的表现,她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对日常生活有准确而精微的把握,她使日常生活成为小说中的氛围与力量,在人与日子、人与生活的对抗中形成叙述的张力,逼出生存的意义。梁弓对小说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他的文学积累使他对小说的功能、小说与阅读者的关系有许多独到的思考,从而让他在调动小说艺术资源,在多种风格的融合上游刃有余。这次新人奖除了这三位获奖者之外,徐玲与张羊羊也相当优秀,虽然因名额的问题他们未能获奖,但他们的创作成绩与发展潜力同样值得重视,徐玲是江苏儿童文学创作的后起之秀,她的作品在小读者中已经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而张羊羊的散文与诗歌创作也得到文学界的好评,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对语言的追求使他成为江苏文学新的唯美的求道派。
三是注重创新,文学风格更为多样。江苏文学一向注重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本届紫金山文学奖不但依然体现出这一传统,而且提供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的审美经验。黄蓓佳在小说创作与儿童文学上都有相当的成就。在本次紫金山文学奖上她展示的是她的儿童文学新作,5个8岁的孩子的系列之一《草镯子》,从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管窥这个系列对儿童文学的贡献。它们是“儿童史诗”或“儿童诗史”,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具有开创性和探索的意义。作品中人物的故事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表面的故事固然可圈可点,更重要的是黄蓓佳在通过各时期的典型叙事对不同时代氛围的营造与不同时代精神的把握,这样的努力不但体现于故事、人物,同时体现在风俗、生活方式、话语重心,以及叙述语言与描写风格上。这种努力的意义显然超越了文学,它在历史叙事、儿童教育等多方面都具有探讨的价值。苏童以《河岸》再次证明了自己小说诗学的有效性与在这一文体上的创造力。作品除了人文意义建构上的野心之外,在艺术形式上也相当讲究,它通过一个少年讲述了几代人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际遇,童年的视角,成长的主题,残酷的青春,历史的浮沉,河与岸的象征,意象包裹的语言,是苏童小说元素的一次完美组合。叶兆言的《玫瑰的岁月》同样体现了作者的小说智慧,他对传统与现代、俗与雅、人物与故事、传达与接受这些小说文化的关系项都有独到的理解,同时,作者又具备相当的知识储备,因而在写作上总能驾轻就熟,从容自如。作品以老道的语言和手法叙写了一个书法家坎坷的人生命运,小说出入于书道人道,流光溢彩,元气充沛。荆歌的《鼠药》叙述上也极为讲究,借助于现代小说策略,他对传统的文学文体作了新的整合和配置,书信、笔记、评点的组合拓展了使叙述更具动作性,它使人们对古老的叙事资源生出新的希望与信心。裴指海是位部队作家,这次获奖的中篇小说《亡灵的歌唱》构思奇特,叙事人穿行于阴阳两界,以一个亡灵的视角讲述乡村与城市、道德与人性的复杂纠结。宋世明、李明耀的报告文学《法医迷案》当得上中国人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作品虽然是非虚构的,但却将纪实性、知识性、悬疑性熔于一炉,在让读者领略法医主人公高超专业技能、感动其神圣使命感的同时,获得阅读的愉悦,在报告文学创作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章红的《估衣廊》别出心裁,将现实生活中的一条街巷演绎幻化成美丽的童话世界,想象丰富,构思新奇。而庞余亮的《薄冰》则在极短的篇幅里尽可能容纳进丰富复杂的内容,其对时间与空间的文字处理显示出短篇无限的表现力,作者无疑是一位短篇小说的成本管理高手。在这次评奖中,苏州的几位女作家的表现可圈可点。这几位在文坛上已负盛名的小说家将短篇艺术演绎得五光十色,摇曳多姿。戴来《之间》的轻逸而不乏激情、叶弥《桃花渡》的温婉智性、朱文颖《花窗里的余娜》的细致入微都给人如走在山阴道上风光应接不暇的喜悦。本届诗歌奖同样给人以春兰秋菊各秀其时之感。孔灏的《漫游与吟唱》诚挚、飘逸,游走于诗意和禅意之间,具有突出的抒情特色且富于歌唱性;胡弦的《阵雨》擅长在瞬间捕捉记忆和现实的交叠与碰撞,在细微处体味生命与存在的微妙处境;小海的《大秦帝国》以诗剧与人物志的组合,剪取历史大树的斑斓叶片,再现了一个帝国的兴衰;车前子的《像界河之水》延续了诗人怪诞、灵动的风格,对现实人生的细敏参悟,对心灵直觉的情感体验均堪称独步;陈义海的《被翻译了的意象》贯穿着浪漫主义的诗性与崇高性,同时吸收了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诗歌流派的表现方法,注重意象营构、语言淘洗和艺术思考的深入。
四是关注文化传承,地方性写作得到提升。这次紫金山文学奖参评作品呈现出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对传统文化与地方性元素的反映与思考。储福金在长篇小说《黑白》以后,继续往返在围棋与小说之间,他的系列短篇《棋语》构思独特,把围棋这一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技艺化为文学的载体,将社会、时代、文化与人拢于棋枰之上,收入文字之中,以棋写人,由棋及人,以人化棋,借此观照中国文化的秘密和幽深的人性世界。这次参评的《棋语·立》叙述的只不过是一次对弈的先胜后负,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杨守松的报告文学《昆曲之路》是其创作的重要而成功的转型。作者以访谈的呈现方式,叙写了作为中华文化之瑰宝的昆曲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全景式地展示了昆曲的历史与现状,从文化自觉的高度表现出面对这一艺术未来命运的期望与忧患。沈国凡的报告文学《“红灯记”的台前幕后》对轰动一时并影响整个中国的京剧《红灯记》的来龙去脉作了翔实的调查和报告,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对这一独特的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新梳理与阐释。诸荣会近年专注于江南文化的打捞和书写,这次参评的是文化散文集《风景旧曾谙》,作者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徜徉于江南山水风物之中,或凝望斑驳的亭台楼阁,或晤谈飘逝的陈旧人物,感悟历史,抒发性灵,于沧桑中透出敏锐与智慧。在这次的参评与获奖作品中,许多以地方文化与风情为抒写对象的作品其意义值得重点申说。徐风的紫砂文化散文《一壶乾坤》是一部紫砂艺术家的系列传记,又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国紫砂艺术史。徐风借鉴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以人写史,以人代史,以人观史,通过对几十位紫砂艺术家的传书,展示了紫砂艺术的历史传承。作品对古往今来的紫砂经典之作进行了富于个性的鉴赏解读。这种鉴赏除了为其艺术史地位、传承与影响作出准确的分析外,格外注重将人与作品、将时代精神和文化风尚与作品结合起来分析,注重分析作品所蕴含的艺术家的个性气质与精神气韵,以及这些个性气质与精神气韵所彰显出的社会时风,体现了作者对江苏宜兴独有的紫砂艺术史强烈的书写意识。我们在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中看到的是一种与现在的水产养殖业与捕鱼业甚为迥异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看到了许多失传的捕捞技艺、捕捞工具和餐桌上不再见到的水产品,而这些被改变的传统之“渔”都曾经与兴化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成为地方文化的记忆,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但依然有在纸上留传下去的必要,它们已经独立地成为一幅幅诗意盎然的风俗画,哪怕只是话语或记忆中的景象。徐风笔下的紫砂与刘春龙笔下的捕钓是地方性写作的典范代表。在中国,地方志、家谱、日记、笔记等写作都曾成为传统,蔚为大观。在文化多样性日益宝贵的今天,趋于式微的地方性写作更显重要。因为,首先,地方依然存在,经验的差异依然存在;其次,地方性写作作为一种民间或准民间写作是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它也构成一个重要的写作类型与写作风格,并且可以为二次写作提供基础;再次,就中国目前的地域文化与民间经验而言,地方写作显示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地方性写作不是采风,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而是由当地文人书写的当地经验。所以,它在地方文化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江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江苏文学批评的有力支撑,事实上,江苏文学批评一直是江苏文学总体格局中的另一半江山。本届紫金山文学奖文学评论获奖作品的作者吴功正、黄发有、张光芒、张宗刚、林舟都是江苏近年十分活跃的批评家,他们的作品典型地代表了江苏理论批评工作者的批评风格。江苏的批评家们敢于直面复杂的文学现实,提出富于挑战性的理论问题,思想的勇气与敏锐的审美触觉形成富于征服力的批评力量。同时,江苏的批评家对江苏文学情有独钟,无论是对成名作家深入的跟踪性的研究,还是对文学新人的热情推荐和恳切批评,都显示出他们负责任的精神和对江苏文学的关爱,正是这些优秀批评家们勤奋而卓越的工作,不但使江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镇,也使江苏文学创作的宣传、推介与经典化获益良多。
文学奖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是文学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彰显文学价值、明确文学标准、推介优秀作品、引导文学消费和参与文学经典化的功能。江苏的紫金山文学奖历经四届,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确立了自身的权威性,得到了江苏及全国文学界的认可。这个奖的成功举办是江苏作家和省内外专家学者支持的结果,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委,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不仅给紫金山文学奖带来了公正与声誉,更给江苏文学带来了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