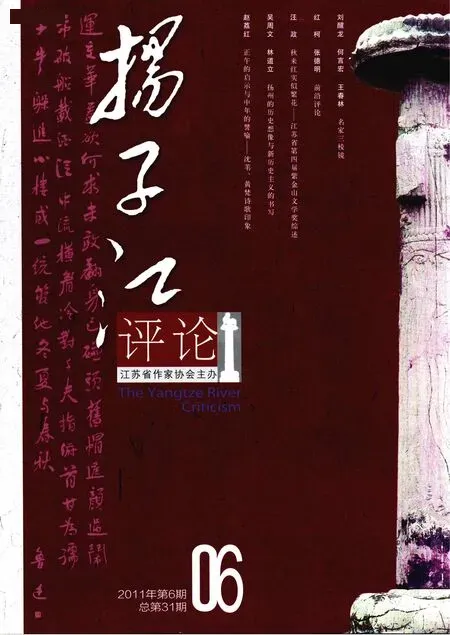正午的启示与中年的譬喻——沈苇、黄梵诗歌印象
2011-11-19赵荔红
赵荔红
引子:回想今年在太仓聚会,时值柔刚诗歌奖颁奖,五月微熏暖风,陌生而熟悉的江南小镇,祥和平宁的气息,高兴、叶辉、黄梵、沈苇、丽莉和我,喝了点黄酒,微熏,在子夜的太仓街头缓慢散步,居然有星空,听沈苇、黄梵、叶辉在谈汉诗词汇的优雅。我所认识的沈苇和黄梵,都已步入中年,在气质上有着中年人的“心平气和”……
沈苇:正午的启示
诗人沈苇说,一首诗的诞生是一个重要而神圣的时刻。当我叙述一个诗人的诗歌时,也绝对是一个“严重时刻”。心中充满双重怀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用语词去“重述”一个诗人的语言、道德、心灵深处的隐秘,“重述”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诗人和他的诗在我的笔下“失真”了吗,或者解读如同万千树叶在光线下明明灭灭变幻,如同云影瞬间转移充满深不可测的隐喻,我的解读不过是其中的一小片叶子,尽管闪闪发亮;再一层怀疑,我触抚到了“那个”诗人了吗?里尔克对茨维塔耶娃谈他的两个“自我”,作品的自我,与作为肉体凡胎的自我,哪个是更鲜活而具有持续生命力的?难道二者是可分的?是的,我们有时会厌倦那个随时间流逝而面容黯淡形体松弛的皮囊,转而将深切的偏爱的目光投向诗歌中永恒停伫的伟大心灵,以及那些超越时空充满意义的瞬间词句,于是我们赞美、喟叹精致的语词,伟大的美德,神性的光辉,将典籍中闪耀群星的光芒投注在眼前这个诗人,从他身上发现一种应和,一种坚持,一种传继。同时,我的内心又有着隐秘的快感:在诗人语词制造的崇山峻岭、黄沙漫漫、沟壑溪洼间,我跌跌撞撞,悄悄地搭桥铺路,小心翼翼运送薄冰,呵,我快要抵达那个盛大花园了,诗人的隐秘之所,在棉花织就的云朵里,在发出金属铿锵之声的叶片中,在一千朵玫瑰间,诗人正微笑地等待我;而诗人呢?正如纳博科夫说的:“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缘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文学讲稿》)
正午:太阳与玫瑰
正午,当然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个词同时具有空间性。因为只有在新疆,天空湛蓝,大地辽阔,群山起伏,空气透明澄澈,正午的阳光才是那样垂直热烈,“阳光流泻,缺乏节制。一切都是垂直的。/光线像林木,植入山谷、旷野、村庄、畜群/在周而复始的生育、繁衍之后/它们将继续受孕。一切都是垂直的/正午取消了谜团似的纠缠的曲线/事物与事物的婚姻只以直线相连/因此万物看上去单纯、简洁而深邃”(《正午的忧伤》)。
在沈苇的诗歌中,正午作为一个诗性意象存在,还代表着他所追求的美学趣味及生存状态。他的诗歌血液充满热度,洋溢着一个豪放诗人的激情,是属于男性的刚毅、正直,尤其早期诗歌,充满太阳、火的味道,速度感、节奏感很强,诗句是充满热度地“滚”出来的,诗歌色泽闪亮、透明、澄澈,声音是高亢的嘹亮的,是大声正声。最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与生存态度,必须端正,他曾和我说,只有端正,才能更大、更远。他需要的是丰盈高过贫乏的生活,是扎根于大地、精神高翔如大鸟之翅,是一种生死之外的辽阔,是从低处抵达到高处,他知道什么是端正之美,什么是至善的追寻,“假如你真的站在秘密的中心说话/说出:真诚、勇敢、善良/你不是在揭示,而是在奋力保护/双手按住那颗快要飞走的心脏”(《看不见的手》)。
与正午意象相关的,是沈苇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太阳与玫瑰,都具有火的热烈、鲜艳,都是红色,都代表激情。正色,正音。在新疆,群山连绵,大团大团的阳光四下铺展,“人很小,太阳很大”(《旅途》),“飞鸟的正午,太阳滚进十个村庄”(《新柔巴依》),这种风景进入沈苇的诗句,演化为对太阳的灵魂追求。行走在阳光暴烈的旷野、村庄、泥屋、沙漠,诗人发出这样的喟叹,“我往太阳里派遣激情,派遣野蛮的公牛”,“当我在向日葵中午睡,忧伤如冰块融化/我承认低低飞过的太阳是我惟一的祖先”(《状态》),“让荒原覆盖我全身。说:一切,我要!/太阳俯下身,像王者垂青于我的作为。”太阳意象,在沈苇诗歌中意喻真善美,代表一种方向,无论从什么道路,向上的或向下的,都要去追寻和抵达的方向;是信仰,是生命的意义,是高处的天籁,是诗人说的高翔的翅;是光,是热,是激情维系之所在。沈苇要毕生进行新夸父逐日运动,也许永不能抵达,而他已经上路;也许焦渴而死,死后也要将手杖化为桃林。
如果说太阳代表一种信仰与方向,玫瑰则象征爱。它们拥有同样的激情、热度,同样需用正午精神去看护与坚持。当那些“少女们开遍了大地”如同玫瑰开遍原野,诗人以火焰般的热情歌颂她们。爱与信仰,太阳与玫瑰,都是那么纯正,那么真切,那么简明、热烈,都是纯而又纯的色调。所以在诗集《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开篇一首,诗人就端出了这两个意象:“中亚的太阳。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那人依傍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一个地区》)纯粹的色调,透明、澄澈、热烈的画面,后来一直呈现于他的诗歌中。早期《向西》一首,明朗色彩与血液热度铺满纸面。沈苇的诗句,青年时期更为热烈、激情,即便中年后的沉思、质疑,也绝对没有丝毫暧昧、阴暗,连同痛苦都明明白白端正呈现。
正午的诗性精神,在沈苇中年之后,开始有了深思与忧伤意味,一览无余的阳光天空,开始有了云影,光线微微倾斜,年轻人那种一往无前轰响着推进的速度缓慢下来……也许是时间之伤,也许是地域的巨大裂豁,也许是现实困境,诗人对生命意义的质疑,表现在《正午的忧伤》中:“但稍等片刻,随着太阳西移/一切都将倾斜:光线,山坡,植物,人的身影/从明朗事物中释放出的阴影,奔跑着/像一场不可治愈的疾病,传染了整个大地”。又如《闪闪发亮的正午》:“别再追问什么事物在闪闪发亮/被正午放大的寂寞与惆怅/在此地、他处,那无法看见的/越是飞速流逝的,越在闪闪发亮”。有阴影,有倾斜,有质疑,美与好的飞速流逝,被正午精神放大的惆怅与寂寞,内心的孤寂,追寻的困境,现实的伤害,诗人一辈子都在追问,追问自己,追问历史,追问当下处境,正午并一直轰响地存在,唯其如此,一个诗人的处境才具有真实性,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
辽阔与细微
诗人当然关注细节。里尔克说“: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沈苇多年来游吟于“辽阔”与“细微”之间(梁雪波语)。或者说,他诗境的辽阔乃是落实在细节的微小上。西域地界阔大,地貌复杂,民族杂居,文化多元,多年来行走在森林、雪地、燃烧的峰巅,徘徊于石头、壁画、古瓷、经籍之间,所见的是鲜花与刀,冰与火,旷野与蓝天,大朵大朵瞬间转移的白云,成团成团无遮无挡的阳光,诗人不可能不辽阔。在畅写叶尔羌、喀纳斯、龟兹、楼兰、天山、克孜尔、喀什、伊犁、那拉提山谷、博格达峰的这些诗篇中,必定具有空间的辽阔感。可以说,沈苇诗歌中的辽阔境像首先是空间造就。
辽阔还在时间之中。时间的推移让诗人发出生之辽阔、死之辽阔、悲哀之辽阔的喟叹。“一千年的麦粒等待发芽,三千岁的胡杨/流下硕大的泪滴。风沙四起又归于平静,/一次又一次,锋刃与经籍碰撞出火花。”(《新柔巴依》)诗人在所有的诗歌中,都在叙写时间转移、运命变化的辽远,由此带来对生命、自我以及现实之意义的追问。如《昭苏之夜》,从辽阔的空间,一下子转移到时间的辽阔上,在昭苏草原,被月亮和睡眠呈现的,是现场场景与过去与未来的连接。从当下的昭苏草原,一下子进入到梦、月亮中,进入到更辽远的年代、花容,那些闪烁的故事传奇,马背上的纷争,文明的撒播……开阔的意境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
辽阔更是心灵的需求。在许多诗篇里,诗人都在不断追问、诉求、怀疑,对自我的审视,寻找答案。诸如《看不见的手》、《自白》、《回忆》、《状态》、《你我之间》、《混血的城》、《谦卑者留言》等等。归根到底,从典籍、雪山、草原、旷野,以及现实处境出发,诗人“透过可能的缝隙,他爱着一种辽阔/一种生死之外的辽阔”(《肖像》),这种辽阔,乃是他从专注于个人痛苦走出,飞翔到更高更蓝:“如果我只专注于个人的痛苦/那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眺望》);“你左边的心只为一个人珍藏,/右边的心要献给更广大的世界……”(《墙是不存在的》)
混血者的理想
2011年,沈苇46岁,刚刚好在浙江湖州生活了23年,在新疆生活了23年。我曾笑说他的气质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以诗人用词的精确回答说“一半是水,一半是沙”。他说他到新疆,是从“湖人”(湖州)到“胡人”(西域)的过程,他要“以潮湿的方式进入干旱和坚硬”(《墙是不存在的》),要在异乡建设故乡(《新柔巴依》)。就其诗篇看,新疆(西域)生活给他的印迹是现场的、进行的,而江南故乡则存在于记忆中,在不断返回的梦境中。但沈苇以为,从地域出发的困境,毋宁说是从心灵出发。江南也好,西域也好,都是他心灵成长的盛大背景。文学固然是要扎根于大地,更要挣脱地域性牢笼,飞翔在天,“我的双脚长出了一点根,而目光/时常高过鹰的翅膀”(《混血的城》),他将之归结为一句话:“文学是根,也是翅。”
沈苇个人的经历是“混血”的,他居住的乌鲁木齐更是一座“混血的城”,他所处的阔大新疆是一个“混血的疆域”。地貌多样化,物产丰饶,多民族杂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文化的差异性融会——西域,曾是真主的沙盘,是启示录的背景,多处又曾是著名佛国;这里埋葬着在巴格达学习的维吾尔圣人马赫穆德·喀什葛里、智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身戴铁镣的苏非兄弟曾赤脚在这里漫游,而基督徒斯文·赫定、马林等也在此流连,访求佛经的玄奘也曾步履匆匆、风尘满面行过,《古兰经》、《圣经》、诸多佛经,以及《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这样的典籍均汇聚在这里。文化是如此丰美、盛大。风俗也是多样,沈苇说,在这里能感受到浓郁的印度味、阿拉伯味、波斯味乃至希腊味。新疆,长期来保持着一种“向西开放”的胸襟和姿态,同时,这里又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的“接吻”点。以这样的“混血”文化为背景,更兼多民族的杂处繁衍,诗人沈苇,便心生出一个混血者的理想:“墙是不存在的”,他想要一个综合的上帝,要绵羊能自由穿越国境漫游,要一种真正意义的民族和谐与融合,要从血液中混合真善美,取消一切教义的藩篱、文化的屏障,以及血液与皮肤的色彩。所以,他天真地在《有时候我觉得》一诗中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阿拉伯人,是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有时我觉得自己分裂成许多个人:/黑人、白人、黄种人……”“我是我,也是他们。到处都是/人的生活,到处都是可以筑居的地方”;在《混血的城》中他这样写:“无论是汉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蒙古人/是时间中的兄弟姐妹”。
然而,这个混血者的理想,在现实的击打中瞬间坍塌、颠覆。那个重大伤害剥夺掉数千人的生命,更令诗人的梦境化为乌有,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永远是一个乌托邦。这个伤害与打击对诗人的摧毁是根本性的,他不得不写出长诗《安魂曲》。假如说《安魂曲》是为了告慰亡灵,是他,一个富有正义感,一个具有正午精神的诗人的追问与呐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的哀告、关怀与悲悯,按照他自己说,却仅仅是一幕人间惨剧的诗歌记录,一份亲历档案,他希望读者永远也不要读到这组诗、他也永远没写过这组诗,但它的确从他的手里、泪水里、血里流了出来。惊心动魄的诗句!!同时,这组诗也是一种宣泄,是使他自己在理想坍塌后免于崩溃的宣泄。我不知道,这个重大事件后的诗人,《安魂曲》后的诗人,将何去何从?
卑微者的天籁
23年前,那个年轻诗人,告别故乡,漫游在西域大地。人很小,太阳很大,黄沙漫漫,旷野荒凉,八千米高冰山,三万米长沙漠。在阔大的自然面前,人是多么卑微、虚弱;而绵远浩大的文明,复杂多样的生态,也同样让诗人意识到自己的弱小。诗人说,“我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个移动的点”(《自白》)。时间迅速转移,人命如落叶,诗人难免因时间之浩大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意识到自己的卑微,才能成其阔大。自然是他的导师,经籍是他的导师,牛羊民众都是他的导师。诗人一次次告诉自己,审视自己,纠正自己,坚持自己,在一个倒退的时代,永不妥协,朝向太阳奔走。重要的是克服自己,“去攀登另一个更高的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谦卑而微弱,应和着最高的天籁”(《看不见的手》。谦卑,最低微,最卑小,才能最高最强有力。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沈苇在《自白》中这样写:“除非一位小孩子,我愿意/用他的目光打量春天的花园。”所以他珍惜每一个瞬间,在贫乏中体会丰盈,在无意中认识意义,他如同沙漠中的西西弗斯,想用一生在沙漠里种树,树被烤死了就再种,究竟也能活下五分之一,虽然“离永恒,总差那么一步、那么一点点”。
渐近中年的沈苇,被时间与现实的双重利刃,一再划伤,他有了反弹的坚韧,也减缓了年轻时轰响的一往无前,诗歌中滚动的热烈的抒情性减少了,多了理性的沉思。明朗天空云影移动,是沉淀的智慧,或是激情的遮蔽?“缓慢些,有时还需要停顿和静止”,这是他的理念?抑或是“岁月疯长的荆棘逼他写下心平气和的诗”?他似乎不再迷恋漫游似的狂想与抒情,而偏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阅读,这也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仿《柔巴依》格律,他写了《新柔巴依》;仿哈萨克民歌,有了《谎歌》;仿突厥文,写出《占卜书》,甚至写出诗歌体县志《鄯善 鄯善》,还写了大量反映新疆人文地理的散文。而长期阅读《古兰经》、《圣经》、《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经籍,使他写出一些箴言式的诗句。
云杉的阴影,悬崖的阴影,移动的、半明半暗的未来。我不知道沈苇的诗歌会有多少变化,或许如他目前说的,朴素是好的,平实是好的,笨拙是好的,在他的停顿与静止后,会是一个飞跃?正午的诗神高高直立,面容皎洁,目光垂直,充满热度,一览无余;而傍晚阳光,因为云影转移、山体褶皱变化,更为宁静沉思有意味,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金色光线也具有更醇厚的质地。我知道,无论怎样状态,诗人始终以卑微者之卑微自足,又始终谦卑地认识自己,一直向前向上,从而阔大,渴望抵达最高天籁。
黄梵:中年的譬喻
阅读沈苇的诗歌,集中在他的两本诗集,《我的尘土我的坦途》、《新疆诗章》,时间跨度20年,在写他的诗歌印象时,侧重于时间的纵深。而阅读诗人黄梵,则集中于他近期的诗作。这些诗歌传达的气息,与我认识的黄梵的气质,在时间上是同步的。但他们都沉稳,声音不高亢,惯于沉默或沉思,都成了“好脾气的宝石,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中年》)
当然他们气质是不同的。沈苇更加明朗,即使在中年,依旧保持“正午”的热度。黄梵则忧郁,身上有一种倔强的孤寂感。我倒并不觉得,这种孤寂感是他的生活经历造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他那带有自身成长印迹的长篇小说《第十一诫》中,那个喜欢写诗的年轻主人公身上,也同样有强烈的孤寂感。只不过,年轻时的孤寂,会变异为激烈的不群的叛逆行为,而中年的孤寂,则有着好脾气宝石的孤单闪光的落没感。读黄梵的诗,常会浮现他的形象:右肩斜背一个包,帽子永远遮没头发前额,穿烟灰偏蓝T恤或赭色带格子衬衫,身子有点倾斜,不知是背包的重负或是习惯,仔细看,甚至有点躬着身,“我只是像炊烟,躬一躬身,听山涧轻声地啜泣”(《英雄谷》),这句诗描绘的形态,几乎就是他自己,走路选择溜边,经常性低头,在南京荫翳阔大叶子的梧桐树路上,他的身影隐没在铅灰的晚色中,与那个六朝古都面目如此协调。他总有一种想将自己尽量隐藏起来的感觉。声音是低的,可你不能说他有气无力,因为他仅仅简洁温和地把想法传达给你;你很难用“盛开”来形容他的笑容(或者男子的笑都是如此?),笑容一闪即灭,却并不演变成冷峻,并且你不可能认为他是对朋友不热情;他的好脾气似乎是对世事了解而通达地宽容,他温顺地合群,温和地存在,安静地呆在那里,但你永远觉得他会随时陷落在自己的世界,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中,永远是一个人。
我读到的黄梵近期这一组诗歌,正是他中年心态的写照。诗歌抒写性灵,诗歌中的那个自我,与现实那个自我,相互叠加,也许能让我更接近诗人。在这些诗歌中,黄梵将中年心态赋予如下譬喻:
蝙蝠。《蝙蝠》一首诗,让我对蝙蝠意象印象如此之深。在我以前写的文字中,总是尽量避开蝙蝠这种奇怪的黄昏动物(或鸟)的黑暗,而喜欢用“蝙蝠的衣服都是花的”来消解黑暗。我想我是对黑暗有畏惧感。但黄梵将蝙蝠的黑暗明白呈现出来,却消除了我心中存有的恐惧感,而赋予蝙蝠之黑暗更多的孤寂感。“蝙蝠在这里,那里/头顶上无数个黑影叠加/顷刻间,我的孤独有了边界”。这首诗有两层意思:这里那里,无数蝙蝠在黄昏飞翔,无论再多,蝙蝠和蝙蝠如何“合群”,依旧只是“黑暗”的叠加,“我开始感到它们振翅的温暖”,蝙蝠们振动翅膀,仅仅为了相互取暖,这种暖意,只能反衬出一个个蝙蝠个体的孤独感。“当蝙蝠慢慢拖动霞光”,不是霞光映照蝙蝠,而是成群的蝙蝠拖动霞光,是黑暗映衬出亮色的微弱浪漫,而不是光亮给与黑暗希望,在这里,直接描绘蝙蝠的生存状态,他们的黑暗气质,相互取暖带来个体的更加孤单感,是主导;第二层,将“我”与蝙蝠连接起来,“假如我浮上去/和它们一起沐浴/我会成为晚霞难以承受的惊人重压”,我的孤独有了边界,因为我在蝙蝠的黑暗中、孤独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孤寂感,我和蝙蝠是互为譬喻,互为存在,互相映照,无数黑影叠加的蝙蝠,是晚霞不能承受的,而“我”浮上去,如同一只蝙蝠,我的黑暗、孤寂感,晚霞的光亮与浪漫也是不能承受的。中年的“我”,再合群,如同蝙蝠成群飞翔,依旧不过是黑暗的相互叠加,即使振翅取暖,依旧是孤寂的一个,“我”和蝙蝠的相同在于:“不能交谈,却如此接近”。在另一首《蝙蝠给我画像》中,那只蝙蝠要撞上“我”的脸,因为“我”浅色的脸,如同一个洞穴,蝙蝠要往里飞。将自己的脸譬喻为一个空虚的洞穴,蝙蝠的黑暗是为了探测出我的生活的可疑的漏洞,可疑的空虚,借助回声(时间、记忆?)。多么大胆地直面“我”的现实状态!让人毛骨悚然。这个中年的“我”,似乎对黑暗有深沉的迷恋,黑暗,也许还可以理解为阴影、幽深,与直白的热烈、光照形成反差。孤独或沉静,沉思或寂灭,丰富或空虚,似乎都在黑暗中酝酿,所以,诗人说蝙蝠,“我对他们的等待,就是对恋人的等待”,蝙蝠之于黑暗,是精神现状的呈现,与自己中年命运的暗合。不知是这种命运引导诗人走向黑暗,还是他固有的黑暗迎合那种命运:“凝望雁阵,我看清了心里那么多的幽暗——”(《雁阵似剪刀》)
二胡手。《二胡手》一诗,有着诗人惯有的简淡、客观、理性语气。场景出现,如同在一个故事中。“二胡手”在拉二胡,在“旁观”的我(其实在叙述中,我已经转化进入成为二胡手)耳中,那些曲子仅仅在叙述两个词:“忧伤”和“过去”。“他有理由让弦曲中的毒蛇伤及路人”,“此刻,我感到过去就是他的表情/不再渴望新生活,就像哭湿的火柴头”。忧伤和过去,都是与“现在”相对的一个词,正因为“现在”的孤寂感、落没感,才唤起对时间流逝之痛感,过去只是“哭湿的火柴头”,过去并不能唤回多少温暖,多少激情的回忆,现在的“忧伤”,仅仅是被过去所触动,曾经年少的一切,在“现在”已经如哭湿的火柴头,再擦不出激情的火花。诗人问,“过去离现在到底有多远?”是时间之质问,也是生活状态之质问。是否能如过去一般“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青春尽管充满仇恨,激烈,残酷,却能面对任何的“骨头”迎面而上,充满激情地乱啃一气。这个与“骨头”对峙、擦出激情火花的日子,已经散落在过去的幽暗中,对于“现在”,只剩下忧伤。是忧伤时间的流逝,也忧伤中年生活的无力感、疲倦感。诗歌中,“我”的中年状态与二胡手的面目以及所拉出的弦曲叠加在一起。二胡手也好,“我”也好,“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它也一声不响……”(《中年》)这种中年的无可奈何感,一种对生活司空见惯寡淡无味的描述,被黄梵清晰记录。我不得不佩服他对自己中年之“伤”的理性认识。黄梵的厉害还在于,他意识到,中年的疲倦,并不是说他会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恰恰在于,他的动心,与年轻时不同,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是骇人的。比如,他说,“人要挺住的,不是悲痛,而是春暖花开”,这句诗,具有深刻的时间伤痕:当我们年轻时,会为每一次痛苦、伤害掉泪,每一次都要挺起精神去承受,每一次,他都觉得是经历了人间大事;而当人到中年,历经沧桑后,悲痛叠加,如此之多,已经让那久经磨难的心起了老茧,抵御的力量如厚厚的钢板,心不为所动,这时候,反倒是“春暖花开”的美好,一种“轻”,一种柔嫩,会突然,一下子触碰到内心最脆弱的部分,为之潸然泪下。二胡手的弦曲,也许那时候正好触碰到了旁观的“我”的某个柔嫩部分。又如,《哭泣之歌》,诗人说,“眼泪是常有的事,尤其到了中年”,但“眼泪常是别人的磨难,在你体内受孕而成的”,“你常忘了为自己而哭”。年轻时,只有一个“自我”世界,至于中年,自我对生活所起的坚硬的抵御,会羞于为这个“自我”而哭泣,这时,万事万物有所感,他人的苦难,就会“移情”到自己身上,借助为他人的苦难撒泪来浇胸中之块垒。
梧桐。如果说,蝙蝠是中年的具象表现,二胡手叙述了时间之伤,而梧桐及梧桐路,则展现了一幅中年的生存背景。在南京,你不可能不感觉到梧桐存在。春天发芽,夏天荫翳,初冬时种子飘落如绒毛,而深冬,“是它们扎起长辫的时节”。无论春夏秋天,梧桐却总有一种中年气息,他们理所当然地存在,平稳,厚实,既不让人欣喜,也不轻易枯萎,梧桐似乎能够见证所有一切欢乐苦难,忍受所有该发生和已发生的。南京这个六朝古都,裹挟着黯淡的、过往岁月的热重,在梧桐的荫翳下稍稍喘息。诗人行走在梧桐树下,树冠高耸枝桠杂多,阔大叶片遮蔽烈日与暴雨,梧桐树无限延伸,没有尽头,这里那里。在这个梧桐无处不在的六朝古都,诗人意识到,中年,如同“一排风华正茂的梧桐,多么优美/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才能/一样的多情一样的陡然忍受”。在中年所有的日子里,悲伤、喜乐,仅仅只在内心激起小小的波澜,初恋已慈祥,爱情成挽歌,一切都曾经历,又怎会带来巨大欣喜或悲戚?所有的日子都是旧日子,而所有行过的路,都已栽遍了梧桐树,甚至,“我要把去过的城市,都简化成一条梧桐路”(以上皆引《金陵梧桐》)。在这样的路上,诗人说,“我在日子之间奔波,已经染上梧桐的秋色”,“我目不斜视,但依然是一个过客”(《十月》)。在一个个日子之间奔走、忙碌,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时光流逝,回首看看,所有的日子竟然惊人地相似;“我”已经清晰地看见了前进的方向与目标,甚至可以清晰看见未来生活的每一天,连如何抬脚起行,道路中出现的小小分岔,也都一清二楚,但我更加清楚的是,即使接近了目标,走对了方向,即使不误入歧途,我依旧只是一个“过客”。匆匆我来,匆匆我往,我这个中年人,明白所有的行路,依旧停不下脚步,依旧坚定地朝前奔跑。这种命定的奔跑,并没有飞翔在天的喜悦,仅仅出于惯性。越是目标清晰地奔跑,越是心中充满茫然、飘忽之感,“如果茫然像继续像风,从枯叶上哗哗飞过/如果翅膀不再对天空着了迷……”直到落叶飘零,鸟声寥落,阴雨埋葬了落叶,就如同埋葬我们的欢乐,“已经开始腐烂……”从梧桐刚刚发芽,到秋色变黄的时节,就已经嗅到了落叶的腐烂气息,中年的“我”,还在安慰自己,阳春三月,梧桐还会发芽……目前“我”要心平气静,要“在一道夕光里,只是假装走得像树影一样安详”(《一个下午》),虽然,“就算追上最后一道夕光,也安慰不了落日”(《异乡》)——这就是一棵中年梧桐的宿命。黄梵以锋利的笔触,不断地削剥着他的中年处境,毫不留情。一个勇敢的诗人,敢于直面自身的困境,询问自身的来路与去向。诗人在解剖个体的同时,诗歌也同时具有了普遍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