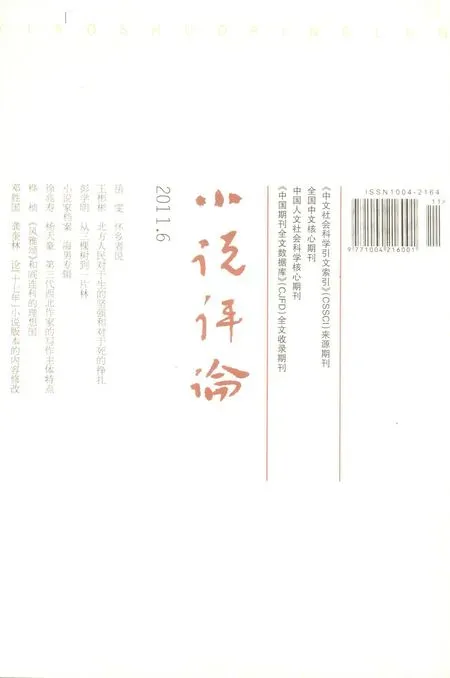殊途同归:“美的极致”的审美追求——沈从文与孙犁之比较论
2011-11-19魏洪丘
魏洪丘
文学工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意图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就其共同的目标而言,不外乎都是要创造文学形象,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中最热门的种类之一,自然表现得格外突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乡土小说领域,如果以创造美的形象、表现“美的极致”、实现审美追求的成效来评判,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沈从文和孙犁两位。
两位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了受人赞誉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孙犁笔下的白洋淀,都享誉文坛,得到人们的推崇、学习,因而也形成过相应的艺术流派。但是,两位作家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小说流派,却在创造美的形象和审美追求上,表现出的观念和主张却有着惊人的差异。30年代沈从文及其以他为代表的京派小说“有意识地让文学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而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之中,来与现实丑相对抗。”①而孙犁和以他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小说则“一直是把政治与现实生活视为一体的,政治与文艺本不是对立面,艺术家只能如实地反映二者的自然关系,人为地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将创作引向歧路:或者让艺术成为形式技巧的空壳,或者滑向公式化、概念化和虚伪矫情。”他们对待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样的截然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他们同样创作出了青史留名的美的文学形象,表现出“美的极致”,影响深远。
一
沈从文被誉为“自然与生命的歌者”——“在沈从文的湘西理想中,‘自然’与‘生命’构成其精神家园的两个核心概念。‘生命’是与人的现实存在相对立的神圣存在,如沈从文所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同时,‘自然’成为沈从文美学之最高境界。他所醉心的人性与生命形式,就是这种充满原始生气、自由自在的自然形态,它是迥然不同于文明理性的生命状态,也是重振一个‘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一剂良方。”②
人作为宇宙中的生物,自从有生命以来,繁衍承续了不知多少代。作为自然形态的生命,人类有其生存的基本模式,人类也有其本能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没有理性而不可抑制的。在生存过程中,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都会对人类产生一定的影响(或促进、或抑制、或推动、或阻碍)。因此,人的生存过程、人的自然属性,就成为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表现并反映人的生存过程、表现并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就成为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沈从文在创作中歌唱的“自然”与“生命”,也正是在于此。它们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之一便是人性的探索。原始淳朴的人的自然本性的探索与赞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他一贯声称自己是“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③因此,他的作品都与人的自然属性密切相关,尤其是原始淳朴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美。
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从内容上看是一个委婉缠绵的爱情悲剧故事,但围绕着这个悲剧故事,他是在展示人性美——茶峒这个原始古朴的边城中的“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兄弟之谊、邻里之睦”等美好的世态人情。在这个边城里,无论贫富军民、地位高低,人们的心灵都非常美——质朴、健康、美好。作品的主人公翠翠。无疑是人性美的化身。她天真纯洁、乖巧善良、聪明美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然之女”,她没有受到丝毫的世俗污染。在她身上表现出山城人民对生活的诚挚、对爱情的忠贞,体现了自然朴素的人性美。而傩送兄弟则是心灵美的呈现。他们出身富家,却不为金钱所惑,不以地位财势选择配偶,表现了对世俗的挑战,体现了美好的情操。他们在爱情上还宁愿成人之美,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纯洁无私的心灵。在这个用人性编织起来的古朴边地里,即便是悲剧,也往往都有美好的出发点,或者是因为误会造成:翠翠母亲的殉情——生不能相伴、死也要相随;老船夫为翠翠提亲受到刺激而逝,则是因为船总顺顺由于儿子出事(天保翻船、傩送离家寻找)而无心谈亲事、无意中冷落了老船夫。
他的短篇小说《月下小景》《萧萧》《丈夫》等,也都始终落点于人性的描述。这里所表现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性爱。古语说,食色,性也。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说更是把性视为人性的根本。人生过程中凡饮食男女都无法回避性爱与婚姻,都会受到性的自然本性的约束。《月下小景》写了一对苗族青年男女的恋爱,面对“女人只能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同第二个男人结婚”的野蛮习俗,为捍卫自己性爱的纯洁与坚贞,双双口服毒药而亡的故事。《萧萧》则写了“小丈夫大媳妇”的童养媳旧俗对人性的扼杀,而萧萧以人的性爱的自然本能,越过了旧习俗对人的生命和性爱的限制、压抑。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丈夫》写的是人性的扭曲和旧习俗对妇女的人性、人格的摧残。在人格尊严受到残酷的打击后的丈夫的觉醒,揭示的是人性的回归。
可见,沈从文的作品都围绕着人性的主题。在原始淳朴的人的自然本性的探索与赞美之外,也有对非人性的事物的揭露与评判。只是他没有从社会角政治的角度去深入展开,而是着眼于人性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丑恶——原始野蛮习俗的揭发、贬斥。这也是对人性的表现,只不过是人性的丑陋的另一面。
为了使自己的人性的探索(尤其是人性美的赞美)呈现更美的形象,表现出一种美的极致,沈从文采用了人性主题和自然景物的合一的写法。他将对人性的极致的赞美,融化在优美的自然景物描写、人物的人性人格追求,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神话故事传说之中。如《月下小景》的月下景物的美丽神秘氛围、具有哲理性的奇特传说与苗族青年男女对理想爱情境界的追求融为一体;《萧萧》的开旷自然的山野与萧萧本能的性爱意识的萌发相得益彰。这也就导致了沈从文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注重意境的“纯化”,把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尽量融入人们简朴的生活情致之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原始清新感、神秘感的民间风情。在这里,单纯、朴素的自然环境成了人性的外化。也即是人们所说的,沈从文作品表现了原始、古朴的人性美;悠远、恬静的自然美;这二者相加,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牧歌情调的艺术美。人们把沈从文的小说作品称为“抒情诗体小说”。其人物是诗化的(人性美的化身)、景物是诗化的,是现实与梦幻的水乳交融。其自然、人性之美,溶注着作家的情感、体验、回忆、想象,体现着作家的美学追求,也是作家人生体验的投射。
可以说,沈从文的创作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一份成功而有益的范式与经验。特别是当人们经历过一段段社会政治历史阶段,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产生一定的厌倦之后,人们往往走向疏离社会政治而选择人性的回归。人性被认为是永恒的主题。而抒情诗体的模式则更加容易为浮躁、空虚的人们所接受。这时,沈从文式的创作便得到更多的人们的肯定,沈从文被推崇到极致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二
孙犁被誉为“儿女情怀与时代风云”——“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的传统,并赋予其革命的色彩;一方面又在关于革命的叙事中,突出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清新与阴柔意味,从而在实际上展示了一个为人低调、襟怀淡泊、情感阴柔的作家在革命时代对于人生的某些独到发现”④。与沈从文相比,孙犁则完全是另外的一种风格和模式。
同为乡土小说大家,孙犁的小说“着重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⑤孙犁笔下的荷花淀(实际上是冀中平原一带),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一样,自然、美丽,但孙犁则更多地着眼于时代,着眼于社会政治,着眼于革命,表现社会的人——灵魂与人情。
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因而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有更加突出的社会属性。因为人是社会的一员,人的思想、行为、性格、气质、修养、文化……无一不受社会的影响。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且人也要主动去适应社会环境,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人有悖于动物的人的理性。人既然有理性,那么人必定有思想、感情、态度,有对价值的判断,有信仰的追求。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人的品德、情操、气节,都是不同于自然属性的人的品质。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和推动历史发展潮流的人的社会属性,可歌可泣,长期以来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催人奋进。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孙犁生活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这是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亲身感受到生死存亡的人生关键时段,天天都有死亡的威胁,我们的民族也正经历着生存与灭亡的考验。孙犁作为一个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他的小说创作所描写的时代自然离不开抗战。抗日战争那艰苦卓绝的斗争、血与火的考验、战争的残酷,时时伴随着人们的人生,令人无法逃避。孙犁选择不去表现丑恶、残酷,而是让读者从战争的残酷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在欣赏美的过程中得到愉悦和补偿。”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易单纯的文字,写出了人物身心的内在的美,生活斗争和自然风光的诗意。”⑥茅盾称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风云变幻”⑦的。
他的代表作《荷花淀》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紧张的矛盾冲突,没有惊险的战斗场面,所描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而这些场景又都是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虽然处在抗战的紧张危难时期,白洋淀人民仍然乐观自然,像水生嫂在荷花淀边编席子的夜织图就凸现了一个“美”字。作品集中描写了新一代农民水生和农村妇女水生嫂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尚的民族情操、坚强的斗争性格。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为了民族解放而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们的形象是美的,是民族图存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的呈现,是抗战时代中国人们的理想性格,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的斗争也是诗化了的:荷花淀的伏击战——“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战争很快就获得了胜利,战士们开始打扫战场、在水中捞取战利品。丝毫没有残酷的气息,人们则沉醉的美的熏陶中。还如《芦花荡》,这篇写日本鬼子放冷枪伤害中国人情节的作品,虽然像在直书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但是孙犁并没有把它作为主题,而是表现老船夫复仇的决心与行动。老船夫为了给被鬼子冷枪打伤的孩子报仇,设计将鬼子引入自己的鱼钩阵,然后像敲水葫芦那样,一篙一篙地敲碎鬼子的脑袋。整个战斗也是诗化的,在美丽如画的白洋淀里,一位老人用自己的智慧与残忍的鬼子斗争,只身一人巧妙地杀敌,最终取得了胜利。读后令人心大快。我们不能不佩服老船夫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机智勇敢的斗争方式。
另一重要代表作《风云初记》也是如此。作品没有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战争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有常见的普通农民、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芒种和春儿这对青年人期待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太平幸福的生活,可战争打破了他们的梦想。他们不得不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一参加抗日武装浴血奋战,一做后方工作积极救亡,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作品中也不乏诗情画意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青年妇女们对未来生活的幻想、幻想被日寇打破后送别情人上前线、自己也投身于抗日斗争;一幅幅普通的生活画面,显示出冀中平原乡村的风光美和人情美,以及他们命运的变化,从中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还如,芒种随部队爬上长城岭上关口的城墙,和战士们一道,在落日的余晖中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虽不是正面作战的描写,却更好地再现了战士们英勇战斗的豪情和气概,给人以美的享受,让读者产生内心的共鸣。作品还集中笔触去深入这些普通农民和村妇的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写出他们的爱与恨,他们的追求与幻想,写出他们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的轨迹。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反映出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
人们常常用“武戏文唱”来高度概括孙犁关于以战争为背景的题材小说的特点。
三
沈从文与孙犁作为现代小说领域中表现“美”的极致、塑造美的形象的代表,得到了人们的赞誉和喜爱。他们的作品载入文学史册,具有崇高的地位,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们同样都是文学流派的典范作家,创造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影响了一代作家与文学。追求“美”、表现“美”,显现了他们共同的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
他们又同为乡土文学的代表,都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的笔下是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独特的湘西世界,古老原始而朦胧的人性美;孙犁的笔下则是冀中平原的白洋淀水乡,清新淳朴充满时代气息,高尚的民族情操和心灵美。他们的小说都具有抒情、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都堪称“抒情诗体小说”。
但是,沈从文的小说更多的是表现原始古朴的人性美、悠远恬静的自然美、牧歌情调的艺术美;而孙犁的小说则集中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心灵美、平凡生活中普通人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美好的情操。他们一个专注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探索,一个则集中于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而无论自然或社会,他们要表现的都是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与崇高。
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潮泛滥、人们热衷于政治追求的日子里,许多人把社会政治视为小说创作的最高目标,“主题先行”和“假、大、空”成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模式,人物形象则成为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今,那样的作品已经为人们所唾弃。但是,许多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视社会政治为污垢,一听到“革命”、一谈及“国家”“民族”等社会政治命题便嗤之以鼻,而由“阶级”转向“人性”的表现,仿佛只有“人性”才是永恒的主题。于是乎,过去的“左翼”作家、革命作家遭到排斥,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便成为文学创作的偶像,许多人便醉心于人的自然属性——“人性”的探索。在重新审视历史、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颠覆”成了一个标志——颠覆经典(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现象屡见不鲜。被颠覆的当然是以往那些“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而被捧为至宝的当然是当年非“左翼”非革命的作家、作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在当年的阶级社会里,中国人民正在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民族解放才有个人的解放,只有民族的发展才有个人的幸福。他们看问题自然是民族为先,基于“民族”的立场。立足于社会政治的革命的观念,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学创作的目标也是如此。这无可厚非。而随着民族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级社会性质的改变,人们观念的变化也是必然的。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重新改写,纠正过去“左”的错误,重新认识一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也是必然的,也无可厚非。文学本来就应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成就也不应该以革命、非革命来判断与划分等次。我们不能过去只追求“革命”,现在则否定“革命”。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由过去的只肯定孙犁、否定沈从文,而发展成只肯定沈从文、否定孙犁。孙犁对社会政治的追求,并未损害文学形象的创造,而创造出了永垂青史的文学经典;沈从文对人性的探索,也是创造文学形象的又一途径,他同样也创造出了永垂青史的文学经典。虽然选择的对象不同,创作的路径也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同样给我们创造了美的形象,受到人们的赞誉,并永载中国文学的光辉史册。这就是孙犁和沈从文带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魏洪丘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第88页。
②陈国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35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选集(5)[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231页。
④张志忠主编:中国当代文学60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46页。
⑤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22页。
⑥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335页。
⑦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J],人民文学,1960(8),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