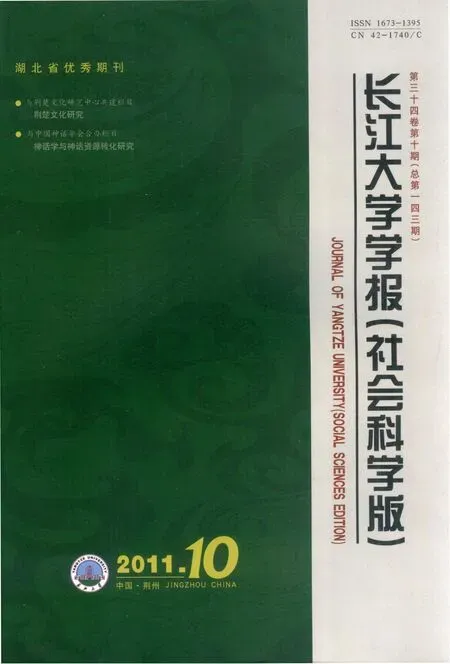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水车堵装饰艺术
——以厦门新垵村传统民居为例
2011-10-28赵胜利
赵胜利
(集美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水车堵装饰艺术
——以厦门新垵村传统民居为例
赵胜利
(集美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水车堵装饰艺术是厦门新垵村传统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在特有的自然环境、人文背景和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新垵村传统民居水车堵的装饰特点以及形成原因,探讨其文化内涵,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化生态;水车堵;装饰
水车堵(水车垛)这个名词是闽南的方言组合而成,“水车堵”的“水”与闽南话的“美”同音,“车”与闽南话的“斜”同音,指很美的墙上斜垛,这一称呼流行于漳、泉、厦与台、澎一带的建筑界。[1](P171)水车堵的位置较高,故需将人物与景物前倾,以便观赏,在视觉上,也以免人物头部过小而失真。
水车堵是一条狭长的水平带状装饰,宽度约为10-20公分,深度约为8-15公分不等。水车堵线框底部一般压在大门门廊石上,以砖叠涩出挑。在视觉上,层层出挑的砖线如同阶梯,能增强建筑的体积感,打破大面积墙体的单调性;在功能上,水车堵具有墙体收头的作用,使墙体有顶,称为墙的边缘。水车堵有时还兼有悬挑及止水的功能。在水车堵的装饰上,分为堵头与堵仁,堵头又称为“线肠”,堵内常用泥塑,剪粘构成装饰带,作为红瓦屋顶与红色砖墙之间的过渡。其装饰内容多为山水人物、花卉、虫鱼等题材泥塑或交趾陶艺。考究者以玻璃罩封护,以防雨淋或脱落(图1)。水车堵为闽南建筑中一个特殊的构件,在设计与制作时往往需要由专业的匠师承制。
一、新垵村传统民居水车堵装饰特点

图1 玻璃罩封护的水车堵
新垵村传统民居主要以闽南红砖厝建筑风格为主,少量地出现灰砖建筑。厦门、金门、漳州一带民居的水车堵,多由正面延伸至山面;泉州一带则仅至角牌为止,用“景”作为结束,称“水车出景”。
新垵村传统民居水车堵堵头图案多分为抽象的几何形、具象的动物纹样与文字的适合纹样,线条极为细致,通常只有二分或三分宽度,但凹入的深度多达八分或十分,为深剔底的雕法。其中较为抽象的几何形为回型纹、卷草纹、如意纹、云雷纹等;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动物纹样为螭龙、蝴蝶、蝙蝠等;文字的适合纹样如寿字、喜字等。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素有“五福”、“四喜”之说。“五福”出自《书经·洪范》:“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但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精练为福、禄、寿、禧等以表达其丰富的内涵意义。另外,多采用抽象的几何形与具象的动植物纹样进行组合的原则进行装饰。堵仁是装饰主题的安置之处,题材丰富多样,有直接采用中国花鸟画的方式来进行彩绘的,风格为写意、工笔或兼工带写的形式,且一些水车堵的装饰借鉴了中国传统国画中青绿山水的画法;另外,在大部分装饰中采用平面绘画与立体亭台楼阁相结合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镶嵌的手法,如同我们今天在综合绘画中采用的技法一样。一些工匠常直接把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场景与故事运用到水车堵的装饰上来,通过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戏剧戏曲情节来表达他们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表达忠孝节义的气节,通过祥瑞景物、男耕女织与渔樵耕读等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善恶美丑的认识,部分的装饰还图文并茂,让观者能很清晰地感知当时的工匠想要传达的内容与意境。
二、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水车堵装饰艺术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传统建筑,由于受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以及受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社会与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影响,为各地建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在各种民间艺术中,地方建筑的装饰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载体之一,它反映各个地区的气候、风俗、宗教信仰等特点,也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
(一)地理环境与气候对水车堵装饰的影响
海沧镇位于厦门市海沧区,以西北群山为屏。其群山主峰马青山海拔485m,有汀溪发源于此,向东南流入马銮湾。新垵属于海沧区的一个乡村,地处厦门与漳州龙海交界处,与南安市官桥镇相邻,位于磁灶的北部,距磁灶镇区7公里。新垵村因新垵水库而得名,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新垵村特殊的文化氛围。新垵村总体区域面积约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255亩,交通十分便利,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324国道穿境而过,磁新公路连接磁灶镇区与新垵村,通向晋江市区。截止2008年,新垵村有13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4500人,1045户,外来人口1000多人。
新垵村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长冬短,年平均气温22.3摄氏度,夏季多台风,降水量980.5毫米。受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影响,新垵村主要以红壤和砖红壤土质为主,为建筑的红砖大厝奠定了材料基础。新垵村盛产陶瓷,为建筑的装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为水车堵的装饰提供了镶嵌的材料。
新垵村一共有600多栋老房子,一条龙式地排开。建筑选址大多为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大厝背后是高山,左右有山的支脉,山中流出的泉水,或汇于村前水塘,或绕村逶迤而去。前方平原田畴,视野宽广。
(二)水车堵装饰材料的生态性及其制作方法
新垵村传统民居的水车堵主要是采用灰塑、彩陶、彩绘与镶嵌为主,其中灰塑又称灰披,是闽南传统建筑上特有的一种装饰手法。灰塑以传统建筑中的灰泥为主要材料。灰泥由蛎壳灰(或石灰)、麻丝、纸筋、煮熟的海菜,有时添加糯米浆、红糖水,搅拌捶打而成。其中蛎壳是闽南人向大海索取的建筑材料。牡蛎,闽南人也称海蛎、蚝,是固着在沿海岩石上生活的贝类。用蛎壳、蚌壳等烧成的白灰,俗称“蜃灰”。宋人方勺《泊宅编》中提到:“闽中无石灰,烧蛎壳为灰……故用灰(桥墩)常若新,无纤毫罅隙。”[2](P152)福建侯官人郭柏苍在《海错百一录》中说:“凡蛎壳烧灰,名壳灰。斥卤之地……壳,海物也,得咸气与土性合。石灰,山产也,其味淡,南省傅墙壁,尤经久。”[3](P553)
从施工工艺看,灰塑一般以铁丝或砖瓦搭出骨架,于其上敷灰泥,边披边塑,直至成型,最后在半干的泥塑表面彩绘,也可以在灰泥中直接调入矿物质色粉。灰塑是趁湿时制作,较砖雕、石雕有较大可塑性。[4](P166)灰泥干硬后色泽洁白,质地细腻,常被误认为是陶制作品。灰塑因未入窑烧造,坚硬度不够,易风化褪色(图2),所以目前很少留下较为完整的水车堵装饰。

图2 灰塑水车堵
上面提到,新垵村盛产陶瓷,建筑工匠将陶瓷艺术巧妙地运用在建筑装饰上。水车堵上的彩陶以半圆雕或者浅浮雕的方式出现,或者直接将陶塑作品置于凹入的水车堵内,以增强立体视觉效果与空间深度感。由于受佛教与道教思想的影响,水车堵中的彩陶,常见的有假山、楼阁、亭榭等形象,以塑造人间仙境或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新垵村建筑装饰的彩陶是一种低温彩釉软陶(图3),以800摄氏度至900摄氏度的温度烧成,釉层较软,外观粗拙而湿润,色彩艳丽,但硬度欠佳,容易破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彩陶制作的水车堵已经残破毁坏,甚至完全脱落。

图3 软陶水土堵
剪粘,是闽南古建筑上的一种装饰工艺,主要的技法为“剪”与“粘”。在新垵村传统建筑水车堵的装饰上,同样出现大量采用瓷片剪贴镶嵌的景物和人物(图4)。当地人称之为“堆剪”、“剪花”、“堆花”、“剪瓷雕”或“贴瓷花”。剪粘一般是趁灰泥塑未干时,在坯的表面粘上各色瓷片、玻璃片或贝壳。各色瓷片主要来源于窑场的废品,如破损的花瓶、碗,按斤论价,也可将窑场所产的单色薄碗打碎,然后根据需要剪成各种图形进行镶嵌。

图4 水车堵饰物
新垵村传统民居中彩绘主要是体现在水车堵装饰上,彩绘工具主要是采用各种毛笔与排笔。彩绘颜料是由工匠在油漆行购置,调入桐油后制成。这类颜料皆为矿物质粉末,若颗粒过大,则需研磨后再调入桐油使用。在技法上,当地的工匠经常采用传统国画中工笔重彩退晕法与罩染法等。退晕,当地工匠称“化色”。在水车堵彩绘中,他们一般使用他们称之为的“大色”,即原色颜料如红色、青色、黑色等和在“大色”中掺入白色,形成粉色系列,他们称之为“二色”,使其淡化,从而达到退晕效果。
(三)客家文化的影响
新垵村的村民基本上姓邱,从祠堂与民居中的对联足以看出他们是客家人后裔。祠堂的对联为:“枕文山还忆龙山远脉,对溪水转思沂水源流。”在另一处民居上石刻的对联为:“沂水溯渊源家风宛在,新江县俎豆世泽长存。”对联中多次提到的沂水为沂水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沂水县位于鲁中南地区,秦代即在此置县,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因沂河过境而定名,迄今已1400多年。在八姓入闽的传说中,其中一姓为邱。唐林蕴序《林氏族谱》云:“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乾隆《福州府志》卷七五《外纪》引路振《九国志》云:“永嘉二年(308年,永嘉为晋怀帝年号),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从以上资料可以得出新垵村为客家村落,他们的祖先是从河南与山东省迁入的。
众所周知,中原地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尊崇的礼仪制度影响着客家的先民们,且世代传承,成为客家人日常行为的准则,并净化着人们的心灵。虽然生活的环境与场所发生了改变,但“礼”、“义”、“仁”、“孝”等儒家思想观念仍然体现在客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新垵村传统民居的水车堵装饰上,雕刻的题材多选择以人物、花鸟、山水、走兽为主,人物题材多为表现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历史与民间传说故事,且按照年代的不同依次排列,如年代久远的排在左边,近代的安置在右边,体现出儒家人伦之等级制度。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新垵村传统民居水车堵的装饰上,汇集着崇文重教的传统理念,如在堵头与堵仁上经常可以见到书卷的纹样。“客家人哪怕境遇不佳,也会保持他们的书卷气。他们似乎很有些空闲的时间,一边叼着长长的烟斗,一边读书,至少他们会拨出时间来这样做。”[5](P53)这是一位西方人眼中的客家先民。另外,在新垵村的水车堵装饰上,经常可以见到梅、兰、竹、菊题材的绘画。
(四)外来文化的影响
新垵村是一个拥有众多侨民的乡村。明清时期,厦门港兴盛,新垵村村民跨海出洋谋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进行掠夺式开发,新垵村人移居海外再次形成高潮。他们和众多的侨民一样积极进取,勇于开拓。“衣锦还乡”是很多在外拼搏的客家人当时的梦想,许多富裕的侨民自南洋归来,往往在家乡兴建住宅、宗祠,以光宗耀祖。目前,新垵村许多传统民居就是他们出资营建的。在建筑的形式与装饰上,吸取了南洋风格以及其他的外来风格。因此新垵村传统民居建筑从总体布局到细部装饰上,都能明显地看到西方及南洋文化影响的痕迹。
佛教约于三国时传入福建,唐、五代时,随着闽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兴盛,寺庙遍布。《宋史》载:“其 (福建)俗信鬼尚祀,浮屠之教。”宋人吴潜在 《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中统计说:“寺观所在,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西浙不如福建。”
在各种外来宗教中,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较大,留下的宗教遗迹也最为丰富。由于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从唐代至元代,阿拉伯、波斯等地穆斯林来泉州经商传教。在长达数百年的交流史中,阿拉伯人对闽南地区民间社会的影响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拿建筑来讲,闽南建筑中繁复的装饰、艳丽的色彩,都隐约地受到伊斯兰艺术的影响。伊斯兰艺术十分注重装饰,在早期的伊斯兰建筑中,继承了亚细亚一带的巴比伦、亚述帝国的镶嵌饰板做法,经常以釉面砖或彩色瓷片构成图案,镶嵌在墙面上。这种装饰多用阿拉伯文字、几何图形、植物图形等元素创造出精致复杂的图形,组合变化,千姿百态。这种装饰构图,具有抽象性、延展性、连续性及反复性等特点。新垵村水车堵堵头的装饰 “如意纹”、“蝴蝶纹”以及用中国传统篆书体拼成的吉祥文字等,都能感受到吸收了伊斯兰装饰的风格。特别是在用色上,新垵村的水车堵多用蓝色、白色、绿色等颜色,而这几种颜色又是伊斯兰装饰中的常见色。从对现存的新垵村传统民居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客家先民们对受西方建筑空间文化影响的南洋建筑样式的接纳态度是包容的,也体现出归国华侨对故乡的眷念。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又想突显出自己在外拼搏的业绩,所以回国后将自己的祖房修缮一新,或者重新盖房子,红色的墙身,繁缛的装饰,张扬的形式,多种风格的融合,使人联想起现当代艺术中的 “艳俗”艺术。
(五)海洋文化的影响
新垵村生产主要以农耕、鱼盐及海洋贸易为主,生活与生产方式塑造了闽南人的性格特点。厦门气候炎热,濒临浩瀚无穷而又变幻莫测的海洋,故民众性格活泼而偏爱装饰。上面提到新垵村传统建筑装饰大量运用蓝色与白色,除了受伊斯兰建筑装饰的影响外,还受海洋文化的影响。蓝色与白色也是海洋的基本色。新垵村村民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点,敢于冒险,追求财富。
海洋文化也造就了闽南人炫耀斗富的性格,明人王世懋 《闽部疏》说:“泉漳间……民居皆俨似黄屋,鸱吻异状。官廨、缙绅之居尤不可辨。”感叹闽南民居有点像帝王的宫殿,官府衙门与士绅宅邸装饰怪异,不可辨认。清人赵翼 《檐曝杂志》云:“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名尚气。凡科第官阀及旌表节孝之类,必建石坊于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数百坊,高下大小骈列半里许。市街绰楔,更无论也。”[6](P338)道光 《厦门志》中提到: “富贵家率用兽头、筒瓦。”[7](P515)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在闽南地带,百工技艺发达,特别是新垵村的客家人,祖传下来的手艺与地方技艺相结合,各种造物思想的交融,所以风格独特,雅俗兼具。明代张燮著 《清漳风俗考》中提到:“百工鳞集,机杼钫锤,心手俱应,……前此未有也。”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新垵村民在建筑内外大肆进行装饰,住宅建筑是他们炫富的最直接表现之一。
在新垵村传统建筑的水车堵装饰上,经常可以见到出海船只的图样以及渔民与海浪搏斗的场景(图5)。惊涛激流时常考验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喜欢海洋同时又惧怕海水吞并了他们的生命,从而转向了对海洋的崇拜。在水车堵装饰上经常会出现一些西洋船只,表明当时与海外的交流比较频繁 (图6)。另外,新垵村人民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漂洋过海寻求发展。另外,许多侨民出于对海外拼搏经历的记忆,往往把当年飘洋过海的场景刻画在建筑的装饰上,让子孙们铭记他们曾经的辉煌,以启迪后辈传承进取的勇气。

图5 出海船只

图6 西洋船只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厦门市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发建设的趋势也逐渐向郊区蔓延,海沧区新垵村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镇区,古宅深巷高悬着各式各样的商业招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现代文明正一点点吞食这个古村落。被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包围的古民居,也正逐渐淡出现代人的视野。生活在这里的客家先民的后代,也难以忍受老房子带给他们的不便,最终搬出了老宅子,出租给了外地民工。大部分民工在生活的压力下,只图有个遮风避雨的场所,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内部结构与功能,部分老民居成了废品收购集散地。照这样破坏的速度,新垵村的传统建筑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殆尽。一些值得保护的标志性大宅院,也没有见到政府树碑立牌表明是受保护的文物。
新垵村传统建筑上的水车堵装饰,由于常年经受风吹雨打,大量的水车堵只剩下边框,堵仁完全消失,甚至堵头的部位也没有任何附着物。先前讲究的人家采用玻璃保护的水车堵,如今玻璃残破,里面的水车堵装饰所剩无几,当然人为偷盗的可能性也极大。一些反映历史题材、民间故事的人物以及戏曲故事中的场景已经非常模糊,难以从图像中进行考证。尽管如此,水车堵具有的装饰、收边、止水、悬挑的功能仍然不可忽略。从文化生态视野下看新垵村传统民居上水车堵的装饰,可以感知这些装饰的形式存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以推断当时客家先民的审美需求、经济状况、人文背景以及心理状态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水车堵装饰在新垵村传统民居虽已成为一道残存的风景线,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仍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1]戴志坚.闽海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方勺.泊宅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郭柏苍.海错百一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曹春平.闽南传统建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5](美)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6]赵翼.檐曝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周凯.厦门志[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
TU-883
A
1673-1395(2011)10-0167-05
2011-08-11
赵胜利(1963-),男,安徽蚌埠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民间美术与美术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