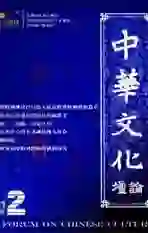汉魏六朝时期的纪梦诗文
2011-10-21时国强
时国强
[摘要]汉魏六朝时期的梦观念大致可以分为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类,有神论认为梦为鬼神显灵,预示吉凶祸福;无神论认为梦为虚幻之像,不能预言祸福。纪梦诗多表达思念之情,纪梦文多表达较为严肃的主题。梦作为抒情手段,纪梦诗文的表达方式基本一致。总体上看,纪梦文表现出更为丰富的想象力。
[关键词]汉魏六朝;梦;诗文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87-5
梦作为文学表现对象,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就有大量记载,其中《左传》的描写尤为突出,但这些记载大多为了占卜吉凶,具有迷信色彩。到了汉魏六朝时期,思想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梦的关注却并没有衰减,文学作品中仍有大量纪梦诗文。所谓纪梦诗文主要指具有梦境描写的作品,既包括以梦境作为主体的作品,也包括片段的梦境描绘,还包括以梦作为讨论对象的作品。以此为衡量,汉魏六朝纪梦诗大致有90首,纪梦文大致200篇。下面仅就这些作品反映的梦观念、情感内容及艺术表现,略作分析。
一、关于梦的观念
梦本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现象,但因其虚幻奇异,导致人们的种种猜测和迷信,对之所作出的解释,也往往赋予了各种梦本身之外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西汉初期盛行黄老思想,对于梦的解释多道家色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淮南子》。《淮南子》认为梦是受到现实干扰心思分散的结果,若能体道为一,摒除喜怒哀乐,元思虑劳神,就能其寝不梦,表现出—定的唯物倾向。它还认为:“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否定了梦的神怪色彩,而将做梦与否与梦之吉凶归结于主体的思想修养,显示出无神论的色彩。其后儒术独尊,董仲舒将原始儒学掺入阴阳五行灾异感应等内容,这一时期的儒生多借梦来宣扬天人感应,使梦具有了某种怪异神秘色彩。东汉谶纬迷信大行其道,对梦的解释更为荒诞离奇,对此,王充《论衡》做出了全面深入的批评。首先,他认为梦不能预言吉凶祸福,“人梦不能知觉时所作,犹死不能识生时所为矣”。所谓吉凶感应都是儒生的穿凿附会,他说:“梦与神遇,得圣子之象也。梦见鬼合之,非梦与神遇乎,安得其实!”同样所做恶梦也不代表必然受灾,他以昌邑王梦蝇矢而龚遂占以将用谗言为例,说“蝇之为虫,应人君用谗。何故不谓蝇为灾乎?如蝇可以为灾,夫蝇岁生,世间人君常用谗乎?”否定了梦之善恶预言吉凶的观点。
其次,他认为梦境皆为虚像。“人梦所见,更为他占,未必以所见为实也。何以验之?梦见生人,明日所梦见之人,不与己相见”,“人梦杀伤人,梦杀伤人,若为人所复杀,明日视彼之身,察己之体,无兵刃创伤之验”。即使有应验之梦,梦中所见也是虚像,“何以明之?直梦者,梦见甲,梦见君,明日见甲与君,此直也。如问甲与君,甲与君则不见也。甲与君不见,所梦见甲与君者,象类之也”。所谓梦为魂行也是解释不通的,“使魂行若飘风乎,则其速不过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梦上天,一卧之顷也,其觉,或尚在天上,未终下也。若人梦行至雒阳,觉,因从雒阳悟矣。魂神蜚驰何疾也!疾则必非其状。必非其状则其上天非实事也”。总之,梦是单向的,梦者与所见之物不能互感验证,所以见到的只是假象而已。《论衡》戳破了梦的种种虚妄,但梦的神奇性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好奇心理的驱使下。占梦之风从未停歇过。王符的《潜夫论》有《梦列》一篇专为占梦而设,认为“君子之异梦,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异梦,非乘而已也,时有祯祥焉”,而有时不能占验的原因则在于梦的朦胧不明了,或因不能详细的道出,或是“说者不能连类传观,故其善恶有不验也”。但王符并没有将梦看做不可违背的天命意志或鬼神显灵,反而认为梦的吉凶取决于人,“借如使梦吉事而己意大喜乐,发于心精,则真吉矣。梦凶事而己意大恐惧忧悲,发于心精,即真恶矣”。若能“无问善恶,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便能转祸为福,反之则会转福为祸。
魏晋时期关于梦的观念,以《列子》论述较为详细,《列子》虽是战国时期的典籍,但现在流传下来的《列子》,一般认为是魏晋人的伪书,反应了魏晋人的思想观念。它认为梦是同一物类之间的相互感应,做什么样的梦与主体的现实境况密切相关,“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沉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外物干扰而致梦,所以它说“神遇为梦”,神凝则梦消。与《淮南子》的观点接近,反映了道家关于梦的认识。傅玄则进一步否定了梦的预言性,认为“梦攀日月,觉而不上天庭;梦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说,偶中耳”(《傅子·补遗上》)。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以彼岸世界为皈依,认为人的魂灵不死,可以轮回转生。所以它一方面借助梦来宣传因果报应鬼神灵异,一方面又常常借梦来否定现实表达虚幻之感,表现出颇为矛盾的态度。如释玄光《梦中作罪顽痴之极五》:“或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夫人鬼虽别,生灭固同,恩爱之情,时复影响。”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梦的真实性,在此影响之下,一般士人也往往把梦当做神魂的出游,萧琛《难范缜<神灭论>》还分析了各种梦境:“或反中诡遇,或理所不容,或先觉未兆,或假借象类,或即事所无,或乍验乍否。”此皆神游所遇,难以现实常理检验。而信佛的宗炳却在《又答何衡阳书》中说:“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缘合而有,本自无有,皆如幻之所作,梦之所见,虽有非有,将来未至,过去已灭,见在不住,又无定有。”不但否定了现实,也否定了梦的真实性。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悖论,范缜彻底否定了梦为神游的观点,他说所谓梦作蝴蝶并不能真做蝴蝶,梦见“肠绕阊门,此人即死,岂有遗其肝肺,而可以生哉”,所以“梦幻虚假,有自来矣”。(《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意识形态领域中,往往新旧观念交错并存,即使同一时期,甚至同一个人的观念也有矛盾抵触处。刘向一面说“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一面又说“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说苑·敬慎》),既把梦当做鬼神显灵,又否认梦的先验决定性。其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北齐刘昼《刘子·祸福》在谈到怪梦时皆持此观点。因此,前文所梳理的不同时期的观点,仅就当时主流的、重要的思想认识而言,并不排除其他的观念认识。而事实上,巨细无遗地详细论述各种观念认识,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二、纪梦诗文所传达的情感内容
纪梦诗文表达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借梦的描写来表达想念之情。这种想念之情,或是对贤臣良将的期盼,或是对亲人家眷的牵挂,或是对知己友朋的渴求,或是对故乡故都的思念,或是对某种生活的向往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男女相思别离的作品,东汉描写男女
之情多限于夫妇之间,较为质朴自然,深挚真切,梦境的描写一般为概括性叙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曹魏三国时期,晋代梦境的描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南朝以梦写男女相思则出现了艳情的势头,如鲍照的《梦归乡》写其梦中返乡夫妇相见之景,说“开奁夺香苏,探袖解缨徽”,详细到松解香囊的地步,暗示了恩爱之情。此后,随着艳情宫体诗的兴盛,借梦写艳诗的也多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胆直露。如庾信《梦入堂内》王僧孺《为人述梦》沈约《梦见美人》等,庾信的作品还只是借梦写女性的闺房、梳妆、服饰等,营造暧昧的气氛而已。而沈约的《梦见美人》、王僧孺的《为人述梦》则直接写了铺床就枕的情景,如“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梦见美人》);“以亲芙蓉褥,方开合欢被”(《为人述梦》)等,充满了暗示与挑逗。
文章本来更适合展开详尽的描绘,但纪梦文借梦来描写男女之情的内容,却远远不如诗歌描绘的细致,其表达的情感与方式都没有多大的变化。汉武帝《李夫人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借梦表达思恋之情,还有些具体的场景描绘,如“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李夫人赋》),“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长门赋》)。到了建安曹魏时期出现了应玚《正情赋》、王粲《闲邪赋》、陈琳《神女赋》、杨修《神女赋》、阮璃《止欲赋》等借梦言情之作,却反而没有了梦境的描绘,如《正J隋赋》“魂翩翩而夕游,甘同梦而交神”,《闲邪赋》“排空房而就衽,将取梦以通灵”等表达对恋人的渴慕,都过于简单,没什么内容。到了晋代出现了潘岳《寡妇赋》“梦良人兮来游,若阊阖兮洞开”,陶渊明《闲情赋》“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遥而不安”这些梦境的描写,也只是恢复到了汉代的水平,总体上看纪梦文对于男女之情的描绘不如诗歌。
作家们除了用梦来表达思念之情外,也用梦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胸襟怀抱等较为严肃庄重的主题。如韦盂《在邹诗》写韦孟辞职还乡之后,仍然“心存我旧”梦回王朝,谏诤王室。而韦孟最为突出的品质也正在于其忠贞耿直,因此这一梦境的描绘完全可以看作是其胸襟志向的自我披露。诗歌毕竟以抒情为主,像这样借梦来表达志向的作品不是很多,而主要集中于纪梦文中。较早的作品是班固的《幽通赋》,《幽通赋》的第二段皆为围绕梦境展开的叙述,其梦登高山而与神遇,象征了道术将通前途光明;梦“揽葛藟授余兮,眷峻谷日勿坠”,则是对自己的告诫与明训,非常形象的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以及建功立业惜时进取的美好愿望。有时也用来表达哲学观点,如苻朗《苻子》:“燕相谓王曰:‘奚不飨之?王乃命宰夫即膳之。豕既死,乃夕见梦于燕相日:‘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之珍,而欣君之惠,将报子焉。”以生为忧患,死为解脱,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对庄子“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庄子·大宗师》)的另一种形象阐释,其表现手法也与《庄子·至乐》中髑髅论道的方式相一致,都表达了舒张生命、追求自由的道家思想。除了这种寓言的形式外,释真观《梦赋》则直接以梦中人物来进行论辩,阐发自己的见解主张,相当于驳难性质的议论文。文中的奇宾劝自己及时行乐,或者修德扬名,仕宦流芳,批判佛教违亲背主,憔悴自苦。“我”则对客的劝告逐一进行了批驳,认为所有的享乐名利都是短暂不可靠的,俗世的贪欲带来的只有苦难和痛恨。唯有佛教才能超脱苦海,让人萧散优游,神清气静,甚至傲比王侯,保持了精神的至尊与高洁。从而全面否定世俗,达到宣传佛教的目的。
三、纪梦诗文的艺术表现
纪梦诗在表达思念之情时,大多先叙想念之情,次写梦中之景,后写梦醒之叹。第一部分为梦之缘由,暗示了梦中之景,奠定了情感基调。第二部分为前文的自然延伸,并通过梦境的描绘,达到情感的高潮。而后的梦醒又将虚幻的满足带到残酷的现实,情感从高处猛然跌落。这样梦中的欢愉与梦后的失落形成鲜明对比,情感经历了一个发展,高潮,低落的起伏过程,表达得更为曲折尽致酣畅淋漓。如蔡文姬《胡笳寸叭拍》“身归国兮儿莫之随,心悬悬兮长如饥。……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悟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显然这里的梦是其思子之切而产生的幻觉,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其渴望超越现实困难获得团聚而终不可得的无奈与心酸。至东晋杨羲《梦蓬莱四真人作诗四首》,表现方法出现了新的变化。它不是在现实创作中插入梦境,而直接截取梦中的一个场景片段,使纪梦诗由部分的梦境描写向整体写梦过渡。而且这几首诗假托为梦中仙人所作,则所作之梦也系有意虚构,不再是简单地描写一个真实的梦象,转而虚构梦境,借以抒怀表意,已把梦当做了更为自觉的艺术表现手法。类似的创作还有许翙《梦诗》刘宋时的《陵欣歌》梁代周子良《彭先生歌》等。梁代何逊《夜梦故人》姚翻《梦见故人》,则既不是梦前、梦中、梦后的写法,也不是梦中之景的直接呈现,而侧重于描写梦后的情景,对梦境作进一步的申发。何逊《夜梦故人》对梦境的描写只有一句“言与故人同”,其后就写了梦醒所见,以空床、斜月、长风等抒发凄凉哀伤之情,末尾三联慨叹己之流离相思之苦。在这里梦只是触发心绪的契机,抒发自己漂泊羁旅的孤寂之J隋,才是诗的重点与本意。姚翻《梦见故人》则完全略去梦境,而以议论的手法抒写梦后的怅恨,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其后王僧孺《为人述梦诗》、萧纲《十空诗·如梦》、梁武帝《十喻诗·梦诗》、谢灵运《维摩经十譬赞·梦》等,皆使用了议论的方法表达虚幻之感。其中王僧孺之作虽有艳情的梦境描写,却是以反衬的手法来论证梦的虚幻,二萧及谢灵运之作皆宣传了佛教空无的思想,当是南朝佛教盛行的反应。
纪梦文以纪梦作为一种抒情手段,其表达方式与诗歌基本一致。如司马相如《长门赋》的最后一段,表达陈皇后失宠之后对汉武帝的悲愁思念,说“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梦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对于心理感受的形象描摹,梦中的相得快意与梦后的怅惘失意相对比,衬托出孤寂哀伤之情。但西汉纪梦文更多的与政治联系紧密,如龚遂《蝇矢对》、匡衡《祷高祖孝文孝武庙》、王莽《上奏符命》等,这些文章对于梦虽然也怀着崇敬畏惧的心理,但在对梦的描述时并没有过多的奇异性,也并不过分渲染梦境,只是利用梦来阐释自己的见解主张,把梦当成了干预现实政治的工具。至东汉关于梦的描述出现了一些怪异之景,这些荒诞的梦境被信以为真,并进而影响到现实境况。如桓谭《新论·祛蔽》说扬雄作《甘泉赋》“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尽管荒诞,桓谭却据此论证尽思务神有损于身体。总体上看,这些关于梦的描写大多是利用梦的神奇性,把梦作为一个例证或论据来加以描述的,目的在于来增强说服力和权威性,多为简短的片段,处于从属的地位。东汉末年王延寿的《梦赋》通篇描写梦境,标志着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题材。此后徐干、缪袭都创作了《嘉梦赋》,可惜这些作品都已失传。现在所能看到的篇幅较长的作品,是隋代释真观长达1500多字的《梦赋》。此赋不像江淹的《别赋》《恨赋》那样铺陈各种别离、感恨之事,而是集中笔墨描写梦中之景,虚构了奇宾客与自己的辩论。虚拟主客问答是汉赋常见的表达方式,形式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此处的运用却别有新意。因为此赋宣扬的是佛教出世的思想,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世事如梦,这一空无的思想与梦的表现形式契合无间,有种惝恍迷离之感。王延寿《梦赋》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描绘了与群魔搏斗的陆离场面。该文为其恶梦之后,为排遣恐惧自我激励所作。文中详细描绘了各种鬼神之变怪,有“蛇头而四角,鱼首而鸟身,三足而六眼,龙形而似人,更为奇特的是作者挥手振拳,打得这些鬼魅“或盘跚而欲走,或拘挛而不能步。或中创而婉转,或捧痛而号呼”,战胜了这些妖邪之怪物,表现出丰富奇特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