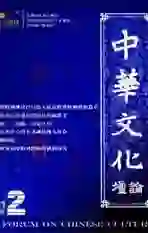从树林到冰雪世界:无望的救赎
2011-10-21邹涛
邹涛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柏子的《美国,我不说爱你》这三个文本,展现文学中的乌托邦之梦在空间建构上的变化——从树林到高原到极地。这种变化既是日益恶劣的现实生存环境的写照,也体现出作家们对现实的抗争精神以及对救赎之路的苦苦追寻。
[关键词]《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环湖崩溃》;《美国,我不说爱你》;树林;救赎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80-7
一、自然空间与乌托邦想象
纵观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未经或少受人类劳动加工改造的自然是激发艺术想象力的重要源泉,容易诱发“心向往之”的浪漫情怀,成为乌托邦艺术构想的重要部分。
在自然中,树林这一意象的核心象征意义之一是代表神秘、美好、生机勃勃的孕育之所。无数以树林/丛林为活动背景的童话故事、浪漫喜剧、探险小说都帮助把树林,丛林的这种意象沉淀到人们的潜意识里。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仙女、莎士比亚笔下的淘气小精灵和追逐嬉戏的恋人、罗宾逊等绿林好汉这些在林间出没的有趣形象都在促成奇妙生动的林间意象。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强调了树林对心灵的教化作用;苏格兰名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指出,树林之所以对人类心灵这么有吸引力,主要不在于它的美,而是它微妙的氛围、它散发的古树幽香使疲惫的心灵变得轻松释然。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尤为突显树林的作用,认为它可帮助人“重返理性和信仰”、修复生活中的一切不幸并与神灵相通。也就是说,林中之行被赋予了_一种宗教仪式性的崇高地位和超验主义的神秘色彩。类似的树林乌托邦构想者在文学史上层出不穷,如库柏(JamesF Cooper)、劳伦斯(D.H Lawrence)、梭罗(HenriDavid Thoreau)、巴勒斯(John Burroughs),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树林/丛林代表人类童年记忆里身心合一、万物和谐自由的奇妙家园。令人悲哀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树林,丛林受到极大的破坏,“雨林正以每年1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2.8亿人沦为环境难民。”同时,树林也不再显得那么纯净神秘了。在刘易斯的《巴比特》中,成功的商人巴比特希望借助野外之旅寻求心灵的放松与解脱。他问自己的丛林向导:“乔,如果你有很多钱你会怎么办?你是继续坚持当向导呢,还是回到丛林过独立自在的生活?”没想到乔听到他的话第一次显得格外欢快起来,他满怀向往地回答:“我曾经设想过的。如果我有了钱,我会下山去开一家大鞋店。”可见,树林似乎已难以承载现代人的乌托邦之梦。反应在文学上,其表征之·就是乌托邦之地从树林到高原到极地,甚至到海洋深处或者外太空,其纬度不断上升,其距离伸至幽远,其生存环境走向决绝。
与树林/丛林相比,长年积雪的冰雪/冰川世界更少受人类的侵扰,其冰清玉洁的形象让厌倦俗世凡尘的人们满心向往;同时,它也戴着神秘面纱,但是,这种神秘感伴随着深深的敬畏,因为其零下几十度的深寒让绝大多数生命惧怕。所以,与人类关于树林的奇妙家园想象不同,长期冰天盖地的世界引起的更多是成人世界的探险征服欲。当然,对于本身生活在严寒地带的少数群体而言,冰雪,冰川承载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与想象。不过,在整个文学史上,浪漫的冬天故事虽然不少,尤其是圣诞节、新年等节日赋予飘雪的冬日无限的温情与诗意,但在常年的冰雪世界建构乌托邦的例子却是非常少的。在风靡全球的幻想小说里程碑似的作品《纳尼亚王国传奇》和《指环王》系列中,冰雪世界虽然神秘迷人,但总是充满了太多的邪恶与危险,反映出人类心灵深处对深寒之地的恐惧。那么,如果有本身并不生活在严寒地带的作家硬要把心中的乌托邦设置在极地冰雪中,那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本文将通过三个文本的分析来展现文学乌托邦在空间建构上的一种趋势,并探讨这种趋势带给我们的启示。本文选取的三个文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面简称《查》)、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以及柏子的《美国,我不说爱你》,在空间上跨越中西,在时间上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在主题上都聚焦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问题及其可能的拯救之方,三者之间既有暗合、又有发展。共同演绎出全球现代性症候的典型特征及发展脉络。
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林子里的生命绽放
劳伦斯是构建树林乌托邦来对抗工业世界的典型代表。他生于诺丁汉郡一个矿工家庭,其家环绕着煤田和牧场。在成长的过程中,旧式的森林、牧场和新兴的钢铁、煤矿直观地向他展示出工业化与自然的对立。他亲眼目睹工业化操作对人性与生活的异化,痛感“机械化的贪婪世界”的狰狞可怕,觉得“煤与铁把人类的肉体与灵魂深深地吞食了”。他把树林看成启迪饱受工业化之苦的现代人重新发现自我、拯救麻木心灵、重返生命本真样态的灵性之所。在他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里,树林正承担着这样的角色。
他理想中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应该生动、活泼,而崇拜伟大的自然神潘,只有他才永久是群众之神”。在《查》中,生气盎然的树林集中体现了自然潘神的精神与美。自然潘神代表着旺盛的繁殖力,劳伦斯笔下的树林万物竞发,生气充盈,动植物都在泼泼辣辣地展现着慑人心魄的生命孕育之美。那些还拥有一颗敏锐的心灵、能感受到林子里活跃的生命脉动的人也会与自然潘神心灵感应,激发出身上沉睡已久的生命本能力量。当康妮感受到正在孵雏的母鸡那天然的母性流露时,她“差不多心碎了”,“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失落无依,毫无用处,全不象个女性,只是一个恐怖的可怜虫罢了。”她出神地欣赏着小雏鸡粲然的生命力,心中在呐喊:“这是生命!这是生命!这是纯洁的,闪光的,无恐惧的新生命!这样的纤小,而这样的毫无畏惧!”“她对生命孕育之美的渴慕完全触动了守林人梅乐士的心,激发他心中无限的柔情,两人此情此景下的激情喷发也就非常自然了。而当康妮开始真正怀着和梅乐士幽会的目的来到树林时,有这样一段情境描写:
所有的树都在静默中努力着发芽了。她今天几乎可以感觉着她自己的身体里面,潮涌着那些大树的精液,向上涌着,直至树芽顶上,最后发为橡树的发光的小叶尔,红得象血一样。那象是涨着的潮水,向天上奔腾。
正如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来自春意盎然的林子里的一次冲动可能比所有圣人教给你更多善恶问题。”在这样的情境中,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人,都已然成为自然潘神的化身。人卸掉一切束缚,传统的羁绊彻底消解,人之性器无异如植物之花,美丽而坦然。于是,梅乐士与康妮用鲜花香草点缀性器官、在雨中裸舞做爱的浪漫场景就显得
如此自然、毫不矫情。在茂盛的花草树木中,在滋润万物的天雨里,康妮和梅乐士的身心在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中沉醉,人的生命之花与自然之花竞相绽放,人也就成为了真正的自然之子,与天、地、雨水、千草万木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诠释着潘神精神,演绎着劳伦斯心中的“血胜”宗教。
梅乐士引领着康妮和这片生气蓬勃的林子融为一体,与外面的煤铁所代表的乌烟瘴气、了无生趣的工业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梅乐士虽然也受雇于有钱人,但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富有生机的活动空间一片树林,比那些整天在地下劳作、身心倍受恶劣环境摧残的矿工更具生命的活力,这样一种活力是那些沉浸于阴冷污浊的煤铁世界的矿主和矿工们所无法拥有的。在劳伦斯眼里,矿主是冷酷无情的有产者,矿工是萎靡无奈的无产者,两者都是了无生气的,是在现代文明中被异化的产物。而靠着生气充盈的树林的庇护与熏陶,以梅乐士和康妮为代表的人得以重现生机、还人之本真。尤其是对于身陷工业化氛围而身心日渐萎缩的康妮来说,每一次林中之行都代表着生命力的进一步复苏;在林中小屋里,“康妮完成了由退化的女性向圆满的母性的转变,”身心恢复润泽,“一如那雨后的古老却满溢着生命力的榛树林、橡树林”。林中之存在因此被赋予了一种宗教救赎似的崇高地位和神秘色彩。
三、《环湖崩溃》:杨志军的荒原悲歌
有“荒原作家”之称的当代作家杨志军,因其作品展现出的生态意识而倍受称赞,可谓中国生态写作的领军人物。《环湖崩溃》(1987)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获《当代》文学奖,有学者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在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杨志军笔下的荒原实指青藏高原。山广成原,原高为山,山高成极,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兼具山、原、极地三种地貌的很多特质,生存条件艰苦,自然风光壮丽。这样一个离天最近、人烟稀少的地方,成为现代中国人编织乌托邦之梦的精神家园。
在杨志军的小说里,青藏高原由“洪荒和文明化合”而成,是“介于神话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第三种世界”。这里和劳伦斯的树林一样,充满了激荡的生命力,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雄性的欲望”、“母性的激情”、“恣意汪洋的春情”,都在荒原上灿烂盛开。牧羊女卓玛意勒在男女情事方面热情奔放、心安理得,这种态度“烙印了人类童年的记忆,又似乎预示着未来。它是不朽的,不朽的生命的动力”。
不过,杨志军笔下的荒原是一个远比梅乐士所栖居的林子更为广袤复杂的空间,各种力量在这里交织、博弈,形成一幅悲壮的历史画卷。
工业化时代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冲突与影响在《环湖崩溃》中得到深刻的展现。该小说采用的是第—人称叙述,凸显出在场的历史感。在“跃进”旗帜下,父亲带着“我”和一群军人满怀革命的激情来垦荒。“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力气,大荒原有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于是,春草萋萋的草地成了战士们挥汗如雨的战场,“那翻起的土浪,那土浪上面被热阳晒枯了的草叶草根,又一次加固了我们对荒原的征服意识和那种报效祖国的荣耀感。”垦荒队所代表的农耕文化与牧民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当牧民向垦荒队发出“快走,再翻草皮,佛爷不容”的警告时,垦荒队意识到,他们不仅要和“荒原的自然蛮力”搏斗,还要受到“神秘”牧民的威胁。牧民头领洛桑带人驱赶垦荒队后,因担心被捕而躲在寺庙里。可是,当他得知垦荒队在转移中被困雪中生死垂危时,他一脚踢伤了见死不救的女儿,冒着被捕的危险出去营救垦荒队。随着垦荒队与牧民交往的日渐增多,彼此的关系也由对立到相互学习。当垦荒队离开的时候,垦荒之路却在延续。
垦荒代表着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激情,也带来了料想不到的后果。曾经的光荣变成了耻辱,“漠风一天比一天肆虐了,荒地日日扩张着,草场渐渐缩小了,牧草一片一片地死去了。”垦荒者有了深刻的反思:“当初我们拓荒者的荣耀,我们的热血的象征,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豪风吹跑了疏松的土壤,卵石裸陈。大荒原中又有了戈壁滩来增饰荒凉和恐惧。”
面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断恶化的局面,曾经的垦荒少年又一次燃起生命的激情:“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上帝呢?我何不以天神的姿态来一次挽救环湖草原的呐喊呢?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我也是一颗光彩耀亮的神圣的天体,”他开始朝绿色卫士的方向努力。不过,他逐渐意识到,同样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暴殄自然与保护自然这两股“并行不悖却又对抗不息的力量”将推动人类的悲剧向纵深方向发展。
柏子旅美回国后写出的《美国,我不说爱你》也是一本当代畅销小说。在该小说中,作者把理想人物的生存环境安排在阿拉斯加的多津塔那,它靠近北极,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积雪冰封,是地球最北端的小镇,有着“穿透人的心脏和大脑”的、“可以涤荡一切的寒冷”;而且,这里的冬日是全黑的季节,一夏日则成了“日不落”王国,如此环境真可谓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非常不适合生存。那么,选择这样的生存环境似乎可以突显主人公生命意志的顽强与勇气。
首先,生活在多津塔那的“森林男人”算得上是现代社会的苦修僧。因为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留不住女人,两性比例极不平衡。他们的先辈在血腥的战争中,曾经只剩下三个男人,为了保持生命的延续,其中一个叫凯特的印第安首领从沿海一带带回一百多个男人和十个妓女。这十个本是奔着美好前程而来的女子面对皑皑白雪感觉上当受骗了,可是她们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凯特威信和武力并用,硬是教会了多津塔那男人怎么去爱女人。”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这些女子,并且决不能随意靠近她们的身体。因极度渴望女人而违反禁令的,要么被凯特杀死,要么自残。慢慢地,他们养成了守身如玉的习惯,即便没有妻子,也决不出去嫖妓。
可是,生命力终归需要释放,于是苦修有着独特的狂欢形式来补充。当寒冷的、暗夜的冬日过后,凯特扎起豪华的舞台,让男人们跳上去尽情表演,向台下的女子们展示他们的威猛、勇敢、生命的激情与魅力。这些平日苦修的男子们,似乎等待千年,就为着这一刻的尽情绽放。女子们睁大眼睛,选出她们心仪的男子,共度良宵。第二年,多津塔那就多了-一批强健的小生命。凯特发明的这种做法后来衍变成一年一度的“森林男人拍卖会”。世界各地的女子都在这一天纷至沓来,寻找她们理想的情人。这个拍卖会对于多津塔那的“森林男人”来说,也就成了“一个展示生命的节日,一个释放生命的节日,一个让生命走向辉煌的节日”。而对于来到这里的女人来说,“森林男人拍卖会”是“一个可以让人超越生活的逻辑来理解情感的载体”。在玉洁冰清的环境中,这样的狂欢不仅不让人觉得色情,心中反而有了一种圣洁的感觉。
多津塔那的“森林男人成为现代女人白日梦中的美妙伴侣。他们—方面身体剽悍、身心纯洁,
充满阳刚之气,体现出顽强的生命意志。正是从“森林男人兰斯那里,主人公桑迪懂得生命原来可以如此美丽。兰斯带着她去北极看神秘莫测、美丽无比的北极光,并对她说:“……你难道不觉得,我们生命的光,比这个有形的绚丽的光,更加夺目更加丰富更加精彩吗?”在兰斯看来,“生命是一根碳火棒,只有燃烧了,发光发热,才有意义。生命就应该是顽强的,哪怕你是在一个寒冷的角落,也要借着狂风,滚到那火堆中去。”桑迪那被硅谷生活无情摧毁的生命主体意识被充满生命活力的兰斯重新唤醒。从多津塔那回来以后,兰斯已经成为桑迪生活中的一个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由两样东西构成:生命和生活。”另一方面,多津塔那的“森林男人”并不缺少都市男人的文化修养,懂得用现代化的科技成果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尽可能便利和舒适。譬如说,这里真正的森林男人几乎人人会驾驶飞机。同时,他们温柔懂爱,对女人极尽呵护之能事,可谓原始与现代最美妙的结合体,其情爱与人格魅力对女人,尤其是都市女人,有着非常的震撼力,在“征服你肉体的同时。还征服你的灵魂”。
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森林男人”的生存境界和以硅谷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里的人所表现的生命的脆弱、生活的异化形成鲜明对照。在硅谷,科技、高效率是核心理念,可谓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绝佳战场。硅谷人总是雄心勃勃,“是那种想改变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改变的人群”。工作几乎成了他们的全部,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生存寄托。在一种永不停顿的物欲追求中,生命本身却成了虚空。人们似乎忘却了生活本身,他们已不再是鲜活的生命,大都成了工作狂人、科学机器。被神话的高科技也只不过是“资本家们获取利益的工具”。
五、无望的拯救
从《查》可以看出,劳伦斯作为工业社会的拯救者寄希望于依靠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力来对抗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残障,追求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工业文明之前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人是自然之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只要有工业文明的干预,其结果就会是悲剧性的。这从其小说里无数的自然之子形象中充分体现出来。这些形象如《白孔雀》中的农民乔治、守林人安纳布、《儿子与情人》中的矿工莫瑞尔等,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工业文明之圈相交后,其自然的生命活力都受到极大的、甚至毁灭性的创伤。
在《查》中,劳伦斯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努力宣扬他的“血性”救赎之路,在忧患中极力表现出一种对信念的坚守。可是,另—方面,对工业文明的恐怖早已沉淀为无意识,会抓住一切缝隙渗透出来。从小说里,细心的读者可以读出这条救赎之路的徒然无望。梅乐士的栖居地一一那片生机勃勃的林子是归工业主拥有的,并且与工业化的世界只隔咫尺。他站在山顶上,同样能感受到工业区的夜的“不安和永久的恐怖”,他可以看见“高炉在发着清淡的粉红色”,史德门的电灯光“又尖锐又刺眼”,是“多么令人难解的含恶意的光辉!”所以,哪怕在树林深处,“树林的僻静是欺人的了。工业的嘈声把寂静破坏了。那尖锐的灯光,虽不能见,也把寂静嘲弄着。再也没有谁可以孤独,再也没有僻静的地方,世界再也不容有隐遁者了。”他时时感到自己“被一种恐惧压制着”,“他恐惧着自己和她要被外面那些电灯光里含恶意地闪耀着的‘东西所吞食。”他渴望可以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去和外面的机械世界抗战,“去把生命的温柔,女人的温柔,和自然的欲望”这些宝贵的财富珍藏起来,可是,“所有的人都是在那边,迷醉着那些‘东西,胜利着,或惨败于那机械化的贪婪或贪婪的机械主义铁蹄之下”。所以,在作者的内心里,有两种声音—直在交锋,一种代表着不屈的信念,一种代表着残酷的现实。只不过,他一厢情愿地要为世人、同时也为自己撑起一根信念的支柱,只好在工业化世界之中用想象之刀辟出一片精神飞地林出来。
当我们走出劳伦斯的树林,来到杨志军的荒原这个与工业文明相对更远的空间,我们的乌托邦情结仍无所归依。《环湖崩溃》中的“我”似乎也拥有梅乐士的生命激情,但是,血性宗教的救赎之路却难以在他这里实现。当他和所爱的花儿不小心走入沙漠中的死亡圣地,面对绝境中的奇观,他们在绝望、敬畏、手足无措中摆脱了衣服的裹束,变得赤身裸体。这和《查》中的康妮在树林里裸舞颇为相通。衣服象征文明,当人卸下文明的包裹,原来的道德禁锢也就不复存在,“人类在自己的童年,神祗在自己诞生的年月,不需要任何可笑的遮掩,如同我们,此时根本想不到用手去阻挡对方眼光朝自己最隐秘处的纵情流泻。”悲哀的是,当花儿摆脱了一切精神束缚时,“我”偏偏在此时失去了雄性的力量,无法与花儿实现灵肉的合一。无独有偶,“我”在此之前曾经在卓玛意勒的大胆调情下落荒而逃,在和花儿的雪地相拥中也用道德的力量抑制了自己的冲动。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劳伦斯的救赎之路的可行性多了几分怀疑。文明已为我们的肉体与心灵穿上了_一层又一层的“衣服”,我们又如何回归亚当夏娃的乐园?此外,比起独善其身的梅乐士,《环湖崩溃》中的主人公多了一份中华民族所钟爱的济世情怀。但是,他也抵挡不住历史的洪流,最后渴望的是在高原湖泊的开湖圣境中殉道而去。
“恢弘而磅礴的万物枯死的荒原”难以承载我们的乌托邦之梦,冰雪/冰川似乎成为地球上的最后圣地。多津塔那的人在冰天雪地里顽强的筑起自己的温暖之巢,但他们的谋生方式却是城市化的,他们可以架着飞机穿梭在工作地点与栖居地之间,这和那些选择居住在郊区的高薪一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反映的是在自然环境日益缩小的情势下现代人千方百计想要靠近自然的愿望。只不过,他们自愿选择纯净但艰苦的栖居之所过一种苦修式的生活。由此看来,后工业社会的拯救者面对现实生活对科技成果的更大依赖性,似乎已不再对文明成果一律排斥,而主要求助于精神、意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柏子的小说里仍充满人与自然的张力,人更多地是体现出面对艰苦环境的不屈精神。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凡是人迹可至之地,已无处不受商业意识的侵蚀。时至今日,人们能想到的最后一片地球净土大概只有白雪皑皑的极地了,因为这是唯一一块生存资源太少而普通人无法涉足的地方。那么,当作者选择这样的地方来安置身心疲惫的主人公时,她所体现出的是一种绝望之下的寻觅与抗争。
作者不能无视极地严酷的自然条件这一现实情况,女主人公桑迪三进三出多津塔那也正反映出一种退隐于这样的环境时的矛盾。桑迪虽然希望自己是森林男人兰斯一生中唯一的女人,但她对要在如此严苛的自然环境中住一辈子心怀敬畏,那么这一愿望就自然难以实现。尝试调和的办法是把爱情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生活为依托的爱情,一种是以精神为依托的爱情。从第一次见到兰斯,桑迪感觉自己已经得到了精神的爱情,这也是她为什么总是在经历人生的高峰或低谷的时候就想念多津塔那,想念兰斯。可是,实际生活层面的爱情,桑迪却历尽坎坷而始终没有结果。这其实意味着这种调和方式的失败。极地的严苛的自然环境、都市的严重异化的生活环境,这两股力量撕扯着乌托邦构想者的心。构想者如何消解这种张力呢?
正因为极地生活近乎于一种坚苦卓绝的苦修,所以深具人文关怀意识的创作者非得在一望无际的单调雪白里画出几抹鲜亮绚丽来。大概是受了劳伦斯的影响罢,虽然柏子的乌托邦之乡一年大部分时间积雪冰封,她却依然把乌托邦之乡的主人公称为森林之子,并用她现代都市女人的白日梦幻想谱写了一首极地狂想曲——“森林男人拍卖会”。拍卖会上激情洋溢,被拍卖的“森林男人是男人中的精品,充满生命的活力却又不乏修养与柔情,女人则完全拥有选择的权利。在《环湖崩溃》中,也有一处类似的场景:“我”被一群牧家女在空中抛来抛去、衣服也被她们胡乱扯掉时,卓玛意勒得意地怂恿姑娘们来一次真正的争夺,“像哈萨克人的叼羊那样,谁抢到手,今夜我就属于谁。”如果说,荒原上的狂欢还靠体力取胜的话,“森林男人拍卖会”的游戏规则却是金钱说了算。女人选择的权利全赖于她们手中的财力,每一位被拍卖的男子都是由出价最高的竟拍者买走。如果女主人公桑迪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她就无法阻止别的女人拥有兰斯,而兰斯想和她在一起的努力也就成为徒劳。所以,多津塔那神奇的美景也好,男人拍卖会上活力四射的森林男人也好,作者只是为现代人的异化生活提供了一种调节剂,而无力真正重建新的价值体系。并且,在我们身后,树林、草原、冰川都在以我们不敢想象的速度消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