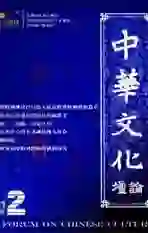李白 杜甫诗论与唐诗嬗变研究
2011-10-21申东城
申东城
[摘要]李白诗论从文学流变史角度,表达了对之前诗歌的看法,李诗多宗《风》《骚》、友建安,复古知交,亦不废齐梁风雅清真之作,李诗清水芙蓉,天然飘逸,奔放豪迈,多比兴。杜甫诗论多从个案上,对历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学习方法、师法对象、诗歌风格等进行论述,杜诗多祖《雅》《颂》,出六经、班《汉》,博学能化,杜诗写实事、求技巧,骨重沉浑,多赋法。李、杜肩负的时代使命和需解决问题不同,故诗论侧重点有别。李、杜诗论践行在他们的创作中,并体现出二人对唐诗发展演变的不同贡献,李诗多总结前人,是唐诗“正宗”,杜诗多大变先贤,系唐诗“大家”。
[关键词]李白;杜甫;诗论;唐诗嬗变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74-6
李白、杜甫诗论相对较少且零散,学界已有一些关于李、杜诗论比较的文章,但将其与唐诗发展演变联系起来的几无。李诗是盛唐之前复古的正宗,杜诗是中唐以后新变的大家,他们的诗学主张不仅关乎其创作,而且对唐诗嬗变影响很大。本文拟尝试比较李、杜诗学思想,并阐述其在唐诗发展中的转折之功。
一、李、杜对其前诗歌的异同看法
李白诗论集中体现在《古风》中,余散见于《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江夏赠韦太守良宰》等诗。《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就表达了李白对先唐文学发展简史的看法。他认为后世文学对《诗经》风雅精神的继承,随着时代发展而不同。平王东迁,不能复振大雅国风之诗,战国至秦,中正之声渐远。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虽多哀怨之声,但仍为“正声”之继。李白将形式主义文风溯源到汉赋里,扬雄、司马相如代表的汉赋承上启下,已是变风变雅、愈走愈远了。至于他对建安文学的观点,学界多有异说。然李白与陈子昂“先后合德”(孟綮《本事诗》),他们所合之德,其中就包含对汉魏风骨的继承,再结合李白对“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肯定,可知他对建安文学并非持否定态度。《古风》其三十五又云:“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李白的复古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诗经》这一正,统御后世之万变,他要恢复的“正声”、“宪章”就是正风正雅。当然对于楚辞、汉、魏诗作,他并非全盘否定,对屈原的褒奖,就是明证,“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他还常以屈原自况。
,
李白是复古的健将,对六朝文学批判中有继承。太白尝言:“齐梁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綮《本诗诗》)南朝诗歌夸尚“绮丽”,摘章绣句,竞为新奇,雄健之气,自此衰萎,李白贵情真、贱绮丽,对之总体倾向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并不包括所有作家诗作。李白所批判的是与风雅正声相背离的作品,其对于六朝的谢灵运、谢眺、陶渊明等不少作家作品仍是推崇的。
杜甫的诗论主要见于《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同元使君春陵行序》、《偶题》、《咏怀古迹五首》等作品中。与李白诗论从文学流变史角度谈不同,杜甫诗论多从个案上,对历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学习方法、师法对象、诗歌风格等进行论述,从而表明了自己的文学思想。《戏为六绝句》从多角度,分别对楚辞大家屈原、宋玉,南朝庾信,初唐“四杰”进行了赞扬。《解闷十二首》也褒誉了汉代苏武、李陵,南朝阴铿、何逊,及盛唐王维、孟浩然诗作。
和李白一样,杜诗论也宗祖《诗经》,“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就是其意。值得注意的是,虽说李白诗论中提到他志在删述,恢复大雅之道,但李、杜诗论的宗经侧重点是有别的。正如元戴良云:“李之诗似《风》,杜之诗似《雅》。”杜诗侧重二《雅》,多赋法,李诗偏爱《国风》,多比兴,这也形成李、杜诗风的不同,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的。杜诗论不仅宗法《诗经》,而且推尊《骚》体。他不仅对楚辞诗体无限向往,“骚人嗟不见”(《偶题》),而且极力推崇屈原、宋玉,“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其五),“(宋玉)风流儒雅是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李、杜皆认为《骚》为风雅正声的传承,这方面二人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杜甫认为屈、宋的“清词丽句”和儒雅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前者从诗歌风格、语言着眼,后者从诗歌内容、精神上落墨。而李白更多的师《骚》之浪漫精神和写作手法,如善用人名入诗之法,就是学习楚辞的结果,明谢榛曾云:“堆垛,古人谓之点鬼薄,太白长篇用之。白不为病,盖本于屈原。”
杜甫醉心汉代苏、李诗,谦虚地说愿意师从他们。其实苏、李诗风“淡宕”,杜甫诗风“沉雄顿挫”,他们“殊不相类”,可见其所师资,“不在形声相似,但以气味相取”。杜甫论诗重气味与李白同,李太白诗歌,“神气与味皆厚”,究其因,源于二人诗风皆同源《风》、《雅》,李白更继承了《古十九首》貌淡实厚之精髓。
杜甫对汉魏诗歌是肯定的,“汉魏近风骚”(《戏为六绝句》其三),认为其更接近风雅正声,这与李白论诗观点一致。与李白一样,杜甫对汉魏诗歌的看法,也可从对陈子昂的仰慕上得到旁证。杜甫不仅让朋友捎去对子昂的同情,“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且后专访其故居作诗褒赞陈“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陈拾遗故宅》)若说从陈子昂诗论中,可见李白对汉魏风骨的肯定,那么从杜甫写陈子昂的诗作中,则见到的是杜对陈能继承骚雅忠义精神的盛赞。不同的是,李白诗论对于扬马之赋颇有微词,而杜诗暗含对扬马的大力美颂。
李、杜对齐梁诗歌的看法大致相同。李白认为建安以后诗歌“绮丽不足珍”,但并非全部鄙弃齐梁文学,他对南朝一些著名诗人如江淹、鲍照、刘琨、祖逖等都有高评。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虽不满南朝重形式、轻内容,绮艳淫靡的诗风,但与李白有选择的肯定南朝诗人一样,杜对南朝名家庾信、阴铿、何逊等人饱含深情颂扬。杜甫还以这些南朝阴铿、何逊诗作比李诗和己诗。李白、杜甫将齐梁诗歌的精华汲取而来,尤其对南朝部分大家清新诗风大力肯定,并作为自己论诗作诗的追求高标,这是他们共通性的一面。
李、杜对自己生前的唐朝诗歌看法有别。李白《古风》其一(圣代复元古)中的“圣代”,即诗人所处的唐玄宗盛唐时代。李白认为盛唐诗堪称上接风雅正声,是复古的典范。但是《古风》其三十五对那些只知模拟、雕琢,丧失天真自然的诗歌进行了强烈批判。李白“志在删述”、垂映千古,从而创作出能“复元古”、并具盛唐特色的文质兼有的诗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大力创作、实践其诗歌主张的。正如李阳冰《草堂集序》称:“至今朝诗体,尚有齐梁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他用盛唐“清真”的至高诗美,与建安以来“不足珍”的“绮丽”诗风对举比较,不仅应证了自己“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等复古诗观,而且明确把握到盛唐诗风的命
脉,开出救世的良方。
李、杜生活的时代,文学风气发生了变化,二人面对的文学时尚、需解决的问题不同。《旧唐书》载崔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新唐书》亦云:“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靡相矜。”可见从初唐至盛唐李白之前,重文轻质、重技巧轻内容等南朝形式主义文风仍然留存,并占有相当的市场。陈子昂虽“古风雅正”,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故李白批判前贤,总结经验,承变、弥补了陈子昂重内容轻形式的弊病,从而创作出风骨兼备、文质彬彬的盛唐诗歌典范。而杜甫所面对的时代,有“李翰林之飘逸”、“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诗歌已经处于“盛唐之盛”状态。
若说李白肩负着破前人、立自己、重创造的时代使命,那么杜甫面对的,是怎样解决当时文坛悄然流行的厚古薄今风气。故杜甫对症下药,在《戏为六绝句》中,批评了那些“嗤点”庾信和“哂”王、杨、卢、骆“当时体”的“今人”、“尔曹”、“后生”,而对他们嘲笑的对象极尽赞美,并具体指出庾信和“四杰”的值得学习之处。从杜甫论唐诗作家作品中,可透露出如下两方面的信息:(一)“不薄今人爱古人,如何正确认识、学习前贤;(二)彰显出自己的评诗标准、审美倾向和创作体会。杜甫认为后人因为“递相祖述”,守旧因循,故看不到前贤的变革之功,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上,杜甫认为要“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只要能上接《风》《骚》的,又自成变化的我们都要学习,从而提出要有“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学习态度。杜甫学习前人思想是开放的、睿智的、冷静的,他不仅以王、孟清秀诗风为例,强调学习“清词丽句”,而且指出诗风要多样化,既要接受鲸鱼碧海、雄伟阔大、“沉着痛快”的壮美气象,也要兼具翡翠兰苕、自然清新、“优游不迫”的优美风格。这其实是对盛唐诗风的一个总结,也恰是杜甫能集前人之长而知变的过人之处。李、杜批判所指尽管不同,但其皆从现实需要出发,指出绮丽淫靡诗风的危害性,要求诗歌在改俗矫弊中担负起积极的社会作用,这一点是相同的。
总之,李、杜皆学古,但二人有不同。李白学古,得峭峻,词胜于理,有豪气,杜甫兼得峭峻和幽忧不平;李、杜皆学风雅、又兼魏晋,文辞、内容皆善,但他们皆不能学到汉魏古诗之高古,大致是李白学到风雅“清新警策之神”,杜甫学到风雅“沉郁顿挫之体”。
二、李、杜诗论对唐诗嬗变的价值意义
中国诗歌的演变发展是渐进的。《诗三百》自汉代尊为经后深入人心,为万世诗学程法。汉末,《古诗十九首》既加大了诗歌容量,又拓增了诗歌形式。
魏晋文学与经学成功分离,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南朝诗歌无论内容、形式,较之前代皆有长足发展,但绮丽柔靡,骨格不振,影响消极。
唐初,王、杨、卢、骆针对六朝诗风试图革弊而不能尽善,不过他们带领诗歌“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走向江山塞漠”。
初唐诗坛继承“四杰”,大力吹响扬弃前朝诗论号角的当数陈子昂,而接过陈子昂复古革新旗帜,并取得全面胜利的是盛唐李白。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的诗论核心内容主有两方面:一是风骨,二是兴寄。清刘熙载说:“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风”类似“气”,刘勰云“意气俊爽,则文风生焉”,“气”重抒情,指诗歌浓烈昂扬的感情,也即情思浓郁、昂扬向上。骨实气虚,“骨”指诗歌劲建刚直的思想,侧重于义理。刘勰日:“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正是陈子昂所追求的汉魏风骨具体所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从陈的风骨说,可见他是主张声情与辞采并重的,他也不排斥声律、音节的顿挫,这方面对重诗律、求技巧、重内容的杜甫有逗启之功。而陈诗有重骨轻风倾向,其诗更多的是重思想力量,给人有乏情之感,这在李诗中得到纠补。李诗继承陈诗论而并重风骨,他将充沛丰富的情感和昂扬健举的思想完美结合。若说风骨是对诗歌创作的要求,那么兴寄则要求有感而发,是对创作目的要求。刘勰云,“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起情者,依微而拟议”,“兴则环譬以托讽”。可见,兴,指兴发感情,寄,指寄托,兴寄,指有感而作,寓寄托于其间。陈子昂的“兴寄”重在“寄”上,认为诗歌应有为而发,虽拓宽了诗歌内涵,以《感遇》诗践行,并影响到李白《古风》。但陈子昂又与李白不同,陈有为寄托而写诗之嫌,较李诗乏情少韵,陈诗寄多兴少,而李诗兴多寄多,这是李诗对陈诗的继承变化。杜甫诗论和作品中,对陈子昂也非常崇敬,陈诗的寄多兴少,正如王夫之评陈子昂《感遇》云:“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可见陈诗重寄托、议论、说理,其正是杜诗取法对象之一。
李、杜诗歌各有面目,究其源,与二人诗论关系较密。李、杜诗论皆各有所指,太白欲以雅诗救诗道流敝,加之其天才放逸,故李诗自为一体,李诗中才情较多。子美追慕屈、宋之骚,不欲步齐梁绮靡艳丽之风,虽貌似批评齐梁诗风,实是对其吟风弄草、丧失风雅之道的不满。杜转益多师,故众体兼备。杜甫奉儒守业,诗中多纲常风化,实是风雅之道继承者。杜诗以德性为重。杜诗认为后人诗不如前人诗,是因递相祖述,因袭过多,缺乏创新,并提出师法众家之长,方可复归风雅的解决办法。
李、杜诗论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并体现出二人对唐诗演变的不同贡献。陈绎曾《诗谱》说李白诗“格高于杜,变化不及”,其正指出李、杜诗的不同处,李格调高古,实是学风雅汉魏古诗的结果,而杜擅长律诗,善于翻新变古;李诗以古为律,杜诗以律为古;李诗复多变少,杜诗变多复少。李诗欲以复古体诗道,弃绮靡诗风为己任,古体较多,且喜于复古中翻新出奇,其诗风清新自然、意境浑成;杜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近体较多,广学前人而善变,其诗转向写实、写时事、重技巧。也即“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到宋、明以后,可谓开派。”
李白主张的诗风是清真自然,正如王安石所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结合李白《古风》其三十五诗论,可知他是将质朴“天真”、清真自然、浑然一体的诗歌,视为能上承雅颂正声的典范。自然本是道家之语,南朝钟嵘《诗品》用之诗歌,提出“自然英旨”的诗美。迨盛唐李白,则将其变成自己写作纲领,其也成为盛唐诗人普遍追求的、代表盛唐诗美的理论主张,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王之涣、王昌龄、岑参、崔颢,群星璀璨,各领风骚,但他们都共同追求着这种朴素自然、清真平易的诗美。李白也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清真自然诗美主张的,其作品不仅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的天真烂漫、率真可爱,而且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明白如话、浓郁情感,更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比喻夸张、奇思妙想、“以自
然为宗”。“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李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朱熹说:“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从容于法度之中,正是李诗自然之美诗论的实践结果,是高度凝练后的自然,也是盛唐诗歌的极致之美。因李诗“沛然自胸中流出”,故能“不烦绳削而自合”。《诗经》中写景多为起兴,汉魏之景,常景有余而韵味不足,南朝诗歌景物描写虽较细致入微,但情景较乏浑圆统一的步调。而李诗的清真自然之美,不但是以他为代表的盛唐诗歌外化,而且其内涵“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求”,是盛唐诗歌隋景交融、浑然一体的至美意境。盛唐诗歌的“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在李白诗论和创作中多有存在。
杜甫虽也曾经历过开元天宝盛世,但他已预感到盛唐危机四伏、大乱即将到来,安史之乱前,他就以无比敏锐的笔触,深入到民生疾苦和人生现实的层次中,叹惜自己不遇、同情百姓疾苦、批评开边战争、讥讽权贵豪奢,创作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写实名句。不过,成就“史诗”称誉,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杜甫诗作,多产生在杜甫备尝艰辛的后期人生,“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更造就了诗人的成功,从而创作出《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等写实名篇。杜诗写实既体现在叙事、议论及细致传神刻画景物、即小见大等手法的运用上,又体现在“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的炼字炼句上,还体现在其“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追求功力学问的苦学创作上。这已经改变了李白等盛唐诗歌主抒情、重意境,忽略细小景物等特点,并洞开了中晚唐诗歌嬗变的大门。学界多说杜诗是对前人的“集大成”,但笔者感觉杜诗的价值和意义,更在于对中晚唐诗歌的开创之功。杜诗贴近现实、爱国忧民、美丑兼具、沉郁顿挫,其“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清叶燮指出杜诗影响之广'泽及唐后数朝:“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霁,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
要之,李、杜诗论中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指导二人创作的航标和灯塔,是贯穿在他们诗作中的灵魂和主线,而这恰成就了李、杜不同的创作方向和特色。李、杜正是在这种不同诗学思想的指引下,高屋建瓴,瞻前顾后,前疏后导,站在唐代诗歌演变发展的制高点,总结高扬、转折变化了唐诗走向。明于慎行说杜诗“能变化”古人,“不露痕迹”,而李诗对古人“未免有依傍耳”。李诗的“有依傍”,恰是其学古的体现和留存,杜诗的化而无痕,实为变古后的自创新意。李诗总结前人,杜诗引领后代。清蒋湘南亦云:“少陵之诗,变《风》变《雅》之遗也;太白之诗,正《风》正《雅》之遗也。欲复古道,必自太白始……正《风》正《雅》之遗,太白_人而已。”其正道出了“太白志存复古”,承前为正,“少陵独开生面”,启后为变。清陈廷焯更将李、杜诗风的正变,及杜诗之变对后人影响说得明白之至,“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又“自风骚至太白同出一源。”“咱杜陵变古后”,“后世更不能复古。”。也即李诗总结前人而知变,是《风》《骚》精髓延续,是唐诗“正宗”;而杜甫面对李诗对前朝诗风的成功纠正、发展,另辟蹊径,不仅注重对前人诗歌的学习、继承,而且大变,系唐诗“大家”。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李、杜诗论是唐诗嬗变的深层内因和动力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