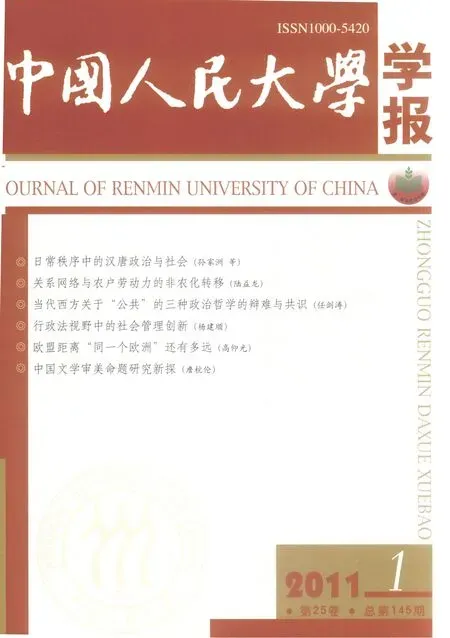中国特色之工业化与中国经验*
2011-10-16董筱丹温铁军
董筱丹 杨 帅 薛 翠 温铁军
中国特色之工业化与中国经验*
董筱丹 杨 帅 薛 翠 温铁军
经典的发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消费者的消费节余形成国民储蓄S,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投资I(即S=I)”,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原则,这一假设前提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得到证明,因为任何工业化都不可能逾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之核心在于:中国在面临工业化启动期资本稀缺的制约而遭遇发展陷阱之际,为化解外部投资稀缺程度为负值的危困局面,能以国家有效动员的高度组织化来打造以大规模集中劳动弥补资本稀缺的制度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内生性地决定不同的制度类型,并且导致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中国经验;原始积累;劳动替代;制度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曾经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对全球的减贫贡献高达67%,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在增加。无论外界怎样热炒“中国经验”,本文作者之一多年来始终坚持强调: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国家工业化”中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同一般,中国经验才堪称“中国特色”。①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温铁军在多次国际交流中认识到,西方先后提出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泛政治化炒作应由政治家应对,中国学者的责任是应对西方从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出发讨论“中国模式”。本文之所以强调“中国经验”,是对包括所谓“中国模式”在内的任何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予以质疑。
温铁军在1996年明确提出“资源禀赋—要素结构—制度前提—路径依赖”的逻辑关系。[1]与之相关的是,早在1988年就开始不断加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的认识和描述。[2]1993年,温铁军指出:“资本原始积累是任何制度条件下的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至于是由国家、抑或资本家来完成,则属于派生的问题”。[3]由于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是制度差异的内因,本文延续20年来的研究,进一步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逻辑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在不可能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获取财富、转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完成内向型自我“剥夺”:一是以公社化为载体提取农业剩余;二是成规模地、准军事化建制地使用劳动力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来替代稀缺程度趋于零的资本。正是几乎覆盖全部经济领域的举国体制,把社会资源资本化对接产业资本经济并创造了对产业资本的国家需求,完成了维护独立主权条件下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第二,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内生地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并对其后的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举国体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经济基础,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起,共同构成了产业资本扩张和反映其扩张需求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第三,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大办“开发区”所致。但实际上,这是由于在国际产业资本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金融资本主导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产业资本路径依赖地依托国家权力快速扩张并进行结构升级,逐渐集中于国家赋权的金融资本和石油、电信等战略资源的垄断性行业,而地方政府“复制”中央政府的“政府公司主义”制度经验赶超推进地方工业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使地理区位成为影响区域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遂有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不同所有制的产业资本都遭遇“条块分割”利益固化的体制内困难,却要靠所有产业资本都参与的体制外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嫁制度成本来化解。这既是路径依赖,也是中国历次经济危机只要能向三农“转嫁”就都“软着陆”,从而保证中国整体工业化进程不中断的核心经验。①关于历次经济萧条中城市向农村转嫁危机的情况,参见温铁军:《危机论——从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危机的转化》,载《经济学周报》,1988-05-15;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1978年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的相关性分析》,载《管理世界》,2008(9)。有关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对于弱化中国转型期制度成本的论述,参见南开大学课题组:《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载《改革》,2009(7)。
因此,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相统一的原则,研究中国近当代经济发展历程,应该把中国如何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作为分析的起点。由此还引申出: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梳理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点,不是中国当代出现的资本扩张和升级,而是前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资本的“自主性”及其极度稀缺时的替代机制。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经验”时最应该注意甄别和了解的。
二、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是“中国经验”的核心
按照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似乎在于近乎无限供给而成本极低的劳动力资源。但亚洲大多数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也都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却没有形成结构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原因在于,拥有充足的劳动力固然可以降低工业化起步时的劳动力成本,但在资金极度稀缺的情况下,这显然无法对储蓄如何转化成投资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又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实际上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所整合,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大多处于产业梯度结构的下端或维持着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单一经济结构。仅从实体经济来看,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不断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致力于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高附加值领域,具有加工制造能力的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和环节,还有一些国家的国际贸易以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矿产品或初级加工品为主。在这个按照所谓“比较优势”形成的贸易框架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质上是通过一系列的过低定价,将本国的能源、资源、环境和劳工福利等各种“租”让渡给了发达国家,而换来的外汇储备却很难形成有效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这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是这些收益大多归于无意发展本国工业的“工头”或“买办”阶层。
从经济发展史上看,工业国家在从前工业化向工业化跃迁的过程中,实行的经济政策都强调“重商主义”,而不是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无论是18世纪的英国,还是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其后的美国、日本,都是在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本国“幼稚产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之后,再借助国家军事干预的国际贸易进行资本扩张的。正如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军事和重工业体系后,于70年代初期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资,随着外资生产力形成对生产关系改变的要求而推行改革开放,逐渐加入国际贸易市场。
综上所述,除小国和特殊国家以外,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不能帮助前工业化国家形成储蓄转化成投资的有效机制;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及其后续的路径依赖缺乏解释力。
三、研究“中国经验”的逻辑与历史起点
关于中国工业化经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数聚焦于1978年改革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少数学者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研究始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近60年的工业化进程,只是她百年来四次追求工业化的一个篇章,从属于近半个世纪来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工业化,乃至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国家工业化的大系图谱。因此,当代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中国如何在一个农民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向金融资本阶段跃迁的发展过程。[4]
中国前两次的工业化,都在尚未来得及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前,就被相对于西欧呈后发崛起之势的日本谋求在亚洲次区域的霸权而发起的战争所打断:第一次是1894—1896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宣告了清末地方军政势力主导的地方工业化的失败;第二次是19世纪30年代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20年代起步的包括“民国黄金10年”在内的民营工业化进程。从世界系统论的角度看,这只是日本复制西方依靠国家暴力掠夺海外财富的工业化模式而已。
中国1949年以来的两次工业化,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发工业化国家对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中,也同样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左右。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70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美苏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5]一方面,这与日、韩、越等东亚国家在战后毫无例外地实现了以平均地权为国民动员基础,在短期内完成国家政治建设之后的工业化起飞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当外国投资于50年代末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中断乃至人道主义灾难,而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成了“惊险的一跃”,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 (或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完全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是“中国经验”得以成立的独特之处。
四、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与机制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演变
事实上,在1949年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最初曾试图通过新民主主义道路来逐步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工业化;中国政府向苏联争取援助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地缘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同意出兵朝鲜才促成了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才有了实质性进展。苏联在1950—1956年向中国援助了合计达54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投资①另有一说为66亿旧卢布,参见沈志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真相》一文对于贷款数额和用途的讨论,http://history.news.163.com/0910319/08/540NL53700011247.html。。随着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大量引进,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且主要按该体制的要求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①参见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另据财政部历史资料,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到当月底,全国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这意味着通过革命战争形成的单一政党的集中体制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生产要素的“政府所有制”:(1)土地。1954年2月,中央对地方“以土地换取建设资金”的做法作出批复:“凡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占用市郊土地,不必采取征收土地使用费或租金的办法。”这意味着城市和工业占用的、能够产生高收益的土地所有权变性收归政府 (农村土地所有权1956年以后归村集体),政府得以直接占有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②与土地资源无偿取得相关的则是50年代中期的一轮“圈地热”。“据1956年对武汉、长沙、北京、杭州、成都和河北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几年间这些地区共征用10.1万亩土地,浪费用地达4.1万多亩,占总数的40%以上。其中长沙市征用了2万多亩土地,就有1.6万多亩浪费。武汉市33个建设单位征用9 000多亩土地,长期闲置不用的就有2 600多亩。”参见周怀龙:《乘风破浪正当时——新中国60年土地市场发展回眸》,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11-02。(2)劳动力。政府几乎封闭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借此集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劳动力资源于国家基本建设,得以占有全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3)资金。政府绝对垄断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所有金融部门,得以占有铸币税和经济货币化的增值收益。
这样,基本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就被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政府所有制为财产基础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 (government corporatism)”经济。后来,“政府公司主义”在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作用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时间,又有利于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的制度类型。促成这种集中体制形成的,正是苏联提供的并非无偿的援华贷款由中央政府主导大规模集用于工业化原始积累。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和地方工业化的兴起
西方经济学把要素的稀缺性作为市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条件,其中资本处于组织要素配置的龙头地位,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对”稀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中辍投资之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本的“绝对”稀缺。
孤立地看,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突然中止对华投资是在中国拒绝其继续对华实施军事控制的要求后采取的应急行动。进一步分析,50年代末苏联完成重工业体系建设之后,客观上要求加入西方贸易体系以提升本国产业结构,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下降将是必然的。[6]所谓国际社会,其实是一个大国强国唱主角的舞台,边缘、半边缘国家是“蝴蝶效应”的承受者。苏联表现出类似“宗主国”地位③之所以称其为类似“宗主国”,依据的是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论断。,以中止所有援建资金和技术的极端方式调整对华的外交政策,这对“一边倒”地倚重其贷款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变故,中国不仅经济上遭遇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难以实施的困境④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书中指出,“二五”计划实际上只有一些控制数据而完全没有执行;“三五”计划则由于“三线”建设等情况难以列入计划而没有制定出来。,而且政治上也面临两个方面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出于“核保护伞”的需要而不能马上公开中苏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得整肃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国家上层建筑;另一方面,要继续工业化原始积累,但事实上又不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主办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军重工业。对外,还需提前偿还苏联对华的军事和经济建设贷款。
投资中辍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是残酷的,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比如,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赞比亚的外资铜矿企业纷纷撤离,导致赞比亚国内失业率攀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有国家因外资突然中止而爆发严重的国内冲突和大面积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中国,这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认同、并于1958年推进“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替代方针,将财政、金融和部分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的原因。①根据财政部的历史资料,1958年3月上旬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讨论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物价、商业、教育等方面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重点是实行地方分权,把若干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4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4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逐步实行“双轨”的计划体制,以处理“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放松了对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查管理。4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收入项目和分成比例改为基本上固定五年不变的通知》,取消了原定基本上3年不变的规定。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把工业、交通、商业、农垦各部门所管辖的企业,全部或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推进地方投资为主的地方工业化,发动人民公社办“五小工业”是这种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一些省份1958—1960年三年地方财政的基建开支和上缴中央的企业收入之和,是1957年的10倍以上。中央政府在依靠加强对地方的汲取,勉为其难地维持苏联援建项目的后续投资3年之后,于1960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际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工业化投资由外资主导转为完全的内向型自我积累。1961年中央又提出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新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中,总体上以中央工业化为主,但客观上存在着1958年之后中央放权于地方政府的地方工业化阶段。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在历史上就是幅员辽阔的中国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的地方分权,是中央政府在苏联投资中辍后由于难以维持原有“集权”模式而被迫进行的制度变迁。②80年代的地方分权改革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因财政巨额赤字难以正常运行而进行的以“甩包袱”为实质的制度变迁 (详见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1978年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的相关性分析》,载《管理世界》,2008(9))。而80年代一度举世瞩目的农村工业化,其渊源正是1958—1960年这轮地方“大办五小工业”。
(三)资本稀缺条件下地方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机制
一般而言,产业资本运动需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 (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商品资本(产成品)三个阶段,这是西方企业在产业资本阶段的主要运行模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7](P44)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货币资本通常是二者之间的结合剂,而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地方工业化,在外资撤出、内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是如何完成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的?换言之,是什么替代了资金在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机制?在不能如先发国家向海外转嫁制度成本的情况下,中国是如何化解工业化进程中的负外部性的?
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应对上述问题的相对有效的经验,就是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 (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③在“劳动力资本化”中形成的职工民主 (如鞍钢宪法归纳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与70年代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从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生产线管理,是两种因本质不同而严重对立的企业治理模式,二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治理难、劳动者消极怠工等问题普遍发生,在1978—1979年因财政严重赤字的危机导致的“放权让利”指导思想之下,催生了80年代中期起步的实质性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微观方面以经理承包制、奖金制和宏观方面的“拨改贷”、“利改税”等方式,承认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主导地位;之后,势所必然地出现90年代以来宏观方面的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化、货币化进程加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本人格化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者共同追求占有资本化收益的利益最大化取向所造成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毕竟维持了工业化进程不中断和新政权稳定。在此期间,替代资金要素在社会大生产中发挥龙头组织作用的是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和均分制的土地改革形成的国民动员基础与传统村社的社会资源再资本化形成的社会资本。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S=I。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经济高速增长,但也有大量研究指出,新中国从建国到改革前30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令人瞩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52—198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6.25%,1979—200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9.69%(见图1)。

图1 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与路径依赖
50年代末的中国地方工业化进程中,没有条件及时建立工业化学习机制的地方政府唯一能参照的历史经验,就是苏联大规模投资期间的高增长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于是,作为“制度路径依赖”的结果,出现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地方工业化“大干快上”遍地开花,这是“大跃进”造成极大损失的一种过于单薄的解释,或者也可轻描淡写地归因于地方工业化支付的“学习成本”。①当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参加了“大炼钢铁”的工业化劳动,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在回忆录中记载:“1958年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了9 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而离开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援,地方干部根本不可能懂得如何发展工业,这段时间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高成本、高浪费”的,这不只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客观上也造成了后来的农业粮食减产。
虽然这种地方主导的二次工业化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的代价都比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的工业化更大,但这些代价基本上不可能由成千上万个地方政府承担,而是被转嫁给了社会大众,也由此导致了长期的低工资、低消费、低福利 (及后来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这一成本之所以能够相对温和地转嫁而不至于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又恰是由于东亚社会传统小农家庭不计成本的劳动力投入机制。此后,关于中国“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很少注意分析这种“非典型”发展主义增长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也几乎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制度成本的实质作为后续改革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据。
特别值得国际比较学者进一步研究的是: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维持财政金融双赤字 (见图2)长期化之下的稳定,更不可能发展。

图2 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财政赤字及金融机构存贷差
五、基本结论
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要求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可知大多数著述都强调投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并以此作为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模型、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的大推进理论等,虽然学科派别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发展主义的典型的“以资为本”。这些理论都假设投资I来源于国内的储蓄S:整个社会中有消费者和厂商两大部类,消费者的消费节余形成国民储蓄S,S转化为生产者的投资I,若I在抵补设备折旧之后能使生产增加,全社会就会实现经济增长。这些理论关注的都是如何使投资I实现最大的产出效率,如对均衡与不均衡型增长的研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变动的关系,制度环境对于投资收益的影响等。主要差别在于不同理论侧重的经济增长机制不同,越往后来的理论,在资本 (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上雕琢得越发“精致”。因此,S=I是“理解所有增长理论的基石”。[8]
这些解释体系无疑有完整的理论逻辑,但要与真实的历史经验吻合,达到“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统一”,才能检验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路径对于后来者的可复制性,这就需要对模型中的S和I的内涵重新考察。
人们都知道,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S并非初始和主要来自于工业化国家内部的消费节约,而是来自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韦伯语),即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的海外拓殖、掠夺和国家暴力干预的殖民地贸易。同样,生产能力增加(包括后来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是I的主要内容,相当多的投资用于军事领域——西方国家国内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形成和扩张的每一步,都与其海外帝国主义密不可分。随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对资源、原料和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私人资本主导的自由竞争上升为国家垄断竞争,I甚至由生产投资为主转变为战争、军事相关投资为主,二战后这些军事投资转向民用而成为当今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而冠之以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名义。比如欧洲的铁路建设之迅速壮大是因为欧洲战争,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最早也是缘于冷战时期的需求。[9]
上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共性“经验”,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0]。此类资本原始积累一般都有公然使用国家机器反人类地暴力犯罪的经验过程。因此,这一过程中 S、I的内涵应该被完整地表述为 (见图3):

一般增长理论模型首先建立在“孤立国”的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的假设上,继而再纳入国际贸易变量进行拓展讨论。但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中,S=I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并非是可以在个别国家实现的内部宏观经济均衡[11],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跨国非均衡”,即先发国家的本土投资、生产和海外殖民地资源、市场组合在一起,才能在依托国家暴力的条件下形成完整的经济循环。
这种殖民主义的发展方式在二战后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但剩余流向依然如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名义主权上摆脱了殖民化统治,但实质上其经济和政治仍然难以挣脱“新殖民化”或“后殖民化”的发展陷阱。①与人口增长或历史预期理论中所谈的“陷阱”不同,这里的“发展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冀图依靠工业化摆脱被殖民化,却在追求工业化中陷入被先发工业化国家“后殖民化”、“新殖民化”的状况。参见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三个发展阶段,强势国家为最大化获取收益而主导了三次大的制度变迁②参见温铁军、董筱丹、杨殿闯:《致贫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经验研究》,工作论文,2009。关于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的矛盾转嫁,王建、王小强等做了很精辟的分析。参见王建:《货币霸权战争——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王小强:《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载《香港传真》,2008-12-26。;根据制度歧视模型[12],强势国家占有较多的制度收益,却只承担较少的制度成本;弱势国家恰好相反,要承担较多的制度成本却少有制度收益,每一次变迁都毫无例外地强化了以发展中国家被剥夺为本质的国际秩序。
综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是不可能复制先发工业化国家殖民扩张的历史经验的;其次是国内经济剩余持续外流,使得可用于本国工业积累和投资的资源少之又少;其三,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从传统部门提取剩余,要将有限的剩余集中为成规模投资,必须解决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问题,总体剩余越少,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越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因缺少足够的原始积累S而普遍依赖外资,然而,发达国家数百年的殖民化统治使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形成路径依赖,有限的外资援助难以形成有利于推进其工业化进程的投资 I。所以,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恶化了全球贫困状况。
迄今,原住民人口1亿以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形成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①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过亿的有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其中只有中国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非洲至今还没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拉美国家中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人口过亿的只有巴西和墨西哥,但其原住民占比很低。依靠国际地缘战略中的特殊优势接受发达国家投资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普遍疆域狭小且地理位置特殊,对于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工业化路径不可复制。而中国之所以能用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中国的原始积累与西方人之最大不同,在于这个资本化过程是大多数劳动者被国家这个资本实际占有者以‘继续革命’名义动员因而大部分自觉、少数不自觉地参与其中的特殊形态”。[13]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国家资本属性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私人资本属性,在动员民众几乎无偿地“被集中”投入属于自己的劳动的作用上,确实不同。
若然,则如果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原始积累阶段没有建立“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属性,就意味着没有起码的制度条件来动员民众低偿或无偿地集中投入成规模的劳动,也就不可能在大众不得不忍受低工资、低消费和低福利的时候,以劳动力的规模使用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也就没有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可能。
同理,这种“中国特色的基本制度”的形成过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很可能是那些同样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一般发展中国家 (例如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大部分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如果从制度文化层面看,在近代殖民主义全球化中相对处于非主流的、几乎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了的东方文明,由于早年地处相对于欧洲而言的“远东”,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且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中国人不仅没有在殖民化时代由于西方列强几近灭绝而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两个方面的近现代国家政治建设——通过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争——得到加强的集中体制建设中,得以在维护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一是群体理性,借助漫长农业文明历史遗产中的核心——群体文化,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外部性问题”;二是农户理性,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具有的“不计代价的劳动力组合投入”的机制来缓解突然出现的资本极度稀缺问题。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构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易于形成以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为国民动员工具、更快地进入工业化的条件。
在阿瑞吉看来,“东亚的模式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并不像西方的发展模式那样,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有如此根本的关联。对于全球南方来说,这一模式有可能提供一种可供模仿的典范,而西方模式并不能做到这一点。”[14]笔者认为,以上从与历史文化传承相关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到微观经济主体内在机制的中国特色,正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的“比较经验”之所在。但愿这些“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使中国不再是“原教旨主义”的S=I模型的孤证!
[1] 温铁军:《两个基本矛盾制约下的三农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6(3)。
[2] 温铁军:《危机论——从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危机的转化》,载《经济学周报》,1988-05-15。
[3] 温铁军:《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载《发现》,1993年秋季号。
[4][13] 温铁军:《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载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 温铁军:《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成本和收益》,载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 孙家恒、孙秀峰主编:《苏联对外经济贸易》,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7]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11] 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 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董筱丹、温铁军:《致贫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不对称性分析》(致贫经济学系列论文之下篇),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
[14] 海裔:《和安德森关于〈亚当·斯密在北京〉的通信》,载《中国经济》,2009(8)。
State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a's Experience
DONG Xiao-dan,YANG Shuai,Sit Tsui,WEN Tie-ju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for Sustainabilit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ll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theories share a common assumption that could be formulated as“S=I”,which presumes that consumer surplus i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savings(S)and that when S is turned into producer investment(I),national economy grows.However,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primitive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asn't accomplished just through domestic amassment.It means that the assumption of S=I doesn't apply with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of“the origin of history as the origin of logic”.Because any industrialization cannot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how to carry out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What is peculiar in China'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that when encountered a sudden scarcity of capital,she managed to mobilize a highly organized society effectively and to build up an institution based on the intensive labor substitution of capital.Therefore,China was able to get out of the crisis,and finally succeeded in accomplishing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t is the specific nature of China's experience.We thus argue for an institutional derivation that different institutions come from differ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d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path dependence for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fterwards.
China's experience;primitive accumulation;labor substitution;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董筱丹: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讲师;杨帅: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薛翠: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武京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的原因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教育部应急课题 (2009J KJR023);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首都经济学科群建设项目 (2010—2012);中国人民大学“985”三期项目“中国农村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本文是温铁军组织的关于致贫经济学 (亦称“穷人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之中篇。上篇题目是“致贫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经验研究”。初稿是温铁军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年组织的学术论文之一,原是为上海复旦大学与香港《开放时代》杂志联合于2007年10月30日召开的研讨会准备的论文。后应印度友人之约,于2007年11月改写于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阿玛达巴德,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博士参与观点讨论并对修改予以协助;再次修改是为了参加北京大学2008年“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此为第三次全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