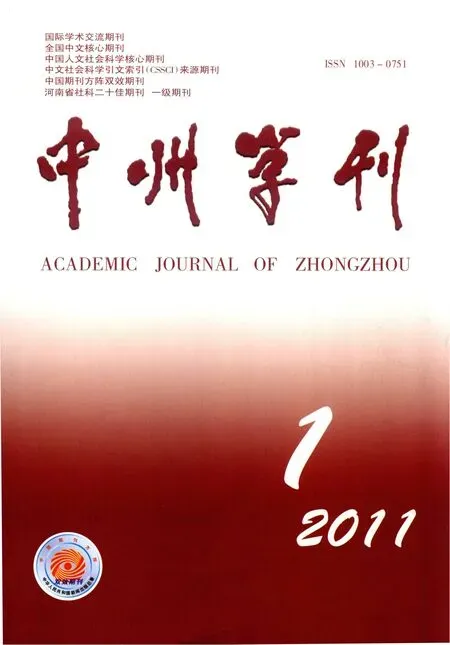生命来源观:中国家庭养老内在机制新探讨
2011-10-09谢楠
谢楠
生命来源观:中国家庭养老内在机制新探讨
谢楠
“血亲价值论”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是由一种存在于观念和价值层面的报恩意识所驱动的行为模式。从“血亲价值论”的论证思路及结论来看,血缘只是子代对父代生成报恩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儒家文化圈中所奉行的“父母于子女有恩论”的生命来源观则是报恩意识形成的关键。生命来源观是一个族群对个体生命源出何处的一种文化认定,是对父代生育子代这种生命延续状况的文化理解。社会转型时期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将改变传统的生命来源观念,从而影响子代对父代养育之情的认可,进而削弱子代对父代的报恩意识,最终将深度瓦解中国家庭养老的生存机制,使中国家庭养老陷入新的困境。
家庭养老机制;血亲价值论;生命来源观
一、文献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延续了几千年,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已然成为东方文化的特色。费孝通先生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分析养老问题,提出与西方“接力模式”所不同的“反馈模式”①。在西方社会中,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义务。而在中国,子女却对父母负有义不容辞的赡养责任。西方“接力模式”与中国“反馈模式”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后者存在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子女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会出现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是利益的驱动还是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驱动?在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中,是否存在超越社会经济发展制约、长久维持的文化理念?对此,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国外学者多以“理性经济人”为理论前提来分析解释家庭养老。在西方老年学理论中,家庭养老属于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范畴,反映的是代际关系,其代表性理论包括权力和协商论(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互助论(mutual aid/exchange model)和合作群体论(altruism/corporate group model)。②运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解释中国家庭养老机制,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即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的行为很难说是一种完全依靠内在道德规范驱使的行为和完全利他的行为,代际间交换客观上的广泛存在确实在家庭养老的延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存在着固有缺陷,即缺乏对个体价值观念等超越性理念的考虑。事实上,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长期延续与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价值观念和家族延续的人生追求密切相连。
国内学者在家庭养老内在机制方面存在交换论、功能论、生产方式论、文化论等观点。我国早期社会学家潘光旦通过比较中西方伦理道德的差异来分析中国特有的养老机制。他认为西方伦理的特殊性在于用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来理解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关系,但中国社会的伦理观中并无此内涵。“中国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子代对父母的赡养和照顾,应该大都是处于亲情和情感的自然流露。”③也有人提出责任内化论,认为数千年来孝道的弘扬,已将关于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完全内化为中国人人格的一部分,成为人人认可的一种责任。④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姚远教授从家庭中特殊的血缘关系出发提出的血亲价值论。这是一种用血亲价值观点来阐释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养老模式的理论,认为血缘联系的报恩意识正是形成家庭养老机制的先天动力的关键所在⑤。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家庭养老模式内在机制的认识。然而,就研究视角而言,这些研究大都没有从家庭养老所内含的价值和伦理基础来讨论问题,很难揭示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深刻文化内涵及其意义。少数研究从文化视角对养老问题进行研究,但大都停留在思辨的层面。比如“血亲价值论”指出家庭养老运行的基础是血亲价值。“血亲价值论”的提出对中国家庭内在养老机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家庭养老内在机制的认识。其一,“血亲价值论”区分了中国家庭养老的两个层面——价值观念层面和行为实践层面:前者主要包括子代基于亲子血缘所产生的对父代的报恩意识;后者指子代为父代的养老提供的各种资源。这种区分使我们能更清晰地解析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分析其中容易变化的部分和相对稳定不变的部分。其二,“血亲价值论”通过将子代对父代的报恩意识构建在独特的血亲联系上,从而较好地回答了社会交换论中所无法回答的“为什么代际之间的相互支持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问题。其三,“血亲价值论”通过将伦理价值建立在血缘上,论证了家庭养老模式中包含的超越性价值理念,清晰展示了家庭养老的东方特色。但是,笔者认为,血亲价值论在论证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对中国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进行新的思考。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二、“血亲价值论”解构
1.“血亲价值论”概述
血亲价值观是指一种以血亲利益为人生价值的观念,在此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子代将赡养亲代视为人生职责。其中蕴含两种动力:先天动力和后天动力。前者是由于亲代与子代之间的血缘联系在具体生活中深化为一种共同的情感,在此情感上子代自然会产生一种报恩意识;后者则是反映出一种人生价值观所造就的动力。这种价值观是子代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接受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教化”(父辈的言传身教、社会的教化和舆论监督以及国家的制度),成为“承担养老责任的自觉者”。“血亲价值论”包括四大特征:血亲核心性、非均衡性、超经济性、亲代主导性。⑥
2.“血亲价值论”的论证思路及缺陷
姚远教授提出的“血亲价值论”的论证思路为:第一,亲代与子代由于血缘关系组建了家庭。“生物性的血亲关系,既是家庭存在的基础,也是家庭代际关系确立的基础。”⑦第二,亲代与子代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深化了情感。第三,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子代通过对父母生身之恩和养育之恩的认定,逐步形成一种报恩意识。第四,这种基于血缘联系的报恩意识正是形成家庭养老的先天动力的关键所在。“血缘联系、情感建立、报恩意识反映了先天动力形成的三阶段”⑧,其中报恩意识是形成家庭养老先天动力的关键。如下图所示。

对于这一论证思路,本文认为,它无法解释在中西方家庭中都存在着血亲联系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家庭才形成独特的“报恩意识”的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在基督教文化圈还是儒家文化圈里,亲代和子代都是依靠血缘关系组建家庭,同时亲代与子代也几乎都是在共同的家庭中生活,自然也能够深化亲代与子代间的情感。但为什么西方的血缘认同薄弱而东方这种血缘认同强烈且还对子代形成一种报恩意识呢?简言之,为什么血缘联系在中国就会形成报恩意识呢?这其中应该存在着论证的跳跃性。笔者认为,连贯上述血缘、家庭与报恩意识之间的关键就在于儒家经典学说中所提到的对个体生命来源的论述,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⑨。
三、“父母于子女有恩论”与生命来源观
1.“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是子代对父代形成报恩意识的伦理起点
如前所述,血缘与家庭都是客观存在的。由血缘形成家庭、父代与子代共同生活深化亲子之情,这是东西方家庭发展史上都出现过的状况。唯有生活在东方家庭中的子代产生了对父代强烈的报恩意识,而西方家庭中则没有出现这种报恩意识。对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受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及认识方法的限制,同时也受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客观自然层面的血缘联系和家庭环境与意识层面的报恩意识之间存在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影响着子代对亲子之情的理解,促使子代形成报恩意识。在东方文化中,我们将这种影响人们理解血缘关系的观念称之为“父母于子女有恩论”。

“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是东方儒家文化圈中较为普遍的亲子观念。在一些关于亲子关系的传统书籍中,存在大量涉及父母生儿育女艰辛的内容。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欲报之德,昊天罔极”⑩。《劝孝词百章》说,“亲亲孩儿儿养亲,算来也是一轮回。如何我养双亲志,不及双亲养我身”[11]。在儒家文化圈中,人们普遍认为,个体由父母所生所养,生命由父母所赐,父母于己有莫大的恩情。这种观念通过父辈的言传身教、社会的教化和舆论宣传,深深植入子代的内心,成为其信奉的伦理规范。伴随着生活中子代与亲代感情的逐步加深,子代心中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报恩意识。只有个体真正认为自身来源于生身父母而非某种超验神的创造,才可能对父母的生身之恩心怀感恩之心;只有个体真正感受到自身的成长应归功于父母的含辛茹苦的奉献而非某种超验神的恩赐,才可能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报恩之情;只有个体真正认为父母对自己的养育是亲情的体现而不仅仅是投资,才能对晚年父母心有赡养之责。可见,“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深刻影响着子代对父代养育之情的认可,是子代对父代产生报恩意识的伦理起点。
2.“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是中国传统生命来源观的体现
(1)生命来源观的含义。“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个体生命源于父母这种自然状况的一种文化理解,反映出了中国传统伦理中特有的生命来源观。生命来源观是一个族群对个体生命源出何处的一种文化认定,是对“我是谁”这类关乎生命存在问题的形而上哲学思考,是对生命延续这种自然状况的文化理解。生命来源观是人们在面对有限生命时,为消除紧张和恐惧感所产生的一种观念。不同的族群对自身生命源于何处自有不同的解释,但“慎终追远”几乎是每一个族群都会进行的行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生命来源观的表述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一种典型的祖先崇拜。我们崇拜祖先是因为祖宗是我们生命之所出,是生命之源,而子孙则延续了祖先和我们的生命,实现了生命的永恒,消除了我们因生命有限而产生的心灵的紧张和恐惧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祖先崇拜回答了“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人生存在问题,同时我们通过子嗣延续,回答了“我将往何处去”这类关于生命如何超越有限、实现永恒的问题。宗教和哲学形而上意义的生命来源观在现实观念层面的反映即强调“父母于子女有恩”——父母赐予子女生命,没有父母便没有子女的存在,因此父母之恩大于天。可见,“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是中国传统生命来源观的重要体现。
(2)中西方在生命来源观上的典型差异。生命来源观是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族群认同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基础是文化认同,包括情感归属、社会分层、政治组织、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认同形式的多样性促成了认同层次的产生。认同的最基础部分是阶级、亲属关系、村落,继而是本地、方言社区、省,最高层次是什么人(people),然后是社会的或民族的大区域。[12]无疑,生命来源观属于族群认同中最基础的部分,它形成族群对自身来源的认同。世界范围内的华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注重修宗谱、族谱,在重大节日时隆重祭祀祖先。这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上帝信仰构成鲜明的族群差异。发端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西方文化,在回答“我是谁”时,将个体的生命起源置于“神创论”的体系下。与中国传统中将生命起源置于祖先崇拜之中不同,西方人将上帝作为其在“天上的父”。如果说中国人以祖宗为神圣的话,那么西方人则奉上帝为至上和神圣。西方人认为,上帝的价值是第一位的,父母的价值是第二位的,人伦关系以神伦关系为基础,爱上帝要胜于爱父母和家人,一生都要对上帝负责。而中国人则一辈子都要对父母和家庭负责。[13]
(3)中国式“生命来源观”的产生原因解析。中国式“生命来源观”的产生原因是多重的,包括社会原因和哲学伦理原因。首先,中国式“生命来源观”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中国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形成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个体的日常生活长期处在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之中。个体只是存在于血缘亲属关系为经纬的关系网中的某一节点。个体无法也无力从某种超验的神秘力量中探寻而只能从日常的体验中获得“我是谁”以及个体存在的意义,即每个个体都是由其母十月怀胎而生。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体验中获得个体存在意义的方法途径正符合孔子儒家学说的安排和要求。“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世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时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的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这一点以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半准宗教的角色,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较为罕见的。”[14]可见,中国式生命来源观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适应了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意义的塑造具有独特性。中国的传统哲学在论证人的存在意义(即“什么才是人”)时,十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及对自身生物性的超越性,不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而反复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以通过论证“人禽之别”塑造人的意义。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人禽之别的意义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只是把人只看作自然的人,而着重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这区别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有社会的人文的生活”[15]。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人有天赋的仁义理智的四段,其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6]荀子也将“人禽之别”作为重要问题提出。“人之所以为人,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17]在此,中国传统哲学便将父母对后代的抚育进行了哲学意义和伦理意义的提升,以此与自然界禽兽之间的自然抚育分开,赋予了其更多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
四、生命来源观的嬗变与家庭养老的新困境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不是一种利益交换机制而是由一种存在于观念和价值层面的报恩意识所驱动的行为模式。血亲价值论认为这种报恩意识根植于亲子血缘之中,但是血缘联系和共同的家庭生活并不必然使子代产生报恩意识,血缘只是报恩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更准确地说,子代对父代的这种报恩意识生发于自然亲子血缘,由社会观念和社会环境所塑造,其中社会观念和社会环境起决定性作用。观念的重要性在于影响人们对自然状况的理解,使其对同一自然状况产生不同的理解。体现着中国传统生命来源观的“父母于子女有恩论”,影响和塑造了子代对父代的报恩意识,成为子代对父代形成报恩意识的伦理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成后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观念一旦形成便具有长时间的生命力。但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会使原有观念受到侵蚀。20世纪后半时期,随着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迅速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受到了强烈冲击,“父母于子女无恩论”重新兴起,家庭养老陷入新的困境。
1.生命来源观的嬗变与“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的兴起
针对父代生育子代这种生命延续的自然状况,伦理思想史上存在一种与“父母于子女有恩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它对“个体生命来自父母”进行了重新解读:父母生育子女首先是为满足自身需要,是父母自我意愿的表达,因此父母自然应对子女的成长负责,而父母于子女并无恩情。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孔子的直系后代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18]其意是父与子并无什么恩情,究其根本不过是父代满足自身情欲的结果罢了。子女与母亲也无什么特别,不过就像把东西装在瓶子里,拿出来就分开罢了。现代著名学者胡适也认为,父母生子不曾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条生命,因此父母于子无恩,只有抱歉,而且应对子女以后在社会上的行为负一部分责任。[19]这种“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在前现代社会不过是一种极特殊的思想现象,并不具备典型意义。但当中国社会开始迅速的社会转型时,这种“父母于子女无恩论”便以种种变形大行于世,它伴随着个体日益从血缘亲属关系为经纬的关系网中挣脱出来的趋势,成为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父母于子女无恩论”与家庭养老的新困境
中国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价值观念层面,子代对父代有报恩意识;二是行为实践层面,子代赡养父代的行为,为父代养老提供各种资源。以往针对我国家庭养老弱化有很多论述,但这些论述大都属于行为实践层面,阐述的是因客观原因而使行孝有心无力,或是因为个人价值趋向上的多元化而导致个体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不再将奉养老年人作为自身的人身追求。而“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对人们的影响则意味着人们在价值观念层面上逐渐放弃了对父代应有的报恩意识,在观念层面上逐渐接受了或者说默认了“父代对子代天生负有养育责任,子代无需反馈回报父代”的看法。这种观念层面的变化比行为上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它将逐渐消减子代对父代养老的责任感,使得中国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彻底终结。
据此,我们对农村家庭养老的许多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为什么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的老年人(特别是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有可能陷入“养老足球赛”(子女之间相互推卸赡养责任,将老年人当皮球一样推来踢去)的困境?这是典型的“旁观者效应”[20]:当有人需要紧急救助时,目睹此情景的人数越多,任何一个人出面相助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难以清楚计算个人责任。无疑,这些子女或许已经淡忘或者忽略了父母对自己曾经的生身之恩和养育之恩,只将其视为父母当年理所应当的责任。当老迈的父母不再能为他们贡献价值时,他们不愿分担养老的经济负担或者因无法精确计算彼此应承担的经济负担而宁愿选择漠视或者相互扯皮。
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时期,子代对父代这种基于血缘的报恩意识依旧存在,因此家庭养老能够在生产方式变化后的社会中继续生存。但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当下,子代对父代的报恩意识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削弱。这已危及到家庭养老的根基。《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强调要逐步建立健全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努力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可见,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家庭都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为重要的支持之一。我们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稳固、保持并发展这种可贵的报恩意识,使家庭养老能够在生产方式变化后的社会中继续生存。
注释
①费孝通:《家庭结构变迁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②Yean-Ju Lee.Sons,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9,No.4(Jan.,1994),p1010-1041.③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4—238页。④张新梅:《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人口学刊》1999年第1期。⑤⑥姚远:《血亲价值论:对中国家庭养老机制的理论探讨》,《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6期。⑦⑧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第80、82页。⑨胡平生:《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1—2页。⑩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0年,第626—628页。[11]向燕南等:《劝孝俗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页。[12]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13]肖群忠:《孝与友爱:中西亲子关系之差异》,《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1期。[1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15]钱逊:《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1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73页。[17]安小兰:《荀子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72页。[18]《后汉书·孔融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19]胡适:《关于“我的儿子”通讯》,见钱理群:《父父子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5页。[20]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1]杜亚军.代际交换—对老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90,(3).
[2]范成杰.代际失调论——对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种解释[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3]洪国栋等.论家庭养老[C]//石涛.家庭与老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4]刘爱玉,杨善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0,(3).
[5]米峙.影响北京市女儿养老支持作用的因素分析[J].西北人口,2007,(1).
[6]王爱珠.从经济看代际矛盾的转移和化解[C]//石涛.家庭与老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7]王冰,徐云鹏.养老与家庭[J].人口学刊,1986,(2).
[8]熊跃.需要理论及其在老人照顾领域中的应用[J].人口学刊,1998,(5).
[9]熊跃根.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老人照顾[J].中国人口科学,1998,(6).
[10]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J].人口学刊,1995,(6).
[11]阎卡林.关于我国一些地区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及对策[J].人口学刊,1983,(4).
[1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3]张文娟.儿子和女儿对高龄老人日常照料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6,(6).
责任编辑:海玉
C913.6
A
1003—0751(2011)01—0125—05
2010—08—24
谢楠,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