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上的独舞
——论“个人化写作”思潮
2011-10-09陈桂芳暨南大学中文系广州510632
⊙陈桂芳[暨南大学中文系,广州510632]
悬崖边上的独舞
——论“个人化写作”思潮
⊙陈桂芳[暨南大学中文系,广州510632]
“个人化写作”思潮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潮流,它以晚生代作家为主力军,呈现出一种贴近平民现实生活、注重表达个人生存体验的创作倾向。它的兴盛加速了世纪末当代文学的转型,但由于在个人化方面日趋极端的发展,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令人触目的无意义性和狭隘性。
“个人化写作”特征晚生代作家群
“个人化写作”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是评论界有关世纪末文学创作讨论的热点之一。个人化首先是作为一种写作立场而出现在小说、诗歌、散文等诸多领域的,主要以毕飞宇、朱文、陈染、林白、沈浩波、尹丽川等晚生代作家的创作为代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参与其中,这种立场对文学创作所形成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并渐渐转变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最终加速了世纪末当代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本文试从思潮的视点切入,通过对“个人化写作”的概念及过程的分析和界定,阐述其特征,品评其得失。
一、概念界定与过程溯源:众声喧哗中的独自吟唱
作为上个世纪末当代文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潮流,“个人化写作”刚一崭露文坛,就引发了诸多争议,而对其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都未形成定论,甚至连对其溯源及过程厘定也众说不一。尽管“个人化写作”思潮已经褪去了昔日的斑斓色彩,但它对文学史及文学创作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有必要对“个人化写作”的内在涵义及过程予以澄清和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个人化写作”的定位,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扩大了其含义范围。比如有的论者通过对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诗歌的分析,认为他们这种抒发个体情感的创作就是“个人化写作”。①这一溯源显然忽视了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个人化、欲望化的内在特性。二是窄化了“个人化写作”思潮的覆盖范围。有些论者就认为只有卫慧、棉棉的创作才是真正的“个人化写作”,而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的写作充其量只是其滥觞,而在论述时更是只字未提毕飞宇、朱文等人的创作。②三是将“个人化写作”区分为广义、狭义两类。有的论者细心地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观照“个人化写作”,认为从广义上而言,它是指“那种疏离了统一的思想规范和艺术规范,以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作为特征的一种写作方式”;而从狭义上看,则特指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以表现女性的身体隐私和生活隐私为特征”的女性文学创作现象。③这种定义虽然看上去较为全面,但是它却只是停留在文学创作现象的层面来观照“个人化写作”,而没有将其上升到思潮层面。
“个人化写作”思潮以晚生代作家群的创作为代表,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鲁羊、东西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创作中描绘个人的现实生存体验,并杂糅了自我的审美感受和思考,始终恪守个人价值理念;第二是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与第一阶段作家不同的是,她们在创作中普遍将视角圈定在女性人物身上,用灵动精细的笔法刻写女性生存的隐秘感受,以欲望推动女性意识的觉醒,用理性反叛男权话语世界;第三是卫慧、棉棉们的“身体写作”及以沈浩波、尹丽川等人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和“胸口写作”,他们彻底抛弃了在前两个阶段的作家创作中尚有余温的理性原则,放纵躯体及物质的欲望,追求一种“肉体的在场感”,从而将“个人化写作”带向了危险的境地。这三类侧重点不同的文学创作现象逐渐扩张,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从中抽象出来的“个人化”作为他们创作的共性,也就由一种话语实践转变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潮。
因此,所谓的“个人化写作”思潮,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之下,以晚生代作家群为主体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在个人的自我经验与记忆的基础上,以个人的视点去观照历史及当下生活,用绝对写实的笔法书写来自个人的生存体验和内心感受、宣泄个人的内在欲望冲动,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及个人话语的表达,由此形成的一股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文学创作潮流。
二、特征表述:一个人在路上
“个人化写作”思潮内部各个阶段作家的创作有其不同的个性,但是紧紧围绕个人化这一中心的立场又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多方面的共性特征,如描绘个人的生存现实、采用个人化、欲望化叙事等等。因此,“一个人在路上”无疑是对其共性的最佳表述。
1.“生活边缘”:世俗生活碎片的记录
“个人化写作”思潮影响之下的作家们在其创作中普遍关注作为个体的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他们不再关注经典、关注时代民族等宏大的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当下的世俗生活,刻写小人物繁琐的原生态生活。正如邱华栋所说:“没有多少‘文革’记忆的我们,当然也就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中了。”④
世俗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琐碎、平淡和无中心。朱文的《去赵国的邯郸》抒写了小丁在电厂的乏味生活——每天长跑、参加无聊的舞会、打牌等等,看似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却缺少了精神内核的支撑,且每天单调地重复着,成为了“空心人”的表演。尹丽川的《普通生活》一诗截取了“我”在集市买菜的一个生活片段,全诗没有运用任何典雅诗性的语言或是灵活多变的诗歌技巧,只是忠实地记录下集市混乱不堪的场景,刻画出现代人的冷漠,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
除了琐碎之外,现代人生存的艰难、挣扎与无奈也是“个人化写作”的重要题材。陈染的《时光与牢笼》中的水水最为勤快肯干,但是考勤表上的小对勾却最少,面对失衡不平的生存现实,她虽然愤怒不已,但仅限于在睡梦中发泄满腔怒火,在现实中面对领导时依旧低声下气、卑微不已。沈浩波的《原谅》一诗中那一句对工作难找的咒骂——“这年头/到他妈哪儿/找去啊”,还有那个为了工作而不得不向老板请病假去堕胎的女孩⑤——这些事件的陈述矛头直指当下就业困难、工作压力大等尖锐问题,体现了小人物生存的艰辛与无奈。
同样是叙写世俗生活碎片,“个人化写作”思潮内部各个阶段的作家们也有各自不同的情感倾向和侧重点。朱文、韩东等在刻写笔下小人物的艰难生存时,虽然不曾明确表露作者的情感态度,但在字里行间无不隐藏着作者深沉的怜悯和同情;陈染、林白等在追踪女性人物生存经历时,更加注重融入自己的真切体验与深沉情感,使作品常常流露出一种自恋自虐的倾向;而沈浩波、尹丽川等第三阶段作家则彻底告别了这种悲悯情怀,他们用极端冷漠的目光观看笔下人物的挣扎与痛苦,沈浩波的《死亡》一诗就鲜明地传达了这一特点,该诗陈列了一系列死亡事件:遇难的登山队员、坠毁的飞机、被烈日晒死的非洲女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诗人甚至连问号都吝啬,只用小小的逗号传达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为“零度疼痛”!而正是这一越来越狭隘自私的创作走向,使得“个人化写作”危机四伏。
2.“私人生活”:个人化叙事的狂欢
晚生代作家对当下世俗生活尤其是小人物的生存的叙写,只是平面化地展示,而很少深入探究其生存表象之下的内在品质,颠覆了之前文学代集体言、代政治言的宏大叙事法则,用这种个人化叙事法则阻隔了集体叙事的入侵。他们普遍注重对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体验的细腻表达,以一种绝对个人的话语谱写内心的欲望轨迹。鲁羊在创作中就“希望传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坦言自己的作品是其“个人体验的一种外化形式”。⑥
个人化叙事法则还体现为对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孤独主题的迷恋,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有助于作家更好地书写自我与个体的感受,表现孤独的主题。毕飞宇在《雨天的棉花糖》就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了主人公红豆被俘后大难不死回归乡里的曲折经历:他的归来受尽了旁人的冷眼,甚至得不到家人理解,他被逼向了孤寂的绝境,内心苦痛不堪,最终绝望地选择了自杀。
与毕飞宇等人笔下的主人公同现实环境做歇斯底里的对抗不同,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在追踪女性人物成长历程时,更多的是突出她们在现实生存中受挫之后回归自我的理性选择。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林多米等女性主人公起初都对外部世界抱有极大的期望,渴望通过真挚的爱情和全身心的付出得到男权话语世界的认同,但她们最终都只落得伤痕累累,于是她们绝望而又无奈地逃回自己内心封闭而清幽的世界,她们选择了孤独以守护理想的真爱和内心的高洁,从而完成了自我的回归,也表现出对男权世界的理性批判与反抗。与这种选择自我回归的理性不同,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作品中的主人公纷纷沉迷于喧闹的酒吧和膨胀的物欲当中,她们不再苦苦寻觅那些虚无缥缈的情感,如爱情、信念等等,而是用极度放纵的欲望麻醉自我、消解理性的成分,最后义无反顾地扑向了非理性的享乐主义世界。
3.“我爱美元”:欲望旗帜的高扬
个人化写作者不再隐藏笔下人物不可遏止的欲望,他们放弃了所谓的崇高、正义、理想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大量描写暴露人的本能原始的欲望,掀起了一股“欲望化”叙事的高潮。
首先是裸露现代人的性欲望。诚如波德里亚所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⑦韩东笔下的许多人物,就无所畏惧地宣泄自己的性欲望:石林(《障碍》)与朋友的女友在私守中狂热地发泄着内心骚动的性欲,王一民(《为什么?》)在夜宿朋友家的时候竟与朋友之妻通奸。晚生代作家在描绘这些人物的性欲望时,大多采用细腻的笔法,尽可能地真实还原人物交欢时的细致场景与过程,而这些人物的性狂欢无关道德、无关爱情——是一种纯娱乐的游戏。
欲望化叙事也大量涌现在女性个人化写作者的作品中,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徐小斌《双鱼星座》等都充斥着男女交欢的赤裸场景。除了与韩东、朱文等人一样关注两性之间的性欲望之外,这些女性作家还将笔触深入到了许多令人惊悸的审美表达,诸如同性之恋、自我抚慰等。徐小斌《羽蛇》里的羽和金乌之间的同性之恋和相互抚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里林多米体验自慰带来的快感等,这些女性隐秘体验的表露通常被视作是女性自我回归的理性表现及其对男权话语世界的失望和反叛。
卫慧、沈浩波等作家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仅存的理性,将欲望化叙事发展到了极端。他们让人物——有时甚至是自己肆无忌惮地去追逐感官刺激,使之沉溺于躯体的欲望中不能自拔。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赤裸裸地展示了倪可多次与自己根本不爱的已婚男人马克性交的场面;沈浩波的代表作之一《人老乳不老》中流露出对肉体感官的膜拜:“一个耸着漂亮乳房的女人/即使年纪大些/也可以说是风韵犹存”,只要乳房漂亮,年龄、爱情等曾经重要或神圣的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
其次是描写现代人对金钱、名利等物欲的追逐。朱文《我爱美元》中的主人公“我”是个作家,但他坦言自己写作只是为了钱,他甚至打算将自己的灵魂打折出卖,打几折没有关系,关键的是“我要的是他妈的美元”——彻彻底底的拜金主义者!物欲的实现又常常与肉欲密不可分:陈染《无处告别》里的缪一为了名利地位,竟然与“谁谁的儿子”——一个“毫无出息的文化流氓”同居并结婚……
在个人化作品中,“欲”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扬,而“情”却备受冷落;人狂热追逐物质享受,甚至被物质异化,而精神却遭到了唾弃;身体与思想分离,在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对性的极度渴求之外,身体也已经被物化,沦为了以金钱为核心的物欲实现的手段。
4.“银河虚构”:现代叙事技术的熟练运用
晚生代作家在刻写个人经验、描绘个人欲望时,大多采用写实的笔触,除此之外,他们也灵活运用各种现代叙事技巧,注重对文学形式,如语言、结构、叙述等方面的探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很多个人化写作者在创作中都表现出诗性语言的执著追求,如陈染就用鹅绒圆球、艳红的樱桃、茵茵的芳草等富有诗性的意象,来指代女性的身体器官和个人私密的感官体验,使得一些原本羞于启齿的隐秘场景变成了意境幽远且优美的图画,让人叹为观止。
诗性语言追求的实现需要借助大量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这又使文本往往呈现出象征化、寓言化的特点。李冯在《最后的爱》中通过“爱情频谱仪”、“爱情芯片”等看似荒诞却极具寓意性的意象,揭示了现代人感情的滥用。
从结构和叙述方面来看,个人化写作者在创作中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把自我的经验熔铸于主人公身上,模糊了创作主体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有时甚至直接“以‘元小说’的叙事方式构思小说,作家自己成为作品中的人物或叙事者”⑧。朱文《我爱美元》中的主人公兼叙事者“我”与作者同名,也叫朱文,也从事写作。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很多时候都等同于作者自己的,就像鲁羊所说的,他“经常把自己当成别人,又把别人当成自己”⑨。
“个人化写作”思潮发展到“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及“胸口写作”时,则完全抛弃了对诗性、理性、寓言等较深层面的探索,而追求一种完全平面化的无深度的写法,使作品成了纯粹的个人欲望的展览。正如“下半身”诗人李师江所言:“‘下半身’的出现意味着营造诗意时代的终结。”⑩朵渔、伊沙等作家热衷于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姿态,调侃、颠覆文化、传统、经典等“上半身”因素。朵渔的诗歌《银河虚构》以反讽的笔调嘲讽调侃了乌托邦理想和空洞的爱情。伊沙的诗歌《车过黄河》以一个正常却不优雅的生理性动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嘲弄并消解了黄河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及历史文化。这些后起的晚生代作家的个人化创作姿态日趋激进,他们创作的视野和题材也随之狭隘,最终不仅束缚了自身的创作,也将“个人化写作”思潮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三、成就与局限:悬崖上热舞过后的致命坠落
“个人化写作”思潮在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作为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元,它推翻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中长期的霸权统治,为文学脱去了政治、阶级、民族等沉重的外衣,使其重新关注个体;张扬了人在实践、精神方面的主体性,有效地引导主体进入“自我生命的潜在部位”;营造了个人生存体验的维度,特别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果敢地开拓了女性写作的新空间……在以个人化的利刃刺破了主流话语和公共秩序的巨大蛛网时,“个人化写作”思潮也加速了世纪末当代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但人是群体的存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群体、时代而独立存在。因此当个人化写作者将视野圈定在绝对个人化的生存表象上时,一方面令读者耳目一新,而另一方面却走向了危险的悬崖。首先,始终坚持书写个人的自我生存感受与心理必将导致题材的狭窄和枯竭,个人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个人化写作者的笔下经常出现自我重复的叙事。其次,对琐碎平庸的世俗生活进行过于细致的观照,虽然凸显了生存之真,却忽略了它的善与美。第三,在书写人物躯体欲望时,回避理想、放逐诗意,而过分沉溺于对个人性经验过程的细致描绘,使文本缺乏应有的审美内涵而显得有点卑琐与无聊。诚如当代著名评论家洪治纲所言:“对世俗生存现实的过分认同,对欲望化人性的过分沉迷,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⑪因此,极端的个人化之舞必将使晚生代作家走向无路可逃的悬崖,从而面临致命的坠落。
若要摆脱上述困境,晚生代作家必须自救。
从对“个人化写作”思潮特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内部三个阶段的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极端的发展趋势,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无节制的极端发展最终束缚了“个人化写作”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也阻断了“个人化”经典作品出现的可能。正如陈染所言:“懂得节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不会自制的‘艺术家’便破坏了她自己的艺术自由。”⑫因此,“个人化写作”最好的出路是跳出过于个人化和欲望化的泥淖,找到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契合点,由此生发开去,拓宽自己的视野;在写实基调的基础上,融入对生活之善与美的观照;在细致描绘世俗欲望之时,渗透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超验性的终极关怀”。
如今,“个人化写作”思潮已退去了昔日的狂热,但它犹有自己的阵地以及一直坚守阵地的一批作家,它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适宜的发展环境。而作为“个人化写作”思潮的主体,晚生代作家们正处在创作精力旺盛、思想不断成熟的年龄,因此他们完全有可能为它带来“第二个春天”。
①龙泉明、汪云霞:《初期白话诗人的个性化写作——论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诗歌的精神特征》,《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
②周晓燕:《当代文学的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北方论丛》,2001年第2期。
③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
④邱华栋:《城市的面具·自序》,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⑤沈浩波:《沈浩波的诗》(5首),《诗歌月刊》,2007年第6期。
⑥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⑦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⑧王铁仙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
⑨鲁羊:《在北京奔跑·自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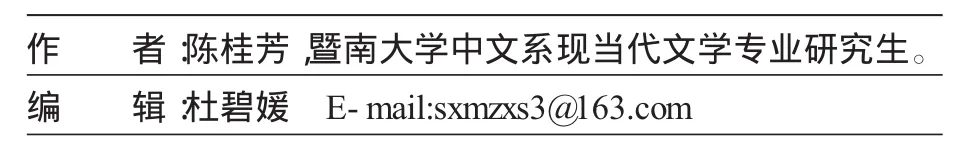
作者:陈桂芳,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编辑:杜碧媛E-mail:sxmzxs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