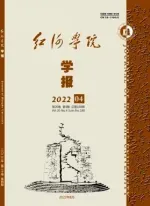论唐继尧对云南近代教育的贡献
2011-08-15王丽云
王丽云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论唐继尧对云南近代教育的贡献
王丽云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唐继尧作为中国和云南近代史上褒贬不一的风云人物,一生从政从军的同时,还躬行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云南的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继尧对云南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是其政治理想——成为“东大陆主人”的产物,透过他在云南近代教育史上的这些作为,可见其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旧军阀儒雅知文的另一面。他在教育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救民的情怀、开阔的现代视野、远大的抱负和知行合一、勇于实践、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是云南近代民族文化的精华,虽以军事立身,却能以文治省,神威奋勇、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应该是唐继尧较为客观的历史形象。
唐继尧;云南;近代教育;贡献;历史形象
唐继尧作为中国和云南近代史上褒贬不一的风云人物,其主要成就并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一名有远大抱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一生从政从军的同时,还躬行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云南的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唐继尧的教育观及其教育贡献进行论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观照唐继尧其人,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他的客观认识。
一 唐继尧对教育的认识
唐继尧对教育的认识来源于他的爱国救民思想及其实践。1883年,唐继尧出生于云南会泽县金钟镇三道巷,他生性聪颖,6岁入私塾,15岁中秀才,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功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救民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我良知最清明者,为爱国救民四字”(《笔记》之七十九),“如背爱国救民之旨,则一切修行,废而无所用矣。”(《笔记》之一四一)[1]身处国祸民难、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唐继尧,上下求索,不断探求爱国救民的道路。1904年,唐继尧被当地官府推荐到日本留学,在许多人视留学为畏途的时代,新婚刚刚三个月,年仅21岁的唐继尧却毅然踏上了留学的征程,出发前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2]唐继尧出国前夕,由父亲带着去拜见昆明学者陈荣昌。陈荣昌提倡实业救国,乃劝唐继尧学工科,于是唐继尧便照填志愿书,和省内其他留学生一道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的主要基地。孙中山先生经常来往于东京、横滨等留日学生比较集中的城市,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目睹国土沦丧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的唐继尧,很快就接受了军事救国和革命救国的思想,断然弃工就武,进入东京振武学校改学陆军。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作了解释:“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3]纵观青年唐继尧这一时期的思想行为变化,无不以爱国救民为宗旨。
在爱国救民思想的指引下,除认真学习军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外,唐继尧还对怎样实现爱国救民的目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所得集中反映在他1905—1909年留日期间的随笔体著作《会泽笔记》中。在笔记中,唐继尧在学习和考察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国弱的病根,提出了颇富远见的五条措施,“发展教育,唤醒国民”即为其中之一。在约25000字、共185册的《会泽笔记》中,直接提到教育的就有十余条,我们从这些文字可以窥见唐继尧对教育的认识,就其主要,摘录如下:
“教育,强国之基础也,故欲复兴中国,须自教育下手。”(《笔记》之一○九);
“国之兴亡,在民德之高低。”(《笔记》之四十);
“中国人自私自利之习染已深,于自己无直接利害之事,则淡然漠视之……外侮侵袭,苟不刀临项上,仍然不痛不痒,全不相干,呜呼,如此麻木不仁之国民,果不施以严格彻底之教育,刷其恶腐之心,欲图复兴富强,何可得乎?”(《笔记》之十七) ;
“统一国民精神,须使宗教、政制、教育、习俗,不可退于庞杂” (《笔记》之三十三);
“高尚之人格,健全之国民,皆可自我人手中教育培养以完成。”(《笔记》之三十四);
“心田不打扫干净,虽施以良好教育,亦无益也。”(《笔记》之二十七) ;
“教授不独在于学术,更应注重培养学生之精神。”(《笔记》之二十六)。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唐继尧对于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不仅认识到了教育与强国的关系,还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教育强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精神的培养上,他提出了教育应以德育为主,以倡兴国学来培养国民精神的独到见解;虽说这些见识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影响,但作为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能有此见识难得可贵,最为重要的是唐继尧主张“空谈不如实行” (《笔记》之三十八)。在主滇政14年间整军经武的同时,不忘实践教育强国、以倡兴国学来培养国民精神的主张,为云南的近代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唐继尧对云南近代教育的贡献
少有大志的唐继尧,踏上日本国土不久,便在他自己的一颗水晶图章上,刻名自号“东大陆主人”,表明了他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不甘心再做奴隶的雄心壮志。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军事救国、革命救国、教育强国等思想的影响下,1909年学成归国的唐继尧一心革命,在从军从政的过程中,在云南教育因护国、护法等战争陷入困难时期的背景下,他依然不忘实践自己的教育主张,在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均作出了不俗的成就。
在军事教育方面,唐继尧一是亲自执教,在担任云南新军军官的同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与同时归国的士官学校同学同时执教;向学员灌输民主思想,讲授阳明学说,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把讲武堂办成革命熔炉,保证了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二是在云南主政期间,创新云南近代军事教育,提升了云南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其中以军事创新对云南近代军事教育的影响最为深远。军事创新是唐继尧急于实现“东大陆主人”的政治抱负,或曰政治野心的产物。护国战争后,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已初见端倪,对于其后期“联省自治”的政治选择。孙中山说他得了贵州,还想四川,甚至于广东、广西境内,都有他的军队。但这些作为,都非唐继尧的政治远图,“空谈英雄者,不能实际努力者,庸人也”(《笔记》之四十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须增强军事实力。唐继尧审时度势,敢为天下先,在云南近代军事教育方面进行了以下创新:
1.为制度创新,在地方军队中首创“将校队”。 1920年,唐继尧为进一步培训高级将领,在讲武堂内创办“将校队”,他自兼总队长,增设日文等外语课程,学制仿照日本陆军大学。其中最重要的是 “将校队”结合实际,对教育、训练、管理和设备等多次作了很大的改进,使之更加正规化、系统化和现代化;尤其是不拘一格,广揽人才。除广聘留日学生上课外,还聘请日军上校苫米地四楼主授战术、战史,包括图上战术、现地战术、沙盘战术、兵棋演练、参谋施行、实兵指挥等课;日军炮兵中校铃木一郎主授炮、工、筑城学、军事交通学等课,并兼任讲武堂劈刺教官;日本陆军中校山县初男讲授军制、军队教育等课。地方“将校队”的设立和中外教官同在一校登堂授课,这在当时中国地方级的军校中纯属首创。
2.为办学创新,开地方军校在全国办分校之先河。早在1913年,唐继尧任贵州都督时,在贵阳开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刘法坤任校长,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外省开办的第一所军校,引来当地很多青年投考。之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应四川但怒刚、石青阳两师长的请求,在校内为川军开办了下级军官速成教育两个班,培养了400多人。护法战争时期,滇军遍布西南及华南各省;为补充干部的需要,云南陆军讲武先后在贵阳、成都、泸州、韶关等地开办了讲武堂分校。此外,北伐战争时期第三军军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朱培德和继任者王钧先后在广州大沙头和南昌、徐州等地开办过与云南陆军讲武堂一脉相承的短训班和军官教导团之类的滇军干部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可谓创中国地方军队在外地开设分校之先河,影响之大,报考人数之多,为全国讲武堂之冠。
3.为招生创新,打破陈规招收海外学员。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名声大振,邻国的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唐继尧打破云南讲武堂只招收云南人的陈规,特派使者到南洋各地招募华侨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从第11期至17期,在讲武堂招收的学员中,华侨学生有500余人,马来西亚、越南、朝鲜等国学员有200多人。[4]其中,原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健次帅、韩国首任总理李范奭、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都毕业于这里。云南陆军讲武堂中外青年济济一堂,演兵习武,这在当时的中国各所军校中实为首创。
4.为办学创新,建立航空学校,成为云南航空教育之始。1922年春,唐继尧重主滇政后筹集巨款购买飞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云南航空处,开始发展云南的航空力量。为培养航空人才,唐继尧派人在昆明、贵州两地招生,筹建云南航空学校。12月25日,航空学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学制3年。云南航空学校从1922年至1935年10多年时间,先后办了4期飞行班,2期机械班,除第一期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办外,其它都在巫家坝机场办。航空学校共培养了飞行员、地勤人员200余人;最为特别的是在当时云南乃至中国封建思想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唐继尧不仅选送了夏文华、尹月娟两位昆明女学生进入航校学习,而且特批了几名华侨学生和朝鲜籍学员李英茂、李春、张志田以及女生权基玉来校学习。这样,在云南航空学员第一期学员中,不仅有云南学员,而且有外省学员;不仅有归侨学员,而且有外国学员;不仅有男生,而且有女生,尤其是有外国女学生,成了中国第一所打破男女界限跨国招生的航空学校。这种情况不仅证明了这所航校的知名度和云南当时的对外开放程度,还充分地反映了唐继尧开明的思想和广阔的视野。云南航空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之一,其创立为抗日战争中云南成为中美空军最重要的作战基地,为解放后云南成为中国的航空大省、为昆明巫家坝机场成为今天全国的五大国际空港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创新活动,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24年,唐继尧应孙中山之邀派出教官协助创办黄埔军校,唐继尧的军事教育的实践成果可见一斑,云南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得以迅速攀升。通观唐继尧在军事教育上的这些作为,虽然是他的政治抱负或曰政治野心使然,但从客观上讲,在清末一直属于贫困省,每年除朝廷拨款外还要靠邻省接济才能勉强维持运行的云南省,能在中国军事史上有此突出的表现,唐继尧功不可没。
在文化教育方面,一心想成为“东大陆主人”的唐继尧深知教育强国的真理,他一方面重教兴学,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现代化教学改革,支持设立师范、实业、法政等学校,创办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另一方面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除加强教育厅工作外,还专设与教育厅平行的沿边教育行署以发展边疆民族教育;在昆明设立“国史学校”,倡兴国学。1914和1915年两年中,唐继尧派出去的官费和半官费的留学生超过以前的总和。[5]在所有的教育举措中,以东陆大学的创办影响最为巨大。
20世纪20年代的云南,教育经费拮据,小学教育尚未普及,中学教育也未办好,人才缺乏,兴办大学实为不易。但唐继尧一直认为:“治天下,以大学为基础,立人格,以英雄为楷模。”[6]在他执政的14年中,从未放弃过要在云南创办大学的想法,即使是在军阀混战、争权夺地的时期他也在努力寻找办大学的机会与途径。早在1913年,他执掌滇政后,就考虑过云南自办大学的问题;1915年,民国政府召开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云南政府代表提交了滇省创办大学的计划,但因云南首义护国而未能实施; 1918年,唐继尧又倡议滇川黔三省在云南联合办大学,因故中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主、科学之风吹遍全国,云南自办大学的呼声高涨,海外滇籍留学生论及家乡,莫不以滇省“速办大学,作为育人材、救济时艰之拟”[7]为中心议题。唐继尧在此背景之下又提出了废督裁兵、休养生息、振兴实业、发展文化等主张;1919年9月,他提出创立大学之案,“屡经筹议,卒以库款支拙,未能为具体支规划。现本督军兼省长力图整理内政,对于教育全部,均积极进行,大学校只设,必期于成。”[8]表明了他创办大学的立场和态度。但最终仍因社会不安定,经费无着落而半途夭折;1920年,非常关心家乡教育发展的云南首批留美学生董泽、杨克嵘等人学成归来,云南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创办大学的呼声日高,形成了云南兴办大学的契机。唐继尧不失时机的抓住这些有利条件,把创办大学立为己任,积极筹备办学事宜,拨翠湖水月轩为筹备处,任命其妹婿董泽为大学筹备处处长。就在筹备工作渐次展开之时,1921年顾品珍倒戈反唐,唐继尧被迫流亡香港,大学创办之事就此搁置;1922年,唐继尧重主滇政,任命董泽为大学筹备处处长,延揽返滇留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24人为筹备员,大学筹备工作得以重新恢复。从东陆大学创办前的一波三折足见唐继尧对在云南创办大学的执着信念。
东陆大学从1915年开始正式计划、酝酿、筹备到1922年成立前后历经7年,在整个创建东陆大学的过程中,唐继尧始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物质上,他不仅个人带头前后捐资达51万元,还利用其权势,尽可能地把公产、公款拨给东陆大学;精神上,唐继尧积极支持东陆大学 “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传播正宜真理”的办学宗旨,提出“东陆大学者,东亚人之大学,非滇一省之大学。”“东陆大学之成立其所负文化上之使命不限于云南一省,将进而谋西南诸省文化之均衡与向上,以与中原齐驱,而同欧美争衡。”“今后教育,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8]可见他的视野是何等开阔,正是在唐继尧远见卓识推动之下,在云南各界社会贤达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东陆大学才得以运转成功,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由此揭开了序幕。
1922年10月,经民主选举,董泽当选为校长,唐继尧、王九龄为名誉校长。又仿照欧美惯例,以创办人唐继尧的别号“东大陆主人”,命名校名为“东陆大学”。 12月8日,省公署正式批准成立大学,启用印信,随后即宣布大学招生简章,云南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大学宣告成立。从筹备到成立,仅5个多月的时间,其干劲之足,速度之快,都是罕见的。东陆大学创办后,仿欧美学制,根据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需要,开设文、工两科,仿照欧美实行学分制,毕业时学校授予学生“学士”学位。在进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东陆大学的办学效果在 1927年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视察东陆大学报告》中说而很清楚:“就同类机关如上海南洋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比较之,该大学所有以往成绩与效率居优胜地位,以其时间之短,进行之速,与办理之认真,至有今日所致之效果,可谓难能而可贵矣!”[9]东陆大学后经省立东陆大学、省立云南大学、国立云南大学三个阶段后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大学。私立东陆大学,既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全国最早设有现代科系的20所大学之一。1946 年,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到建国前,云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文、法、理、工、医、农门类齐全,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全国知名大学。云南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校方公布,该校曾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人才五万七千余人,这些人才极大的推动了云南社会的进步,唐继尧创办东陆大学,功莫大焉。
综上所述,唐继尧对云南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是其政治理想——成为“东大陆主人”的产物,透过他在云南近代教育史上的这些作为,可观见其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旧军阀儒雅知文的另一面。他在教育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救民的情怀、开阔的现代视野、远大的抱负和知行合一、勇于实践、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是云南近代民族文化的精华,虽以军事立身,却能以文治省,神威奋勇、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应该是唐继尧较为客观的历史形象。
[1]唐继尧.会泽笔记[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8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2]李世沛.从《会泽日记》看唐继尧的爱国思想[KB/OL].唐继尧研究网:http://www.yntjy.org./detail.asp.
[3]吴达德.留日学生与云南辛亥革命[C].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8:94.
[4]http://hi.baidu.com/og/item/f19b2c8d46098517b21bba79.html.
[5]吕志毅.唐继尧的治滇善政[J].云南档案,2002,(2):21.
[6]刘光顺.唐继尧研究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16.
[7]温梁华. 唐继尧与云南高等教育[J].云南社会科学,1986,(6):122
[8]云南大学志.大事记[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32-48.
[9]云南日报理论部. 云南百年[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62.
Tang Jiyao’s Contribution to Yunnan’s Education Development
WANG Li-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China)
As an influential person in modern Yunna and China, who is either praised or criticized, Tang Jiyao devoted himself in Yunnan’s military and cultural education while he acted as a military man, making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Yunnan. The contribution he has mad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result of his political ambition: to be the master of the East Asia. All his contributions and achie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Yunnan show the other side of Tang Jiyao as being intellectual although he was mainly considered as a revolutionary, politician or military lord. His devoted patriotism, wide scope, great ambition and pioneering spirit all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Yunnan’s cultural heritage. We can say that although established in military, Tang was also an intellectual who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Tang Jiyao; Yunnan; education; contribution; historical image
K26
A
1008-9128(2011)05-0054-04
2011-08-09
王丽云(1974—),女,云南石屏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 自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