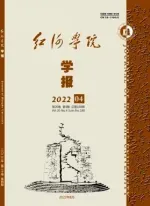越战后越美关系的发展
——一种建构主义视角
2011-08-15李忠林
李忠林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 昆明 650091)
越战后越美关系的发展
——一种建构主义视角
李忠林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 昆明 650091)
越战结束之后,美越两国在互动过程中逐渐结束了以前的敌人身份认同,建构起了新的朋友身份认同,从而使双方关系从对立走向了合作。这种发展轨迹体现了建构主义的主体间建构的重要性。用建构主义的观点解释越战后美越两国关系的巨大转变与飞跃,对于在当今世界各国间化矛盾对立为合作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指导因南海问题而复杂化的中越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越战;美越关系;建构主义
一 引言
从1986年起,越南开始实施革新开放政策,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越南对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开始进行逐步调整。在1986年12月份越共召开的六大上,越南提出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越南国内经济服务”的外交总方针。越共十大确定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对外路线,实行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政策,把全力发展同传统友好国家、邻国、周边国家、大国四类国家的互信合作关系作为对外工作重心,积极参与国际地区合作进程,主动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努力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1]。现在,越南新的外交战略框架已经基本确定,全方位对外交往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大国外交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最近几年美越关系越走越近,双方入世谈判、核能合作、军火贸易、高层互访等方面的进展出人意料。2009年,美越关系发展迅速。2010年,借东盟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召开之机,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唱一和,更是让人很难将“死敌”与“世仇”这样的词与两国联系起来。是什么原因促进美越关系在短短的冷战后不足20年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呢?
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从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论和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认为是两国的国家利益使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两国调整了对外政策来适应形势的发展进而谋求国家利益。也有人从自由制度主义入手,认为双方互有所图,合作有助于实现美越各自的利益。这些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驱动力和终极目标。但是,这种传统主义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虽然建构主义同样不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但是认为角色或行为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界定自己的身份,是认同决定利益。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认同,离开观念因素利益将失去实际意义。国家利益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是通过社会认同所建构的结果。因此,本文将采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观点,从身份认识与主体间建构的视角,对越战后美越关系的巨大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揭示身份认知是如何影响两国的行为方式的。
二 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及其简介
建构主义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逐渐兴起的一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后被称为三驾马车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它强调运用社会学的视野重新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最早提出该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奥勒夫,但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提出了建构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规范、认同和文化。规范,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可以理解为行为体在特定的环境下共有的理解和期望。作为一种社会约定,它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俗”等内容,这是这些内容构建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认同,即是行为体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一种身份界定,从而区分“我”和“非我”之间的利益。建构主义主张从认同的角度对国家利益进行分析,寻求其建构过程并追溯其来源。文化,建构主义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国家认同[2]。而且,不仅存在着国内文化,还有国际体系文化,而且物质结构的意义取决于文化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提出了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命题。第一,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不反对传统主义所坚持的结构的物质性,但是认为世界政治体系不仅包括物质结构还存在着社会结构。而且温特还认为,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它需要通过社会性因素才能起更大的作用。比较类似我们通常所说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软实力源于硬实力,但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能起作用。第二,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构成关系,即施动者的互动导致了结构的构成。[3]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它包括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和互为朋友的康的文化。第三,建构主义是一种动态的、演进的文化。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既然能够被建构,也能被解构并重新建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利益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通过人们的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但是由于人们的认同与身份界定会发生变化,所以利益的概念和内涵不是永恒的,它会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且其界定还往往受制于决策者的主观意识活动,犹如三种文化可以互相取代一样。
总之,建构主义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尤其是利益。它从个人和国家的实际需要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为出发点,给国际关系研究铺上了一层浓厚的主观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也充实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无疑给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
三 敌人与对手——建交前美越关系的相互定位与身份认定
建构主义认为角色或行为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界定自己的身份,区分“我”“非我”之间的关系,进而确定自身的利益。“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认同”[4],是认同决定利益,国家利益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是通过社会认同所建构的结果,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国家利益。按照建构主义理论,一国对他国身份的认定将会引发对自身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和判断,进而影响该国外交行为方式[5]。从二战结束到越战结束,越南整整经历30年的战争状态,而从支持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的企图到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再到遭到惨败而从越南撤军,美越双方一直处在敌对状态,双方的长期的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了鲜明的敌人和对手的相互定位与身份认同。而且这种定位和认同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发生逆转,并长期影响着主体的对外行为。温特曾举例说,“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6],原因就在于在美国人已经把英国界定为可以信赖的天然伙伴和盟友,后者拥有再多的核武器也不会对自身构成威胁;而朝鲜正好相反,朝鲜是敌对国家,再少的武器也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可见,对两国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完全是美国自己对两者的身份认识和界定不同,仅此而已。这个例子也十分适合越美关系。
战后初期,在美国人看来,冷战的压力使得“即使远在地球那一边的越南共产主义也必须予以回击”[7]。法国企图卷土重来,在越南和印支地区恢复早已过时的殖民统治,而当时法国国力衰弱,是在英国、美国军事装备的情况下才得以在越南支撑局面。美国表示“从不怀疑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早在1945年5月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就第一次承认了法国在越南的主权。在越南方面看来,美国人是法国人的帮凶,是对越南的间接侵略者。
无能的法国人退出越南之后,美国开始支持吴庭艳政权,向其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美国此时还给予了南越巨大的经济援助,仅1956-1960年这种援助就高达16亿美元。后来美国更是直接卷入了越南内战,到了1966年8月,已有多达42万名美军士兵驻守在越南。在越南人看来,美国此时是直接的侵略者,要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就必须打败美帝国主义者;而在美国人看来,要想遏制共产主义及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要取得冷战的胜利,就必须将越南战争继续下去。
但美国人并没有取得想要的胜利,傲慢自大和越南人民英勇的抗争是美国遭到惨痛的失败,不得不于1975年最终离开越南。至此,越南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两国间相互建构起的对方是敌人与对手的观念取向仍然长期影响着彼此的相互政策。对越南而言,美国是曾经的死敌,给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沉重的灾难,是对越南抱有帝国企图的霸权主义者,所以越南仍然把美国视作其“基本的、长期的敌人”。对美国而言,美苏冷战还尚未结束,越南作为共产主义政权和苏联的盟友仍然被定位为是需要加以遏制的对象、长期的敌人。而且,美国耗资1500亿美元、死亡5.7万人的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伤亡人数仅少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耗资仅次于二战的战争,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竟然完败于一个亚洲小国,美国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对越南的恨依旧强烈。之后,美国继续对越南实施贸易禁运等经济制裁措施,并在1975-1976年间,三次单方面否决了越南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在70年代末,越南地区霸权思想膨胀,在苏联的支持下公然侵略主权国家缅甸,而美国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越美关系改善的最重要的条件,并公开谴责越南出兵柬埔寨,赞成联合国大会作出的“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的决议”[8]。此阶段虽然双方为改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是柬埔寨问题、阻止了双方相互形象的改变,敌人与对手的相互定位与身份认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 朋友与伙伴——建交后美越关系的相互定位与身份认定
虽然上述身份认同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并非不能改变,身份认同是双方在互动中建构的,也会在互动中改进而重新建构。新建立起的究竟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是康的文化,彼此身份如何转化,完全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结果。是和平还是战争与冲突,是敌人与对手还是朋友与伙伴,这完全是一种选择。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朋友或者敌人的身份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美国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美两国经过不断磨合和积极互动,从霍布斯文化(敌人文化)、洛克文化(对手文化)最终发展到康德文化(朋友文化),双方的角色认同实现了从敌人关系到对手关系、最后到朋友关系的转变。[9]而越战后的美越关系发展的轨迹也是如此,经历了从敌人、对手到伙伴、朋友甚至是盟友关系的转化。
越战结束以后,尽管双方仍旧都把对方视为敌人,但是出于实际需求,这种观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彼此都认为可以而且需要同对方进行接触。比如,越南要发展社会经济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和援助,也需要美国放弃制裁措施;而美国也需要寻找在越南的美军失踪人员,也包括寻求填补因冷战结束苏联撤离后留下来的力量真空。虽然双方关系长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总体上美越关系渐渐的走向缓和与接触,这种情况直到1995年双方恢复关系正常化和正式建交。
任何国家政策和国家关系都是时代的产物。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苏联不复存在,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多极化是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经济外交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点,意识形态的因素正在淡化。在这种形势的冲击下,美越对对方的认知和定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彼此都不再视对方为不可变更的敌人,而是进行尝试合作的可能性。如上所述,认知决定利益,利益影响行为。因此,两国都迅速调整了对外政策,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互动的新阶段。1995年7月,克林顿宣布华盛顿将与河内建立外交关系。8月份,克里斯托弗进行了1970年以来的美国国务卿对越南的首次正式访问。1998年9月至10月,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在出席第53届联合国大会后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越战结束后越南高级领导人首次对美进行正式访问。2000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越战结束以来越南首次邀请美国防长访问。7月份,美越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为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这是双方在越南战争结束25年之后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2000年底,克林顿成为越战后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2005年6月,越南政府总理潘文凯访问美国。2006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访问越南。2007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应美国总统布什邀请率领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2008年6月,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第三位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越南高层领导人。2009年6月,越美举行第二次政治、安全和防务战略对话。
由上不难看出,美越关系在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这说明双方身份和认识的重现建构已经完成。对越南而言,革新开放以来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和援助;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东南亚地区大国梦;要应对中国的崛起等,美国都可以而且应该是越南合作的伙伴甚至是盟友。具体到对华政策与对美政策而言,无论中国在历史对该地区做出过多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现实当中都是越南必须加以防范的对象,是该地区和平的最大威胁,是需要予以‘遏制和改造’的敌人;无论美国对该地区做出过多么血腥的殖民统治和野蛮侵略战争,现实中都是越南亲密的战略盟友,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中坚力量[10]。对美国而言,要重返东南亚、要占领越南巨大的国内市场、要完成对中国的遏制、要实现对越南的改造并将其拉入自己的战略放轨道,这一切都需要越南的合作。如今美越都视对方为自己的朋友,认识到发展与对方的关系符合自己的利益。至此,原来的彼此视为敌人与对手的身份已经完全瓦解,一种全新的“文化”经在美越之间建构起来,并将影响着今后的美越关系。
五 结语
在理论上,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一旦对他国身份的认定将会引发对自身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和判断,而且这种定位和认同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发生逆转,进而影响该国外交行为方式。与此同时,建构主义还是结构理论和进化理论,这种身份认同虽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并非一成不变,身份认同是在双方在互动中建构的,也会在互动中结构进而重新建构。所以,主体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敌人,也可以是朋友;国际冲突也并非无法调和、不可避免。主体间建构的结构可以具有合作性质,也可以具有冲突性质,其对政策的积极意义是国家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
建交前,美越是一对死敌加世仇,彼此是对方为“头号敌人”,然而正是这一对冤家在冷战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在进入新世纪后越走越近。这正说明了主体间建构的重要性,说明了美越间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彼此对对方的观念和认知的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则取决于国际共有观念层次上的共有规范造就的。身份的构建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双方究竟是走向霍布斯文化还是康的文化,完全取决于主体间的建构。美越关系相互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对于充满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的中越关系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成功范例。努力扩大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形成两国间良性互动进而建构一种康德文化,从而解决南海争端诸问题,促进中越关系良性发展不是没有可能。
[1]外交部.越南国家概况[EB/OL].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5/.201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28.
[3]秦亚青.译者前言[A].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Z].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26.
[4][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01.
[5]赵伟明,杨明星.美伊核博弈的建构主义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 2 0 0 5,(7):2 2.
[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323.
[7][美]罗兹•墨菲.亚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 0 0 4:6 0 5.
[8]王国平.从对手到伙伴:革新开放以来的越美关系[J].东南亚南亚研究, 2009,(1):30.
[9]赵伟明,杨明星.美伊核博弈的建构主义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5,(7):25.
[10]陈乔之.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7-28.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US Relations after the Vietnam War——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LI Zhong-l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After the Vietnam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gradually ended the former enemy identity in an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constructed a new friend identity, mak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This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To interpret the great change and leap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after the Vietnam War with the points of the Constructivism has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anging from contradictory into cooper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guidance of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or Nanhai issue.
Vietnam War;US-Vietnam relations;constructivism
D81
A
1008-9128(2011)05-0032-04
2011-01-10
云南大学笹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10KT005)
李忠林(1986-),男,河南商丘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 张灿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