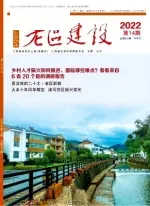再论卢梭与浪漫主义
2011-08-15杨文臣
●杨文臣
欧美文学史上,卢梭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开拓者,被尊为“浪漫主义之父”。不过,卢梭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浪漫主义运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雷内·韦勒克在那篇旁征博引被视为浪漫主义研究经典文献的长文《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概念》中对卢梭言之甚少;近来国内有的研究者甚至提出“卢梭思想是非浪漫主义”的观点。对于卢梭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这个课题,我们还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
如果去追踪“浪漫”一词的起源和演进,那么浪漫主义和卢梭显然没有太大关系。十七世纪人们就开始把“浪漫”一词用在中世纪的传奇上,意指“离奇的”、“荒诞的”,现在我们谈论浪漫主义时依然保留了这重意思。之后,“浪漫”和“浪漫主义”一词间或被人使用,但大多限于个人的意义上。直到十八世纪前后,也即卢梭之后,欧洲各国才先后出现了具有统一性的浪漫主义运动。不过,在文学的体裁、手法和意象的选用上,卢梭和后来的浪漫主义差别很大,很难看到直接的传承关系。
在韦勒克看来,标示出欧洲文学史上统一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准是其独特的自然观、想象观和象征观。与十七世纪机械的自然观不同,浪漫主义主张一种泛神论的、有机的、象征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观与卢梭的自然观只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在卢梭笔下,大自然生机勃勃,令人心旷神怡,“河对岸的路上,都是一些垒成高台的花园。那一天,天很热,夜色迷人,露水滋润了发蔫的青草,没有一丝的风,万籁俱寂,空气清新,一点不冷。太阳落山以后,在天空中留下了一片片红霭,余晖把水面映成粉红色。高台上的树木栖息着夜莺,歌声此起彼伏。我溜达着,恍如梦游仙境,任感官和心灵去享受这一切。”[1](114)自然有其自身的美,它慑服我们,使我们沉醉其中。但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自然并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它的美有赖于主体心灵的投射。塞南库尔的《奥伯曼》中的一段话对这种自然观做了生动而充分的阐明:“感到自然就存在于人的关系之中,万物的能言善辩只是人的能言善辩。肥沃的土地、无际的天空、潺潺的流水不过是我们心中产生和包含的各种关系的表现。”[2](165)在很多浪漫主义诗人笔下,自然是一个由符号、契合、象征组成的体系,充满着神秘和梦幻。卢梭的自然绝不神秘、晦涩,它不受主体心灵的辖制,而是以难以言喻的美卸掉主体思想的重负使其沉迷其中。“只有我不动脑筋思考的时候,只有在我完全处于忘我状态的时候,我的梦才最甜蜜,我才心醉神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愉快感觉,可以说,它们简直使我融入了天地万物的统一体系,使我和整个大自然结合成一体了。”[3](90)
“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诗人据以洞察生命、发现自然之美的工具。华兹华斯认为想象力是诗人创作中必不可少的能力,在诗歌中打动他的东西都是具有想象力即与无限打交道的东西;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关于想象力的论述更是名闻遐迩,借助想象诗人得以将零散的事物再创造为一个整体。索普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浪漫主义想象观的一个总结,“这就是创造性想象的能力,一种洞察、调和和结合的力量抓住旧有的东西,透过其表面,解放沉睡在那里的真理,经过重新组织,又化作一个重新创造的、披着华丽盛装和充满艺术力和美的大千世界。”[2](175)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卢梭并不缺少想象力,他的“梦思”便是一种感性化的、自由而富有想象力的精神活动,以此卢梭重新发现了未受文明玷污的纯净自然以及蕴涵其中的宗教和道德意义。但对比卢梭和浪漫主义诗人们展现出来的想象力,还是有区别的。卢梭的想象清新自然,他厌恶文明世界的污浊,在自然的触发下展开遐思,追问被深深遮蔽了的人性,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浪漫主义诗人们的想象奇崛恢弘,总是诉诸于无限、永恒和神秘。按照浪漫主义者们的标准,卢梭身上的“崇高”和“浪漫”气息应该算是非常淡薄的。
至于象征的使用,卢梭和浪漫主义诗人们就更少共同之处。“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都是神话创造者和象征主义者。他们的实践必须通过他们试图给予世界的一种只有诗人才能领悟的神话解释来理解。”[2](181)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象征,是隐藏在其后的宇宙精神的象征。而在卢梭那里,象征的使用极为罕见,他的语言细腻感伤,却也相当的素朴和明晰。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轻易否定卢梭对于浪漫主义的影响,毕竟,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和乔治·桑等人都曾坦言接受过卢梭的影响。看待卢梭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着眼于文学的选材、手法、风格等层面,而应着眼于卢梭的态度、思想和情感之于浪漫主义的传承关系。简言之,我们应该透过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去探讨卢梭的影响。
二
浪漫主义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E·B·勃拉姆说,“谁试图为浪漫主义下定义,谁就在做一件冒险的事情,它已使许多人碰了壁。”[4](1)在利里安·弗斯特的《浪漫主义》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几种界定,立足点分别为自我、情感、无限、心灵、想象、自然、生命意识,等等。事实上,不同的浪漫主义者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差别很大,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也面目各异。只有超越了这些表层的差异性,寻求各种浪漫主义者在精神层面上的同质性,才能把握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为此我们对浪漫主义的理解甚至要超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首先意味着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新的生存可能性的寻求。中世界传奇和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作品最早被冠以“浪漫”一词,尽管这些作品不能称为是浪漫主义的,但其具有的传奇性和怪诞性也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平庸、刻板的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充满奇迹和情趣的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传奇性和怪诞性在塞万提斯、斯宾塞和让·保罗等人的作品得以延续。到了十八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社会情绪躁动不安,人们或希冀、亢奋,或失落、沮丧,对现实不满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体现在文学中,人们或是用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想象去构想美好的乌托邦蓝图,或是在对逝去了的“乐园”的追忆和祭奠中悲伤地转向过去、自然和内心世界。于是有了“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之分,二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不满现实,追求更完美的生存状态。
并非任何“不满”和“追寻”都能成为浪漫主义的。真正的浪漫主义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它拒斥文化和文明对于人的“异化”,对人性和存在展开严肃的思考和追问。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品格才使其超越了特定时代和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拥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浪漫主义者们主张一种泛神论的、有机的自然观,试图恢复自然的神性和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以此反对十七世纪的机械论世界观展示给我们的了无生气的世界图景,以及资本主义的物质崇拜带来的人性的沦落和心灵的干涸。这样一种自然观和思想立场持续地对后世产生着影响,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荣格建立在远古人对于自然的神秘参与之上的“集体无意识”理论、马尔库塞对于产生于自然的“爱欲”的呼唤,以及其他众多思想家的璀璨的思想成果,都在精神上和浪漫主义一脉相承。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浪漫主义推崇的“自我”、“情感”、“想象”、“无限”等概念,便能发现其中隐含的对于荒漠化的人生和异化的人性的批判意味。“自我”的对立面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后者以“正义”、“秩序”、“义务”等宏大话语压制个体,贬低个体的权利和独立性,以维护封建秩序和王权,对“自我”的张扬从而具有了思想启蒙的意味。“情感”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指的是个人化的、人性化的心灵世界,没有了情感的滋润,生命会失去光泽,存在沦为“荒原”。“想象”使超越功利化、物质化的现实世界成为可能,它就像柯勒律治的长诗《古舟子咏》中的那只信天翁,一旦丧失,世界将成为一片死寂。至于“无限”,是浪漫主义者们提倡的泛神论世界观和对想象力的推崇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无限是难以蠡测的宇宙精神,也是不受任何束缚的个体心灵。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对人的越来越深的异化,文学需要以更沉重和犀利的笔触达成自己的使命,浪漫主义对“自我”和“无限”的沉迷受到了质疑。正如休姆所批评的,浪漫主义的态度好像是环绕着和飞翔有关的隐喻在韵文中具体化了,他们总是在高高地飞翔,从来不试图回到地面上。[5](8)之后,象征主义兴起,浪漫主义运动走向没落。不过,批判异化、寻求超越的浪漫主义精神并没有销声匿迹,它悄悄隐身于之后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之中,无论是艾略特的《荒原》还是梅特林克的《青鸟》。而众所周知,是卢梭最先认识到文明发展必然带来对人的异化,也是他打出了“回归自然”(同时也是回归完美的人性)的口号并以此对文明和异化展开了尖锐的批判。
三
质疑卢梭之于浪漫主义的重要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卢梭的思想是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他说的是纯粹理性主义的语言,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普遍信念并不悖逆。[6](12-13)笔者也认可卢梭思想中的理性主义色彩,但对于以此断定卢梭是“非浪漫主义”的做法却难以苟同。浪漫主义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是因为后者以理性的名义对个体进行束缚和压制以维护封建秩序,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本身一定是非理性的。如前文所述,浪漫主义精神的实质在于抵制人性受到的异化,寻求更理想的生存状态,这种抵制和寻求显然是对于人类存在的理性思考。事实上,浪漫主义的兴起和高举理性大旗的启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之一的自然观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启蒙哲学开启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它对十七世纪笛卡尔的二分哲学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质疑,认为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相互作用,自然界中生命现象无处不在,并不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在有机界中随处可见的种种生命形式和自我意识之间,不存在鸿沟。从最基本的生命过程到最高级的思维过程,从黯淡模糊的感觉到最高级的反省知识,贯穿着一系列不间断的阶段。”[7](76)这种思想在莱布尼茨、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等人的作品中反复得到申述,并在一种连续性中过渡到歌德以及后来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其中,卢梭明确将这样一种自然观贯彻到文学中,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卢梭的作品中,无论是《忏悔录》、《新爱洛伊丝》还是《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梦》,自然之美比比皆是,优美、险峻、雄奇、蛮荒……几乎是应有尽有。卢梭告诉我们,“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8](5)面对自然,卢梭总是满怀深情,只有在自然中,他才感到自己是完全的自己。卢梭在赞美自然的同时,也赞美了那些生活在自然中的山野村夫,他们勤劳、淳朴,身上保留着未被文明玷污的完美的人性。与之相反的,是大城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在那些繁琐的礼节之后掩盖的是虚伪和欺诈,一切自然的情感秩序全被颠倒。在《新爱洛伊丝》中,卢梭借圣普乐之口指出,“巴黎这个所谓的审美观最强的城市也许是世界上最没有审美能力的城市,因为人们在这里为取悦别人而费尽心机,反而损害了自己真正的美。”[9](183)人们迷失在扭曲了的人际关系中,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在华兹华斯的代表作品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咏水仙》中,我们感受到的情怀和卢梭如出一辙。
卢梭对自然的爱也是对自身存在的关怀,回归自然也是回归完美的人性,回归自然的存在。卢梭高度重视自我,重视理性。他信仰上帝,但他断然否定教会的权威,并对基督教义、教规和敬拜仪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狭隘的教义不仅不能阐明伟大的存在的观念,反而把这种观念弄得漆黑一团;不仅不使它们高贵,反而使它们遭到毁伤;不仅给上帝蒙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而且还制造了无数荒谬的矛盾,使人变得十分骄傲、偏执和残酷;不仅不在世上建立安宁,反而酿成人间的烧杀。”[8](426)教会奉行的是野蛮的蒙昧主义,并不能使我们接近上帝。“只有大自然中不可改变的秩序才能给人们指出那掌握自然的睿智的手”。[8](431)上帝存在于神圣的自然之中,只有培养和运用自身的理性,才能学会认识上帝。这样,卢梭将人们从对教会和教义的盲从中解放出来,指出人们靠自身的理性就可以通往上帝,把握无限和永恒。对理性的推崇也是对自我的张扬。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诗人们动辄将心灵诉诸无限和神秘,这种倾向在卢梭那里已经萌芽。
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和情感并不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正是因为卢梭理性地观察这个世界,才极力推崇情感。在他看来,矫揉做作、勾心斗角的上流社会中,人们的情感被扭曲了;而一切真诚、淳朴的自然情感都是符合理性原则的。推崇情感不是为了缩进封闭、感伤的自我世界中,而是为了使人性更润泽,世界更美好。对此,苏珊·朗格应该是深有同感,“一个忽视艺术教育的社会就等于是使自己的情感陷入五形式的混乱状态,而一个产生低劣艺术的社会就等于使自己的情感解体,这恰恰是统治者和政客们所要利用的一个主要的非理性因素。”[10](88)一个理性、开明的社会应该是人们拥有丰富的、精致的情感生活的社会,在这一点上,理性和情感取得了一致。浪漫主义文学中情感至上,是为了抵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实利主义、拜金主义导致的情感的荒漠化,也是为了使世界更富于理性和人性。
四
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庞大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复杂的经济运作体系,越来越深奥和专门化的科技及其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完全超出了个体可以感知和理解的限度,甚至逐渐超出了人类的控制。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一个自然被日益挤压趋于消失的世界,不仅个体的想象力受到束缚,个体的情感和存在也变得无足轻重。相应地,文学也失去了浪漫主义运动时曾拥有的宏大抱负:通过想象力把握这个世界,通过诗歌把世界还原为一个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文学开始展现现代世界这个庞然大物的荒诞本质以及个人置身其中的晕眩感和渺小感,展示个体无意义的、卑微的存在。然而,尽管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浪漫主义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文学仍在执着地寻求摆脱异化的可能,寻求更理想的生活状态,在这种寻求中,自然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乌托邦三部曲”——札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可谓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和专制集权结合——我们的现实世界中这种趋势隐然存在——带来的令人窒息和绝望的黯淡前景。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启示我们:如果世界还有拯救的可能,希望就在对于自然的回归。《1984》中温斯顿一再梦想的“黄金乡”,《我们》中“大墙”外面的世界,《美丽新世界》中的“保留地”,都是自然世界,也是人性依然存在的世界。自然和人性永远是抵制异化的最终依托,无论这种异化是来自物质、政治还是科学。在近年一些影视作品中,我们也能见到这种深入骨髓的浪漫主义精神,比如《兵人》中托德在那个废墟星球中种下的小苗,《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上纳威族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都发人深省,也使得这些作品拥有了超越娱乐层面的严肃意义。
总而言之,虽然浪漫主义时代已经远去,但浪漫主义精神却永不会泯灭;只有从内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卢梭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不断加快的今天,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文化生态都受到严重损害,人的异化也在不断加深,深入研究和发扬卢梭和浪漫主义的精神遗产仍有重要意义。
[1][法]卢梭.忏悔录[M].陈筱卿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2][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 [M].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3][法]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梦 [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英]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 [M].李今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5]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申扶民.被误解的浪漫主义——卢梭的非浪漫主义和康德的反浪漫主义[J].学术论坛.2010,(7).
[7][德]E·卡西尔.启蒙哲学 [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8][法]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法]卢梭.新爱洛伊丝[M].陈筱卿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0][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