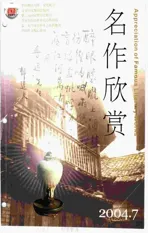文化是“根”
——写作解析·之七
2011-08-15北京孙武臣
/[北京]孙武臣
文化是“根”
——写作解析·之七
/[北京]孙武臣
有一首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抒发了“落叶归根”之情。还有一首歌曲《中国心》,抒写了中国人特别看重“落叶归根”的情意,无论你走了多久多远,总也抹不去你身上的“中国印”。
这里所歌唱的“根”和“印”是指什么?文化制约人类,文化铸造性格,用心理学常用的一个专业用语,即文化积淀着从无意识、潜意识、前意识到有意识的心理结构,养成着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自然也决定着人的命运。
于是,答案是:文化是“根”,没有根就没有绿叶;文化是“印”,永远无法抹去。
那么,“根”和“印”,即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它们又是怎样积淀而成?
问题是复杂的。这里我们抛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横向积淀和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横向影响,只强调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纵向积淀的两种途径。
一是民族历史和社会历史经验的集体积淀,即我们民族性的共性,也是指大文化环境而言。这一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只是点到若干点,就已令外国人感到神奇得叹为观止了。就我对文化内涵的有限思考,大体应该包括衣食住行、器物用品、民俗习尚、婚丧纪庆、典章制度等,都体现着文化。这就涉及包括意识形态中诸如道德伦理、习俗风尚、宗教信仰等人类活动,都渗透着文化,或者说是为文化所主宰。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国学”主体部分的内涵就极为广博,起码有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像我们“国学”这样近乎一个完整的思想道德体系,它涵盖了人生理想中的核心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规范,这样深厚、严整、周全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表征的规范标准,世界独一无二!
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历史经验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对写作者的影响是带有根本性的,中国写作者在思想价值取向,情理指向的主流内涵等重大方面,不约而同地注重追求着真善美的文艺本质;不约而同地决定了题材走向、主题开掘;不约而同地选取了相近与相似的艺术形式,也呈现出相近与相似的民族化的风格和手法。令人一看就能感知与判断出:这是中国的!这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文学创作的共性,也是历经时代变迁而抹不去的“印”。
润物细无声。无意识的积淀也是在自身不能察觉不能直接控制地自然的进行着,所以说它是一种自然形态的心理活动。我们的记者采访英雄模范人物时,总想刨根问底,“那一刻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回答“什么也没想”的,记者很是遗憾,似乎非要讲出“伟大”来才算满意。其实“什么也没想”是对的,“伟大”是平时的教育、学习,已经耳濡目染地积淀过的,那一刻的“伟大”就是这平时积淀的结果。可谓“平凡孕育伟大”。假如一个救人者在千钧一发之时,还要在“救还是不救”之间抉择一番,思想斗争一番,最后在“伟大”的动机和动力支撑下决定“救”,怕是早已错过了救人的时间了。同样,一个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上一边做动作,一边还在想“为祖国争光”,不从平衡木上掉下来才怪呢!那是平常所想,那一刻只能注意力高度集中地想动作。
二是个人、家庭等历史经验的积淀,是指小文化环境,形成的是个性。对于作家而言,这一积淀其实早在童年就已开始了。前苏联作家、理论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有一本值得我们写作者阅读的书,叫《金蔷薇》。其中有一段谈及这个问题:“写作,像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以产生在童年时代……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是作家。”可见,童年多一些诗性生活经验的积淀,对于一个作家心理定势的形成多么重要。许多作家在反思自己创作时都体会到儿童生活经验对自己的影响。冰心离开我们十年了,现代文学史在概括冰心的创作(不仅仅是儿童文学作品)时指出,冰心在北京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基督教的熏陶潜在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心理结构,并且形成了她作品中的那些爱的色彩、爱的情调的突出特征。冰心自己也回忆说:从中学时“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正好印证了她的创作个性。
共性总要通过个性体现。尽管每个作家的个性千差万别,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作家作品中所存的在共同的文化根脉,特别体现在文化对塑造性格、预知命运走向的决定作用。因此不能不思考与研究文化。
从大文化,或者说是广义的文化概念来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大体分为民族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世界性文化主要指文明,即科技、技巧等物质文化而言,它传播快,易于为其他民族、国家所接受与吸收,这是由于它的流动性、全球性和速变性决定的,这是当代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而民族性文化,即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非物质文化,则民族性显著,且不易变化。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保守性,甚至还有排他性,因而民族性文化才得以长期延续,并且它也需要这样的稳定、凝固和完整,否则,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习惯、制度礼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总处在不停顿的变更中,也就找不到自我。武装侵略远没有文化侵略彻底,原因是文化侵略是连“根”拔起的侵略。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写上最后一堂法文课。在时尚流变的当今世界,这篇小说仍有它的不可磨灭的启示意义。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民族文化也不可能没有它的渐变性。比如,当今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在价值观念作用下的婚姻观念,甚至包括节庆习俗(国人现在也过起了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等),一些观念不是已经发生了渐变了吗?尽管有些文化学者为此渐变而忧虑,并且文化部门也有针对性地加强青年人的民族文化观念,提高过民族性文化节日的意识,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但我坚信怎么也改变不了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第一的位置。
之所以谈文化的稳定性和渐变性,是因为涉及到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评价。
改革开放后,文学封闭之门也一下子打开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大约六七年的时间,现代主义文学随着西方的各种思潮再次涌进中国,来势迅猛,以致有评论家一时发出“现实主义过时”论。短短的五六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近一个多世纪出现过的各种流派及手法,我们都几乎玩了个遍。由于文化背景、哲学观念、审美取向、阅读习惯和情趣的不同,许多模仿作品,中国读者看不懂,当时还闹出过看不懂装懂的“皇帝的新衣”的笑话。到了90年代初,现代派文学很快就偃旗息鼓,突然间远去了,从此居然少有人再提及和研究这一文学思潮流派与文学现象。其实现代主义文学中有我们可借鉴之处,可惜只是被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时尚”了一下,如同一阵风掠过,去得无影无踪了。反思一下的确有些悲哀。
“现代派”文学热尚未消退,早有一批作家,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作家在内已经引领另一个文学思潮到来了,这就是“寻根文学”。他们有的用言论,比如,阿城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文化制约人类》;有的用自己的小说作品凸显这个思潮的力量,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等都是至今为人记得的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各有各的开拓性,但都在对于现实人生或历史掌故的富有地域色彩、乡土气息的真实描绘中,透露出一种浓郁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自觉的文化观照意识的力作。尽管这一类小说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对原始生命力的着重张扬等,但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现实主义回归了,并没有过时;二是从文化角度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进行审视,对于传统文化中以儒、释、道为核心内容的哲学观念以及由传统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进行解剖与反省;三是对于地域特色的强调,描写乡土风光、民俗民情以及文化风俗,并且自觉地超越地域特点进行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我之所以略略提到这两个文学思潮与流派,是想说明文化的排他性和保守性及其二者的关系。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它们常常是异质文化。比如,流传到中国很久的基督教很难像印度佛教那样更加普遍传播开来,是因为它们的“质”不同,前者是“性恶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一生要“赎罪”;而后者是“性善说”,和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相吻合。同质文化自然更易传播开来。现代文学思潮终归很快又被现实主义文学的乡土文学思潮取代,其原因正是缘于文化质的不同。寻根文学在“现代派热”中出现,正可提醒不要忘记我们文学的“根”在何处。
当我们理解了文学的“根”的内涵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乡土文学的特质了。乡土文学在文化的概念中,也是见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域的生命历程,于是,作为审美形态的文学中长于呈现家乡的生活风貌、抒发作者故乡情怀的创作就形成了一个重要流派——乡土文学。这就是鲁迅总以绍兴“鲁镇”、沈从文总以“湘西”、孙犁总以“白洋淀”、刘绍棠总以“运河边儒林村”为典型环境的缘起。如果我们取乡土文学的广义概念,也可以理解为每个作家都进行的是乡土文学创作,因为自己最为熟悉和对自己制约与作用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毕竟有限。因此,作者能选取为典型环境的不可能多广,以至于福克纳笔下的那个小镇被称为“邮票”大小的一方故土。其实,不只是乡土文学,就是文学整体的要义何尝不是写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作 者:孙武臣,文学评论家,曾任《文艺报》文学评论部副主任、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撰有专著《文学经纬论》《长篇小说发展论》等。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