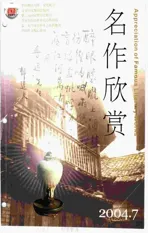聂绀弩及其《北荒草》(上)
——“后唐宋体”诗话·之六
2011-08-15浙江王尚文
/[浙江]王尚文
聂绀弩及其《北荒草》(上)
——“后唐宋体”诗话·之六
/[浙江]王尚文
诗救了他,他救了现代的旧体诗。
人生的苦难无助,往往非亲历者所不能真知。一切都是荒唐、残酷、恐怖,黑暗、冰冷、死寂,看不见任何光亮和希望;只有生的痛苦,因而只有死的渴望。活的愿望太弱太弱了,因为死的理由太多太多了。活下去,是奇迹!活下来,更是奇迹!正是诗,使他活下去——他超越了功利,为诗而诗,生死以之;由于他活下去,才有了活下来的机会。诗,不但使他活下去,而且活得如此辉煌灿烂。他,诗里求生,以诗为生,他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理想、幸福都交给了诗,他和诗已融为一体,他就是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他是诗之圣者,是我国现代诗史第一人。
诗,救了他;诗——旧体诗也借他之身之魂之诗获得了新的生命。用香港学者高旅的话来说,“一涤近代旧体徒尚空言、诛求字屑之衰疲”(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打开了新的篇章。他救赎了旧体诗,挽狂澜于既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奄奄一息的旧体诗奇迹般地重获青春。唐宋体,垂垂老矣;他,聂绀弩,借“诗”还魂,创造了“后唐宋体”。论者早已因他新颖独特的诗风命之为“聂体”,极有见地;我把他放在旧体诗的历史背景中,称之为“后唐宋体”。没有他,后唐宋体难以成体。他是后唐宋体的灵魂和旗帜。
在我国诗史上,致力于变革者可谓多矣,有的,成功了,推动了诗歌的发展;有的,却失败了,或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或心力才能难以胜任。由唐宋体而后唐宋体,是根本性的大变革,是飞跃性的大进步,聂绀弩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是历史机遇与个人才力的巧遇,实为诗史之幸,亦为聂绀弩个人之幸。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诗歌领域而言,必先簸其命运,新其人格,苦其心灵,变其感觉。在监狱里,又遇上了“大跃进”,“政府”——劳改犯对管劳改犯的干部的尊称——命令他写“诗”,他就真的“遵命”写起诗来了。他不可能写学术著作,不可能写小说散文,也不可能写新诗——“政府”不一定接受这种诗体,是吧?常言道,魔鬼就在细节里,历史就这么神奇地给他提供了从事一个惊天动地事业的机会。短小易成,传统的律诗绝句给了他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终于使他得以成为鲁迅所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从此跳出了如来佛的掌心,在唐宋体之外,筚路蓝缕,开天辟地,创造了后唐宋体。后唐宋体,在周作人、胡适、鲁迅多半只是偶尔为之的游戏之作,只是到了聂绀弩的笔下才真正形成气候。
作为孙悟空,他首先造了自己的反。他少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忧国忧民,立己立人,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过自己的探索、思考,在磨难中,出于自己的天真、诚恳、淳朴、坚韧,终于一步一步冲破了极“左”教条的束缚,挣脱天罗地网,“化而为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翱翔于诗歌的天地。同时他也造了唐宋体的反,几乎颠覆了近千年来唐宋体的观念系统、题材系统、意象系统、语言系统,使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得以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而广大读者也得以在他作品里看到被唐宋体所疏离起码是被模糊了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了新的时代气息,感受到了古老汉语新的魅力。
他1934年入党,1976年以“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身份走出大牢。据说,“邓小平听说此事后,大笑着说:‘他算什么军警特!’”(刘保昌:《聂绀弩传》,崇文书局2008年版,第317页)由此,我对“荒诞”有了新的认识,大诗人是可以从荒诞中走出来的。聂绀弩晚年一直“躬”在床上写诗,走时“身体弯得像一张弓”,他以这样的姿势去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不知他们作何感想。我由此对“躬”这个字有了新的领会与体验,难道这个字是专门为他而造的吗?他为诗而鞠躬尽瘁,“躬”而更显示出他的正直,他的坚韧,他的伟大。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不但收了各家对聂诗具体篇目、章句的研究成果,也收了共约二百二十家的一般性评论。我惊喜地发现聂绀弩的旧体诗不但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而且得到了高度评价,研究已经相当细致、深入、全面。我不能拾人牙慧,更不愿掠人之美,只能“接着说”一点自己的读后感想。先从《散宜生诗》的胡乔木序说起。胡乔木对聂诗的赞美是由衷之言:“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话说得好,聂绀弩确实是不可重复的;但作为一种诗歌的特色,别人可以学,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加以延伸甚至丰富,使之更为鲜明、深厚。即使不是有意地学,特色也可以有交集、重合,因此其特色可能并不仅仅属于聂绀弩一个人,而有可能是一群人。事实上,已经存在以聂绀弩为代表的具有相近甚至相同诗风的诗人群体,而且似乎有理由预期这个群体可能会越来越大。后唐宋体因聂绀弩的创作实践和辉煌成就而得以确立,也必将因这一群体诗人的努力而傲然屹立于我国的诗史。
“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胡乔木也许正是因此而当面表扬聂绀弩“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其实,倘若聂绀弩真的“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他就不是聂绀弩了,我们也就没有《散宜生诗》了。王梦奎说:“我对他(指胡乔木——编著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颜欢笑。”(第5页)他的不同看法自有有理的一面,而且似乎还比胡乔木深了一层,但也不全对。试看集中《武汉大桥》十首等作,胡乔木难道说错了吗?况且即使是写“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颜欢笑”的篇什,也并不是“辛酸、无奈和强颜欢笑”所可完全概括的。胡、王所见之异,实在是一个沉重、敏感的话题。平心而论,以胡乔木所谓“思想改造”的标准来看,聂绀弩显然是不及格的;但今天看来,他也是显然被改造过的人。这两个侧面都在他的诗里得到了反映,当然是以前者为主。
再看聂绀弩对胡乔木的态度。1982年6月8日他致信胡乔木:“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至云欲觅暇下顾,闻之甚骇,岂中有非所宜言,欲加面戒乎?然近来脑力大减,不奈思索,知所止矣。”(第4页) 我何能外?他和歌德一样,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要多说一句的是,这样的信似乎不可能出自陈寅恪的笔下。但,他虽不是陈寅恪,却还是聂绀弩。胡“下顾”时,提出要为其诗集作序,他“居然也是木讷讷的,无所表示”。何以故?“他悠悠地说:‘我怕贵人多忘事,耽误我诗集出版的时间啊!’”(第5页)好一个“悠悠地”!真让人高兴与钦佩:诗始终是他的“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这就是聂绀弩之为聂绀弩的真实面目。
《散宜生诗》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第四草》四个部分。《北荒草》是《散宜生诗》的精华。它是聂绀弩的代表作,更是聂绀弩体——后唐宋体的标志性“建筑”,其艺术高度一时可能很难被人超越。它是诗中之诗,美中之美;它是旧体诗诗史上一座突然耸起的高峰,若有幸登临其上,往后看约八百年,是“一览众山小”,对于不少唐宋体作品,只能说它们“好得很平庸”(借用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评论某些外国文学作品的话);往前看呢,“齐鲁青未了”。没有《北荒草》,就没有诗人聂绀弩;没有《北荒草》,后唐宋体就还只能处于学步阶段。据友人见告,有的人于我对唐宋体的批评非常愤慨,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由衷恳请他们花点时间读一读《北荒草》(《散宜生诗》全本1982年版共99页,《北荒草》只有23页),也许就会重新思考我关于唐宋体和后唐宋体的言论。
《北荒草》极大部分都是以日常劳动为题材的,于其主旨,仅仅根据侯本提供的相关资料,可谓众说纷纭。略加梳理,大体上似乎可以归为如下三种见解:一是“歌颂劳动生活”(第20页)。“右派到北大荒改造,事情本来是强迫的,而在那原始而粗犷的劳动中所涌起的诗情,却是自由而美好的……他确实下到边远的地方劳动;但不料这些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又反过来激动了诗人本身。作者采取了讴歌这些劳动的态度。”(第923页)一篇题为《忆叔叔聂绀弩》的文章说:“他写出了北大荒人特有的豪迈精神”,“他写出了北大荒的风情特色”,“他写出了北大荒的生活情趣”。他“热情地讴歌生活,向往未来,干劲十足,《北荒草》是有力的证言”(第923页)。还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有的作品是“向‘政治’硬贴……以媚态邀宠”(第27页)。二是“歌颂是复杂的,复杂到包括了‘滑稽亦自伟’以至于阿Q气”,“有时是‘勉强歌颂’”(第27页);有的论者认为,“人们惊叹他那种与命运抗争的亦庄亦谐亦冷亦热的情怀,却也感到有一种‘阿Q气’”(第922页);有的则说“这些诗充满着乐观而又苦涩、豪迈而又辛酸、悠闲而又沉重的生活情趣”(第923页)。三是舒芜认为它们“是写穷苦的绝唱,写出那样人所不堪的环境中的一个不失人的尊严的人”(第925页);党沛家说:“《北荒草》是战胜自我的胜利之花,它向你展现出血与泪的风采。《北荒草》是一枚艳丽的苦果,它让你赏心悦目,也让你品尝它的苦涩。” (第926页)
《北荒草》和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是一个鲜活、复杂、丰富、深邃的生命体,不同的读者自然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内涵,产生不同的感受。也诚如陆游所说,“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它总是让读者常读常新,永远读不尽、说不完。上引除了“邀宠”一说我完全不能同意外(其实此说也不能认为全是臆造或歪曲,而很有可能出自所谓“恨铁不成钢”的动机),其他各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第三种,于我心有戚戚焉!
不过,一,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二,即使结论基本相同,各自也很可能有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解读。试尝言之。我觉得《北荒草》作为抒情诗,和一般的抒情诗不一样,它其实有两个抒情主体,一个是从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真诚追随革命的革命者,面对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的社会现实,面对由于对党的无限信任响应党的号召而诚恳建言却遭受无情打击的个人命运,因而痛苦、悲愤、无奈的真正的人;一个是身处劳改农场而要继续求生、不得不妥协甚至驯服的普通平凡的人。相对于后者,前者是一个大写的人,而正是这个大写的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却不能不受到后者的掣肘——但其作用也并不完全消极,因为它经常具有类似“安全阀”的功能。在北大荒,时时面临所谓“清查”的威胁。当年的监狱干部回忆说:“‘文革’时监狱经常搞清查,1972年清查时,他所在中队干部对聂用各种纸片、笔记本写的东西,审查不清。我去过他们中队,但有些我也弄不明白,和中队干部商量后,决定直接向聂询问……”(第24页)。即使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他想要出版他的诗集,也得接受出版社的审查,面对一个曾经是“右派”的人,尤其是事关政治,审查一般都特别严格。这是谁都知道的常识。就在他回到北京之后,连胡乔木要来看他,他也有惊恐之感,“闻之甚骇”,担心“中有非所宜言”。聂绀弩,作为一个诗人,激情像火山的岩浆在喷发,他说,“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当然也“希望得到赞赏”,“并印成油印小册送人”(第10页)。诗,情不自禁地要写;而且又要给人看,还想出版:在他身上的两个人即两个“我”就免不了一场又一场的博弈。既是博弈,就免不了有进退、有妥协。他的诗,往往是这种博弈的结果。我们从诗作本身和修改过程都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这种博弈的痕迹。令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和敬佩的是,那个大写的人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的诗作是大写的人伟大的篇章,他的诗歌艺术是两个“我”成功博弈的艺术。
作 者:王尚文,学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