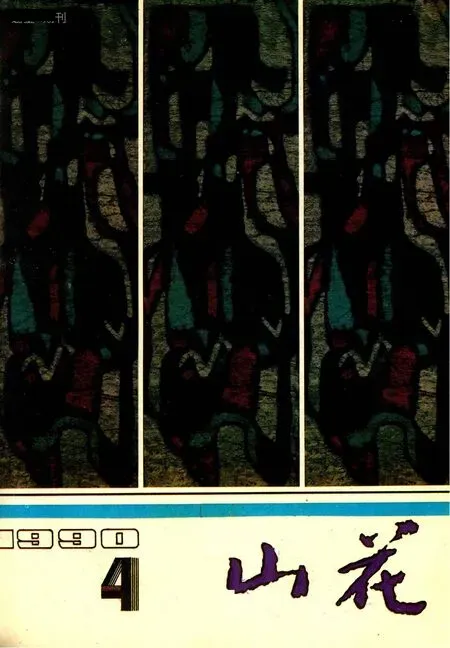中国传统书画关系的变迁
2011-08-15赵振宇
赵振宇
中国传统书画关系的变迁
赵振宇
中国画是以线造型的,与汉字用线结体,不仅在性质上有相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对线条的美学理论的一致。因而,线条的书意美,成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审美前提。另外,由于中国绘画工具和书法工具的相同,以及中国书法美学的早成,这就从观念和实践上制约了中国绘画始终未脱离“写”的特征。如清初著名的花鸟画家浑南田说“有笔有墨谓之画”,这句话很朴素地指出了中国画中笔墨的重要性,很能代表历代画家对中国画的基本特点的看法。
很早以来,画家们特别是士大夫文人画家就将书法的结构、用笔运用到绘画中去,以加强绘画的表现力和艺术趣味。自宋始,人们愈来愈鄙弃五代以前那拘谨刻板的线条勾勒,书法的原则渐渐渗入到绘画中来,使绘画手法愈来愈倾向于“写”而逐渐背离了“描”。于是,到元代出现了泼墨大写意。宋代苏东坡除了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外,其书法成就对他作画亦有很大帮助。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客观世界,而且更在于描绘本身的线条、色彩,它不仅是种形式美、结构美,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结构,传达出人的主观精神境界。元代以前的画多在绢上,自“元四家”起,大多画在宣纸上,这就便于发挥笔墨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些都与中国书法是相同的。
元代开始了画上题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互相补充、结合,这是唐宋和外国绘画所没有的。唐代画家在画上题款,但常隐于石隙、树根处,宋人画上也尽多写一线细楷,处于极次要的地位。元人画则不同,上面的诗文有时多达百余字,占据了很大画面,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方面使书法和绘画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相配合呼应;另一方面也借诗文来明确表达其含义,从而加强画面上的诗情画意。这种利用书法文字再加上朱红印章的配合补充,深刻而灵活地加强了绘画艺术的审美因素,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传统。
从汉隶以后到狂草,书法的象形的特点逐渐消失了,它与绘画之间的联系已不完全是客观形象上的联系,它已经不再是“画”,它有了自己规范的抽象符号,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字的形态不能也不可能从对景写生中获得全新的印象和作出主观出发的表达,唯有从前人代代衍传的约定俗成的基础形态上,作很有限的变动,它不得不以“字”这种特定的具体形象规范为依据,草书的笔画无论有多大变化,无论它颠逸到何种程度,也是可以辨认的字的变形,最终也不能摆脱草字的形象对它的限制,否则,它便不成为文字,而是抽象的线条的飞舞,也就称不上是书法艺术。
对于中国画来说,它十分强调“写”,但作画毕竟是“作画”,而非“写字”。其作品,也毕竟是画而不是“字”。在中国画中,虽然吸收了书法因素,然其书法笔墨已是被融化和转变为它的“画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笔墨无论怎样变化,也始终从属于“造型”之功能,而非脱离“造型”的功能。所以中国书法艺术所创造的形象不同于中国画所创造的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独特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传统书画,同中华民族一道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包括文化的冲击、政治的干扰、经济的侵蚀等,历经沧桑,长盛不衰。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共同构成了世界绘画艺术的总和,当今唯有中国书画能与西洋美术分庭抗礼,千百年来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为中国书画悠久、灿烂的历史而自豪。
近年来,随着西方美术思潮的东进和电脑美术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思想浮躁,中国传统书画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迁。
一、传统书画关系亲如姊妹。
从中国古代书画理论以及传世书画作品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书法和中国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书法和写意画之间,这种关系更为密切。
1.确定评价标准。朗读的评价,在标准上我们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读得是否正确,二是读得是否流利,三是读得是否有感情。
李苦禅曾经说过“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书法喜狂草,绘画尚水墨大写意,“书画同源”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理论,传统绘画的基础就是书法,一位优秀的画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这是人们的传统认识。
在中国传统书画的工具材质上,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都离不开笔墨纸砚,即毛笔,松烟、油烟墨,还有宣纸和砚台。由于毛笔自身的特性,伸缩的幅度极大,其笔画粗细、轻重、刚柔、方圆、浓淡、枯润,变化非常丰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形式使得书法与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书画家的气质、个性、技巧各有不同,在用笔上大有选择的余地,使作品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体态风格,从有限的点线到无穷的变化,充分发挥笔锋曲尽点线变化之妙。传统书画艺术之美,即由此产生。
中国绘画执笔也等同于书法,虽然掺杂着各人艺术禀性或喜好不同,执法也各有变化,但基本握笔姿势仍是“指实掌虚”,执笔灵便的“按、压、钩、顶、抵”五指执笔法。
传统书法与绘画都以线为先,线条是中国艺术表现的灵魂。书法运用线条表现了文字,传达了书者的情感、情绪和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等。中国画无论工笔或是写意也都主要以线来描绘物象,尤其在传统中国画当中,最具审美价值的莫过于线的艺术。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骨法用笔”就说明了这点。唐代张彦远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现代画家潘天寿先生也曾说:“一为点易于零碎,二为面易于模糊平板;而用线则最能迅速灵活地扣住一切物体的形象,最为明确和概括。”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画是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绘画。因此写意画的作画过程必须像书法用笔那样“全其骨气”,同时具有书法的“节律美”,才能形成雄健古茂、圆润苍劲的线条,才能扭转线条的糜弱之势。而这以书法线条入画的手法不叫“画”,不叫“描”,就只能叫“写”。 如清初著名的花鸟画家浑南田说“有笔有墨谓之画”,这句话很朴素地指出了中国画笔墨的重要性,代表着历代画家对中国画的基本特点的看法。
另外,书法与写意画的相同之处还表现在他们的用笔和用墨上。在用笔上,对书法的要求,钟繇曾说“多力丰筋者胜,少力少筋者病”,这在写意画中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写意画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笔断而气连,止笔不轻挑。国画运笔之妙旨在平、留、圆、重、变(黄宾虹)。如将其用于书法也是同样可行。
从传统来看,特别是在宋元文人画出现以后,绘画用笔越发地讲究从书法中得来。南北宋时期出现的许多大文人画家,不仅善书也善画。如黄庭坚、苏轼、米芾父子等,均以书法入画,重视并发展了笔墨情趣和技法。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还有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写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都提出书画同源的说法,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黄慎的写意人物,创造出狂草笔法入画的独特风格。行笔“挥洒迅疾如风”,气象雄伟;吴昌硕数十年写石鼓文,以篆书入画,写意作品浑厚有力,雄健苍茫;黄宾虹晚年把所有的形都化为书法的线,作品呈现出浑然忘我,一片空灵之境;齐白石以书入画,其非凡的书法功力使他笔下的虾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给写意画的发展以十分重要的启示。
用墨上,写意画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对比调和,以塑造主体,烘染气氛。而书法,特别是草书的书写上也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没有关系的对比,就没有作品的丰富性,故书画同理。
而且,在笔墨运用的顺序上,书法和写意画也是一致的。比如国画写生,当第一笔下纸时可能笔头蓄有较饱满的墨水,并且笔尖与笔肚的墨色不一,这样笔随物转,一笔一画由湿至干,墨色也就由浓至淡,此时的干笔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在纸上画出飞白的效果,与之前的湿墨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善于利用各种干、湿、浓、淡的对比,作品才会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受,且效果丰富。纵观书法用笔,大抵如此。
传统书法和写意画都是借助笔墨表现线条形式,强调艺术的象征性和人格的理想化,反映创作主体的“心源”。东汉扬雄称“书为心画,画为心声”,书画家们都是借助书画所特定的程式以抒发自己的感受,来成就不同风格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写意画与书法都是从笔墨的角度出发去感受物象精神的。
宋赵希鹄在《洞天青禄集》有一段话,兼评米芾曰:“画无笔迹,非谓其墨淡模糊而无分晓也,正如善书者藏笔锋,如锥画沙,印印泥耳,书之藏锋在乎执笔沉着痛快。人能知善书执笔之法,则知名画无笔迹之说。故古人如孙太古(知微),今人如米元章(芾),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书画其实一事尔。”这里更明确地指出了书画的密切关系。
书法和写意画之间其实是在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和互为补充中相互发展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书法也是最概括、最抽象的写意画。写意画笔法墨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互为补充。
二、当代书画的关系形同陌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制度逐渐西化,同时应试教育又起了主导作用,中小学校的课程表中,“写字课”却难得一见,甚至彻底消失。国内许多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的教师)写得一塌糊涂,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在这种环境下,美术院校有许多中国画系学生连毛笔的基本技巧都掌握得不够正确。众所周知的是书法和诗歌对中国画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的,没有书法的用笔就没有中国画的笔墨,没有诗歌的内涵就没有文人画的独特审美观念。诗书画印一体往通常是历代画家所极力追求的。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不少年青画家的作品画面平淡无奇,格调不高。李可染说许多青年画家在某些方面超越过前辈,但是笔墨和书法上,还远远赶不上前辈。因笔墨欠缺导致画面软弱,严重降低中国画的特色。他主张青年画家要重视书法因素在自己的创作中的重要性,又强调指出青年书法家们要能够将中国画笔墨线条的审美概念融通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在两方创作中都能体现“书画同源”的核心精神,从而具备相应的书法基础,再次发展中国画的笔墨,就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电脑时代、无纸化办公的来临,人们用笔写字的机会更加少了,代替的是整齐划一、字体相同的打印机产物。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节奏,几乎没人能静下心来潜心习字,因此,硬笔字写得整齐有力的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毛笔,导致当代大多数画家的笔墨衰退了许多。投机取巧的心理便日渐明显,用一些特殊技法来盖住笔墨方面的不足。几乎把能增强画面冲击力的手段都用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画展览几乎是工笔大画一统天下,写意画明显减少,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无款和穷款。可见书法在当代国画中的关系已退到无关紧要的地步,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真正能理解并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画家已经越来越少。时代在进步,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却日益疏远。“书画同源”已经是艺术理论的虚设,如今绘画的发展已不受书法的影响,中国画的创作、教学和评价标准、方法体系已经改变了。“骨法用笔”被当代画家所淡漠,转而去强调没有笔意的图式化、装饰化、符号化,强调肌理、效果制作、刻画、描画、表现材质,“工艺化”成了当今画坛的主流,真正意义上的写意画家已是凤毛麟角,中国人特有的人文精神在当今国画作品中难觅踪影。从当代绘画的开放势头看,好像要使中国画发展和创新,就应该先和书法划清界限。
三、对“书画同源”的再认识。
中国画通过书法艺术练习基本功,并从中吸取营养,中国画与书法共同发展中,一直有互为增益附丽之功,加上中国画以线为主的骨法用笔,就又有“工画者多善书”之说。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审美传统的正常关系。美学家李泽厚说:“不懂书法,就不可能懂中国艺术。”黄宾虹说:“画之法不在位置而重在笔。”由此可见中国画与书法的骨肉关系,不研究习好书法,也很难领会中国画的用笔。
纵观中国书法和中国的发展史,中国画和书法不仅有着共同的起源,用笔技巧和基本思维方面有许多惊人的类似,而且在艺术意境的追求和审美要求上也有诸多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书画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书画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毛笔有其局限性,其适宜表现较小、较细致的东西,对于鸿篇巨制就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当然可以借鉴其他的方法和工具。笔者认为书法入画不是画好画的决定因素,但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不是说中国画的艺术高度取决于书法的水平,但如果完全丢弃这一核心的表现因素,中国画也就失去了笔墨线条的美感和韵味。在实在的工具材料和虚无的文化精神高度一致的书画领域,两者应该相互渗透和借鉴。
[1]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6月.
[2]常平安.论中国书画之关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1988年第三期.
[3]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4]徐晖.略谈书法和绘画的关系——书画同源[J].消费导刊,2010年3月.
[5]周宁.中国书画史话[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赵振宇,工作单位: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