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三叠
2011-08-15刘鹏旋
◎刘鹏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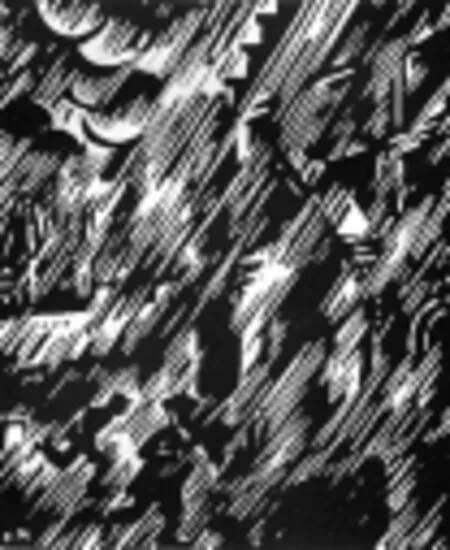
母亲的烟摊
兄弟几个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靠父亲的微薄工资已是难以维持了。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母亲在古镇黄桥最为热闹的大石桥摆起了烟摊,以卖“老宝成”旱烟为主,兼卖些小百货、小杂货之类。
说起“老宝成”旱烟,可谓是闻名黄桥周边的乡乡镇镇。老宝成烟店前店后厂,制作工艺独到,黄灿灿的烟丝细嫩油润,古朴的包装棱角分明。街上的,乡里的,无论贫富,大凡抽烟的,都青睐“老宝成”,只是街上人是托着水烟筒过滤着抽,乡里人是翘着旱烟袋“叭嗒”着抽。
只要是假日,我总是很乐意帮母亲看守烟摊。三分是懂事,七分是迷恋大石桥街头的种种风情。看不够的是满街人头攒动:推车背纤的、肩挑提篮的、携老带幼的,车拥着车,人挨着人,川流不息;听不完的是八方涌动的交响:人挤车拥的吆喝声、妙不可言的叫卖声,炸炒米的爆花声、铜匠担子的丁当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难以忘却的是一个个肩挑生活重担、满脸岁月风霜的旱烟老头:才过四十,黝黑的脸上开始放出光芒;踏过五十,腰板还硬像把弓,叭嗒着抽几口旱烟是生活中最为享受的滋味……
西乡的丁老头又上街了。提着的还是那只古铜色四方篓子。半篓子小麦上放着二三十只鸡蛋,匆匆地走过母亲的摊头。不过一刻钟,匆匆来了,什话没说,解开烟包,三指合力捏起一颗大烟团,往烟袋头里重重一按,叼上了嘴角,因为迫不及待,两手几乎有些颤抖着划着了火柴,火苗紧挨着烟团,干柴烈火般地一口气抽了五六口,没见吐出烟来,只清晰地听见烟袋里发出的“吱吱”响声。丁老头那张绷紧着的脸开始舒展开来,不一会儿,万份满足地朗朗地笑出声来。痴痴地看着丁老头无以言状的快活和陶醉,我只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一袋烟毕,烟瘾未足。丁老头将烟袋头往台板上轻轻一敲,落下的仅是一粒火柴头大小的烟苗。又燃着了满满的一袋旱烟,这才吐出一句话来:为了烟虫子,鸡蛋少卖了一分钱一只,值得啦。向母亲道了声别,丁老头到蒋家胖子烧腊摊子上买一碗牛杂汤、叫二两瓜干白,美餐了一顿;又去珠巷浴室泡了把澡。回家路过母亲摊头时,已是太阳落西了。只见得,丁老头的脸上,皱纹推出了波浪,写满了笑意。母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丁老头弯弯的背影,频频地点着头,自言自语:丁老头今天过年了,知足者长乐呀。
快过年的时候,溪桥的翁老头上街办年货了。搁下担子,一头装的是请的喜笺、对联、年画,一块刚从染坊染好的蓝色土织布,另一头装的五根肋条的猪肉。翁老头乐滋滋的,朝着母亲如数家珍地点说着要卖的杲杳:两只网鬏给老奶奶的,用小钱讨个欢喜;一把四寸木梳,一面六寸镜子给儿媳的,农民佬儿的媳妇也要讲个有头有面;两只气球泡泡给孙子的,伢子儿乐大人也乐;二尺红牛筋给女儿的,见红为喜,明年嫁个好婆家;一支旱烟袋,过年留着客人用,自己抽烟,不能让客人闲着;旱烟四包,正月里就不上街了。母亲也乐着,说了句恭维话:算计好了的八样,合家欢乐,来年大发呀。
翁老头话锋一转,侧指着隔壁的何郎中:就是拔牙的事还在算计呢。上次庄上有个老头被他的老虎钳钳得连人都站起来了。母亲心领神会,装满一袋旱烟,走到何郎中身边,递上烟,点上火,笑道:翁老头是我的回头客,拜托何先生麻药上客气点。毕竟是江湖中人,何郎中一边应声“好好好”,一边从案板下面取出一支麻药水,衣袖一挽,三下五除二,就将翁老头的一颗蛀牙轻松拔出,塞上棉球,“铛”的一声,蛀牙落在瓷盘中。翁老头立马道谢:妙手回春,妙手回春,过年好吃肉了。哈哈一笑,刚塞进的棉球随着笑声蹦了出来。何郎中随手补上棉球,“嗬嗬”直笑:刘家奶奶拜托的事,有什好说的,以后多给她来点生意就是了。翁老头付了拔牙钱,又从竹筐里取出卖剩的三只有点破的鸡蛋送给何郎中,以表谢意。
我始终在一旁注目着,心里清点着身边的快乐。翁老头抿嘴笑着,鱼尾纹四射着光芒,喜乐而归;何郎中受了恭维,做了人情,得了回报,乐在其中;母亲做生意如做人,为了生活,为了儿女,其乐无穷!
父亲的乌蓬船
父亲是只身搭乘一叶乌蓬船来到黄桥的。
做牛马活、遭饥寒罪、受打骂苦,当属那个年代穷人谋生必跨的一道槛,如同孩时学步总要跌跟头一样,只是父亲跨这道槛的年龄让人心酸——才十四岁。三年学徒,身单力薄的父亲也许是苦活重活干得太赤诚了,留下了两侧走肠的患疾,不用那钢板别子束在腰间阻抑着走肠是不能走路的,这种被束缚着的痛苦让他背负着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父亲满师时,爷爷奶奶已经故去,孤单单一个人靠帮店家到江南一带跑单帮糊口。恰是父亲至诚厚道被外婆家看中,与母亲成婚。外婆家在小镇上开的“天顺昌”肉铺颇旺,母亲在家最受宠爱,亦因父亲孤身穷汉一个,外婆家的陪嫁很是丰厚。母亲上轿前又撒了一会娇,让外婆又在陪嫁中增加了五十枚“袁大头”,才让父亲得以开了一家碗店,名曰“发达磁号”。告别了孤苦、穷困,父亲为刚出生的哥哥取名鹏春,愿景着家连着店的一叶乌蓬摇向春天。令父亲一直痛恨于心的是当年突起的那场金圆券风潮,让碗店被刮得近乎于倾家荡产。父亲曾告诉我,南京政府快崩溃时,强行向百姓收购黄金,改以金圆券流通,刹时间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一落千丈,早上五十万面值的金圆券买到一打火柴,到晚上只能买到一盒,大小商家顿遭灭顶之灾。碗店被迫歇业后,又逢母亲四年生下四个子女,父亲在自家门前摆着修钢笔的小摊,日日所得无几,母亲的陪嫁被卖得精光。父亲背负着六口之家生活的全部,举步维艰。
公私合营那年,父亲经好心人介绍进了供销社,时年三十四岁,工资三十四元,年岁与月薪之和竟是“禄发”。父亲相信会带来好运,珍惜着养家糊口的饭碗,直到六十六岁单位准他退休,年年先进工作者榜上有名,救济榜上亦年年有名,且数额最高,在单位是出了名的。
经父亲之手保管过数以万计的山珍果品,他从没沾过一点滋味。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得了浮肿病,他也没打过库存商品的主意。实话说,我倒是沾过,也让我难忘。日杂仓库在西门桥下时,父亲管着茶食坊,那香甜味儿对吃不饱肚的孩子是诱人的。那次看着师傅们做着冰糖,我不由自主地流着口水,有师傅看在眼中,端给我一碗清洗料盘的糖水,让我透心地甜至今日,那师傅却遭父亲说了不是。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馋了,偷吃了两颗黑枣,父亲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打得父亲自己眼含泪水。那是唯一一次让我看到父亲动怒的样态,嘴唇颤抖着,五指颤抖着,看出父亲的心好一阵平不下来。父亲是把公家的东西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把儿子的品行看成是自己的尊严。春哥说,父亲是供销社的末代忠诚,倒是没有夸张。父亲管的仓库,堆放的商品如同接受检阅的列兵方阵,从来没有走样的;计划供应的商品,凭票券供货,多出的那怕是一斤白糖、一只锅盖,从来没有自行做主的;跨年度的干果,夏天伏晒装缸,缸底置酒防蛀,缸口密封防潮,从来没有霉变虫蛀的;入库的商品一一过手,稻草裹扎的碗二十只一支,手一托便知破损几只,从来没有出入差错的;年终的算帐盘点,必定是帐物相对一清二楚,从来容不得秋毫之差。那年黄桥中学扩建校舍,每个学生要交一箩碎砖铺基,春哥到仓库要一箩碎碗瓷片交差,父亲便要捡出碗砣,春哥不解:“碗砣有份量,瓷片能有多重?”父亲告诉春哥:“碗砣不行,报损是要凭数说话的。”虽说事小,让春哥明白凡事总有界限的道理。我暗自解读,父亲对工作的这种忠诚,是自己人格的一种保持,是直面人生的一种态度,是比钱值钱的一种价值。
父亲退休回到家里,却让母亲从过去想到眼前,从发根想到发梢,唠叨着说着往事。而父亲苦够了、忙够了、退休了,却没有听够母亲的唠叨——“老头子,我在娘家哪个不宠,一年四季享着福,跟着你为奴,衣食住行都得愁,愁得我白了头。”“老头子,你蹲仓库苦得不经风雨,我街头摆摊是风刀霜剑啊。”“老头子,我娘家陪的金银首饰、亮橱雕床无所不有,你得陪我。”
那天全家为父亲七十寿辰祝寿,是母亲自己为父亲斟的酒,也是母亲第一个举起杯说着祝辞的:“老头子,我在娘家还享了福,你是苦了一辈子,我嘴上唠叨,心里高兴啊,当年你乘的那只乌蓬船在风浪里走、苦海里行,终于苦过来啦,刘家儿子们争气胜过家财万贯,祝福你啊……”
哑巴兄妹
租住在成家大院的时候,我家与两个亲兄妹的哑巴相邻,童年的记忆使我至今难以忘却。
兄妹俩从乡下而来,与成家大院前后三进的主人皆为门房兄弟妹。女哑巴珍珠住后院一间便房的两廊屋,男哑巴长林住后院的一间厢房与我家紧邻。各自凭着一双手揽百家的活计,品百家的滋味。
女哑巴珍珠,操一手令人羡慕的针线活计。踏进主家的门槛,随身带一只针线匾子,装着的便是量尺、粉片、剪刀、针线包、火熨斗。从量体开始,一家老小要做的衣裳一次量毕,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分寸尺度尽印记心中;随摊料裁剪,划粉线如行云流水,下剪刀则干净利落,将一件件衣裤剪裁得明明了了;待针线上手,一根银针在十指间穿梭流星,让大大小小的片片布料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最是熨烫整形,燃一块木炭,让熨斗热情满怀,熨遍条条线缝、边边角角,顿叫件件衣裤显露芳容、抖出神采。珍珠做的衣裳,胖子穿着精神,瘦子穿着合身,年长的穿着年轻,年少的穿着美丽,其手工之精巧令人叫绝。然而,珍珠所执着的是只做中式衣裳,一概手工缝制。
男哑巴长林,体格健壮,专司上门浆洗的活计。只要主家相邀,全凭一双大手、一根浣杖,衣裤被褥蚊帐一律手工搓洗,随后下河汰净,待挂晒晾干,衣裤叠放整齐,被褥缝摊到位,蚊帐悬置停当,满屋便飘出阵阵水花清香。长林不洗的是女人的裤子,日子久了小镇上没有人不知道的。兄妹俩珍珠小长林八岁,分开着过日子,生活上相互照应着,要算珍珠更能体贴细微。长林一身整洁的衣裤鞋袜珍珠包揽着不在话下,过节包扁食、端午裹粽子、中秋涨烧饼、春节做元宵,珍珠操持为主,长林打打下手。平日,长林的米坛空了、衣衫破了、手头紧了,甚至哪日晨起见着长林扔了牙膏壳,总是珍珠送上“及时雨”,兄妹之间流淌着浓浓的手足之情。
兄妹俩虽共生无言的世界,却脾性各异。成家大院的老老少少日日品味着他俩脸上挂着的喜怒哀乐。珍珠性格朗朗的,每天早早而出,从后院踏过三进屋子,直至走出院门,一路满面微笑,给大院的家家老少送着问候;每天日落而归,带着笑容从院门一直飘进自己的小屋。长林则喜怒于色,开心时还露点笑容,笑得很是直白;遇有侵之秋毫,那张涨得像猪肝的脸,谁见着都毛骨悚然,甭说大院里,就连布巷一条街上,谁家的孩子或倔犟、或闹夜了,大人们只要说一声“男哑巴来了”就能吓唬住的。
那次真让我见着长林发怒一回。调皮的春哥疯玩时碰翻了长林门前晾着的糯米粉。顿时,那副猪肝脸上一对眼珠愤然欲出,张大的嘴“怒吼”着,右手操一把菜刀追向春哥逃脱的方向。母亲见状,急切地横路一挡,一面频频点头哈腰讨饶着,一面急促地打着手势,先是双手捂住胸口表示“我”,双手朝前一摊示意“赔”,随即赶忙从衣袋里掏出两块钱塞到长林手心。只见他那愤怒的脸陡然折转成笑容,头连同整个身子摇个不停,示意是吓唬的。这有惊无险的一幕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其实,母亲平日与哑巴兄妹俩一直相敬相帮。家里偶尔一次的改善伙食,母亲想着的就是长林。记得那日母亲病了,是长林帮家里挑满了一缸井水。尤其是珍珠,我们兄弟几个见着她时总是满脸的春风拥着笑容,让人倍感亲切的。那天,珍珠和母亲正用手比划着聊天,见母亲的衣襟划破了一道口,随手掏出针线为母亲就身缝了起来。母亲被感动着,转身回去从箱子底拿出珍藏多年的旗袍送给珍珠,那是母亲年轻时在上海霞飞路买的。
次日早晨,珍珠一跨出房门,真是让人看呆了。母亲送的那件旗袍配在珍珠身上再合适不过了,紫罗兰色的织锦缎面、领口袖口上绣着彩蝶花丛。那精致的做工、精美的图案与珍珠眉清目秀的脸蛋、端庄匀称的身材、垂至臀部的长辫相映衬,流泻出珍珠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美丽。母亲是因直面生活贫困的朝朝暮暮而淹没了修饰自己的那份心情,珍珠独自在无言纯真的世界里无时不涌动着对美好的向往。从此,珍珠迷恋上做旗袍,用一双巧手为自己装点打扮,当她一路走过,简直就让小镇生动了起来。
那年,镇上办阶级教育展览,展出的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绫罗绸缎的面料、衣衫、绣花鞋,引人入胜的是几十件款式各异、花团锦簇的旗袍。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不外乎受教育的、看稀奇的、凑热闹的。唯有珍珠是看美丽、看精致、看奥妙的。展览了三天,珍珠痴迷了三天,快乐了三天……
时光流逝这么久了,我真的忘不了哑巴兄妹,从心底里钦佩他们,那无言的世界里有那么多的纯朴和美丽,让多少伶牙俐齿的男男女女自愧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