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2011-07-26沈念蔡世平
■沈念 蔡世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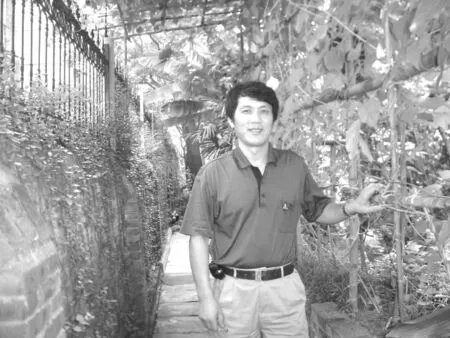
沈念:“熟土难离”,这是您最近一首新词“卖花声”的主题。我们就从您今年8月进京说起吧。有很多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您会选择在已过知“天命之年”远离家乡,只身到京城工作?
蔡世平:我是今年7月31日进京的。7月4日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先生约见我,商调中华诗词研究院工作。来得突然,开始有过短暂的犹豫,但还是答应了。毕竟北京的舞台大,对我有吸引力。人生短暂,有生之年能在北京文化高层生活和工作一段,还是很有价值的。
沈念:那要祝贺您到中华诗词研究院任职。今后,研究院主要会做些怎样的工作?
蔡世平:中华诗词研究院2011年9月7日在北京钓鱼台揭牌成立。国家给了15个编,为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兼任院长,三个副院长,我还是年轻的。中华诗词研究院为国家成立的首个专门诗词研究机构,主要工作是旧体诗词的研究、创作、评鉴和对外交流,旨在繁荣和发展优秀的中华传统诗词文化。
沈念:对旧体诗词的研究和重视,自然会促进其繁荣发展。我留意到,几年前,像纯文学期刊《芙蓉》、《黄河文学》,如今还有《诗刊》、《诗潮》等刊物都辟有版面刊发旧体诗词和评论。旧体诗词被主流文学刊物所关注,说明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瑰宝在当下没有消亡而是被激活,您认为其意义何在?
蔡世平:我是在2003年开始写作“当代旧体词”的,这之前主要是写散文。正因为我有两方面的写作经历,既没有站在主流文学这一边,否定旧体诗词,也没有站在旧体诗词这一边否定新诗。应当说,我关注了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只要客观地、宽容地看待问题,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是应有旧体诗词一席之地的,而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应允许旧体诗词这一文学样式存在。近些年来,主流文学已经关注并重视到旧体诗词创作,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国家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不仅是促进旧体诗词的繁荣和发展,而是促进整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沈念:我注意到“五四”以来,新诗取代旧体诗词,成为文学主流。同样的包括戏剧、小说、散文等都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写作,而没有引起争论,唯独旧体诗词与新诗在今天仍然有争议,而且很激烈,这是为什么?
蔡世平:这个问题提得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时代的必然。如果今天还用文言文写作,读者就不买账了。但任何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旧体诗词就有它的特殊性。旧体诗词是不可与文言文划等号的。比如我自己,读文言文有时很困难。但旧体诗词大多情况下一读就懂,相信许多读者都会有这个体会。究其原因是旧体诗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白话文”写作,没有什么“之乎者也”的东西,读者没有阅读障碍。另一方面是旧体诗词极端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美质。只要汉语言文字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以及文学表达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旧体诗词就一定会存在下去。这是毫无疑义的。辽阔的、深厚的汉语言、文字体系,是旧体诗词赖以生存的土壤,亦如白居易的“原上草”,是“春风吹又生”的。所以时代再怎么发展,改革开放再怎么深入,西方文化再怎么冲击,但是中国人吃饭还是用筷子,中国人说话还是短句子,中国人写文章还是方块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厢情愿地去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起码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度是不可能的。
沈念:推动当代旧体诗词融入主流文学,您认为当下旧体诗词创作者该做些什么?文学界从事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的群体又需要以怎样的眼光来打量、理解旧体诗词的存在价值。
蔡世平:当下写旧体诗词的人多,但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旧体诗词作品却很少。这是因为文言文写作时代大多是士大夫阶层写作。这些人都是经过科考上去的文人,写出来的大都可以称作“作品”,现在是人民大众写作,创作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众不可能都是“文人”。又因为旧体诗词有平仄格律的硬尺度,这种“技术活”是比较好掌握的,有的人以为只要运用平仄格律写出来的就是“诗词”,就是“作品”,殊不知当下大多数旧体诗词变成了只有空壳没有灵魂的七言八句,倒了读者的口胃,也败坏了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这就很容易让主流文学轻看了旧体诗词。其实好的旧体诗词还是有的,只是被淹没了。所以恢复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中华诗词研究院在年内召开首个理论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中华诗词的当代审美取向”,以此来提高旧体诗词作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水平,建立起旧体诗词的当代审美标准。我们的小说家、散文家、新诗人也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旧体诗词,自己也可以来写一点,这并不掉份子。曹雪芹、鲁迅、郁达夫等的旧体诗词就写得好。文学精英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很重要的。我读过熊召政的诗,他的旧体诗词也写得好,这使我更加高看他。
沈念:回到几年前,我是您早期“当代旧体词”作品的第一批读者之一。我个人觉得当下能把旧体词写得像您这样“风生水起”、“感觉充沛”,一出手就让人眼前一亮,简直是个奇迹,请问您开始创作旧体词的契机是什么?
蔡世平:2002年春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写了几首旧体词,当时主流文学的陈启文、杨凭墙、李望生等几位文学朋友看了大加赞赏,就这样开始了“当代旧体词”写作,这可能得益于我多年的散文修养。在当时,《美文》的穆涛、刘恪、陈启文等都认为我应当把散文做大。但是我对散文还是缺乏应有的自信,这领域大家太多。我想中国这么大,擦皮鞋都可以擦出名,我就试着来做文学界的一个“擦鞋匠”吧。
沈念:“当代性”、“当下性”,应该是解读您作品的关键词之一,这既是时间的限定,也是语境的约束。您从一开始是如何做到摆脱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普遍存在的表达误区,又是如何找到当代汉语背景之下与传统旧体诗词格律的链接点?
蔡世平:我写“当代旧体词”时已近五十岁了,我感到时间对我的重要。如果说2002年写旧体词只是玩,那么到2003年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文学事业去做了。我从写作实践中看到旧体诗词在今天仍然是活的,并没有死去,仍然可以用平仄格律来表现当代人的情感生活。我对此充满了自信,并提出了“当代旧体词”的概念,这就有了身份的认可。我以为当代人写旧体词一定要有“当代性”。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明确是当代语境下的旧体词写作。我只是借用传统格律的形式来写属于今天的词,成为今天真正的文学。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我认为文学样式不重要,精神质地和艺术含量才是最重要的。
沈念:您创作的当代旧体词是否受到中国传统诗歌或现代诗派的影响,您认为旧体诗词创作借鉴与汲取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蔡世平:两方面的影响都有,或者说汲取了两方面的营养。当代旧体诗词是从唐诗宋词里直接过来的,我在写作中体会到母体的血液还是温热的。传统诗词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到今天还用得上,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而不致贫血。今天的旧体诗词尤其需要借鉴西方文学的表达方式,这恰恰是今天旧体诗词创作非常有利的一面,可以扩大旧体诗词的表现空间。借鉴和吸收的重点,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精神指向,也就是其人文关怀,终极关怀;另一方面是表达方式,可以运用意识流、通感、印象派绘画、先锋文学等许多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来丰富我们的旧体诗词创作。
沈念:创作最大的障碍是重复,最大的动因是创新,您在当代旧体词创作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蔡世平:不仅有这种感觉,而且十分强烈,现在常常感到“江郎才尽”。提起笔来就觉得这个意象、这句话、这个词古人用过,自己也用过,再用就没有意思了。“原创性”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不想重复古人,也不想重复自己。我觉得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词人的创作是有限度的。这个世界好东西总不会太多。制造垃圾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追求是在我的新词作品里,总要有一点新东西,或是语言、或是结构、或是精神意象等。如果没有,我就不想写它。我不靠写词挣饭吃,写多写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得好。我有我的审美标准。我知道今天的好词是个什么样子,我会坚守自己的创作,一旦没有新东西可写,我就不会写了。
沈念:对于日益严重的网络、流行文化,它们对文学特别是旧体诗词影响甚大,您认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其出路和前景是怎样的?
蔡世平:世界总是翻红涌绿,这不必奇怪,也不必惊慌。我并不认为旧体诗词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我甚至觉得旧体诗词的出路是大大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因为汉语言文字还是强势地存在于人类文明中。别的什么文明要想吞噬和取代它,永远只能是单相思和梦想。有着几千年传统,十多亿人口的汉文化,其母语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谁都打不倒她。另外,现在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中国人口这么多,只要拥有其中的一“元”,就是一个大数字。流行文化可以轻看旧体诗词,但却无法灭掉它。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旧体诗词突然又“流行”一下子,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沈念:国内对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评论氛围怎样,您认为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为创作群体的成长提供更丰厚的文化土壤?
蔡世平: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稳定的社会生活和良好的学术条件,以社科院和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对古典诗词的评论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成果十分丰富。但对包括民国以来的近、当代旧体诗词的评论研究还很薄弱,一是受政治的影响,二是受活人的影响,怕费力不讨好,这可以理解。这也给当下旧体诗词评论和研究留出了很大的空间。研究和评论近、当代旧体诗词,给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以指导,具有现实意义。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是把诗词研究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会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今天的旧体诗词创作迫切需要理论支撑。
沈念:旧体诗词在二十一世纪以它特殊的方式复活,将不再是边缘化文学。可据统计,目前中国约有500多种旧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旧体诗词新作在10万首以上,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超过15000人,创作队伍达上百万人。这么庞大的队伍,汇聚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根,您如何看待培育年轻创作者这一新鲜血脉的注入和延续?
蔡世平: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旧体诗词的复苏期,二十一世纪应当是旧体诗词的复兴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民族母语诗歌自信力的一种表现。尽管大多数诗词不能称其为作品,但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要持欢迎的态度,培育中华诗词文化生态。相信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中,一定会产生优秀的诗人词人。我同时希望我们的主流文学刊物能够以宽广的胸怀,重视和关注旧体诗词创作,给旧体诗词以时代温暖。《文学界》能拿出宝贵的版面,给我这样一个旧体词书写者做专题,真的十分感动,我对《文学界》表示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