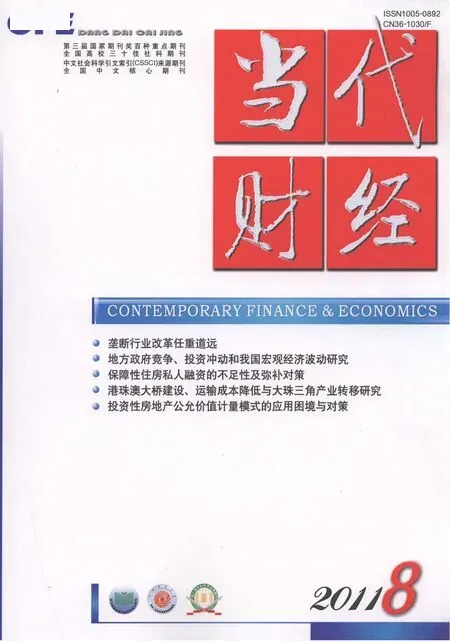电信广电应分业规制还是统一规制——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1-07-02张昕竹冯永晟
张昕竹,马 源,冯永晟
(1.江西财经大学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2.工业与信息化部 电信研究院,北京 100191;3.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一、引言
在当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经济调节、市场规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成为现代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其中市场规制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但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施政府规制并没有统一的模式。2010年初,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电信和广电行业开始互相向对方开放部分业务。为了保障双向进入的顺利推进,迫切需要解决相关的规制制度设计问题。
三网融合是一种生产力变革,它必然涉及到规制体制等上层建筑的调整,以适应三网融合的技术要求。长期以来,由于技术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原因,我国对电信和广电一直实行分业规制,这种规制模式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在网络技术不断融合的条件下,现有的规制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日益融合的技术和业务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国务院要求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规制政策体系。
如何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规制体制,一直是近年来理论界和业界争议的热点话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问题是,是否应该改变电信和广电分业规制的现状,设立一个融合的规制机构,对电信和广电进行统一规制。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应建立统一的规制体制,这将有助于打破部门利益之争;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在我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下,分业规制是更好的选择。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在三网融合时代,我国应选择什么样的规制体制。为了回答这个重要的制度设计问题,本文将利用国际电联的各国电信和广电行业规制机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离散选择模型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一个国家在三网融合时代的规制体制设计,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的规制体制选择。
二、文献回顾与综述
规制制度的出现,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1-2]而规制体制设计是规制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表明,尽管不同国家规制制度演化的路径有所不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共同影响着规制体制设计:一是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它要求规制体制必须满足技术理性约束;[3]二是政府的政治组织架构,[4]这个制度条件要求规制体制必须满足制度理性约束。
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由此导致不同的规制体制选择。运输、公共事业等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规模经济特征,因此通常设置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规制机构。考虑到不同的公共事业需要的规制手段有很多相似之处,为此还常常在地方政府层面设立集中的规制机构进行规制。对于电信、铁路和供电等行业,规模经济要求这些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运营,并且需要的规制手段比较复杂,而且跨区域协调成本比较高,因而出现了国家层面的规制机构。[4]
针对电信业的技术经济特征,Laffont和Tirole(2000)系统讨论了电信规制所面临的定价、网间结算、普遍服务等问题。[5]对广电行业而言,Waterman(2004)、Crampes和Hollander(2008)指出频道规划和内容管制是广电行业面临的独特的规制问题。[6-7]在三网融合时代,Crampes和Hollander(2006)指出,无论是电信企业还是广电企业,它们采取的多业务捆绑策略可能带来排斥和限制竞争问题,这说明电信规制与广电规制存在巨大的外部性。[8]
规制政策不仅需要行政机构去执行,还要求政治体制确保其合法性,因此,规制体制设计必须与国家政治体制相适应,规制体制选择取决于国家的制度能力。[9]即使满足这样的制度条件,规制体制的选择也不完全是自由的,因为一旦某个产业的规制机构被设立以后,该规制机构就被赋予了通过规制政策创造和分配租金的强大权力。此时重新配置规制权力就会变得相当困难,这种既得利益造成的制度刚性,使得规制体制改革很难取得突破。[4][10-11]
国家制度能力对规制体制设计的约束,意味着规制体制选择是一个给定政府制度背景下的组织设计问题。Sah和Stiglitz(1986)最早从组织理论视角,分析规制政策决策者具有有限理性时,如何在分业规制和集中规制之间进行取舍。他们认为,如果规制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很大,并且规制机构能力有限时,集中规制是更好的选择,反之则应选择分散规制。[12]这意味着,对于决策过程缺乏保障,沟通成本比较高,并且人力资源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应该选择统一的规制体制。
现代规制理论文献开始利用机制设计理论,分析统一规制和分散规制面临的权衡。根据规制制度设计的显示原理,在不存在合谋且合同完备的条件下,即便规制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仍然可以通过集中的规制实现最佳规制。[13]但现实情况是,规制过程普遍存在合谋、合同不完备等问题,因此存在统一规制和分业规制的权衡问题。
沿此思路,大量文献开始研究在什么情形下,分离的规制体制比集中的规制体制更符合效率原则。Laffont和Martimort(1999)认为,假设规制机构与企业可以合谋,那么分散的规制体制可以有效地防范规制机构与规制企业合谋。[14]根据这个结果,如果政企合谋的可能性很高,并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分散的规制体制更好。Baron和Besanko(1992)认为,如果缺乏信用机制,那么分散的规制体制可能更有效。[15]Bardhan和Mookherjee(1999)也分析了分散规制比统一规制更效率的条件。[16]
目前为止,规制理论文献比较清晰地揭示了技术经济和政府制度变量如何影响分散规制与统一规制的权衡,但这些文献的局限性在于,它们都是在部分均衡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无法全面描述技术经济理性和制度理性的要求,更无法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正是规制体制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17-18]实际上,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规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规制体制选择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
已有很多实证文献分析各类制度因素对规制制度的影响,比如Djankov等(2002,2003)和Shleifer(2010)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规制制度的影响;[19-21]Kaufmann等(2007)构建了系统的政府治理结构指标;[22]Laffont(2005)利用离散选择模型研究了私有化问题;[4]但总体看,分析规制体制选择的实证文献比较少,特别是尚未出现基于国际经验研究三网融合时代规制体制设计的实证文献,本文将试图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本节设定三网融合下规制体制选择模型,以便在分析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对规制体制选择的影响的同时,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研究制度选择的经典方法是Probit选择模型。基于可获得数据,本文选择了横截面Probit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对电信和广电实行分业规制还是统一规制的选择变量。本文设定1表示电信规制机构同时负责广电规制,0表示电信和广电分开规制。
前面文献的综述表明,影响规制体制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技术因素和政府制度变量。在本文中,我们用通信市场指标来表示技术和经济因素,用规制体制设计和政府能力变量来表示政府制度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我们无法用时序数据来分析技术驱动对规制机构变动的影响,但各国电信市场发展的不同部分地体现了技术驱动因素。此外,解释变量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变量。
下面设定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不同国家选择统一规制或分业规制的概率,其具体形式如下(Green,2000):[23]

其中Pi表示国家i选择统一规制的概率,Φ(β′X)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β1,β2,…,βn表示待估参数,X=(x1,x2,…,xn)为各种解释变量。β′X为Probit函数的指示函数,βi则表示变动一单位引起Probit指数变化一个标准差。而变化一个单位引起的概率变化(边际效应)等于对应的正态密度函数与βi的乘积。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规制机构数据和世界银行的信息通信产业(ICT)数据。[24-25]ITU规制机构数据包含对不同国家电信规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信息。世界银行的ICT数据则包括不同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ICT产业市场结构、供给能力以及ICT经济绩效等方面的指标。
具体变量含义如下:一是规制机构设计指标,这部分数据来自ITU规制机构数据库,主要包括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电信规制机构是否负责广电的规制、在融合的情况下是否负责广电内容规制以及电信机构是否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规制等指标。根据ITU定义,电信规制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性是指在电信机构授权范围内,电信规制机构是否具有制定规制决策的自主权;电信规制机构是否负责广电规制是指电信和广电规制机构是否统一;电信规制机构是否负责广电内容规制是指对网络实施统一规制时,融合的规制机构是否还负责广电内容规制;是否对互联网内容规制是指不管电信和广电规制机构是否融合,规制机构是否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规制。
根据表1,从涵盖105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来看,规制机构具有独立性的均值为0.88,电信和广电统一规制的均值为0.58。电信和广电机构融合后,规制机构负责广电内容规制的均值为0.18,电信机构负责互联网内容规制的均值只有0.11。

表1 变量定义和基本统计量
二是社会经济指标和通信市场指标,这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ICT数据库。在通信市场指标中,包括固网产权结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竞争,以及互联网竞争等市场结构指标。在固网产权结构中,包括完全私有、完全国有和部分私有三种状态。为了量化固网产权结构,我们定义完全私有取值为1,部分私有为0.5,完全国有为0。对于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竞争,存在完全竞争、管制下的竞争和垄断三种状态,我们将这三种状态分别取值为1、0.5和0。使用同样方法,我们对互联网产业的竞争进行了量化。由表1可知,固定电话产权私有化的均值为0.58,国际长话竞争程度的均值为0.72,移动电话竞争程度的均值为0.78,互联网竞争程度的均值为0.90。此外,我们还从世界银行ICT数据库得到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资费和普及率指标。
三是政府治理指标,这部分数据来自Kaufmann(2007),这是世界银行建立的度量各国政府治理状况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政府的可问责性、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的控制等几个指标。[22]这个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世界银行商业环境问卷调查、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30多个世界著名机构建立的政府治理数据库。世界银行通过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数据进行加总和加权处理,得到描述各国政府治理状况的权威数据库。
四、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面设定的模型,我们使用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来进行估计。为反映规制机构独立性对规制体制设计的影响,我们设定了两个不同的模型,其中模型1不考虑规制机构独立性的影响,模型2则反映了该变量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2列和第5列为参数估计值,第3列和第6列给出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即相应变量每变动一单位,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将变化多少。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表2中给出的边际效应,如果所对应的变量是虚拟变量,则边际效应反映的是该变量从0到1所产生的选择概率变化。
规制制度设计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规制机构应保证其独立性,以避免政治力量对规制过程和规制决策的干扰。为此,从实证角度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是否影响规制体制设计。理论上来讲,融合的规制体制意味着规制决策更集中,因此,政治力量更容易干预,这也是为什么在计划体制下,主要通过设置大而全的超级行政机构,来对经济实施有效控制。但另一方面,集中的规制体制又可以减少协调成本,提高规制效率,这正是实施大部制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显示,规制机构独立性对于是否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三网融合的规制体制设计,这个实证结果的含义是,从规制机构改革的路径来讲,可以在没有建立独立规制机构,或者说在没有实现“政监分离”之前,先实现规制机构的融合,对电信和广电实施统一规制。

表2 电信规制机构独立性与电信、广电规制体制的Probit选择模型
在模型2中,除规制机构独立性变量不显著外,还有一部分经济社会变量和通信市场变量不显著,去掉不显著变量重新估计得到模型3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电信、广电规制体制的Probit选择模型(模型3)
估计结果显示:第一,经济社会因素对是否选择统一规制机制有显著影响。人口总数越高和密度越低,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可能性越大。一方面随着人口总数的增加,规制的复杂性就会随之增加,统一规制有助于协调各方诉求;另一方面人口密度越低,覆盖地域面积就越广泛,集中的规制机构越能更好地保障规制一致性。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当人口数增加1百万和人口密度减少1人/平方公里时,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分别增加0.05%和0.01%。
第二,电信技术和市场发展程度对统一规制机构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是,互联网引入竞争的程度越高,互联网普及程度越大,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就越大。其中,当互联网市场由垄断变为竞争时,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将提高60%。此外,互联网普及程度每提高1%,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就会提高1.53%。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互联网规制与三网融合下对电信业务和广电业务的规制有相似之处。目前,电信规制机构普遍具备了互联网规制的经验,包括市场、技术、业务等方面,如果互联网竞争程度很高,说明电信规制机构更有可能借鉴已有规制经验,有效地承担三网融合以后的规制职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当今,电信和广电部门又都面临相同的内容规制问题,只不过两者的定位略有差异。另一方面,互联网代表着电信和广电未来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模型中的互联网变量代表了这种技术融合的影响,而这种技术融合要求统一的规制机构,这正好反映了规制机构设计对技术理性的依赖。
除了互联网以外,移动电话资费也会对是否选择统一规制机构产生影响。模型结果显示,移动电话每月资费每提高1美元,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减少4.2%。由于在基础电信业务中,移动电话是竞争程度最高、收入份额最高的业务,因此,移动资费水平越高就意味着电信市场成熟程度越低,从而融合后广电进入电信领域的盈利空间越大,规制机构出于行业保护的目的,限制对方进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更需要统一规制机构。但另一方面,在电信市场成熟程度比较低时,市场空间相对比较大,限制对方进入的必要性就越小,选择统一规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限制竞争对规制机构设计的影响相对更大。
另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电信产权结构对是否选择统一规制机构也有显著影响。我们在模型中用固定电话的私有产权比重来刻画这种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固定电话的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可能性越小;反过来讲,融合的规制机构更适合于以公有产权为主的电信市场的规制。
第三,政府治理能力变量对规制机构设计的影响。理论上讲,规制机构的制度理性意味着规制机构设计要与政府能力相吻合。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可问责性越强,政治稳定性越高,选择统一规制的概率越大。政府腐败控制能力提高1%,选择统一规制机构的概率提高0.78%。前面综述中已经分析过,分设规制机构的重要原因是防范或限制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形成“政企同谋”。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政府越清廉时,就越不需要通过分设规制机构实现相互监督,而应该直接选择统一规制机构。
我们的实证结果还显示,法治程度对统一规制机构选择的影响是负的。对于规制机构设计来讲,法治程度越高,规制机构间的职责划分就越清晰,相互交叉或重叠的职能越少;同时,即便有规制冲突,也可以依法处理,因此,就没有强行设立融合统一规制机构的必要了。此时,分设规制机构将更有助于发挥各个规制机构的专业规制能力,提高规制效率。
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结果与现有经济理论基本一致,我们不但证实了产业技术经济特征和国家制度安排将影响三网融合下规制体制的选择,而且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会对此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不同国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同,最终设置的规制架构也有所不同。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国情条件下,我国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规制体制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采用基准比较的方法(Benchmarking model),利用前面估计出的模型来预测中国选择统一规制体制的概率。代入相应变量的中国值,就得到表4的预测结果。

表4 中国选择电信和广电统一规制的概率
表4中的预测结果显示,相对于样本中采用统一规制体制的均值(0.58),无论相对哪种模型设定,我国选择统一规制的概率都非常高,这意味着我国应选择融合的规制机构。根据我们的模型设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数很大,规制机构的决策目标更为复杂,统一规制有助降低协调成本;互联网市场已引入竞争,普及率也在快速提升,电信和广电的技术和业务趋同度增强;电信和广电都是国有控股,私有化程度很低,分设规制机构必要性很弱;中国的法治发展程度尚不完善,设立统一规制机构有助于减少推诿扯皮、选择性执法及限制竞争等行为,提高规制效率。
五、结语
本文通过建立三网融合时代各国设置电信与广电行业规制体制的Probit选择模型,利用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分析了信息通信市场、国家制度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因素对三网融合下规制体制设计的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与现有规制制度设计理论一致,产业技术经济特征和国家制度环境,是影响三网融合下规制体制设计的重要因素。此外,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会对此产生重要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对于规制体制的影响非常复杂,这说明尽管规制体制设计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但不同国家可能会依据不同的国情得出不同的选择。
利用国际基准比较方法,我们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我国应该选择统一规制体制,以适应三网融合的要求。在中国现有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下,导致这一结果的首要因素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为了适应融合的技术趋势,促进业务和市场的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制框架来推动,这是技术理性的内在要求。在国家制度层面,不同的制度参数对于规制体制的影响是不同的,但总体来看,现有的制度能力也支持设立融合的规制机构,以减少协调成本、选择性执法和限制竞争等问题。
我们的实证结果对于后三网融合时代的规制改革也有重要意义。尽管从长远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是树立规制权威、提高规制效率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但是建立统一的规制体制并不一定以规制独立性为前提。这意味着,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电信和广电规制机构除了需要承担促进市场竞争的职能外,还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承担产业发展、国资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等职能,但这种制度设计并不妨碍推进以融合为导向的规制机构改革。实际上,选择统一规制体制也是与我国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方向一致的。
[1]Glaeser E.L.,A.Shleifer.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XLI):401-425.
[2]Majone G..From the Positive to the Regulatory State∶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in the Mode of Governance[R].Working Paper,Estudio,1997.
[3]刘俊杰.技术创新、规制重建与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J].当代财经,2005,(5):94-97.
[4]Laffont J.J..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5]Laffont J.J.,J.Tirole.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M].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6]Waterman D..The Economics of Media Programming[M].Handbook of Media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Londo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2004.
[7]Crampes C., A.Hollander.The Regulation of Audiovisual Content∶Quotas and Conflicting Objectives[J].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2008,(34)∶195-219.
[8]Crampes C.,A.Hollander.Triple Play Time[J].Communications&Strategies,2006,(63)∶51-71.
[9]袁明圣.政府规制的主体问题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5):58-62.
[10]Stigler G..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1,(2)∶3-21.
[11]Peltzman S..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 after a Decade of Deregulation[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Microeconomics,1989,1-60.
[12]Sah R.,J.Stiglitz.The Archite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Hierarchies and Polyarch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716-727.
[13]Baron D.,R.Myerson.Regulating a Monopoly with Unknown Cost[J].Econometrica,1982,(50)∶911-930.
[14]Laffont,J.J.,Martimort.Separation of Regulators Against Collusive Behavior[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30)∶232-262.
[15]Baron D.,D.Besanko.Information,Control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1992,(1)∶237-275.
[16]Bardhan P.,D.Mookherjee.Relative Capture of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An Essa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on[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9.
[17]Estache A.,L.W.Lewis.Towards a Theory of Regul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Following Jean-Jacques Laffont’s Lead[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9,(47)∶729-770.
[18]陈富良.S-P-B规制均衡模型及其修正[J].当代财经,2002,(7):12-15.
[19]Djankov S.,R.L.Porta,F.Lopez-de-Silanes,A.Shleifer.The Regulation of Entr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37.
[20]Djankov S.,R.L.Porta,F.Lopez-de-Silanes,A.Shleifer.Cour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53-517.
[21]Shleifer A..Efficient Regulation[A].in∶Regulation vs.Litigation∶Perspectives from Economics and Law[M].Cambridg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10.
[22]Kaufmann D,A.Kraay,Mastruzzi.Governance Matters VI∶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6[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280,2007.
[23]Green W.H..Econometric Analysis,Upper Saddle River[M].NJ∶Prentice Hall,2000.
[24]ITU Regulators Dataset[EB/OL].http∶//www.itu.int/ITU-D/ICTEYE/Regulators/Regulators.aspx,2010.
[25]The World Bank.The Little Data Book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R].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