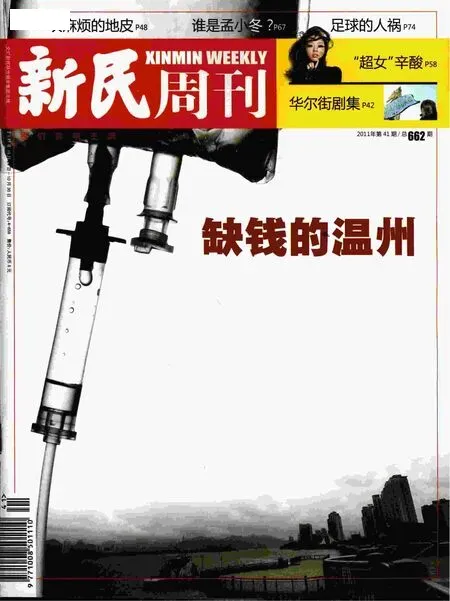田沁鑫:坚持得自己像个英雄
2011-05-30乌力斯
乌力斯



话剧《夜店之天生绝配》正在国家话剧院先锋剧场热演。它改编自电影《夜店》,以一颗名贵钻石的丢失为由头,从一场严酷又荒诞的警察局审讯开始,引出了七个嫌疑人和两个警察或捧腹或伤感的“前史”:城管欺负小商小贩,韩国抢注中华文化遗产,房价物价节节高升……在癫狂的喜剧表演方式下,《夜店之天生绝配》反映出的是当前种种敏感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这一迥异于其之前作品风格的话剧,也让田沁鑫被部分观众质疑。
癫狂喜剧是好莱坞经典喜剧电影类型之一,以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有趣人物为集结,并设计台词、动作激烈,紧密结合当下的事件,曾于1930年代风靡美国。与黑色幽默相反,癫狂喜剧是积极的、光明的、热烈的。
田沁鑫认为,人本身是悲剧,悲到极处便生喜,喜剧是人类的慰藉。“如果无力改变生活,用癫狂或扯淡的态度去面对未尝不可。”这便是她创作本剧的初衷,这部剧关注真实而犀利的生活,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一代人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残酷的青春生活。
如今的田沁鑫,已经做了14年戏。这14年里,她排了18部戏,形式包括话剧、音乐剧、戏曲,甚至还有一部電视剧《生死桥》——不能不说,她是个勤奋的导演。
在和记者谈话的时候,她一直说自己“不会说话”。但她的话就像她排的戏,很简单,很执著,都有一种力量。“我现在希望我认识水平提高,心胸再放大。你的力量不见得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在时代当下有能力将大家包容起来的力量。”田沁鑫说。
《生死场》:突然起了一个高地
新民周刊:你把自己的处女作《断腕》列为你最满意的作品,为什么?在作家行当里,很多人都是第一部作品最好,他把自己的青春期里的爱和恨都放进去了,那也成为了他一辈子最好的作品。
田沁鑫:我觉得《断腕》是一个纪念,是我起步这个行业的第一个作品。我认为最好,是因为我那个处女作保持得最纯洁,是一点点的功利心也没有,一部完全纯洁的作品,纯洁地歌颂爱情。
我现在看《断腕》的时候,如果有学生给我交这样作品的话,我认为他是人才。因为用词之简洁和干净是少见的,而且剧本非常不啰唆,好像才十几页,而且上手就气势很大,一上来结构相对完整。
新民周刊:《生死场》上演,当时《读书》杂志还给你开了研讨会,北京的大知识分子、教授、学者都来讨论你的作品,会议记录还发表在《读书》上,大家都觉得戏剧界突然起了一个高地。
田沁鑫: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当时因为一场昏天黑地的爱情,绝望的爱情,我做了第一部戏《断腕》,完全是为了一种情感表达,非常感性,就是表达了我当时的情感状态。当时,赵有亮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院长,他看过以后觉得不错,觉得我有才华,就约我做一部戏。后来我提出做《生死场》,我喜欢萧红这个作家,所以就做了这个作品。我感谢萧红,因为《生死场》让我得以以一流导演在中国戏剧界里出现,让全行业认可了我,完全是青春作证的作品,所以它风格非常凛冽,非常残酷,非常率真,也非常迅捷,它本身就是青春的记忆。
在这个戏里,抗日是一个主题思想,也是一个背景,但它的核心是人生,人面对在战争、死亡的威胁,人本身的生老病死,民族大义、国恨家仇,是舒展地活着还是被日本人压抑着活着,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生老病死,一上来触及到了一个终极问题,而且舞台上人物各种死法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因为它一点不虚伪。他们抗日也不是为了奔赴美好明天,有多少觉悟,就是不得以生命本能去抗争。在做的时候突出了两个字就是挣扎。
没想到,它得了好多好多奖,政府奖都拿遍了。当时《生死场》上演后,还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发表文章批评这部戏是毒草,颠覆了抗日战争的英勇伟大,一时间压力非常大。最后,当时的文化部长孙家正看了,说这是个好戏,结果所有的争论和批评都没有了,这个戏一下子变成了好戏,拿了戏剧界的最高奖,那年我才29岁。我领奖的时候,就觉得那应该是我老师拿的奖,凭什么就落在我手里了?只能说我运气太好了。
这个作品还在全国演出当中,赵有亮就决定调我到中央实验话剧院,从此,我成为一名专业戏剧导演。
新民周刊:你由文艺青年变成了专业导演。记得你排过一个根据一个大学女生遭遇改编的戏,叫《赵平同学》,那是一部批判中国教育制度的戏,直面现实,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田沁鑫:《赵平同学》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批判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的作品,我带着批判精神来写一个 80后的 “问题少女”的思想和情感故事。我在戏里让80后的学生和60年代出生的老师进行对话。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很讽刺的,也是正面讨论我们的教育问题,但遗憾的是,做话剧不像电影一样受众那么多,但我始终在文化的观照上,还没有太松懈。
《赵氏孤儿》和中国式悲剧
新民周刊:2003年,你做了《赵氏孤儿》,你怎么敢和林兆华打擂台的?当时两版《赵氏孤儿》差不多同时亮相,引发满城风雨。
田沁鑫:我对悲剧挺感兴趣的。你说我没有设定目标,其实我也在设定,要不然我前三部戏不能够做那么瓷实。
那时候我出了一本书《我做戏,因为我悲伤》,我对我所处的时代有遗憾,但是我又不能选择。我也可能是心灵脆弱,我不愿意看到现实社会里非常丑陋的欺诈,缺乏道德感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我做了《赵氏孤儿》。
在《赵氏孤儿》那个戏里,我很彻底地在谈忠义,这个戏能证明我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在一个很娱乐化的时代,我一样能够驾驭大的、沉重的历史题材。我是一定要证明我是一个好导演。
2000年8月,我给林兆华当助手,参与了京剧《宰相刘罗锅》的工作,因为赴台演出,在台北的一家戏院看到了张学津主演的全本《赵氏孤儿》,这个戏给了我很大冲击,从此就有了将此剧搬演为话剧的心思。
我的“孤儿”一登场,已经16岁了。他经常在噩梦中梦见母亲。他有两个父亲,义父屠岸贾病得要死了,父亲程婴要给孤儿讲述16年前的故事,完全的倒叙。一个懦弱的人——程婴如何成长为天地英雄,他要面对的不仅有死亡和背叛者的骂名,还有来自妻子的拷问:“你如何自当义士,自毁家门?”程婴因为一句承诺就能出生入死,这令我为之动容。我在程婴身上强调的是理想中的父辈,“诚信大义”。我们这个民族总爱谈母亲,而从来不谈父亲,这是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
我是借做戏打妄语,把我的灵魂赋予一个男人的形骸,让他塑造一个理想化的父亲的形象,这个诚信、担待的父亲,临死之前还在说着愧对孩子,这怎么可能是真人呢?我要通过《赵氏孤儿》探测一下当代观众还有多少中国的文化精神。所以我要求在舞台上的演员们不仅用台词,而且要用肢体叙述惨烈的故事和内心的困苦。
我觉得我的《赵氏孤儿》是锐利的,我在用一个假想的春秋的少年中国的社会来对照现今的社会。周礼灭绝之后社会一片混乱,几大门阀为权力争斗,在这样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的时候,还有程婴这样诚信和忠义的操守。现在是三千年之剧变,之中国,之当下。我真的是有看法的,我是有期盼的。
新民周刊:中国人不喜欢悲剧,哪怕它再深刻。
田沁鑫:那时候我探讨什么是悲剧,悲剧无外乎是一个深刻的灭绝而产生出的审美,这个是古希腊的悲剧精神,也是跟戏剧有关的,所以我塑造的人物非常的戏剧化,但是里面确实是很中国的故事。
严格意义上,中国堪称悲剧的悲剧就是《赵氏孤儿》,这个是西方人评价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太喜欢悲剧的,东方戏剧喜欢大团圆,你要演一个特别深刻的悲剧,观众就会很绝望,不爱看。
我现在觉得,这个作品还是有它一定的问题在里面,它更偏重于形式,而没有偏重于文本。我不是那个时代的导演,因为我们确实学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维观念。我也确实喜欢中国故事,这个戏剧之间就会有交叉手法去表现。如果现在我再做《赵氏孤儿》,我可能再深入一步,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真实更可贵的。以后我再做作品的时候,我也更希望我的作品真的更真实一些。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再做,会让它更生活化,更反戏剧化的形式,让程婴从庙里的神,回到活生生一个人,回到真实。
田沁鑫:对,我觉得面对救孤这个事上,我会做得纯粹,不那么艺术化地处理这个人,把这样一个忠义的故事做到底。
我们中国的文学里,你仔细看下来,从《史记》开始,包括《红楼梦》也在强调,中国还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道德上有一种感知力的精神,比如说诸葛亮,他失败了,没有什么留下,但为什么大家觉得他非常棒?我们不是以成就感来论他的,他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天才的军师,有一个千年老二的形象。关羽也是这样的,包括项羽在内,其实也是失败的,但这一些人都是英雄,中国人还是有这样一个英雄史诗和一种心态情怀在里面的,极有人文情怀。所以说中国文人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文学气质浩浩荡荡,我不认为是没有气质的,它不是日本那样的注重私人生活的文学,就是一个大国气象。
《四世同堂》的回归
新民周刊:《四世同堂》是一台大戏,你怎么来对待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改编?
田沁鑫:我做《四世同堂》,那么大的人文大戏,每天都是三四十口人在舞台上。有一天朱媛媛就很不满意,很郁闷,她是非常感性的女演员,她说这戏有一些冷,骨子里怎么那么寒凉?这个话我当时听进去了,后来回家我想,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从《生死场》开始,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有一个冲劲在那儿,到《四世同堂》就从容就寡淡了,我还是得让它热起来。
我特别感谢朱媛媛,她像一个非常好的高僧,点拨了我一下,我接受这个信息,一下子接通了,让我开阔了。我后来开始调整了剧本。《四世同堂》小说85万字,很难缩到3个多小时的话剧。好多故事、背景、人物关系都得交待,你不交待观众看不懂,在交待的过程当中又无趣,所以一二幕戏原来是不好看的。后来我就开始调整,让故事、人物出场的节奏更鲜明,一胡同的人议论。大少爷和冠晓荷在小说里没有正面冲突,但是我会让他们两个直面冲突,加强了故事的冲击力,让这个戏好人坏人都那么分明,让模糊的人那么生动。把《四世同堂》从一个家族小说做成一个好看的平民史诗。
新民周刊:其实他里面最感人的,除了人的不幸外,还是国恨家仇,还是所謂的大忠大义。
田沁鑫:对,今天的观众骨子里还是希望它在那儿,要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也不会感动。即使他们找不到,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人。
当一个一个庞大的家族构成的国家出现后,面对侵略和外侮的时候,它的能力在哪儿,它的出路在哪里?是各人只管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还是抛弃小农单干意思,大家联合起来反抗外来侵略?在八年抗战的特殊时期,逼着中国人反思这个事。
我觉得老舍先生对所有丑陋的、在乱世里面所有跳梁小丑的这一些人,他是不屑和否定的,所以他会写他们非常光鲜的一面,反托他们外表下面的脏乱差。这和现在非常像,沉默的大多数中国人,是华夏生命的主题精神。他们大部分是穷人、平民,不显山显水,没有权没有势,默默支撑这个国家向前,以一种无声的坚持,坚持到八年抗战结束。
所以,不管说《赵氏孤儿》、《关圣》这样的古代戏也好,《生死场》、《四世同堂》这样的现代戏也好,我觉得忠义不该放弃,必须坚守我的文化态度和价值立场。
新民周刊:喜欢你的评论者终于看到,田沁鑫借《四世同堂》,又回到了《生死场》的路上。
田沁鑫: 这个戏演到哪儿爆满到哪儿,很少有舞台剧市场好到这个程度。主要是大家都不做这种戏,因为它太累、太费神了。认识了老舍的《四世同堂》,这个对年轻人是多好的事情。
我没有因为商业消减了我的文化态度,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其实是一点不想当英雄的人,内心比较脆弱和敏感,在艺术上比较纯粹比较单纯,但是坚持到现在,我觉得也像个英雄了,一直这样坚持着,到《四世同堂》的时候,我觉得坚持有一点意思了。
新民周刊:你一下做10个这样的大作品,就真的能够继往开来。
田沁鑫:你们太理想主义了,今天这个世道,能到我这个样子已经很罕见了,因为他们都不做了。我觉得这些大戏应该是很多男人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里优秀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了。大家做艺术就像是群居,哥们儿在一起干事,安全,都是寻找一种温暖和安全。生产出来的作品,都是不痛不痒的,完了之后追求商业,得到票房,开了宝马X5了,过了好生活了。艺术圈越来越像一种秀场了。
女导演的困惑
新民周刊:在艺术的路上,你自己秀过吗?
田沁鑫:我没有秀过,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秀,我秀不出来,因为这个不通透。我希望能够登堂入室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从艺术家变成一个有公共话语权的名人,我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我走的是一条正道,作品是言之有物的。我走歪道,我就休息了。因为歪门邪道很容易,秀很简单,但我不需要那些。
其实正道本身来讲很难行,沧桑难行。老天爷把你生为一个女的,当你外形是一个女的时候,你只能走正道了,走正道对于一个人来讲,非常的累,是血与泪的付出,就像老毛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你可能没有修行到那个境界已经先死了。
新民周刊:作为女导演,你怎么看女性主义?
田沁鑫:在泛娱乐时代以前,还有一个泛政治化时代。在中国的泛政治化时代,还有女性很多施展的位置。
女人的自主性在泛政治化时代的时候是很突出的,最好的时间是在“文革”结束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我们上一辈的女艺术家,比如说黄蜀芹导演,她认为那是她人生最好的阶段。她的《围城》完全看不到性别,只不过觉得是部好的电视剧,出手平常、舒展、温暖、大气,而且它的人文含量很高。她女性表达的作品是《人鬼情》,那个是比较好的作品。
像张暖忻的作品《沙鸥》对纯女性化的表达更突出,追捧她的男性比较多一些。因为中国社会里男性有一种女性崇拜,对女性崇拜往往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他对女性的欣赏和尊重是突出和偏执的。
新民周刊:你欣赏过去那个时代?
田沁鑫:今天的泛娱乐化时代是更男性化的时代,凭体力欺诈,靠卖力气摄取目标,攻击性强。它不要脸起来是一个彻底的不要脸,底线是一个小丑,像每年的春天春花开放一样的,会泛滥它所有的丑形,这时候它是没有底线的。
我看曹禺的《日出》,总会想陈白露为什么不跟方大山好?作为一个交际花,陈白露当时不能被社会兼容。她受到良好的教育,穿着打扮和气质不一样,但她下半身是开放的,又有非常清楚的头脑,有智商,你可以去念书,可以做女读书人,但是她显然又不是,就跟自己拧把,最后走向灭亡。曹禺是一个心地善良和坚持男女平等、对女性有深刻认识的作家,他一生在歌颂他喜欢的女性,即便有的女性不可爱,但他也在歌颂。
在泛娱乐化时代,这样的作品反而会越来越少。作为一个女性,我的智力实际上是一个习惯性的男权社会所培养的。比如我跟男孩干活的时候,男孩也不累,时间长了,也确实不把我当一个女人看了。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只剩下非常感性而非常细腻的写作风格。在工作方法上,我确实男性化。在目标设定这种东西上,我们的野心和男人是一致的,我不认为这一点跟男性有任何差别,因为这个社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