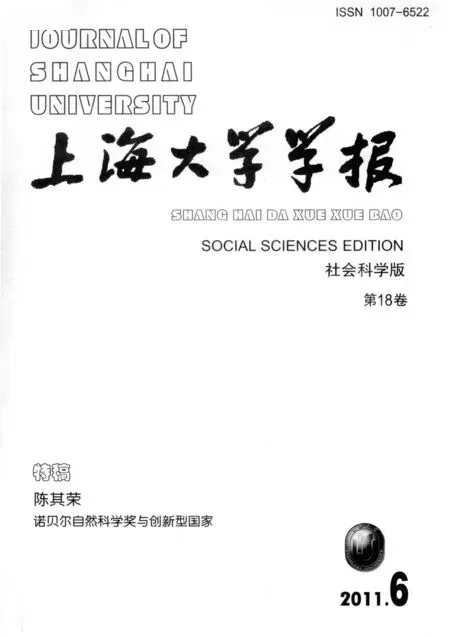晚清东南督抚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中心
2011-04-14彭淑庆孟英莲
彭淑庆,孟英莲
(1.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2.滨州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山东 滨州 256600)
庚子五月,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北方局势动荡,南北通讯阻断。朝廷疲于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此时已经无法对地方尤其是远离中央的南方各省实施有效的控制。东南督抚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如果清廷继续坚持“招拳御侮”政策,必将难逃灭亡的命运。面对清廷的权力混乱和外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在国内革新势力以及外国列强的怂恿下,东南督抚们还利用义和团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准备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自治”的想法也随之而生。这种思想、活动对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们最终又放弃了这一“革命”想法。这一现象虽然昙花一现,却反映了晚清中央政权所面临的深重的政治危机和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李鸿章与“两广独立”计划
根据现有史料和学者考证,这一时期的时局动向以李鸿章参与“两广独立”计划最为典型。“两广独立”之筹议,发端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1900年5、6月之交),其经过大致如下:
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何启,在香港殖民当局支持下,联络在香港活动的革命党人陈少白,建议兴中会争取与李鸿章合作,在广州建立“独立”政府。陈少白极为赞同,随即与在日本的孙中山联系。
革命党方面,孙中山也正在考虑利用义和团运动的混乱形势,着手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他实际上对于跟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曾上书李鸿章,要求维新改良,却遭到李氏的冷遇,故此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觉得“此举设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1]51再加上自李鸿章复出调任粤督以来,对革命党和维新党并没有特别敌视和大肆搜捕,而且“两广独立”的计划又得到香港殖民当局和日本友人的支持,这些都使革命党觉得有机可乘。李鸿章方面,出面联络的是其机要幕僚刘学询。刘氏与孙中山同邑且曾交往颇密,“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鸿章颔之”。刘学询于是向孙中山发出邀请,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2]92
6月11日,孙中山偕党人杨衢云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自横滨起程赴粤,17日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幕僚曾广铨率“安澜”号军舰来接,邀孙中山、杨衢云二人到广州谈判。这时,孙中山得到在香港的陈少白的报告,探悉“鸿章尚无决心”,“督署幕僚,且有设阱逮捕孙杨二人之计划。”[2]93于是孙中山没有上岸,而是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等人代行赴会。当夜,宫崎等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开始谈判,由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三点结束,宫崎等一行即连夜返回香港,其过程极为隐秘。
此次谈判的要点包括:(1)李鸿章声称他在“各国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2]93即只要北京政府存在,两广不会宣布“独立”,言外之意,李虽有“独立”的考量,但认为时机尚不成熟;(2)宫崎等要求李鸿章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并向李借款六万元作为双方合作条件。刘学询在请示李鸿章后均予答应,并先由自己垫付三万元,其余通过邮寄支付。在革命党看来,李鸿章虽然没有给出“两广独立”的具体时间,但也并不排斥此“革命”计划,列强联军很快就会攻陷北京,只要北京失陷,李鸿章很可能会宣布两广独立;更令他们惊喜的是,革命党轻而易举得到了三万元活动经费,这对经费困难的革命党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收入。①宫崎等人离开广州后,转赴新加坡游说康有为,试图力促康、孙联合。然而宫崎等人到新加坡以后,因与刘学询的此次"亲密"接触及所得的三万元经费,而被怀疑是受刘学询的雇佣前来刺杀康有为,并因此被新加坡警方逮捕入狱,直到孙中山赶赴新加坡说明情况,方才得释。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动机,仍是怀疑大于信任,乃命香港的革命党人“分头办事”,“一个月之后便可通盘计算,以观成就之多少,而定行事之方针矣”,[3]190即一面组织惠州起义,一面继续策动“两广独立”。
那么,李鸿章为什么会在庚子政局最敏感的时期,产生“独立”念头呢?翁飞认为甲午以来李鸿章在思想上的变化,仕途失意和对清王朝前途的忧心,使他逐渐倾向于同情变法,进而闪现出与革命派联合的想法。[4]董丛林则认为主要是当时义和团运动的中心甫转京津,局势动荡,清政府生死未卜,李鸿章对顽固派“招拳御侮”的政策,极为不满又迷茫不安,在革命党、港英当局和亲信幕僚刘学询的怂恿下,李一时“冲动”,接受了“两广独立”的计划,这是通过筹划“两广独立”,未雨绸缪,以图自保,同时向清廷施压、挽救大局。[5]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以李鸿章几十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敏锐谨慎的政治风格,“两广独立”之筹议虽昙花一现,绝不可能仅为李氏个人“一时的冲动”。因为当时清政府的政策与东南地方利益产生了严重冲突,并且清廷已无力有效控制地方社会。在这一特殊条件下,图谋自保、巩固和维护自身利益是多数东南督抚共有的想法。李鸿章之所以很快就放弃了与革命党合作的想法,除了翁飞、董丛林二人所提到的李氏与革命党相互不信任、清廷召其北上以及李氏骨子里沉淀的“忠君报国”思想等因素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现实因素——列强的反对和东南互保的制约。
宫崎等人代表孙中山与刘学询谈判完成离开香港两天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清政府驻日公使李盛铎电告李鸿章:“逆犯孙汶,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6]935李盛铎也许并不知道孙中山此行恰是应李鸿章之邀,因而他对李鸿章发出了要警惕革命党的电报。日本东亚同文会高层倾向于支持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和自立军,严重警告在华会员不得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虽然代表了最进步的方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过于“偏激”;相比“革命”,英、美、日政府则更热衷于推行“保全中国”理念,实际上通过与地方实力派督抚的合作,保全清政府的统治。李鸿章外交上的“亲俄”倾向,也使他无法得到英、日等国的全力支持,多数列强反对李鸿章北上,甚至一度拒绝承认其全权议和代表资格,而是建议刘坤一、张之洞作为代表参与议和谈判。
脱离满清政府,或“独立”或组建“新政府”的想法,非李鸿章一人独有,刘坤一、张之洞同样有此意念或受此诱惑,只是李鸿章付诸行动,比刘、张二人更典型罢了。
二、刘坤一、张之洞的“新政府”设想
当义和团运动渐入高潮,清政府的国家权力体系遭受重创,其社会控制能力近乎崩溃时,“独立”、“自治”的思想倾向在当时社会舆论中逐渐凸显。这一构想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如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刊发多篇社论鼓吹联邦自治,谓“满党敌政”,“不能不使南北分疆而离立”,[7]“合诸省为联邦是第一要着”。[8]东南社会的舆论矛头,由痛斥端王、刚毅等二三“满贼”,逐渐延至对“北京贼政府”、“无知满员”的抨击。[9]于是不认满清政府、另立汉族政权,或建立以光绪帝为首的新政府等各种政治主张也随之萌发。这些思想主张与东南督抚密切相关,处于清王朝权力重心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自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00年6月,日本东亚同文会的井上雅二等人曾通过唐才常试探刘坤一对“独立”、“自治”的态度。张謇、陈三立等在成功促成东南互保的同时,还着手策动刘坤一“迎銮南下”的计划。所谓“迎銮南下”实际上是一次政变计划,即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乘乱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汉口或南京,发动政变迫使慈禧归政光绪帝,重开维新变革之局。他们之所以对策动刘坤一抱有希望,系因为刘坤一是在戊戌政变后第一个明确反对废黜光绪帝的封疆大吏。《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云:“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张謇所记,仅寥寥数语,极为简略。陈厚生《张謇传记》对此事之密谋过程叙述更详细:[10]这一主张发端于陈三立,后得张謇首肯,并由张謇将这一计划密陈刘坤一;“坤一颇心动而不能决”,其幕僚施炳燮亦觉得此事重大,未敢表态同意。施炳燮到上海时,何嗣焜、沈瑜庆等又向其力言“不去那拉氏,中国无望”,施亦大悟。于是,施炳燮就带着张謇再次游说刘坤一,最终说服了刘坤一。刘坤一答应考虑这件事情。但是当刘坤一询问张之洞的意见时,却遭张的反对;李鸿章从广东到上海后,刘坤一又派人与李鸿章密商,没想到李鸿章对“迎銮南下”的计划反对更力。自此,“迎銮南下”之政变计划胎死腹中,并极少为外界所知。这一计划反映了东南社会部分“帝党”残余和“维新”势力强烈的变政诉求。
“迎銮南下”计划的背后,有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支持。①东亚同文会是一个由日本官方支持、负责对华情报工作的民间组织,在中国会员众多。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东亚同文会积极宣传所谓的“联邦保全策”,企图将中国黄河以南划分为湖南和湖北、四川、云南和贵州、广东和广西、福建和浙江以及江西、江苏和安徽、鲁豫七个联邦,在南京或者武昌设立新政府(北京沦陷后,如果光绪皇帝还在,则把光绪接到南方重组新政府;若两宫出逃西安,则东南督抚联合成立一个亲日的新政府)。刘坤一在给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的一封信中,竟对组建“联邦”政府一事表示支持。[11]102刘氏还向东亚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表示,若将来北方局面破裂,南方将断然分立、图谋自治。[12]238-239由此可见,刘坤一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确实曾对“独立”或“自治”的设想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响应。
张之洞对于成立“新政府”也曾有所心动。东亚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井上雅二等人于1900年6月中旬,曾利用主持《中外日报》的汪康年劝说张之洞迎接光绪帝至武昌设立新政府,但被张之洞拒绝。不过,这并不代表张之洞没有动心。孔祥吉依据日人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得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张之洞在1900年6、7月间曾有称帝的想法,他还派儿子张权及亲信幕僚钱恂赴日本积极活动。[13]孔祥吉观点的主要证据有三:
首先,宇都宫太郎在6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钱恂的一句话:“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宇都宫太郎7月6日又记:“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13]
其次,张权系张之洞长子,身份特殊,他在日本结识政要、购置军火,行为可疑。
再则,此时的张之洞之所以对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目的是寻机利用,将其变成实现自己“帝王梦”的工具。
对于孔祥吉的上述推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②李细珠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发表了《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亦对孔祥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钱恂对宇都宫太郎始终未提及“称帝”二字,而钱氏所说的在南京组建“新政府”,实际上就是指张謇、陈三立以及汪康年、宗方小太郎等人所密谋的“迎銮南下”;“新政府”的另一含义,最甚不过是如日本东亚同文会和《中外日报》所鼓吹的“联邦自治”,即联合东南数省,建立一个与中央政权并立的联邦政府。这与张之洞的“称帝”完全是性质不同概念。张权在日本的活动以及张之洞对自立会及自立军的态度,与张氏父子欲图“称帝”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另据张篁溪、冯自由等记述,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犹疑莫决”,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对自立会的活动未予镇压,另一方面对唐才常的再三催促,始终“无所表示”,不予正面回应。[14]9-20,18-19据此,张之洞究竟是否确有“独立”或“称帝”的想法,始终是个谜。但是,宇都宫太郎日记的发现,至少揭示出一个重要信息:在李鸿章参与筹议“两广独立”的同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如宣布独立或称帝、或东南几省联邦自治、或拥光绪皇帝重组清廷等)另组新政府的想法,对张之洞的政治心理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
以上分析,其实反映了东南督抚,尤其是在南方呈“三足鼎立”之势的刘、李、张三督,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共有的政治心态。三者差别在于:刘、张二人因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外交政策倾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始终结成唇亡齿寒的政治同盟,并因此促成了东南互保格局的实现;李鸿章远居两广,外交上力主“联俄”,其政治风格和政策倾向的差异以及李氏与刘、张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使三人关系相当微妙。但李氏作为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皇恩”元老重臣,依靠其数十年积累的政治资历、威望和人脉关系,足以自成一体。这也是李鸿章在刘坤一、张之洞主盟的东南互保中,虽表支持却并未正式表态加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较刘、张二人的“新政府”设想,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张之洞反对在武昌设立新政府,却向日本表示,如果要成立新政府的话,应该设在两江总督驻地——南京;而刘坤一则表示,他所支持新政府可以设在湖广总督驻地——武昌。事实上,他们二人都在以对方为借口,试探对方以及列强对于建立“新政府”的态度。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独立”或建立“联邦政府”的想法,谁都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分裂中国、“谋逆”中央的罪名。毕竟革命思潮才刚刚萌芽,并不为当时社会主流所接受。这正是刘、张二人比李鸿章在政治上更高明的地方。对刘、张来说,唯一稳妥且能得到列强和东南社会各阶层普遍支持的方案,就是坚持东南互保,保障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利益,维持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总体来看,李、刘、张三督在东南的鼎立之势,既可以使他们能够合力与中央对抗,同时又使他们之间相互牵制。当刘、张联合其他督抚决心拥护中央,并力邀李鸿章襄助和参与东南互保时,无论是清廷、地方督抚还是外国列强,几乎都把目光集中到资历最深的李鸿章身上。正如翁飞对李鸿章的心理分析:“积其宦海沉浮四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是断然不敢、也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投入一场无把握的冒险。”[4]恰在此时,李鸿章收到了清廷召其北上的命令,于是立即宣布将尽快北上,也借此机会抛弃了与革命党合作的想法,转而大力支持东南互保。以政治威望和政治胆量而论,李鸿章要远超过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不仅在“两广独立”事件中有所显现,而且在东南互保筹划过程中有更直接的表达。在东南互保策划最关键的时刻,清廷的“宣战上谕”到达南方后,是“遵旨”还是“抗旨”,事关东南互保的成败。此时,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同时将目光转向了一直静观时局的李鸿章。李氏虽没有直接参与东南互保的前期策划,但其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此矫诏也,粤断不奉”[15]334),为推进东南互保进程扫除了最大障碍。从这个角度说,李鸿章对东南互保之形成,实有不可低估的贡献。刘、张等人正是利用了李鸿章的政治威望和胆量,最终促成了中外互保格局。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李鸿章得悉东南互保谈判进展顺利后,致电刘坤一,“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搀夺。鸿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6]957这里的“群匪”首要是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彻底放弃“独立”的念头,转而全力支持东南互保了。
三、“独立”、“自治”不是东南社会之主流意识
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社会各种政治意识交错融汇,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东南意识”,为东南互保进行鼓吹和动员。何谓东南意识?它实际是现代史家对庚子时期东南社会舆论潮流或倾向的统称。东南意识的内容复杂,其主要的舆论阵地是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以及《中外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刘学照对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有专文论述,他认为其特点是“以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观察时局和考虑对策”,这种意识所体现的是“上海以及南方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以及从中国自身政治出发,对所谓‘内忧外患’进行反思的内省意识”;它所反映的“南北”地域分化的背后,实质上则是“满汉”、“帝后”、“新旧”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16]119-143这一界定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
东南意识的凸显,为东南互保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方案选择。东南互保是东南地方社会主要针对外国列强图谋入侵长江所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它所确定的只是中外“互不干涉”、“两不相扰”的基本原则,目的是避免南方卷入战争,阻止列强的瓜分图谋,其根本宗旨则是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由于事发仓促,且时局变化多端,战争的主动权又掌握列强手中,因而在东南互保策划之初,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
1900年7月初,战争局势对清政府也越来越不利,清政府随时有覆灭的危险。维新派以及东南社会的一些革新势力以《中外日报》为阵地,呼吁东南各省创立国会,“自立代政之体”,“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乘此画分南北而图自立”。[17]他们还提出将“东南互保约款”作为南方各省脱离清廷,实行“独立”、“自治”的合法依据:“拳匪之扰也,互保之立约也,中国不能不南北分疆而离立,乃自然之势,亦必然之理也。”[7]同时,他们呼吁东南督抚尽快率兵北上勤王,“惟是欲固南疆必先外纾党禁,内集民守,公布新政,而后可图自立之有基,然不乘此东西大兵尚未云集之时,提劲旅以北援,而外助邻战,内讨国贼,则亦未能树独立之义声也。”[7]他们认为东南督抚要勇于担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不仅要巩固南方的和平稳定,还要以“清君侧”的名义北上勤王,清除清廷中的顽固势力。这是最根本的策略。这种策略实际上反映了“保皇派”以及“帝党”势力的心声,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及自立军起义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此时的东南各省,尤其是以上海、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各种会党、政治团体林立,有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兴汉会、保皇会、正气会、自立会、“国会”(即中国议会)等名目繁杂。它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政治宗旨或政治路径的分歧。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之政治分流日趋凸显:一部分如张謇等人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资源网络,与东南各省官、绅、商、学等阶层相互渗透、融合,逐渐成为影响东南社会发展和政治走向的精英分子,他们也因此在东南互保之创议、维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另一部分人则打着“清君侧”的旗帜,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的“保皇会”遥相呼应,并且还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暗中联合、相互利用,积极推行所谓的“武装勤王”运动,筹备自立军起义。
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并向京师进逼,形势急转直下。7月26日唐才常、汪康年等以挽救时局为名,邀请沪上各派趋新势力代表人物在上海的张园召开第一次“国会”,并推举社会威望较高的容闳、严复两人出任正、副会长,唐才常、汪康年、林圭、沈荩等为干事,实际上国会内部仍然以汪、唐两派实力最强。会上就“如何联络外交,如何平治内乱,如何分议防守,如何互通晌械”[8]进行讨论。7月29日,第二次“国会”会议召开,公开提出了“国会”宗旨:(1)保全中国版图与一切自主之权。(2)力图更新日进文明。(3)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人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诸矫传之伪命。7月27日,《中外日报》又发表社论,批评东南督抚继续承认和拥护顽固派掌控的清廷中央,是既“失权”又“失位”的愚蠢之举。社论说:“东南疆臣既已与诸邻邦立约,则东南疆臣已有代理政府之权,身为政府,而更受北京贼政府之命,是谓失权;东南疆臣既己许诸邻邦,以保护之利,则东南疆臣已有亲专国命之权,身秉国命而更听北方伪朝旨之牵制,是谓失位”,[9]强烈表达了南北分治的愿望。
Ap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ce equations in the calculations of matrix power,determinant
东南督抚对于“国会”并不忌讳,张之洞还派亲信陶森甲加入其中,认为国会不过是“汇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已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为例尔。”①张之洞的这番话是在自立军起义被镇压后说的,很可能是张氏对于自己当初之所以默许国会和自立会活动的表面托词。唐才常遂将自立会作为“国会”分支,自立会及自立军的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实际上,从国会的发起动机来看,其隐藏的真实意图正如《中外日报》所言,是要“自立代政之体”、以新政府取代现有旧政府;与东南互保“全宗社”、“保两宫”的宗旨相比,其政治风险要大得多。这些极具政治风险的活动和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远远超出了东南督抚和社会主流意识之政治尺度。对地方政权来说,发动政变以及独立、自治的方案因其颠覆性特点而极具风险,势必引起东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和远东局势的强烈动荡,列强更可能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既不符合东南督抚和绅商阶层的利益,也不是东南社会的主流意识。
在东南互保的酝酿和实施中,东南意识之主流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义和团运动使北方陷入动荡之中,列强在华北的武装干预使中国面临空前的“瓜分”危机,“东南半壁”成为时局转圜之惟一“净土”。义和团运动所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冲击,严重扰乱了东南社会原有的空间秩序。为避免战争升级,东南督抚“惟一”的办法就是将战争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如盛宣怀的重要“智囊”之一、时居苏州的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江苏武进人,亦为盛宣怀的同乡)在给盛宣怀的一封密信中献策:
“现在惟有自保东南,联络与国,安集反策,清查土匪,禁市商之把持,禁愚民之迁徙,禁富人之提款,禁流氓之造谣,禁新党之耸听,禁委员之偷惰,以静待动,犹冀北去而南存,为我大清留一虚号耳。”[18]288
晚清咸、同以后所形成的“内轻外重”之二元格局,使东南督抚成为清王朝最有权势、最为倚赖的地方势力。正如张謇所说:“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东南督抚普遍认为实施“中外互保”是保障地方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唯一出路,“东南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19]1432从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东南精英商定“订约互保”的构想到说服刘坤一、张之洞等做出联合决策,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其效率之高,一方面是“宣战诏书”的客观事机所迫,最根本的则是东南社会在处理国家、地方与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主观“共识”。
第二,“遵旨办理”。当清廷决计“宣战”,战争已不可避免时,东南督抚面临严峻的政治抉择。清廷发给各省督抚的“招拳御侮”上谕,成为东南官僚集团最为忧虑的政治“阻碍”,东南互保的“合法性”很可能因此遭到质疑和批评。在此情形下,“矫诏说”应运而生,中外“订约互保”这一看似“两全”的“创举”被紧急提上日程。东南督抚为了摆脱“僭越”、“卖国”的嫌疑,极力将东南互保“合法化”:他们一面死死抓住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清廷要求他们“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上谕,将清廷此后所发的上谕一律视为“矫诏”,拒不奉从;另一方面极力淡化他们与外国的勾结,将“中外互保”视为“南省自保”、“东南各省联约互保”。“自保”与“互保”一字之差,但主、客体和性质迥异。“自保”、“联保”的主体是东南督抚,客体是东南疆土,保的是“中国”,是清王朝的江山基业;而“互保”则比较复杂,关键是“互”字怎么理解:其一,“互”与“联”同义,主体仍然是东南督抚们之间互相联络,刘坤一、盛宣怀等运作东南互保的“法律依据”,正是清廷要求东南督抚联络一气、共保疆土的谕旨;其二,“互”是强调各省督抚抗“旨”不遵,“僭越”地方权限与外国列强“勾结”,保的是东南督抚们的“势力范围”和东南一隅的“洋人”,性质形同“分裂”和“叛国”。东南互保的策划者们极力鼓吹前者,淡化后者,将策划中外互保标榜为自己“忠君爱国”的丰功伟绩。清廷虽然对东南督抚无视中央权威和京师险境,擅自与外国媾和的做法不满;但北京失陷后,由于时局所迫,惊魂未定的清廷又不得不承认东南互保的合法性,大力表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老成持重和良苦用心。
早在“中外互保”谈判之前,刘坤一就特地指示具体操作东南互保事宜的盛宣怀,“惟兹事体大,各条措词必须得体,留事后进呈地步”。[18]256盛宣怀在中外互保的谈判中也诡称“订约互保”是“遵旨办理”,以获得外国对中方谈判资格的认可。刘坤一、张之洞等对东南互保事直到一个月后才向清廷汇报,其奏折措辞精心雕琢,可谓煞费苦心。六月二十三日(7月19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会奏稿,拟借救使立论,带叙保护事,较不著痕迹。惟弟近日心思枯涩,笔不能达,务求大加改正。”[19]1435他在奏稿正文中则将“订约互保”的起因归于海外华侨的强烈请求,他说:“接出洋华民电禀,请保护各国洋人,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臣等遂乘各领事来商保护商、教之时,会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立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犯我,当照常保护。经各领事电商各外部,臣等亦电各使臣,向各国切实声明。德因戕使,颇持异议,嗣为各国牵制,遂亦贴然就范。”[19]1435刘、张将策划东南互保的行为,由中外“互保”到南省“联保”,行为主体和客体的变化,实际反映的则是东南督抚及其智囊所精心策划的“偷梁换柱”之政治伎俩。
第三,“延宗社”、“保两宫”。“东南互保”的根本宗旨和目的,是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尽管东南互保使晚清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离心力”甚为凸显;但东南督抚和东南社会主流意识之政治尺度,仍然无法超越“延宗社”、“保两宫”的封建政治伦理。皇权是中国封建王朝国家最高权威的象征。戊戌维新中,光绪皇帝大刀阔斧的维新措施,赢得了工商阶层和部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囚于瀛台,并蓄谋废黜光绪帝,却遭到刘坤一和东南社会绅商阶层的强烈反对。刘坤一致函荣禄,明确表示“君臣之义久定,中外之口难防”,反对清廷的废帝图谋。慈禧太后遂以“己亥立嗣”作为“废帝”的缓冲策略,但是此举又立即遭到东南社会的强烈抵制。清廷宣布“立储”的第二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联合东南各界千余绅商名流联名通电,呼吁光绪皇帝勿存退位之心,“力疾亲政”。该电迅速在海内外掀起一场不大不小“保皇”风潮。东南社会各界“群情汹汹,竟传废立之说,士大夫倡之于前,愚夫妇附之于后,万众哗然,四海鼎沸,狡而黠者遂跃然思起,岌岌焉,几有朝不保暮之忧也。”[20]由此可见,尊崇和维护皇权是东南社会的普遍共识。东南互保的另一重要原因,即东南社会认为“拳祸”的罪魁正是大阿哥之父、力主“废帝”的端王载漪,他们把义和团运动看做是端王集团牺牲“国家”利益,篡夺皇权的政治阴谋。因此,在战后中外“议和”的过程中,东南督抚的重要“任务”就是“清君侧”,请求清廷惩治“肇祸”诸大臣。
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社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以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为主要活动空间的维新党、革命党以及哥老会等)争相角逐的政治舞台。东南互保尽管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其“延宗社”的政治宗旨与革命党的“反清”目标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而“保两宫”、继续承认慈禧太后的最高权威,又与新党的变政诉求背道而驰。因此,在中外互保的背景之下,“革命”与“保皇”又构成了晚清东南社会之政治心态和社会异动的两个鲜明特征。正如日本学者永井算巳所指出的那样,“东南互保约款”事实上已经成为镇压自立军的法律和政治上的支柱,它是一个对内具有反对康有为、梁启超派和孙中山派的性质,而对外又具有“反帝”性质的双重结构。[21]328东南互保是东南督抚及部分社会精英最核心的对内、对外政策,一切与之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活动,最终都将被地方政权所排斥和镇压。
四、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自治思潮
尽管东南互保时期所出现的“独立”“自治”思想不是社会主流意识,但也是有来由的,它实际上是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延续和发展。
地方自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潮,早在鸦片战争后一批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认知和考察中就已初露端倪,但其真正演化成较为成熟的社会思潮则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维新派干将以及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人都曾大力倡议地方自治。维新失败后,这股潮流随之衰落而成为社会潜流,革命派则将其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
庚子前后,在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外国列强的武装侵略压迫下,清朝中央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央与地方政权在应对时局上的政策分歧,外国列强(主要是日本)的政治引诱以及国内革新势力的积极活动,对东南社会尤其是地方督抚的“独立”“自治”思想有直接影响。在复杂的矛盾和局势下,清廷的“倒行逆施”又使地方自治潜流迸发生机,东南督抚和一批社会精英从“自治”中得到“启发”和“灵感”,而“地方自治”也因此被衍化为“自保东南”、“中外互保”,东南互保运动以及“独立”“自治”思想由此而起。
义和团运动后,清廷为了巩固统治、顺应民意,主动实施“变法”,刘坤一、张之洞鉴于实施东南互保之经验教训,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大力推动清廷实施“新政”。随着“新政”的展开和立宪运动的高涨,清政府也认识到“地方自治一事,为将来宪政的基础,此实内政改革最大之关键”。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地方自治被纳入清政府的直接规划与督导之下,各省、各地纷纷成立相应的自治机构,地方自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并且声势巨大。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虽然覆灭,但地方自治思潮并未止息,其对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自治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东南互保时期的“独立”“自治”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势而凸显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倾向。换言之,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持续发展和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区域)观念(即所谓的“东南意识”)的不断深化是东南互保运动重要的思想诱因。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无论是李鸿章的“两广独立”(事实上“独立”口号是革命派提出的)还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邦政府”设想,抑或是东南精英所组织的“国会”,尽管其中偶尔迸发出一丝“革命”火花,但终未能突破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政治界限。
[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M].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J].安徽史学,1991,(1):49-55.
[5]董丛林.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0-35.
[6]顾廷龙,叶亚康.李鸿章全集·电稿: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佚名.固南援北策[N].中外日报,1900-07-12(1).
[8]佚名.筹南十策[N].中外日报,1900-07-14(1).
[9]佚名.东南变局忧言[N].中外日报,1900-07-27(1).
[10]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1]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2]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A].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3]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 —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J].学术月刊,2005,(8).92-102.
[14]杜万之等.自立会史料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1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6]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C].苏位智、刘天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17]佚名.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N].中外日报,1900-07-07(1).
[18]陈旭麓,等.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刘坤一遗集[C].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佚名.论中国人心浮动之可忧[N].申报,1900-02-22(1).
[21]佐藤公彦.日本义和团研究一百年[C]//苏位智,刘天路.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济南:齐鲁书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