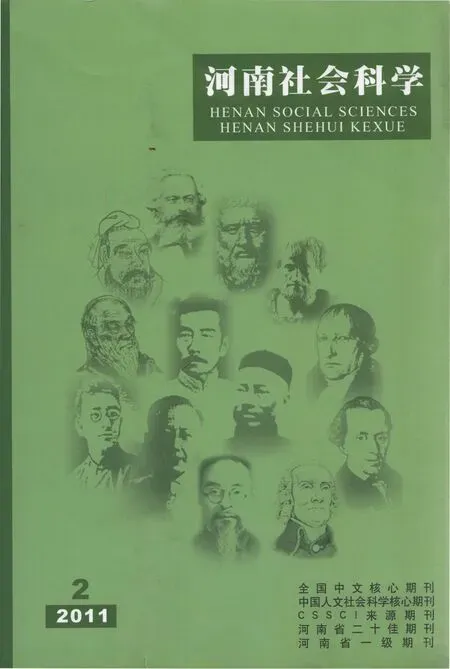论编辑权利及其保护
2011-04-13段乐川
段乐川
(武汉大学 出版科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论编辑权利及其保护
段乐川
(武汉大学 出版科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编辑工作是一项高度职业化的工作,在媒体文化的生产、传播和积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编辑实践中,编辑工作者虽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责任,但是与其相匹配的编辑权利有时却得不到保障。编辑权利的缺失,不仅影响到编辑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也不利于编辑活动主体“六元”关系的协调运行。明确编辑权利,以及探讨编辑权利的保护途径,是编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编辑;“六元”;权利;保护;途径
当代编辑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工作。各种类型的媒体,都离不开编辑工作这一环节,离不开职业化的编辑队伍。在媒体文化的生产、传播和积累中,编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社会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肩负着对信息的鉴审、过滤、加工、优化等重要职责。编辑工作的优劣,从小的方面说影响出版物质量的高低,大而言之则事关整个社会媒体文化发展的状况。但是,在现实的编辑实践活动中,社会在强调编辑工作者需要承担极度重要的社会责任之时,却对与其责任相匹配的权利漠然视之,甚至连编辑本身对编辑权利的概念也不甚明了,编辑权利意识极其淡薄。编辑权利缺失这一状况,不仅影响到编辑主体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且不利于包括编辑、作者和读者在内的编辑活动主体关系的处理。因此,提出编辑权利的概念,探讨编辑权利的确立和保护,既是编辑主体研究的新视角,又是编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编辑权利确立和保护的必要性
编辑活动的展开,是编辑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编辑活动的主体元素指作者、编辑和读者,客体元素是指文本、稿本和定本。文本是既有的社会文化结构,是作者创作稿本和编辑编订定本的基础,也是读者接受编本、进行阅读阐释的基础;定本是编辑对作者稿本进行编修完善的出版物。由主体、客体所构成的这六种元素,在编辑学研究中被称为编辑活动“六元”。编辑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实际上是编辑活动构成要素的“六元”关系。“六元”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作者以文本为基础创作出原创性精神稿本,编辑则代表读者、社会对作者的稿本进行加工完善形成定本。
编辑学者王振铎先生认为:“以‘六元’构成的编辑活动,实际上是作者、编辑和读者以‘媒体’(稿本+定本+文本)为中心,共同参与文化创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的生生不息的‘活动场’。”[1]在这个活动场中,编辑客体元素之所以能够从文本到稿本再到定本不断转换,是因为作者、编辑和读者不断地进行交互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三个主体元素相互影响的社会活动关系。由文本到稿本,包含了作者的首创之功。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编辑的策划之功也不可忽视。编辑从整体文化结构和读者接受需求出发,在稿本的创意构思和选题拟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稿本到定本,更是浸润了编辑大量的劳动。这些劳动主要有:一是对稿本的鉴审,即代表社会对作者的稿本作出价值判断,从而决定对稿本的取舍。我们常把这种鉴审行为称作“把关”或选择。二是对稿本的完善,即以作者的稿本为基础,按照特定的编辑规范来优化稿本,使其趋于完美、臻于至善。完善的过程,当然也包含了编辑辛勤的劳动。三是对稿本的编修整合,即从不同媒介的特点出发,使稿本模式化、定型化。模式化、定型化的稿本,就是我们所说的定本。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读者接受的是作为整体“媒介”的“定本”。而作为整体的“媒介”的定本,不仅包含了作者创造性的劳动,还蕴涵了编辑的策划、鉴审、优化、编修整合等多种具有创造意义的劳动。而且,编辑进行的所有编辑行为都是代表读者,从接受主体出发而进行的积极的、能动的劳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编辑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中介,是作者和读者发生作用的纽带。读者文化需求的满足和提高,需要作为中介的编辑对文本加以考察和策划;作者稿本的传播,需要作为中介的编辑对作者的稿本加以鉴审和完善。编辑的劳动性质,决定了在编辑活动的“六元”关系中,编辑既是文化媒介的创造者,又是媒介文化的传播者,同时还是媒介文化的接受者。这种介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创造、传播和接受的多重角色,赋予了编辑在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中的重要的主体性地位。正如王振铎先生所言:“编辑是编辑活动的主体,是作者、读者与编辑社会关系中积极主动的富有创造力的角色。”[1]
由以上对编辑活动的“六元”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编辑是编辑活动主体元素中比较富有创造力的元素之一。编辑活动的展开,离不开作者的稿本创造,也离不开读者的文本接受,更离不开编辑的定本编修。从文本到稿本再到定本,无一不包含着编辑的创造性劳动。编辑在缔构媒介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但是,与比较强调编辑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的编辑实践很少强调编辑权利。编辑主体存在着权责不对等、不匹配这一现象。比如编辑代表读者、社会进行审读把关,承担着舆论导向、文化导向的重要责任,却没有被明确赋予稿本的审读处置权;编辑对稿本进行优化完善、整合组构,承担着保证文化质量的重要责任,却常常被认为是“为他人做嫁衣”,无法享有应得的社会认同。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中,一些编辑因为宣传导向、编辑规范、编辑质量等问题而受到严肃的责任处分,但在承担责任的同时有关的编辑权利却严重缺失。
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角度来看,一定义务的履行总是以与其相对应的权利赋予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编辑实践中,只强调责任而不重视权利的做法,不符合权责相一致的马克思法理学原则。编辑权利的缺失、编辑权责不对等的问题,表面上看无关大碍,实质上是对编辑主体能动性的否定,是对编辑创造性劳动的忽视。因此,在强调编辑承担社会职责的同时,理应明确编辑权利。明确编辑权利至少有以下两点意义。
一是有利于激发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叶向荣在《编辑概念诸说之辩证探析》一文中认为:“编辑是组织、审读、编选、加工原创作品以在整体上构成新作品(编辑作品)的著作活动及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或专职人员)。”[2]这实际上从整体创构的角度肯定了编辑劳动的创造性意义。王振铎先生提出文化缔构的编辑观,明确指出了编辑在媒体文化缔构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还指出编辑和作者在劳动方式和性质上的异同:“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与创作个体的文化关系。在社会文化大厦的建构中,编辑与作者分工不同。作者侧重预制部件的创造,编辑侧重对预制部件的整合组装。二者优势互补,并没有主从、高低、贵贱之分。”[1]分工不同,劳动性质相同。这就必然要求编辑应该享有与自身创造性劳动相适应的权益。就分工而言,编辑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结构出发,来对作者的著作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这种代表社会和读者所进行的“预制部件的整合组装”行为,较之作者的个体创作行为无疑更具有文化主体创构意识,也更具有文本结构调整的自觉意识。这也必然要求赋予编辑具体的权利,以保证其文化主体创构意识的确立和文化主体创构行为的进行。
二是有利于规范编辑主体的行为,协调好编辑“六元”互动关系。编辑权利的明确,既是激发、保护编辑创造性活力的需要,也是理顺、协调编辑“六元”关系的需要。编辑活动的有效展开,是编辑主、客体元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编辑主体三元素的互动,对于实现由文本到稿本到定本的不断转化,至关重要。编辑“六元”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之一是编辑与作者的主体关系,比如在涉及对作者稿本的处置、加工时,编辑和作者容易出现纷争。编辑因为过度地进行编辑加工而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例子屡见不鲜。解决纷争、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是,明确双方各自的权益范围,确定各自的权利来源和行使方式。这样从权利的角度理清各自的权益界限和责任担当,就容易理顺彼此的关系,规范各自的行为,避免甚至消除双方的纷争、冲突。现有的《著作权法》是对作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至今没有法律法规对编辑的具体编辑权利进行界定,其对作品进行修改、加工的范围和界限等缺乏相关规定,这无疑是导致部分编辑加工行为失当的原因之一。
二、编辑权利的基本内涵
从编辑活动的“六元”关系可以看出,编辑行为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无论是编辑策划、鉴审,还是加工完善、整合,都是编辑代表读者、社会所进行的媒介文化生产、传播行为。编辑权利主要是指编辑的职业权利,是指编辑所应具有的按照编辑活动规律自由开展编辑工作的权利。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不同的是,因为编辑行为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编辑权利更多地具有“公共性”,是一种“公权利”。笔者以为,编辑权利的内容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稿本传播处置权。稿本的传播处置权主要是稿本的选择权。这最能体现编辑在编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最能体现编辑和作者的社会关系。编辑对稿本做出选择与否的决定,实际上是代表读者、代表社会在处理与作者的关系。稿本是被选用还是被弃用,有待于编辑从既定的社会文本结构出发,代表读者对作者的稿本进行价值评估,然后作出决定。明确稿本的传播处置权,是对编辑的编辑行为社会关系本质的确定,也是对编辑在编辑活动中主体性地位的确立。
二是稿本的修改、加工权。稿本是由作者创作的,是用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志的,因此在编辑过程中编辑有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侵犯的责任。但是,从编辑规范的角度来讲,编辑也有责任按照既定的编辑规范对作品进行修改、加工,使得作品符合社会规范,符合媒体模式,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赋予编辑修改、加工权,是由编辑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因为编辑工作具有对作品进行完善、优化的社会责任,只不过该权利的行使应该以尊重作者的著作权为前提。具体来说就是修改加工的内容要受限制,要更多地侧重于编辑规范。在涉及内容的完善上,应该向作者提出建议,由作者完成。
三是编本的人格权。由稿本到编本,作者的功劳最大,但是编辑的精神劳动也不容忽视。作为稿本的创作者,作者应该享有稿本的全部著作权。但是,稿本不等于编本,任何编本之中都包含着编辑的精神劳动。尽管这些劳动是一种“再加工”,但从劳动的性质上来讲,它与作者创造性劳动没有本质的差别。编辑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作为整体媒介的“编本”的编辑作品权利,比如编本的责编署名权。责编署名权,不仅仅是对编本责任的强化,而且是对编辑之于编本精神劳动的尊重和肯定,是一种人格权范畴,是对编辑创造性劳动的尊重。
此外,赋予编辑参与所在出版社或编辑组织民主管理的权利,也是编辑权利的应有之义。这既是基于出版社或编辑组织科学管理的需要,也是对编辑主体地位的尊重。还有,进修培训权也应该是编辑权利的内容之一。通过进修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既是编辑个体发展的需要,又会推动编辑组织整体工作的改进。
三、加强编辑权利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编辑主体意识,树立编辑权利观念。编辑权利保护的前提是树立编辑权利观念。应该通过大力宣传教育,让全社会认识到编辑工作者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确立和保护编辑权利的必要性、紧迫性。整个社会文化建设,既离不开作者的呕心创造、读者的接受传播,也离不开编辑的精心编审。编辑在编辑实践中的选择、优化、导向,不仅从细节上影响着编辑成果的优劣成败,而且从整体上作用于由编辑定本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大厦的建构。全社会应该认识到,编辑工作者在承担社会责任、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应该享有与社会责任、社会贡献相对等、相匹配的各项权利。编辑工作者应该摒弃那种“作者是编者衣食父母”的落后观念,确立编者在编辑活动中的创造意识、主体意识,增强编辑权利观念,加强自身权利保护。在工作过程中,不仅要承担起社会文化建设的责任,而且要敢于、善于维护属于自身的各项权利。
二是明确编辑权利内涵,明晰编辑权利保护原则。明确编辑权利内涵是加强编辑权利保护的基础。学界要充分展开有关编辑权利内涵、内容的探讨和研究,围绕编辑活动的实践,准确界定包含职业权利和一般权利在内的各项权利内容,尤其是编辑职业权利的内容。笔者提出的稿本的传播处置权、稿本的修改加工权和编本的人格权这三项权利,作为编辑职业权利内容,可供讨论。同时,还要认识到编辑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在确立编辑权利内容之时要兼顾平衡,充分考虑到编辑权利保护受到社会法规、作者权利、社会观念、编辑组织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力争既遵循编辑权责对等、编辑权利保护最大化原则,又不至于使编辑权利内容过于原则化,而无法落到实处。编辑行业现在已建立起全国性的自律性行业组织——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编辑学会作为行业协会,应该转变工作观念,拓展工作内容。在作为行业组织对编辑业务、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进行考核的同时,应该承担起保障编辑独立工作、维护编辑合法权益的重任,尤其是在编辑权利保护学理探讨、社会舆论构建和引导上应该发挥重大作用。
三是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建立编辑权利保护机制。权利属法律的范畴,法律法规才是编辑权利保护的关键。在实践中,很多行业都有涉及行业主体保护的规章制度,比如针对教师队伍有《教师法》,对教师职业的权利、义务以及资格任用和待遇都有明确规定。再如,针对律师行业有《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条款。正是这些法律法规,才确保了职业主体的权利保护能够落到实处。笔者以为,编辑工作已经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行业,国家已建立起完善的编辑职业任职制度,但是没有设立对编辑职业主体的权利保护措施。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借鉴其他行业,加强编辑职业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通过法律法规制度建立起编辑权利保护的完善机制。相关部门应该站在推动编辑工作改革发展的高度,进行编辑行业立法建设调研,加快编辑行业立法建设,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编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保护方式,真正使得编辑的权利和义务对等起来。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编辑的编辑权利、作者的著作权和出版社的出版权(复制传播权)应该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著作权是对作为原创性精神稿本所有者而言的,编辑权利是对精神产品生产、传播发挥作用的编辑而言的,出版权则是由著作权和编辑权利出发而衍生出的一种传播复制权。确立编辑的编辑权利,不会削弱作者的著作权,更不会影响到出版社出版权的行使。相反,编辑权利的确定,带来的是编辑主体地位的确立,编辑权责的明晰对等,这必将激发编辑进行创造的活力,从而促使编辑活动“六元”间比较协调的交相互动关系的出现。
[1]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叶向荣.编辑概念诸说之辩证探析[J].编辑之友,1995,(5):19—22.
责任编辑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G214
A
1007-905X(2011)02-0186-03
2010-12-10
段乐川(1981— ),男,河南南阳人,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编辑理论、编辑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