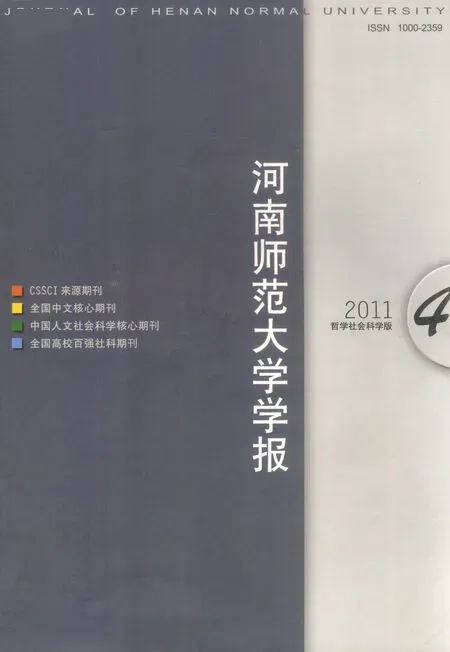属下、飞散与精神家园
——对勒·克莱齐奥《金鱼》的解读
2011-04-12常小静
常 小 静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属下、飞散与精神家园
——对勒·克莱齐奥《金鱼》的解读
常 小 静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金鱼》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一方面展现了黑人女性的卑贱社会地位——“属下的属下”,另一方面探索了黑人女性如何超越这种卑贱社会地位的文化策略——“飞散”式的诗意栖居。作品表达了作者对20世纪种族冲突、民族纠纷的深刻反思和对人类终极家园——“心灵原乡”的不倦追求。
勒·克莱奇奥;属下;飞散;精神家园
让·玛利·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因“新的逃离、诗意冒险和感官狂喜的作者,主流文明外部与底部的人性探险者”而荣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勒·克莱齐奥的一生是“飞散”(diaspora)的一生,甚至连自己的写作都有着强烈的“飞散”性、跨文化性。长期的“飞散”履历与写作中的“飞散”实践,使得他的作品充满“飞散”意味:主人公往往是无根的浮萍,在无垠的异域他乡无休止地流徙、漂泊,饱尝人世辛酸苦痛,但却从未失去对人类美好精神家园的信仰,在一次次的逃离、孤行、求索中,以一种诗意栖居繁衍着一个“飞散”者的“家园”。他的代表作之一《金鱼》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名为莱拉的女孩的“属下”(subaltern)苦难、“飞散”式的诗意栖居以及对人类终极家园——精神故乡的执拗吁求。
一、“‘属下’的‘属下’”之痛
“属下”又译作“贱民”,最早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意指农村劳动力和无产阶级。后来被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家伽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引用,指涉社会地位更为低下、没有话语权力的“他者”群体。在著名的《属下能否说话》《三个女性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斯皮瓦克指出,第三世界妇女作为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既是帝国主义书写的对象,又是男权主义所异化扭曲的文本,同时被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双重“他者”化、边缘化。小说《金鱼》中的主人公莱拉正是这样一位“属下”个体。在渗透着父权机制与帝国机制的异国他乡,白人女性的种族歧视、西方男性的淫威暴行、同样被边缘化的黑人男同胞,共同将莱拉置于“‘属下’的‘属下’”——白人男性的“属下”、白人女性的“属下”、黑人男性的“属下”。它意味着永远被建构、被凌辱、被践踏。
作为有色人种的一员,莱拉6岁时就被拐卖到摩洛哥,在摩洛哥、巴黎、尼斯、波士顿等地,莱拉饱尝非“属下”阶层的欺凌、侮辱与折磨——被男人当作妓女,被女人当作“他者”或是妖魔。在摩洛哥,她被主人佐拉夫妇视作“野孩子”[1]4、“小妖精”[1]14、“杀人犯”[1]14,被禁闭在家中,操持家务稍有不周之处,就会遭到佐拉的谩骂与毒打。三番五次地遭到男主人的性骚扰,甚至是强奸。为了摆脱“属下”苦难,莱拉逃到了法国首都巴黎。但刚到巴黎,就遭到一位白人女性的恶意凌辱:
“你说,小婊子,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连忙向后退,她继续向前逼,两手使劲抓住我的头发,揪着我的头朝水盆使劲磕去,我惊恐地大声叫起来,她这才松了手,嘴里还愤愤地骂道:“婊子!滚,下流胚!”她快速地收拾她的东西:“别看我,闭上眼睛!我让你给我闭上眼睛!你要是再看我一眼,我就杀了你!”[1]70
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中,“女人”是一个等级化概念,白人女性处在中心地位、主体地位、统治地位,黑人女性处在边缘地位、客体地位、被统治地位,黑人女性的唯一权力就是被言说、被压迫、被妖魔化。如果说在白人女性的字典里,莱拉的“黑皮肤”与妖魔同义,那么,在白人男性的字典里,它则与妓女没有任何区别。莱拉深知:帝国主义和男权机制的渗透无处不在,在法庭以及其他所谓伸张“正义”之处,拥有黑皮肤的女人同样处在“属下”的“属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将黑人女性归为“属下”阶层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男性,还包括莱拉的男性同胞,“黑人背叛黑人”[1]125。
二、“飞散”式的诗意栖居与“非家幻觉”
“飞散”(diaspora)这个古老的词源于古希腊词diaspeirein,前缀dia指“散开”,speirein指播种,最初是指植物借助花粉的飞散与种子的传播繁衍生息。后来,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指上帝故意让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由于这种联系,“飞散”就获得了这样的意义:某个民族离开故土家园到异乡生活。20世纪80年代后,“飞散”一词的意思再一次被重构,与全球化、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生产相联在一起,意指民族和族裔的文化和历史必然是在跨民族的关联中以旅行、翻译、“混杂”(hybrid)等方式展示和繁衍自身的。
“飞散”以德里达的“延异”与霍米·巴巴的“混杂”为起点,反对民族主义与“同化”意识,主张身份的跨民族性和文化的混合繁衍。著名“飞散”学家克利福德·詹姆斯(James Clifford)认为:“家园”是非固定的,跨越时空的,应该“在世界中发现家园,或在家园中发现世界”[2],恢复“家园”的自由性;身份的本真状态是“混杂”的、流变的,应该在“他者”中发现“自我”,或在“自我”中发现“他者”,重获身份的主动性。在小说《金鱼》中,莱拉以“飞散”式的诗意栖居挣脱帝国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枷锁,颠覆了传统身份的观念,解构了传统“家园”的意义,创造、繁衍出“飞散”者的“混杂”身份和“本土兼全球”(glocal)式的“家园”,实现了跨文化、跨地域的“差异”解放。
首先,莱拉的出生对传统观念中身份与“家园”的意义构成了挑战。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身份与“家园”始终是固化的、现实的、不容置疑的,不同的身份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可跨越性;“家园”总是特指一个固定的、独一无二的地域空间,有着显在的、永在的疆界与边沿。但其实,身份与“家园”本身是被建构与想象出来的,正如萨特、波伏娃等存在主义者所指出的,“不存在着类似固定不变的个体身份。个体通过选择某项筹划来造就自身”[3],在故事的一开始,莱拉说道:“我不知道自己在出生时妈妈给我取过什么名字,父亲是谁,以及自己出生在哪里的。”这一身份缺失与“家园”虚无的现实无疑对身份与家园的传统观念构成巨大挑战。接着,莱拉以“飞散”式的逃离对自己的“‘属下’的‘属下’”地位进行了抵抗,对传统身份与“家园”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与颠覆,重建了“二律背反”身份和“本土兼全球”式的“家园”。在这种辗转漂泊的生命历程中,莱拉创造、繁衍出了自己的真正身份——“混杂”。同时,也正是在流离失所的迁徙中,莱拉译介、耕耘出自己的“家园”——世界。莱拉的“家园”是跨民族、跨地域的,是持续繁衍的、没有界限的,是本土也是全球的“二律背反”。莱拉的“本土兼全球”式的“家园”指出,人类的“家园”不存在于故国的乡土,而存在于未来的目的地,“家园”的意义在于幸福的归宿,而非乡愁的羁绊。这无疑彻底解构了传统观念中的“家园”逻辑:“家园”不是一个无法穿越的空间,而是实现个体幸福的“世界”——哪里有幸福,哪里就是“家园”。为了挣脱西方话语霸权的监牢,莱拉选择了极端的抵抗方式——“耳聋”。作者勒·克莱齐奥对莱拉听力的阉割,不仅使得西方话语霸权完全失效、瓦解,也为莱拉的身份与“家园”的自由繁衍扫清了障碍。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指出,一些看起来令人恐惧和陌生的现象,实际上来源于某些我们很熟悉的经历。这种心理现象叫做“暗恐心理”(uncanny)。在德文中,“暗恐心理”与“非家幻觉”同义,也与“家园”(heimlich)密切相关。“暗恐心理”或“非家幻觉”实际上根源于“家园”中压抑情绪的移植和复现。在西方世界中,殖民历史的创痛记忆游魂般地追随着飞散者,一旦现实生活条件促成压抑情绪的复现,“非家幻觉”就会出现。那么,在小说《金鱼》中,莱拉的“非家幻觉”是什么呢?那就是被拐卖的创痛记忆。
记得那是一条洒满阳光、空旷且满是尘土的大街,天空蓝蓝的,一只黑色的大鸟掠过天空,尖叫着。突然,几只男人的大手把我投进了一个袋子,我快要窒息了。[1]1
每当莱拉被白人唾骂、指责,或是面对男性强暴的威胁时,这一幕就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三、“心灵原乡”与“精神家园”
面对“‘属下’的‘属下’”的现实地位,莱拉以“飞散”挣脱帝国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枷锁,颠覆了传统的身份与“家园”,诗意栖居在人类的终极故乡——精神家园。那么,作为人之终极归宿,精神家园何以为精神家园呢?在小说《金鱼》中,莱拉以悲悯的情怀在这条道路上不倦地求索着:弃绝异化扭曲的现代社会,回归澄明至远的自然世界;以音乐的诗性沟通净涤语言的荒芜与失落;以永不泯灭的人性重建整个世界的尊严。在全球异化、文化陨落、种族冲突、道德虚无的现实生存境遇面前,勒·克莱齐奥对语言、家园、人性进行了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的观照、反思、书写,表现出深切的人文焦灼意识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自然景色在莱拉的生命历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父权制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无处不在的捆绑与迫害下,“‘属下’的‘属下’”的莱拉体验着不堪忍受的苦痛,但自然世界总能带给她快乐与希望。当莱拉从阴冷的地下室奔到摩天大楼顶层时,她看见了一望无际的林荫大道与如黛的山峦,她说:“我有些激动,感到眼睛微微有些湿润。”[1]94当莱拉从巴黎逃到尼斯时,她看见了浩瀚的大海,她说:“我激动得两眼有些湿润了。”[1]151当莱拉从摩洛哥逃到巴黎时,她看见了辽阔的山谷,她说:“我想这会儿即便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1]61大海与沙漠是小说中频繁闪现的两个意象,它象征着飞翔与自由,是莱拉雀跃欢呼之源和“心灵原乡”之寄。
音乐也是莱拉“心灵原乡”的乡音之一。在莱拉的“飞散”历程中,音乐始终是她医治创伤的一剂镇痛药。当莱拉遭受白人女性的蹂躏、蔑视时,当莱拉被男人诱拐、强暴时,当莱拉在西方世界无立锥之地时,她总会将满腔的愤怒、责问、呐喊斥诸音乐之中:
让我们跳起来吧,
那属于我们黑人的舞。
让我们跳起来吧,
那砸碎锁链、冲破牢笼的舞。
让我们为美丽、善良、合法的黑人,
尽情地跳起来吧![1]112
在莱拉的心中,音乐这种无字的语言是挣脱枷锁、奔向自由的标帜,是超脱俗世、返归自然的象征,也是指引精神故乡的路标与号角。永不泯灭的人性是人类终极家园——“心灵原乡”的核心道德维系。在小说《金鱼》中,养母拉拉·阿玛、贝阿蒂斯夫妇、护士娜达·莎薇正是“向善”人性的代表者。以拉拉·阿玛为例:拉拉·阿玛为了解救这个被拐的孩子,从贩卖黑人的强盗手中买下了不满10岁的莱拉。从此以后,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教育莱拉,处处庇护、照顾莱拉,关系俨然一对感情融洽的祖母与孙女。所以,莱拉才亲切地将拉拉·阿玛唤作“奶奶”。当左娅辱骂莱拉是个“没爹没娘的可怜虫”[2]4时,莱拉说:“我不是孤儿,我有拉拉·阿玛奶奶。”[2]4在作者勒·克莱齐奥的笔下,养母拉拉·阿玛、贝阿蒂斯夫妇、护士娜达·莎薇三个形象的塑造是对道德情怀与人性尊严的一种呼唤,对种族偏见、民族纠纷的一种深刻反思。
在诗意盎然的“飞散”旅行中,勒·克莱齐奥善于在点滴的生活感触与日常经验中,表露深厚的忧世情怀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不倦追求。家园的中心不仅仅是围绕生活场所弥漫出来的气息、心情,更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理念与精神。在跨文化、跨地域、跨语际的文本书写中,勒·克莱齐奥的《金鱼》彰显了“身份即虚无”、“家园即世界”的存在本质。为了揭示生活的本真状态,唤醒沉睡已久的人性,他将现实世界转变为富有“飞散”意味的文化家园,将生命家园的历史记忆升华为一种人类高端的心灵原乡,升华为一种精神信仰、一种生命图腾,并时时为世界上无所不在的善良与仁慈所感动。
[1]勒·克莱齐奥. 金鱼[M]. 郭玉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16.
[3]萨莉·J 肖尔茨. 波伏娃[M]. 龚晓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27.
I106.4
A
1000-2359(2011)04-0195-03
201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