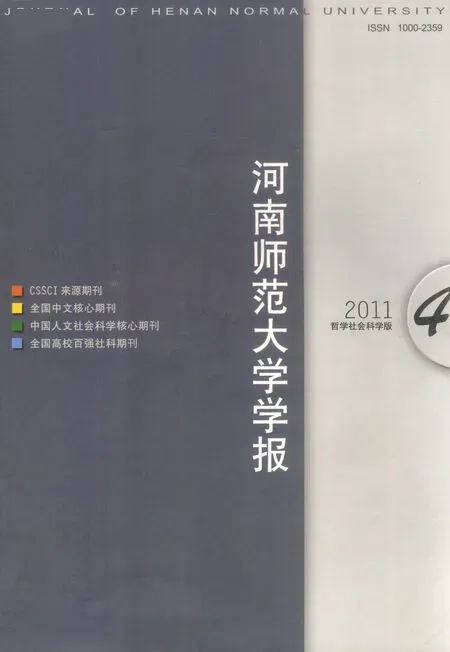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质素探析
2011-04-12柴华
柴 华
(黑河学院 中文系,黑龙江 黑河 164300)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质素探析
柴 华
(黑河学院 中文系,黑龙江 黑河 164300)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以个人化的诗学阐释构建起具有本土化特质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从起步建设到成熟深化及至开放融合的建构轨迹实为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诗学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建构机制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会通,其面对新诗创作实践和张扬新诗本体特质等鲜明的建构特征为中国新诗的本体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诗;象征主义诗学;历程;机制;特征
20世纪上半叶,在极为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语境中,一些现代诗人和诗论家以个人化的诗学阐释,在诗歌本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等方面构建起具有本土化特质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而这样一幅体系相对完整的诗学构图,显然不是封闭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文学现象,突破闭锁态势的发生发展机制,必然决定了它是由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相互碰撞而完成的一种“塑造”。伴随新诗的现代化追求,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不仅经历了艰难的体系建构过程,更以其鲜明的建构特征为中国新诗发展的本体追求作出了贡献。
一、建构历程: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呈现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获得起步建设的契机,经过30年代的探索后而走向成熟深化,最终在40年代的反思超越中迎来自身的开放融合,它不断顺应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以自觉的诗学意识积极开创生存空间,可以说,这一发展进程本身“既受社会外部历史条件的影响,又受中国诗学的内在力量的驱动,是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呈现”[1]。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的新诗坛,本土化的象征主义理论建设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即使谈到象征主义,也大都是通过译介行为来达到介绍的目的,而译介本身因为“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概念的混淆使用,也显现了新诗坛最初接受西方理论时在理解上存有的混乱状况。当时众多的译介文章虽然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法国象征诗人,并对这些诗人的创作、诗论进行了评判,但译介者大都是以自己固有的艺术价值来加以评介的。可以说,由五四到20年代中期的象征主义译介热潮仅仅起到一种浅显的传输作用,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感。就具体的诗歌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真正堪称象征主义的作品也是“缺乏”的,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没能在本体意识上具备向西方象征主义诗潮全面借鉴的自觉性。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政治革命的紧迫形势以刻不容缓的姿态感召和牵引着诗歌的神经,诗歌开始日益偏离自身的轨道,“向外转”的工具色彩逐渐遮蔽其艺术探求的取向。正是在树立“纯诗”风气的浪潮中,以李金发为首的初期象征派诗人崛起于诗坛,诗人穆木天、王独清经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美学思想的孕育,以《谭诗》和《再谭诗》两篇理论文献揭开了本土化象征主义诗学建设的序幕。尽管他们的创作实践并不成功,但诗人对诗歌本体的自觉追求奠定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设初期的基调。颇为遗憾的是,《谭诗》发表后不久,穆木天就完全抛弃了象征主义,认为自己先前对象征主义的沉醉是“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2]。这一诗学立场的“转身”恰恰显明,现代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使得革命政治需要与诗作艺术探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左右象征主义诗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影响着其命题内涵的深度延展和诗学地位的最终确立。
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写就的关于《象征主义》的系列诗论标志着人们对象征主义认识的深化。梁宗岱的诗学建树不仅在理论上较系统全面,而且结合诗歌创作详细阐释了象征主义的本质特征,他关于“象征即兴”说的理解,关于象征之道“契合”论的提出,以及对“纯诗”说和音乐形式的特殊追求,都代表着本土化象征主义诗学建设进入了成熟阶段。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的《诗论零札》和苏汶的《望舒草·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丰富。与此同时,批评家李健吾,对卞之琳、何其芳等现代派诗人的“纯诗化”作品进行了精到深入的评论,并由此开创了现代“纯诗”批评。
从这一时期象征主义诗学发展的现实语境来看,30年代的诗坛始终并存着两种姿态,与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密云期诗人群的战斗姿态不同,走“纯诗”路线的诗人奋力摆脱政治斗争的干扰,他们强调艺术创作的本体精神,积极扭转新诗创作的“非诗化”倾向,从诗歌写作和诗学创建的双重路向出发,努力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但在中国社会日趋动荡的复杂形势下,象征主义诗学想只依靠自身的内驱力来保持诗学内涵的艺术“纯度”只能是美好的“乌托邦”,它不得不在日趋艰难的建构环境中对自身的“纯艺术”立场进行反思,并逐渐意识到要把诗学的发展纳入到时代与其自身的多重关联中。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自觉中获得一种敏锐的诗学创造能力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现实主义成分整合到象征主义诗学体系中,使其以沉稳的发展步伐呈现出明显的开放与综合趋势。袁可嘉连续撰写的探讨“新诗现代化”的多篇诗论文章,在继承30年代现代派诗学传统和借鉴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学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诗学原则[3]220,强调“知性与感性的融合”,注重诗与经验的关系,倡导“新诗戏剧化”,这些具有突破性的诗学创见纠正了此前诗学过于“尊重诗的实质”而回避反映现实问题的偏颇,使象征主义诗学摆脱了此前艺术形式发展陷入窘境的局面,在更具宽容性、包含性的层面上拓宽了诗学体系的生存路径,在一个新的逻辑起点上推动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深入发展。此外,唐湜在这一时期由感悟出发就现代派诗作也写下了大量诗论和诗评文章,他的“诗是经验”说和“意象凝定”论以一种融合中西文化的建构姿态完成了一个特殊时代所赋予的诗学建设课题。可以说,40年代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以“重返大地”的学理反思,较好地解决了通过象征表现现实的问题,找到了体系自身的建构生长点,实现了诗学体系的现代转型,进而达到一个较为深厚而开阔的诗学境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轨迹表明,一种诗学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新诗本体的艺术发展规律,要始终从新诗创作实践的需要出发不断发掘和深化自身的诗学内涵,更要善于在复杂多变的诗学发展境遇中通过自我反思找寻诗学体系的建构生长点,如此才能在诗学建构的曲折历程中赋予自身旺盛的生命力,这不失为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诗学呈现。
二、建构机制:“偶然相遇”与契合认同
“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它的基本指向,就是借用西方话语改建中国诗学话语,实现中国诗学的现代化”[4]。西方话语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主要理论资源,其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历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这一过程中,诗学建设者开放与引进的接受姿态使得西方理论话语一经被“借用”便面临着如何对其“中国化”的命题,而“改建”和“实现”两个指涉诗学行为动向的关键词所呈现的正是诗学建设主体对西方理论话语实行“中国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之所以要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实现中国诗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西方的文论进入中国以至为我们‘化’的前提并不在西方而恰恰在我们自己,是西方文论对于文艺的阐述方式有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困惑才促使我们产生了‘化’的欲望”[5]168。由此可以确认,面对西方诗学的强大来势,中国现代诗人和诗论家是以适应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取舍标准的,而不是完全依附、盲目吸收西方话语资源的。这样,当我们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意义出发,深入讨论诗学建构机制问题时,“便应该竭力从这样的比附式的思维形式中解脱出来:不是我们必须要用西方文论来‘提升’、‘装点’自己,而是在我们各自的独立创造活动中‘偶然’与某一西方文论的思想‘相遇’了”[5]170。由此,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正是缘于“偶然相遇”与契合认同的发展背景和思维意识,在追求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的会通,极大推动了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步伐。
如果考察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中西会通的“起点”,1926年周作人的理论思索可作为讨论的开始,他第一次把“兴”与象征相联结,“为现代诗歌运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理论支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思维获得了符合世界潮流的解释,外来的诗学理论也终于为本土文化所融解消化”[6]。从周作人理论思考的诗学意义来看,这一评价显然有些过高,但也揭示出一个可贵的事实,即在周作人对“兴”与象征关系的理解中已经孕育了中西诗学融会的立场取向,他的“融会”只是针对当时白话新诗弊端的有感而发,是一次“理解的迷误”,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诗学建设。而这以后,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对中西融合的理解渐渐成熟,他们对“纯诗”、“象征”、“意象”、“晦涩”等象征主义诗学核心范畴的经典阐述,已经表明诗学家们在中西诗学会通方面的理论自觉。
毋庸置疑,穆木天、王独清关于“纯粹的诗歌”、诗歌的音乐美和暗示性等诗学思想都最直接地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而梁宗岱凭借对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理论的了然于胸,更是创建了精深幽微的本土化“纯诗”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诗学建构并非是脱离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空中楼阁”,穆木天的“纯诗”论来自对新诗流弊的反思,而梁宗岱的“纯诗”论则是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也就是说,他们的诗学建构是源于中国新诗现代化之路上的自我认识,是一种由自我感受生发的精神创造,他们并非简单地“移植”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素,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理论已完全受命于中国现代新诗自己的滋生机制,实现了向中国本土化的转换。那么,“外来的文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本土转化,这主要取决于双方文艺思想的契合程度、认同程度”[5]167。这种相互间的契合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诗论家们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集体记忆”。如果说象征主义诗学建构初期的穆木天、王独清在这方面还没有更多的表现,那么“在‘象征主义’这样的欧洲文化他者的现代性诉诸文化一体时,梁宗岱所激发的恰恰是对自我传统的文化故乡的深切怀念”[7]。尽管他深为推崇西方象征主义,但他还是认为,中国新诗的创造必须建立在中国“二三千年光荣的诗底传统”之上,他关于象征“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的两个特征及其对象征定义的阐释,一方面深得法国象征主义关于契合论、诗歌语言暗示性特征的精髓,另一方面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情”、“景”、“意、象”等诸多观念。此外,中国传统诗学中追求含蓄蕴藉、借助朦胧意象传达感觉和体验的方式,与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力避直陈与尽述,借助象征的暗示性启引深玄精微的旨趣相暗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较少障碍地认同和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精髓部分。象征、意象等范畴在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中作为界定诗歌本体的核心元素的确立,实际上是缘于中西方诗学双重背景的支撑。
似乎可以断定,在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偶然相遇”时,正是隐藏在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人们对中西诗学的契合认同。中国现代诗学家们深厚的传统诗学修养和文化资源影响了现代诗学的建构,而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则为新诗现代化提供了异质的诗学新内涵,似乎也促成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与传统诗学的历史性相会。
三、建构特征:尊重“蜕变的自然程序”
与古代诗学相比,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诗学在本质上体现出一种现代性,它是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理论表述,它的体系建构是紧紧围绕新诗的现代转型来完成的,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3]21。从这一理解出发来审视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现代构建,其焦点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而在于象征主义诗论家们的诗学趣味和诗学话题的“发生”,以及理论话语模式的形成,与现代诗歌的转型及其发展环境有着怎样的密切关联,他们的感受和解释是否尊重了新诗现代化“蜕变的自然程序”。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最终指向的是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特征。
首先,充分面对现代新诗的创作实践。考察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创建历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象征主义诗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对当时新诗创作的密切关注,始终沉浸在与创作事实密切关联的氛围之中,是活跃的新诗创作不断推动着诗论家们的理性思考。20世纪20年代中期,面对胡适倡导以“文的形式”实现“诗体大解放”,穆木天等人以明确的“中国意识”积极引进法国象征主义“纯诗”概念,其诗歌理论的出发点显然来自中国新诗现代发展的基本现实,并以实际感受建构自己的诗学主张。梁宗岱的诗学命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诗歌创作的理论反应。同样,40年代袁可嘉对“新诗现代化”的自觉追求,也是理论家力图解决“当前新诗的问题”而提出的最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创见。由此可见,支配诗论家诗学建构的主要动力并不是对古代或者西方的诗论加以继承或排斥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解释正在变化着的诗歌创作状况,致力解决新诗创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他们诗学的“个人化语言”全部源于对新诗创作经验的深刻观察和总结,以及对中国新诗创作境遇的实际介入,是丰富的文学事实激发了理论家思考的兴趣、解释的冲动和理论建构的欲望。
其次,努力张扬现代诗歌的本体特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自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一种将文学事业政治化的倾向,与之相比,象征主义诗学立足诗歌本体的艺术特质构建诗学基本命题,并在复杂的时代政治语境中表现出维护诗学体系的学术姿态和本体立场。从穆木天提出的“诗的思维术”和“诗的逻辑学”,到梁宗岱对诗歌语言和形式的现代性的积极倡导,他们在理论层面为探寻现代新诗“诗质”所作出的努力和象征主义诗人在实践中创获的卓然成就,都蕴涵着一种注重诗歌本体的诗学建构精神。尤其需要指出的,这种建构精神大多是在与非文学的政治化倾向的对峙中鲜明地表现出来的。如《谭诗》就是穆木天为纠正新文学建设初期的“时代使命感”而写就的“纯诗”宣言,它首次以理论的力量张扬出象征主义诗学对诗歌本体特质的尊重。梁宗岱不仅在立场上以文艺的自主性拒斥文艺的政治化,更以《象征主义》、《谈诗》等经典性的理论篇章建构起幽微而精深的诗学体系,进一步推动着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深化。相比于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命题所具有的本体内涵,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捍卫文学自主性的诗学立场更显得不可或缺。
最后,具有诗学建构的自觉意识和深入探讨的自觉行动。一位当代诗评家曾谈到自己所理解的诗学现代性,认为“诗学现代性意味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习惯的理论思维”,“意味着一种追求开放、追求创生、不断突破超越的精神”[8]。这显然意在强调诗学建设主体的现代性特质,它其实是诗歌现代化进程中主体行为现代化的积极表现。如果从这一视角审视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诗学建构行为的最终实现都离不开行为主体自身的现代化。随着新诗的现代“进行时”,面对新诗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和体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主体自身始终持有一种超越精神,并以积极的建构意识和深入的创新行为丰富着诗学命题的具体内涵,推动着诗学体系自身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谭诗》就是穆木天对初期象征派诗歌理论的积极构想和开创性建设,完全是一种自觉建构的意识表现,这一具有“拓荒”意义的主体行为在成就了穆木天作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奠基者荣誉的同时,也引发了后继者对象征主义诗学深入探求的自觉行为。1930年代初期,无论是新诗创作还是新诗理论,都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但诗人大都流于对自己创作的说明而难以对新诗发展的总体方向提出深入的见解,而专心留意于新诗研究的理论家几乎没有。面对新诗现代化对理论提升的急切需要和象征主义诗学建设本身的“青黄不接”,梁宗岱以过人的理论见解自觉承担起象征主义诗学的建设重任,他的诗论集《诗与真》的出版正是这一自觉意识的体现。1940年代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转型时期的袁可嘉,凭着敏锐的自觉意识捕捉到诗学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诗现代化的诗学论文,成为推动象征主义诗学成功转型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正是缘于建构主体对诗学建设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才使得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完善,最终在新诗现代化探寻的曲折之路上占有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龙泉明.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J].文学评论,2002(1).
[2]穆木天.我的文艺生活[J].大众文艺,1930,2(5-6).
[3]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龙泉明,赵小琪.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J].文学评论,2003(6).
[5]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0.
[7]陈太胜.梁宗岱的中国象征主义诗学建构与文化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3).
[8]陈仲义.多元分流中的差异和生成——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困扰与对策[J].文艺理论研究,2000(2).
I207.25
A
1000-2359(2011)04-0181-04
柴华(1972-),女,黑龙江黑河人,黑河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新诗研究。
黑龙江省教育厅2010年人文社科项目(11552180)
201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