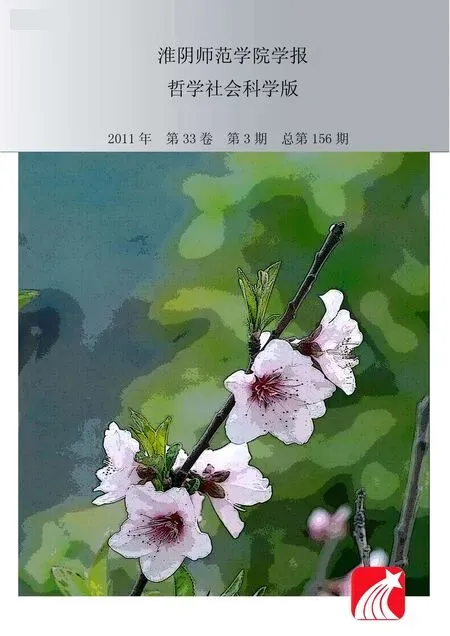在沉沦中寻找此在
2011-04-12黄斐诺
黄斐诺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在沉沦中寻找此在
黄斐诺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它是探讨存在意义问题的一个特殊存在者。理解此在,是指理解通过对“存在”的领会而展开的存在方式。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投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投入到与之关联的世界中去。沉沦,作为此在被抛入世界的状态,是理解此在的关键环节。通过畏,我们才能从在世之在的沉沦中寻找到被遮蔽的此在之身影,从而领会到此在的真谛。
此在;沉沦;常人;畏
《存在与时间》作为海德格尔研究存在意义的著作,一直沿着“日常生活体验本身的形式显示”的解释学方法展开论述。要达到事情本身的领域,只能通过向这个事情的纯投入。而现象学要想对经验进行纯描述,必须以超越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认识论,转而投入到更本源的生活经验中去[1]155。海德格尔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在日常生活中的此在。
有学者认为,“从思想的创新和表达的精巧上看,此书的前一半或达到时间性的前65节(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明显地更高一筹”[2]95。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前半部分海氏的论述是从常人的生活之中展开,层层递进,使此在的生存境况顺其自然地显现出来,而不是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这才让人觉得更为精彩。
一
那么,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此在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说:“此在”既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而是这和那之间的一个中性词,是“人们”[1]162。这个“人们”使此在的本真状态消逝于日常生活之中。当此在自以为是地在为这个世界烦心和操持时,实际上却总是被众人主宰而不得脱身。即便如此,此在也不能脱离这个世界而存在,此在总是在世之在。
此在与世界到底形成了何种勾连,让我们必须通过世界才能理解它呢?海氏以锤子为例,解释了这种关系。锤子能发挥出最大效用,并不在于你对其物性的了解有多清楚。相反,只有不再把它当作一个使用工具,不将它对象化,你才能运用得更得心应手。中国武侠小说中描述过的人剑合一所达到的武功最高境界,就与海氏的锤子理论有几分神似。
此在被抛入世界之中,与世界产生了某种类似锤子“上手”的“调情”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已经被调好弦的琴键与琴,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所以,我们对世界总已经有了某种前反思的、实际生存本身具有的、类似于用得称手状态所泄露出来的那样一种了解[1]85。这种了解首要地和经常地表现为一种不显眼的、平均状态的、日常的和生存空间的理解方式[1]162,这种方式正是此在与世界最本源关系的体现。
这种体现着本源的日常的平均状态,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沦”或“被抛”。沉沦是此在在世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沉沦这个名称并无任何贬义,它表达的是:此在总是在世界之中,隐藏在常人之中。此在作为常人之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最本质的,但却可以让那种最原初的存在样式展现出来。这个原初的样式便是此在的日常状态。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沉沦中被同化,迷失了自我,但这个历程,却是重新找回自我的唯一途径。
沉沦的三种方式,闲言、好奇和两可,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1)闲言。试想一下,其实我们所了解到的一切信息,我们作出理解、判断和决定的所有依据,都是由“闲言”而来。闲言作为一种语言被说出来后,它已经包含着对此在之领会的解释方式。我们用语言来传达情感,同时也相互倾听,但关注的并不是事情的本来样貌,而不过是言谈的内容本身,我们只会按照其他人都会用的方式来理解。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听者对话语里所谈及的存在者置若罔闻,他们按照平均的可理解性来领会话语本身。每个人都可以滔滔不绝,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却不需要为知道的事情负责任。打开电视,听着评论员和预测家们谈论着这个世界,用肯定的语气说着未发生之事。于是,我们自以为看到了表象背后的真相,有时甚至依照他们的言论而采取行动。对闲言自以为是的轻信,把一切新产生的怀疑和询问都搁置起来。公众意见统治着我们,决定着我们想看什么,听什么。而此在就在这些意见之中,公众意见成为了此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闲言没有根据,它是无根的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样式。这种不断的除根保证了此在的此,即“在世界之中”。“除根不构成此在的不存在,它倒构成了此在最日常最顽固的‘实在’”[3]198。(2)好奇。海德格尔把此在“在之中”的展开状态称为明敞。只有在明敞中,视见才成为可能。视见在日常生活中以“看”的方式呈现。“好奇”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看”的倾向。看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哲学历史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许多哲学家们都把看作为揭示存在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方式。看,从来不只是眼睛的官能。英语中“look”一词广义的运用就能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能说,“看看这东西多漂亮”,也可以说“看,这是多美味的一道菜”,还可以说“看,他的歌声多悠扬”[3]199。在世的操劳便全由这“看”引起。作为看的好奇,从不是为了领会任何事情,它仅止于看。好奇不断地从一件新鲜之事转移到另一件新鲜之事,从不在乎事情的真相,而只想将自己放纵于世界之中,通过不断的变化寻求着刺激和不安。而这个世界也为我们的好奇提供了各种条件。酒精、烟草、蹦极、潜水、旅游,层出不穷的事物让我们的精神领会到了兴奋、迷醉、紧张、释放等不同的感觉。我们总有一种不满足现状的情绪,对未知充满了向往。好奇心的驱使,让人们忘记了责任,忘记了自身。“好奇到处都是却一无所在。这种在世样式崭露出此在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此在在这种方式中不断地被连根拔起。”[3]201(3)两可。当人们可以通过“看”到达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并且可以随意地说上一些似乎是真的谈论时,人们就陷入了一种迷茫。他们无法判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我们不再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和目标,走一步看一步,没有未来,只能浑浑噩噩地度过此生。这种暧昧的、含混的、两可的状态,构成了此在在世的第三种存在结构。“这种两可总是把它所寻求的东西传递给好奇,并给闲言披上一种假象,仿佛在闲言中万事俱已决断好了。”[3]203人们之间互相听说,互相猜测,“在互相赞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对的戏”[3]203。
海氏的语言虽然晦涩,但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沉沦状态其实是现代物质社会的一个缩影。常人不断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精神世界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看似“操劳”,实则处于“无聊”的深渊之中。闲言所体现的公众意见,两可所形成的暧昧不清的局面,都让人们自以为知晓了一切。这一切为他们存在的牢靠性提供了保证,他们不再担忧。作为常人,这就是他们认为的真实生活,他们享受的幸福和安定,这就是具有强大引诱力的沉沦状态。
人们以为的安定生活从来不是静默的,而是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对本己一切皆知和对未知的好奇探寻,构成了包罗万象的此在之领会。而到底该领会的是什么?常人根本没有领会。作为常人的此在不断地将自己与他们比较,在这种比较中获得生之安宁。而在这个过程中,此在趋向了异化。这种异化表明,最本己的能在对此在藏而不露,但并不是说,此在脱离自身而存在。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异化,将此在带入了一种“解剖式”的存在方式[3]206。这种异化从来不是把此在交予那些不是此在的存在者,而是将其带入它本身非本真的存在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沉沦在世的安定和引诱还有异化的作用共同导致的结果便是,将此在禁锢于自身之中。引诱、安定、异化和自拘,这些现象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沉沦,海氏称之为“跌落”[3]207。此在跌入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跌入了非本真的存在,也跌入了它自身;而实情是,此在“上升”到了具体的生活之中[3]207。
沉沦作为此在“在之中”的存在方式,实际上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在世,即使这种在世是以非本真的方式。此在要想达到最本真的存在,必须经过沉沦着的日常生活才行。
二
清楚了沉沦的种种形态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该怎样从在世之在的沉沦中领会到此在的本质和真谛呢?此在的本真状态在沉沦中隐藏了起来,沉沦于常人的世界让此在从它本身面前逃开,逃到了“身后”。从存在论角度上说,唯有此在的本身被展现在它面前,此在才可能逃到它自己的“身后”去。由此可见,我们是有希望从这种沉沦的背离中发现一些此在自身展开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畏就起到了能帮我们领会其中奥秘的作用。
畏是什么?首先,它必与怕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但又绝对不等于怕。怕之所怕,是有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不一定真的到来,但它在世界之内,有一定的场所。而畏之所畏毫无缘由,它畏的是整个世界,畏的就是在世本身。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畏之所畏就是在世本身”这句话。(1)畏之所畏从来不知道所畏者是什么,可以说畏是无具体对象的。海德格尔称之为“无何有之乡”[3]215。但这种无并不意味着全然的虚无,它是在之中展开的一般状态。仿佛彼岸花一般,似有还无。它那么远,无法从任何一个临近的范围靠近;它又这么近,仿佛已经逼近眼前,让人感到压迫和窒息。(2)当这种畏偶尔停顿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觉得之前自己莫名的情绪十分可笑。他们会说“根本就没什么”。日常话语表达的往往是对上手之物的操劳。而畏之所畏不是在世的上手之物,所以在常人口中,它便什么都不是。上手状态的无植根于世界之中,世界的本质是在世界之中,也就是此在之存在。因此,这个什么都不是,其实就是世界本身。
由此可见,畏似乎拥有一种将浮华的日常生活消解掉的力量。每当畏的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周围的世界摇摇欲坠,一切幸福安定生活的基础都在畏中土崩瓦解,人们在畏中感觉到的是茫然若失。这就是一种“不在家”状态。常人把安稳的“在家”状态带到日常生活中去,而畏将此在从沉沦中拉回来,日常熟悉的行为方式便自然地脱离开。仿佛一个人在茫茫旷野中行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个体化就在那一瞬间被凸显出来。
从畏之现象我们便能发现,沉沦的逃避到底是在避什么。这里姑且作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较。就像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人的心灵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早已印刻上了各种理念,只是在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被遗忘了,学习只不过是唤醒遗忘的记忆。在我看来,畏也起到了同样的唤醒作用。常人并不是对此在之本真一无所知,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表面的舒适和愉悦而刻意让自己遗忘了那种本真状态。因为直面本真状态会带来整个生存世界的分崩离析,这种巨大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著名诗人海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认为是为情所困,而我认为不然。他离开人世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畏降临到他身上,让他发现了此在的本真状态,从而导致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自杀。
常人在操劳中停驻在安稳的熟悉状态,而毫无缘由升起的畏总是威胁着这种状态,以至于人们常有孤立无援之感。此在孤独地面对着畏,这种孤独,是一种真正的超越的孤独,此在突然发现它早已不在众人的群体之中,畏让他不得不面对那个一直存在却被沉沦所逃避的个体化。因此,通过“畏”,我们就能把握此在在世之在的完整方式,并找到理解此在本真形态的入口。
当然,找到入口还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理解此在的本真状态,获得理解存在本身的时间性,而不是陷入无穷无尽的“烦”中,人们还需要无畏地面对死亡,获得良知。
[1]张祥龙.海德格尔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B516.54
A
1007-8444(2011)03-0307-03
2011-03-05
黄斐诺(1988-),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象学及后现代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