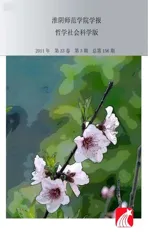他人的“共同此在”与移情的问题
2011-04-12李肖
李 肖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他人的“共同此在”与移情的问题
李 肖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海德格尔对此在为谁的追问与探讨,得出“此在的本质即共在”的命题。与他人共在意味着与他人的照面。他人作为与我一样的此在,在面对面相遇时此在如何去领会这样的此在,即如何去领会别人的心灵生活?于是,类比推论说和移情理论应运而生。不管是传统的现象学家,还是新一代的后起之秀都喜欢谈论对他人的感知问题。他们的批判及批判的批判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思想交战的硝烟图,需要我们慢慢领略。
此在;共在;移情;他者
“此在”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讨论的主角,是贯穿于全书的中心线索。问“此在这一存在者是谁”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海德格尔已经论述过,此在的两个基本规定性——此在就是我自己一向所是的那个存在者;此在的存在一向是我的存在——已经清楚表明:此在向来所是者就是我。但在《存在与时间》第四章中他却问道:“此在向来是我的此在;但如果情况竟是此在恰恰基于这一建构而首先与通常不是他自己呢?[1]134”因此,此在的本质还有待讨论。
他人的此在是如何来照面的呢?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意味着我们如何领会他人的心灵问题。而类比推论说和移情理论,尤其是后者,在现象学家那里是如何被提及的?让我们循着海德格尔的思路进入这些话题。
要弄清楚此在为谁这一问题,核心的着眼点在于分析此在首先与通常滞留于其中的那种存在方式——在世。此在的任何一种存在样式都是与此在在世一道被规定的。此在与世界同时出现,同时在此。当我们对周遭世界进行关注的时候,实际上他人就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工具而“共同照面”了。上手的工具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指引,首先它指向使用它的那类承用者,并且也指向它的制造者或供应者。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常常都是这类人造物品或器材,它们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们包含着对于某些人的指涉。一旦它们存在于周遭世界,上到手头,它们就包含着对他人的指涉。并且,即使他人并不在场,甚至根本不属于我们的同代人,早已不存在于世,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指向他人。这种对他人的不确定的指涉表明了此在总是与他人共在的,此在与他人在共在中“照面”。
当我们对与他人来照面的情况进行描述时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的。这不是先从“我”这个绝对的此在出发,然后过渡到他人吗?海德格尔指出,避免这种误解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谈论“他人”的。他人并不等于除我之外的剩余全体。在这里,他人倒是我们本身与之并无区别、且我也归之于其中的那些人。这种他人的共同存在并不意味着在一个世界内共同地现成存在,这种共同是一种此在式的共同,表达的是一种存在的等同。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因而世界向来总已经是我和他人共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之中”就是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
那么此在如何使他人来照面呢?它并非首先区分自己的主体和其他的主体,从而确定下借以区别自身与他人的东西而使之照面,而是从此在操劳停留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来照面的。“他人是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1]138他人的此在是从周围世界中来照面的,甚至自己的此在也是首先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因为此在总是从他所操劳着的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中发现自己本身的。总结来看,此在是从自己的世界中领会自身,他人的共同此在是从周围世界——更确切的说是从世内上手的东西——方面来照面的。
但此在这个存在者仍然给我们这种感觉:它首先是以一种与他人绝缘的情形下存在,“然后它还能共他人同在”[1]139。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去理解共同此在这个术语。共同此在意指这样一种存在:他人作为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就是向这种存在开放的。他人的共在在世界之内为一个此在从而也为诸共同的存在者开展出来,只因为此在在本质上就是共在。这个命题并不是想宣称,我不是独自存在而是还有无数个我这样的他人存在。它的深沉含义在于,即使他人并不是现成存在,也不被感知,共在也在本质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之共在。他人无时无刻不在共在之中,也只能在共在中不在。此在的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它的可能性恰恰证明了共在的必然性。他者的缺失正是作为他者的在场。另一方面,此在的独自也并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加而消除,共在也并不是由很多的主体积聚而形成的。共在是每一自己的此在的一种本质规定性。“只要他人的此在通过其世界而为一种共在开放,共同此在就标识着他人此在的特点。”[1]140此在的这种本质结构——共在使此在作为为他人照面的共同此在而存在。
与他人共在也属于此在的存在,并且属于此在为之存在的那一存在。因而海德格尔得出一个命题:“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1]143即使某个此在实际上并没有依附于他人,根本不需要他人,隐居于世外桃源,以为自己无关乎他人的存在,它仍然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着。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来说,共在就是“为他人之故”。他人无时无刻不在共在中展开着此在。
现在怎么来看领会他人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和怎样领会他人的心灵。海德格尔的看法是,因为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展开属于共在,而此在的存在即共在,所以在此在的存在之领会中已经包含有对他人的领会。但是这种领会并不是通过认识得出的知识,正好相反,是这样一种领会才使认识与认知成为可能,因为它“是一种源始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自我识认以源始地有所领会的共在为基础”[1]143。
作为共同存在者,此在与他人一道在切近的周围世界中寻视着,有所操劳。而自我识认首先就发生在对这些寻视和操劳的东西的领会上。此在的一般存在被规定为操心,而此在作为共在则被规定为操持。操持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是代庖控制的操持,一是率先解放的操持。前者是指此在仿佛从他人身上拿过操心且在操劳中自己去替代它;后者恰好是要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还给他,为他人的生存做出表率,有助于他人在自己的操心中看透操心,获得自由。日常共处通常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各种混合形态中变换。操持由顾视和顾惜所指引,它们各自都有一系列残缺和淡漠的样式。因为操持常常滞留于这些残缺或者淡漠的样式中,滞留在“陌如路人的无所谓”[1]144中,因而本质的自我识认首先需要自我结识,即此在与他人的此在的一种自我的结识。如果此在的自我被有意或无意地遮掩住了,那么共处就需要特殊的途径去接近他人,深入他人的背后。
首先出现的是类比推论说作为这种感知他人的途径。在我们感知到我们自己表达动作的情况下,“从我们作为自己的个体性自我活动之后果而经历到的同一类表达动作,去推断另一个人身上的自我活动”[2]365。这种理论已经被现象学家们给予了致命的批判。舍勒批评这种类比推论说设想身体和心灵的二分,没有看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寓身”的心灵统一体,他称之为“表达统一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能从心理和物理上区分开,在他的行为中就已经蕴含着他的情绪状态和情感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并不单单是主观体验的特性,它们在表达现象中被给予,也即是说,它们在身体姿态和行为中被表达,并因此被他人视见。”[3]192
为现象学家所普遍认可的是移情理论。胡塞尔用这个术语来标识对他人的感知,亦即陌生感知或者陌生体验。舍勒对移情的解释也是与他的“表达统一体”不可分的。他并不认为移情只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他人正在经历某一体验的问题”[4],而是把它解释为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本质能力:我们有体会其他心灵的能力。在面对面的相遇中,“表达现象,特别是面部表情和手势及言语表达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直接的、非推论的朝向他人体验生活的通道”[4]。他认为我们完全能够感知他人的心灵,我们所不能感知的只是他人身体感官上的感觉和情感体验,正是这种感觉和情感体验才使他人成为他人。但是这些并不能看成是他人的心灵状态。而且即使是这些身体上的感觉和情感体验也是能够被最终超越的。“只有当他超越他的身体状态,逐渐意识到他的身体只是一个对象,净化他的心灵经历,使之不再沾染那些一起产生的感官感觉,他人的经历之事实才会展现在他的眼前。”[2]386
胡塞尔却认为,我们是不可能像体验自身那样去体验他人的。虽然他也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使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够感知他人的体验的,但是这种感知只是一种“外感知”,而不是“内感知”。他人的体验始终不能以和我自身的体验一样原始的方式被给予我,他人的自身意识是我始终无法通达的。我们只能以一种第二或者第三人称的特殊方式去通达他人。而这种通达就是以移情作为桥梁的,“移情是可以为身体方面的共在特征提供依据的呈现”[4]。
海德格尔质疑的正是这种移情的优先性。他不同意我们必须通过移情来达至共在,以前的看法颠倒了移情与共在的地位。对于移情理论,他是这么来解释的:“从首先被给定为茕茕孑立的自己主体通到首先根本封闭不露的其他主体。”[1]144移情所要解决的这个所谓的经验他人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在靠近他人即向他人而存在时,从存在论上来看是与此在向自然之物或上手之物完全不同的。这个其他的存在者与我一样,都是具有此在的存在者,它也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在向他人存在和共他人而在中,这是一种此在对此在的存在关联。这种存在关联是独立而不可还原的。并且,在存在者状态上,这种关联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此在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要此在一出现,这种不可还原的关联也同时出现,即使另一个此在并未现成在此。我们在没有和他人有具体的面对面相遇时,此在就已经包含有对他人的此在的生存论关联。因为此在已经存在。正是这种关联使我们与对方的此在照面,并且我们始终与他们在此在的意义上是照面着的。虽然这种以共在为基础的相互认识常常“取决于自己的此在在何种程度上领会了自己本身;但这只是说,取决于自己的此在在何种程度上使本质性的与他人共在对自己成为透彻可见而无所伪饰”[1]145。因此,这种相互认识必然要求此在与他人同在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对他人的经验是发生在共在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正好相反:移情构成了共在。
在开始我们已经指出过物体的指涉问题。有一类实体即人工物品或器材是包含着对他人的指涉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着这些关系到他人的物品。因此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在本质上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它并不是最初单独存在着,然后在另一个人出现时才第一次获得了它的共在。只要此在出现,它就是社会性的,就是与他人共在的。即使具体的他者是缺失的,“那么这仅仅意味着此在作为共在的构成并没有达到它的实际充实”[3]208。因此我们只能谈论而无法具体感受到此缺失的他者,但是这恰恰是因为此在具有与他人共在的特征。海德格尔得出结论:“此在的共在——社会性隶属于其存在论结构这一事实——是任何对他人之具体体验以及与他人之相遇得以可能的形式条件”;“此在并不首先存在,以便随后迈出超越自身达到他者或世间对象的一步;相反,存在总已经意味着跨出,或者更好的说来,它已经跨出了”[3]209。
因此,海德格尔指出,移情绝不能作为源始的生存论现象;但这并不是说移情理论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移情特有的诠释学将不得不显示:此在本身的各种不同存在的可能性如何把共处及其自我识认引入歧途,并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致真正的领会受到压制而此在却逃避到代用品中去了”[1]145。这一点和扎哈维的理解有相似之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通过共同世界中的背景及交流很好地理解彼此,唯有当这种理解由于某种原因中断时,某种移情的过程才变得相关,它需要我们以特殊的、主体性的方式去把握他人的体验。在我们正常地与人相处时,与他人的沟通并不是问题。但是当他人有意或无意地遮掩自己,甚至我自己也会有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时候,移情理论才应该出现用以去深入理解他人或使他人来理解“我”。此外,移情还不得不显示:“为了能够正确地领会彼此,须把何种积极地生存论条件设为前提。”[1]145海德格尔的回答当然会是:共在正是这种生存论前提。
一种批判一旦出现,对于这种批判的批判也会接踵而至。海德格尔对移情的优先性的质疑、对共在的生存论之本源意义的强调又遭到了萨特的批判。在这里我只是简要呈述大致内容。虽然萨特也同意移情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人的问题,同时和海德格尔一样,他也认为此在作为共在具有社会性;但是他认为,在探讨他人的问题上,这两个视点都是有问题的。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关注如何在保持他者之他者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上去体验他者的可能性,而是应该把核心放在与彻底的他者的遭遇上。他强调的是他者的他异性和超越性。像海德格尔那样,以匿名的共在来抹消与他者的差异性,从而使与他者的相遇没有隔阂的想法,不仅有造成一元论的危险,而且根本不能解决与他人的相遇问题,毋宁说是完全消解了这一问题。
至此,这个问题当然还远远未完结,也许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解之谜。海德格尔对共在之重要性的强调,现象学家对移情的探讨及萨特对所有视点的不认可,这些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与他人的相遇。这一“相遇”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期待着。
[1][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德]马克斯·舍勒.论他者的我[M]//刘小枫.舍勒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丹]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M].蔡文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丹]扎哈维.同感、具身和人际理解:从里普斯到舒茨[EB/OL].(2010-01-01)[2010-03-07].http://114.212.7.87/kns50/detail.aspx?QueryID=6&CurRec=1.
B516.54
A
1007-8444(2011)03-0303-04
2011-03-05
李肖(1988-),女,湖北天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