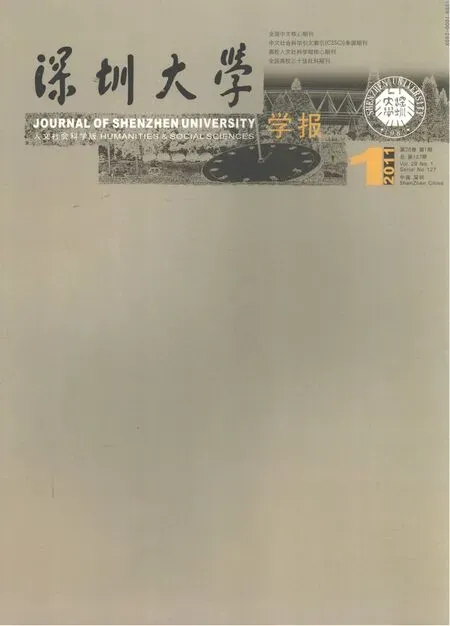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
2011-04-12谭中
[印]谭中
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
[印]谭中
阿莫尔多·沈把泰戈尔1924年访华称为“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当时,泰戈尔把希望着重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重振古代中印两大文明的兄弟情谊而建立全球国际关系的新风尚。当今中印两国逞强心迫切,如果两国继续醉心于强力的追求而摒弃几千年文明传统中的爱心,它们也会蹈昔日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今日美国的覆辙。这就是我们庆祝泰戈尔150周年寿诞最最应该牢记的。
泰戈尔;中印关系;金桥
在中国庆祝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有三大意义:(一)充分肯定泰戈尔这位千载难逢的伟大人物的历史意义,(二)通过泰戈尔的言论与行动来深刻认识中印两大文明的世界地位及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三)认识到泰戈尔式的人物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良好榜样,号召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士积极效法,使不久的未来中国也有不止一个泰戈尔来造福社会与人类。
泰戈尔既是大文豪(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圣人、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还是画家、歌唱家、2232首歌曲以及印度与孟加拉国两国国歌的作者(全球绝无仅有),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非凡的,所有各项成就的总和就变得千古难逢了。
今天我们在中国庆祝泰戈尔寿诞最重要的目的是循着他的教导走出地缘政治范式的怪圈,进入地缘文明范式的思维探讨。“超越”是泰戈尔的符号。他超越种姓,超越语言,超越宗教,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现代,超越物质,超越精神,超越国界,超越东西方文明鸿沟。泰戈尔思想的创造性在于辐散性与收合性的有机结合。他不拘泥于一种思维范式,而是使思想渗透到不同宗教、不同传统、不同文明领域之中,又在吸取了各种不同养料以后把思维聚焦到一点上。
这一点变成概括世界文化的结晶。
泰戈尔以自己的努力与成就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西方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东方人。西方殖民主义者花了几百年功夫把东方的声望打入大牢,泰戈尔一夜之间就把它解放出来了。他的著作与言论不但使东方与西方平起平坐,他还能在西方国家的上层社会指手画脚地用东方文明教训西方,这对与泰戈尔同龄的中国知识精英是无法想象的。泰戈尔这种“长东方志气、灭西方威风”的义侠行为无形中提高了中印两大文明的世界地位。
泰戈尔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摆在很高的地位。1916年,泰戈尔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它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1]我们知道,中印两大文明在两层意义上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它们经过几千年经久不衰(它们的“明灯”没有“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这是世界所有其他古文明没有的现象;(二)两千年以来一直至今,生活在中印两大文明中的总人数保持在人类40%左右(过去经常超过这一比率,现在稍稍下降)。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有一大差异。中国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大一统的政治状况,就是说,它是一个“文明国家”。印度一直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建立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此前则是一个“印度文明”伞下许许多多国家的总和,只能算作“文明世界”。无论如何,以上这两大非常不平凡的现象是相互联系的。
泰戈尔对这两大非凡现象有过精辟的分析,指出文明的力量在过去几千年中把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中国和印度。他指出:“广大辽阔的中国不是受到刀剑统治的约束,而是被宗教的规则变得有纪律性。”他解释说,这“宗教”指的是社会自觉产生的“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左邻右舍”等的人际伦理关系①。我对这一分析深有启发。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凝聚力来自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地球大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由于发展灌溉农业而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泰戈尔的分析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这种共同利益上发展起来的自觉纪律性与和谐人际关系。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们聚拢在一起就产生爱心,就在“己”与“人”之间用爱心的纽带联结起来,“推己及人”,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印度文明同样提倡爱心,叫做“Brahmatmaikyam/梵我合一”(泰戈尔的著作可以说是“梵我合一”的结晶),是爱心使得印度文明像中国文明一样经久不衰。
泰戈尔根据当代的国际形势发展指出人生具有两大要素:“power/强力”和“love/爱心”。西方文明掌握了前者,东方文明掌握了后者。前者的代表是“科学”,是“机器”,是“民族主义”。泰戈尔把西方民族主义比作机器,没有生机、没有灵魂,本身不是目的。“机器的唯一作用在于一种达到目的的运作,在操作过程中认为道德良心愚蠢而不合时宜。”[1](P172)中国和印度文明因为具有爱心得以持续几千年,两大文明的影响使得东方传统色彩与和谐气氛浓厚。西方却由于提倡强力而充满冲突、战争、毁灭,西方强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地缘政治范式提倡的“国富民强”的发展道路与地缘文明范式提倡的世界大同道路是分道扬镳的,一条引导人类走向毁灭,另一条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泰戈尔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在这两条道路上有所选择。他1937年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式上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是合作与爱心、互助互信创造文明的力量和真实优点。新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应该继续发展,使人类吸收科学的成就,管制他们的武器和机器,不然的话,武器和机器就会统治与奴役人类。我知道,很多人会指出中国和印度的衰弱,受到世界残酷侵略的强国的蹂躏,为了避免毁灭必须强调强力与发展。…我们必须懂得对付强国的傲慢而保卫我们人类,却应该小心别仿效它们使我们自己也变得残酷,把我们人类值得保卫的价值葬送。”[2]
应该看到,泰戈尔说以上这番话时,中印两国都衰弱,但他就有点担心我们效法西方追求强力而毁灭人类。现在中印两国都强盛了,就更应该聆听他的教导,与地缘政治范式分道扬镳,走上地缘文明范式发展世界大同的道路。
阿莫尔多·沈的最新文章②把泰戈尔1924年访华称为“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他认为访问结果是不幸的(甚至称之为“悲剧”),主要的原因既不能怪共产党人,也不能怪泰戈尔的东道主。他分析“泰戈尔的思想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情境中回荡”。他也认为泰戈尔在世时被西方知识界的赞扬所误导,使他觉得自己肩负了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这两大因素使泰戈尔于1924年带着这一使命访华,恰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扬弃东方文明而效法西方。“泰戈尔的伟大中国之旅产生的效应是:一个激动的泰戈尔此时来到一个激动的国家,两种激动的情绪相互碰撞,然而并未能和谐共鸣。”这是阿莫尔多·沈的观点。
我认为阿莫尔多·沈的这一解释不但富有新意,而且值得认真思考。我对此的直觉反应有三点。第一,被《时代》杂志评选为2010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的阿莫尔多·沈是个像当年泰戈尔那样的全球知名人士,说话是有分量的。他的祖父克蒂摩亨·沈(Kshitimohan Sen)是随泰戈尔访华的代表团成员,阿莫尔多·沈从小就听到祖父讲述当年访华情景。因此,“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这个名称是具有权威性的,应该在中国舆论界、特别是学术界统一口径,这样就可以减少来自各方的歪曲、误导与造谣中伤。
第二,阿莫尔多·沈以“一个激动的泰戈尔来到一个激动的中国”来形容1924年泰戈尔访华,简直是惟妙惟肖。然而,泰戈尔当时看到的是中国知识界呈现出鸭子浮水(表面上优哉游哉,暗地里斗争激烈)的假象,他不懂中文,所以没有透过假象深入了解中国内心的矛盾,因此也就不能使自己的讲演内容针对中国知识界内心的激动。泰戈尔自己在上海的告别讲话中对这一点有了一定程度的感觉。“我不够认真”,他说:“我没有机会深切地、竭尽全力诚恳地对你们最严重的问题表态。”[3]阿莫尔多·沈说那次“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不愉快的结束既不能怪陈独秀等极左人士,又不能怪梁启超、徐志摩等泰戈尔访华的东道主,这一论点完全正确,但也不是责怪泰戈尔本人。
第三,我的好友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对“泰戈尔与中国”的历史文献、档案进行了彻底调查研究,有新的发现。在她向我们大会的报告中,邬玛发现了泰戈尔访华临行前的激动。他在1924年3月写到中国“如此热情期待”他的访问。“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够格满足他们的期待,但我清楚地看到这一任务已经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必须把启示带往国外。我有时想,这究竟是谁的启示呢?我想不出它的名义来。正像春风中洋溢的欢乐突然变成树藤,那空中游移的启示突然到了我的声音之中。…我现在懂得我自己是许多信使的喉舌。”③
现在我们平心静气来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的反应(包括欢迎与批评的两极在内)都是很肤浅的,对泰戈尔的伟大思想缺乏深刻认识。简而言之,正像阿莫尔多·沈指出的,泰戈尔急切要以东方文明精神来改造世界秩序,当时的印度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日本东施效颦、不可救药,泰戈尔把希望着重寄托在中国,希望重振古代中印两大文明的兄弟情谊而建立全球国际关系的新风尚。当时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表示的冷淡、甚至不敬,是使他伤心的。但他并没有放弃,他于1927年热情欢迎谭云山去圣地尼克坦,1933年热情欢迎“中印学会”成立,1937年热情建立“中国学院”,又在1939年欢迎徐悲鸿时说,他期待着印中两国“一同步入温暖的亲谊时代,期待着(文明)历史力量在东方施展,把我们从四面袭来的黑暗中解救出来。”[2](P850)虽然中国上层社会通过戴季陶、蒋介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到国际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和他在国际大学讲演中对泰戈尔的称赞已经把1924年的不愉快(我认为“悲剧”是莫须有的)抹掉了,但还没有正面、积极地响应泰戈尔联合中印两大文明改造世界秩序的伟大号召。如果最终中国并不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那“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的美言就变成空洞的装饰了。
最后,我们有三点理由证明泰戈尔式的人物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良好榜样。第一,泰戈尔从理论与行动上大力提倡“天人合一”,他既是发扬印度的优良传统,也是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把这种泰戈尔的生活方式发扬光大。第二,泰戈尔丰富生活的多姿多彩,用扩张爱心来增进社会进步与和谐。这一点特别值得中国效法。第三,泰戈尔指出人类发展的两个方向与两条道路,这一点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中间是模糊的,应该以泰戈尔指引的方向来选择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
先谈泰戈尔的“天人合一”,他是自己从小体验到大自然与童真的天生关系,对社会人情把这一关系逐渐切断而发出抗议,因而发展出自己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他有两大生活习惯:早起与敞开窗户。他总是在日出前起床,观察黎明的景象,从中悟出许多重大理论。在他1921年的讲演《真理的召唤》The Call for Truth中,泰戈尔富有诗意地说:
“在世界觉醒的早晨,如果我们民族的奋斗不和宇宙的理想相呼应,那就反映了我们精神的贫乏…当小鸟在黎明醒觉,它并不全神贯注寻找食物,它的翅膀不疲倦地在天空翱翔,它的喉咙歌唱着新的曙光的欢畅。全世界人类今天在向我们发出号召。”
这种生动而精辟的理论,只有黎明前起床的人才能悟出。圣地尼克坦气候炎热,但泰戈尔连正午也把窗户敞开,让阳光照耀到屋子里来。雨季的时候,风雨雷电交加,泰戈尔也把窗户敞开,让风雨雷电和他的身体与思想交流,他的诗中充满了对雷雨的绘描,这也是只有像他那样有“天人合一”生活习惯的人才能创作出来的。由于泰戈尔切身体验“天人合一”,他对中国唐宋诗歌中的“天人合一”诗境也特别欣赏。
关于泰戈尔用扩张爱心来增进社会进步与和谐,我想引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邵葆丽寄给我的文章《泰戈尔与孟加拉社会现代性:妇女进入文化主流》(不久将会发表)来阐述。泰戈尔坚决主张男女平等。起初他著文批评社会风俗习惯,后来他改变方针,用他的社会影响开展社会文娱活动来增加妇女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创造了“Rabindra sangeet/泰戈尔音乐”(包括歌舞),其中女主角与男主角地位平等。由于“泰戈尔音乐”变成了孟加拉与印度上层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参加到“泰戈尔音乐”活动中的妇女自然而然变成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上层社会成员。现在,孟加拉群体中的女性都以擅长朗诵、唱歌、舞蹈、演戏为荣,甚至当作一种资历,就这样,不必通过批评斗争就能使妇女进入文化主流。这是十分值得中国学习的。泰戈尔不但多才多艺,文艺创作丰富,而且他的文艺创作大多成为广大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他作品中洋溢的爱心无形地灌输到社会风气与道德之中,这也是印度社会比较和谐的原因之一。中国最需要也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文化巨匠。
现在最后谈谈泰戈尔指出的人类发展的两个方向与两条道路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泰戈尔所说的人生两大要素:强力与爱心。强力是“我”字当头,唯我独尊,没有群众观点的;爱心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提倡世界大同的。在中国叫“世界大同”,在印度叫“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这在把吃奶的力都用在强力追求上的西方文明中是不强调的。泰戈尔的大量言论以及他在中国讲话的焦点就是要扬弃西方的道路而提倡中印文明的理想。我想引已故国学大师兼印度学大师季羡林的一番话:“从人类的全过程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④凡是了解泰戈尔思想的人都知道,季羡林这番话正是发扬泰戈尔提倡的精神,在人类大发展方向上毫不含糊。
不幸许多评论家对季羡林提出的这一观点缺乏深刻了解。最近有一位哲学家写道:“我不大同意一个想法,认为中国学问可以解决世界一切问题。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觉得都是错误的。当今的世界是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过去‘西方中心论’已经错误了,现在‘东方中心论’不是重复过去的错误吗?”[4]他继续说:“在弘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要继续学习西方,西方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学,而且西方文化也正在发生变化。后现代性的出现,在纠正现代性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建构后现代某些思想,可能和前现代相通,比如我们前现代的‘天人合一’与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是一共同生命体’可以有相通之处。”[4]我认为季羡林的确反对“西方中心论”,但却从不提倡“东方中心论”。他是同意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点的。
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为时太晚,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引经据典作详细的诠释与深入的探讨了。如果我们深刻了解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了解季羡林是企图发扬泰戈尔的理论。泰戈尔吸纳西方文明,提倡接受西方文明的优点,但批评西方发展的道路,先是国富民强,然后扩张侵略,最后导致人类毁灭,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惨痛教训。欧洲国家遭受世界大战的强烈破坏泰戈尔是目睹的,他也预言日本必然会在战争的道路上毁灭。泰戈尔当然没有完全看到美国变成超级大国的进程,但美国今天的窘境似乎也在泰戈尔的逻辑分析之中。美国文化在强力与爱心之间的选择与昔日的英、法、德、意、日帝国主义又有所区别,但它对强力的依依不舍正是它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最重要中的最重要,对印度当然也如此。当今中印两国逞强心迫切,中国比印度更甚。如果两国继续醉心于强力的追求而摒弃几千年文明传统中的爱心,它们也会蹈昔日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今天美国的覆辙。这就是我们庆祝泰戈尔150周年寿诞最最应该牢记的。希望中印两大文明通过这一庆祝结成友好伙伴去实现泰戈尔生前的用爱心改造国际秩序的宏伟愿景。
注:
①引自摩炯达在《泰戈尔与中国》书中的文章,泰戈尔的话出自孟加拉文、英文《泰戈尔文集》,11册,484页。
②指阿莫尔多·沈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的文章《泰戈尔与中国》。
③见邬玛·达斯古普多向本会提交的论文报告。
④http://baike.baidu.com/view/673141.htm
[1]Uma Das Gupta.The Oxford India Tagore:Selected Writings on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46.
[2]Sisir Kumar Das.English Writings of Robindranath Tagore [M].New Delhi:Sahitya Akademi,Volume Three:A Mscellany,1996.713-714.
[3]Sisir Kumar Das.Robindranath Tagore:Talks in China[M]. Calcutta:Rabindra Bhavana,Visva-Bharati,1999.76.
[4]汤一介.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4-21.
【责任编辑:来小乔】
Tagore Is a Golden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AN Zhong(India)
(Center for India Research,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China)
Amartya·Sen called Tagore’s travel to China in 1942“Tagore’s great visit to China”.At that time,Tagore placed his hope on China,hoping to revitalize the friend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the twocivilizations in the ancient time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eth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globe.Currently,the two countries are vying urgently with each other.If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e to be fond of going after power and getting rid of the love in the traditions of the thousands of years,they will not steer clear of the old disastrous course of the Western imperialist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USA.This is just what we should remember firmly when we are celebrating the150-th birthday of Tagore.
Tagore;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golden bridge
G 112
A
1000-260X(2011)01-0010-04
2010-12-20
谭中(1929—),男,著名印籍华人印度学家,曾任德里大学中日系主任、尼赫鲁大学亚非语文系和东亚语文系主任,著述甚多。2010年获颁印度国家学术奖“莲花奖”和中国“中印友好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