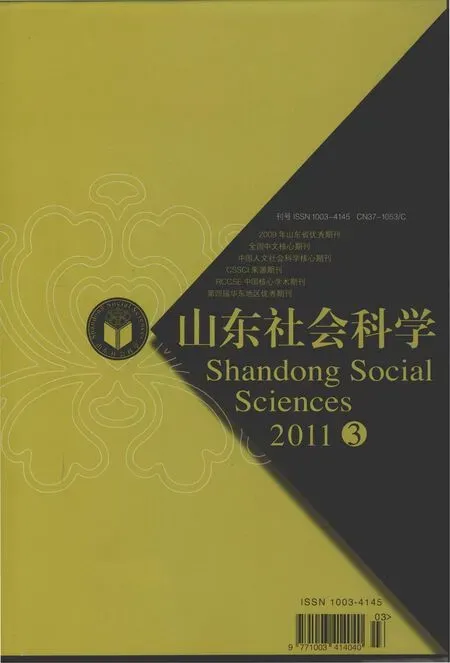杨兆龙卢埃林司法思想之比较及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①
2011-04-12张娟
张 娟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杨兆龙卢埃林司法思想之比较及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①
张 娟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杨兆龙(1904-1979),字一飞,江苏省金坛县人,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后经司徒雷登推荐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受聘为上海持志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法学院教授,1930年兼任上海市地方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镇江地方法院执行律师。1935年取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进行博士后深造。1936年回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法制专员、最高国际委员会专员、教育部法律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曾受中共委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营救爱国学生。解放后曾在东吴法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发表多篇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章。杨兆龙学贯中西,力图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建国后积极建言献策,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奔走呼吁。卢埃林(1893-1962),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191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1923年受聘为耶鲁大学副教授,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1939年起主持起草《美国统一商法典》。1930年卢埃林以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代言人身份与庞德展开“论战”,明确阐述现实主义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温和派的现实主义者,弗兰克(Jerome Frank)称其为“规则怀疑论”。卢埃林构建了以“宏大风格”为中心的法律思想体系,成为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法学家。他们二人生活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都受到了当时国际顶尖法学家的影响,特别是都受到庞德的影响,都是庞德的“学生”,且具有相似的职业生涯。这些因素使杨兆龙和卢埃林的法律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即不但具有思想的深度,而且都关注实践、服务实践。当然,由于社会背景等因素,他们的思想又具有很大不同,在实践上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别。
一、杨兆龙与卢埃林的司法思想
(一)为什么要关注司法
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各种社会危机。杨兆龙认为:“当日中国正在内忧外患之中,需要组织和秩序的程度,恐怕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厉害些。别的国家既然要靠‘法治’以促成组织和秩序,那么中国更少不了它。”①杨兆龙希望利用法律组织社会的新秩序。司法机构虽然在形式上已健全,但实质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亟待改革。当时的法院,“讼案激增;不特第一审法院工作紧张而难以应付,即第二及第三审法院亦大都如是。国家之负担既因是加增(如增设法院添置员额等),人民之讼累随之转重(如延长诉讼耗时费财等)。”②杨兆龙:《论三审制之存废或改革》,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当时对于检察制度的存废也存在很大争议,杨兆龙认为:“我们虽不能否认现行的检察制度有不少缺点,但是这些都是人选配置不宜和制度运作失当所造成的,并非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③杨兆龙:《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监狱(附看守所、拘留所)作为广义的司法机关,主要承担刑事惩罚的执行,“现代监狱问题,可归纳为两类,即关于监狱之疏通者与关于监狱之改良者是”,①杨兆龙:《司法与监狱之改良及管理》,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这些问题都亟待改革以实现刑罚个别化。杨兆龙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领事裁判权往往会发生三个最大的弊害那就是:(1)权利国之人民实际上几可不受中国政府机关之管辖及一切法律之制裁;(2)权利国滥用领事裁判权,使其他外国人或某种中国人不受中国法院及其他政府机关之管辖与中国法律之制裁;(3)中国国家或人民之利益为权利国人民或其他外国人或某种中国人所侵害时,无适当有效之救济办法。”②杨兆龙:《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之觉悟》,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卢埃林认为,法律形式主义所信奉的由规则(包括由判例归纳出的规则和成文法规则)得出确定的判决是不存在的,“我宣称对于引起困难的案件,这种法律确定性从来不存在,也将不会存在;为这种确定性而努力是浪费时间”。③Karl Llewellyn,The Case Law System in America,Micheal Ansaldi译.Paul Gewirtz编辑.Columbia Law Review,1988,88,p1005.需要法官、律师以及普通百姓看清司法的真面目,才能更好地利用法律工具。经过几十年的批判,人们普遍认识到法律形式主义的机械性、欺骗性,也产生了对法律确定性的怀疑,“眼下的危机在于,较老一代的律师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于法院运作确定性的全部信心。这种情形是糟糕的。眼下的危机还在于中年和青年一代的律师可能不仅已经失去了对于法院运作确定性的全部信心,而且也失去了对于法律本身确定性的全部信心。这种情况是糟糕的。眼下的危机实际上在于法院自身可能业已丧失连贯性的倾向和责任感。而这种情形将是最糟糕的。”④[美]卡尔·N·卢埃林:《普通法传统》,陈绪刚、史大晓、仝宗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推翻法律形式主义的确定性给法律界带来了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在此背景下卢埃林试图重建新的确定性,⑤为 了与法律形式主义的“确定性”(certainty)相区别,卢埃林选择了reckonability,有人翻译为“可估量性”(参见《普通法传统》,陈绪刚、史大晓、宗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笔者认为也可以翻译为“可靠性”、“可依赖性”。“确定性”更多的强调客观性,与法律形式主义的由规则得出判决的司法三段论相关。而“可靠性”具有主观色彩,与“宏大风格”的法官判决相关,综合考量司法过程中的(卢埃林主要关注上诉法院)主客观因素。重建律师界对司法的信任和法官们对司法的责任感。
(二)应关注司法的哪些内容
杨兆龙和卢埃林对司法的关注点不同。杨兆龙主要从宏观的制度架构上建议改革当时的中国司法机构,承担更多政治家改革的责任;而卢埃林主要从微观的细节讨论上诉法院做出判决的过程,以及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和能够起什么作用,他扮演了社会思想家的角色。
杨兆龙在论及各司法机关的改革时,强调当时制度的缺点包括财政经费不足、人员缺乏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差)、特别腐败等。对于当时的司法机关的组织及分配,杨兆龙认为县级司法机关组织的不健全表现在,“担任裁判事务者不精通或根本不谙法律”,“司法辅佐人才特别腐败”,⑥杨兆龙:《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他特别列出“司法经费”作为改革司法的重点,“吾国今日之司法经费有三大缺点:预算数额过少、预算数额无保障、与支付保管机关不集中是也”。⑦杨兆龙:《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杨兆龙特别关注监狱的改革问题,“吾国监狱之最大缺点为经费之支绌,经费问题不解决,则监狱之改良必难以实现”。⑧杨兆龙:《司法与监狱之改良及管理》,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页。杨兆龙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要增加财政拨款几乎是不可能的,比较各国监狱改革的实践,他认为应当开源节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曰疏通监狱,以多数人之经费备少数人之用;二曰改良及发展监狱作业,以出品之收入拨充经费”。⑨杨兆龙:《司法与监狱之改良及管理》,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杨兆龙的这些改革司法机关的建议,虽然其有理有据、论证详实(包括国内外各种统计数字、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但作为法学家缺乏法律思想体系应有的整体性建构。
卢埃林开始即进入法学的核心问题——“法律是什么”,他认为给出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是困难的,因为这在囊括进一些东西的同时等于武断地排除了其他的东西,“我理解的概念是建立一个目的。它是思想的工具。它能够使你在处理、使用材料的时候更容易”。⑩Karl Llewellyn,A Realistic Jurisprudence—The Next Step,Columbia Law Review,1930,4,p431.卢埃林采用了功能主义的法律界定。卢埃林始终关注上诉法院,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你们课本上所谓的判例法几乎无一例外的来源于上诉法院”,⑪⑪Karl 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Some Lectures on Law and Its Study,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1930,p17.⑫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5.p246.而在讨论上诉法院判决“可预测性”的《普通法传统》中主要选用了判例汇编,“一是判例汇编的明显优势是它们的可获得性”,“二是判例汇编有巨大的未开发的潜质”。⑫⑪Karl 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Some Lectures on Law and Its Study,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1930,p17.⑫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5.p246.卢埃林以“宏大风格”来恢复法律的“可靠性”,“宏大风格”的法官在做出判决时会考量不同案件的“情境感”,“在所有案件中,‘情境感’的表现涉及两步:原则和政策的形成,以及把案件事实归类为一般的事实情境类型”。①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5.p222 -223.“宏大风格”的法官不同于机械形式主义的法官,其司法资源不仅包括规则,还包括原则、政策、正义观念、传统等工具,而这种行为具有一贯性,至少对于同一个法官的司法判决是可预测的。卢埃林提炼出了十四项上诉法院的稳定因素②这 十四项稳定因素是:1)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员;2)司法原则;3)公认的原则性技巧;4)法官的职责;5)单一正确的答案;6)法院的单一意见;7)来自下级法院的事实冻结记录;8)预先限制、突出和拟定措辞的审理;9)律师的对抗性辩论;10)集体判决;11)司法保障与诚实;12)公知的法庭;13)概论各时期风格及展望;14)专业司法职务。参见[美]卡尔·N·卢埃林:《普通法传统》,陈绪刚、史大晓、仝宗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7页。,重建了以“宏大风格”为中心的上诉法院判决的可预测性,即法律“可靠性”。卢埃林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上诉法院为研究对象,击垮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法律确定性,重建了新的判决“可靠性”,恢复了律师、法官对法律的信任。作为法学家,卢埃林的法律思想虽然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其核心概念“宏大风格”、“情境感”),但从整体上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
虽然杨兆龙的法律思想更宏观、关注制度层面,卢埃林的法律思想更具体、系统、关注操作层面,但是他们都以本国当时的国情为研究背景,特别注意地方性研究,而不是用先进的统一思想套用本国的情况。
杨兆龙在分析了替代自由刑之方法和比较了西方各国的变通适用方法之后(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不能有效预防和改造犯罪的问题),认为“上述之减少监犯之种种方法,系就各国一般之情形理论。其能否适用于吾国,尚不无问题。故此后须研究者,即在吾国现状之下此类方法于何种程度内有采取之价值”。③杨兆龙:《司法与监狱之改良及管理》,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在讨论司法改革时,杨兆龙认为小标的案件由普通法院办理,不适应中国当时地域广大、交通不便的情况,手续繁多而且浪费资财,他建议广设小标的法院,根据区域、人口设立公断所,有地方士绅担任公断。这种设置在西方国家不存在,但“吾国本系农村社会,士绅公断,素所习见,揆诸国情,并无不和”。④杨兆龙:《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杨兆龙了解中国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从本国国情出发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实效的法院设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虽然并未为统治者采纳。可见,杨兆龙在关注每一个问题时,其出发点都是当时的国情、民情、财情,从来没有把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实践作为先进的标准套在中国的制度上面。
卢埃林在构建法学思想时主要是从美国的现实状况出发,甚至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作者对普通法的热爱,批判的热爱和建构的热爱。卢埃林对德国的感情很特别,在一战时曾以德军身份参与对法国的战争,并获得二等十字奖章,德国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以及制度实践都对卢埃林有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卢埃林主持起草的《美国统一商法典》受到德国商法典和德国改革刑事、商事法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影响。⑤参 见 Michael Ansaldi,The German Llewellyn,58 Brook.L.Rev.(1992-1993)pp705-777;James Whitman,Commercial Law and the American Volk:A Note on Llewellyn's German Sources fo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97 Yale L.J.(1987 -1988),p156 -175.卢埃林在早期作品中比较成文法和判例法,认为成文法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判例法在本质上是司法的,“但是与法院相比,立法机关是一匹脱缰的马”,“成文法的基础是概括性”。⑥Karl 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Some Lectures on Law and Its Study,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1930,p77.成文法的法官没有经验的训练,而判例法的法官则需要对判例十分清楚,因此判例法的法官大多来自律师,判例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美国的法科学生需要不断地钻研判例,而且要提早确定自己的执业地区,以便有侧重地研读那个州的判例。卢埃林的思想核心“宏大风格”所涉及的判例大都是美国上诉法院的判例汇编,是美国原有传统的恢复。⑦William Twining认为卢埃林的宏大风格只在四种背景下被发现占主导地位: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夏安人之间的法、美国十九世纪早期和从1940 年起的司法。参见 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1985,pp251.他们的作品不但表现出对法律思想的追求,更凸显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是批判的、理性的但同时更是深沉的,他们积极地承担起了学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杨兆龙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德国进行博士后研究,而且与庞德等世界顶级法学家私交密切,掌握了英、德、法、意、西、俄、波兰、捷克等八国语言,阅读了大量的外文著作,考察了各国的司法状况,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严密思想体系呢?或者说在个人条件上杨兆龙丝毫不逊色于卢埃林(卢埃林除英语以外,熟练地掌握了德语),甚至还在硬件上稍有超越,特别是杨兆龙与庞德等法学家的密切接触也超过卢埃林,但是卢埃林却形成了体系化的、至今对美国法学仍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思想。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射到微观之外的社会背景上,动荡、危机、落后的国家背景,亟待革新的社会,使杨兆龙成为了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卢埃林所在的美国也面临“大萧条”等问题,但国内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中的危机更容易促生出变革的思想,卢埃林的法律思想即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磨练和蜕变,其思想不仅现在仍然影响着美国法律界,也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法学者,显示了其思想的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交流的背景下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是杨兆龙和卢埃林同时分享了当时最前沿的法学思想,特别是杨兆龙除了与顶尖法学家亲密交往以外,多次以官方或者私人身份参观考察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法律制度设置,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所以他总是能以全球的视野透析问题本质,又落脚在细处,实为难能可贵。
(三)杨兆龙卢埃林法律研究方法的比较
杨兆龙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法的方法和法社会学的方法,而这也是卢埃林的方法。杨兆龙在比较法律思想和比较法律实践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例如,他详实地比较了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区别,①杨兆龙:《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216页。在司法机关的改革中杨兆龙都一一比较西方各国的思想和实践,以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所用。也许是受庞德的影响,杨兆龙偏爱社会学方法,特别重视统计数字的价值,在论及检察制度和监狱改革时,杨兆龙以大量详实的数据论证了检察制度存在之必要性、各国积极努力地减少监犯和改善监狱管理,同时也援引了大量的官方数字来详述当时监狱管理的状况。社会学方法(包括人类学方法)是卢埃林最重视的研究方法,虽然“公允的说,卢埃林在一般理论方面没有突破其知识前辈”,“他的主要目标是使法理学更务实,为‘理解力强的民众’一个相当清楚易懂的思想体系”。②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5.p202.杨兆龙和卢埃林在运用社会学方法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而没有进行实际的社会调查。很多学者诟病卢埃林倡导社会学的方法但是本身没有进行过社会调查,而选择“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官方数据。卢埃林认为要像社会学家一样进行经验调查,首先要把自己变成社会学家,而这常常浪费大量时间,也未必能够获得比社会学家们更好的资料数据。只要真正地理解他人的二手资料——包括理解他的出发点、调查背景、调查方法、理论假设等等,正确地运用这些二手资料,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能够事半功倍。③参见Felix Frankfurter,Karl N.Llewellyn,Edson R.Sunderland,The Condition for and the Aims and Method of Legal Research,6 Am.L.Sch.Rev.670-678 1926-1930.而杨兆龙在国内除了在大学教书,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政府官员(其先后曾任租界临时法院推事、司法行政部秘书处科长、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专员、司法行政部法制专员、最高国际委员会专门委员、教育部法律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战犯罪证调查室”主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研。
二、杨兆龙卢埃林司法思想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杨兆龙的司法思想都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关于设立小标的法院、检察机关的存废、审判分级等问题的思想,都充分考虑了当时中国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士绅具有相当权威的情况,而关于监狱改革的思想则充分考虑到经费不足并短期内很难解决的实际,提出开源节流的改革方案。卢埃林虽然深受德国思想家的影响,但其构筑的思想体系完全从美国的实际出发,以普通法传统为背景,探讨司法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实现其社会功能,克服和预防经济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虽然国内国际形势与二十世纪上半叶都不能相提并论,但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司法改革既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而是必须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指出,改革的目标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表明法院改革由审判方式改革到人财物管理改革再到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步走方案的实施。在改革的微观方面仍然必须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比如推行“司法文书”网上公开对于特别偏远的地区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则不仅需要公检法、监狱、看守所等部门的合作,还需要动员其他软性社会力量,比如社会公益组织对青少年受刑人的心理疏导和再教育将发挥重大作用;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成果。
(二)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
民国时期的中国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上存在重大缺陷。杨兆龙在研究司法问题时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利用对欧洲和美国制度的熟悉,充分结合两大法系的优势。他建议借鉴英美国家的巡回裁判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经济发达、司法制度良好的地区渐趋衰落,但杨兆龙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仍然具有重大价值;而对于人们热议的陪审制度,杨兆龙坚决反对,认为在司法制度不健全、法律专业人才缺乏、普遍法治观念欠缺的中国,不具备陪审制度的生发环境。卢埃林对普通法怀抱热情,但同时并不像其他普通法学者一样对成文法嗤之以鼻,认为成文法方便法官、律师适用法律。在吸收德国商人法庭和商法典的基础上主持起草《美国统一商法典》,成为至今为止在美国接受程度最高的法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大法系逐渐融合。我国司法改革在国际大趋势之下需要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成果,《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在我国成文法的传统下所进行的判例法制度探索,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制度创新点。司法改革应当不断结合成文法的清晰性和判例法的灵活性,在社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纠纷时不是一味地重新立法、修改法律,而是在尽量维持法律体系稳定性的前提下,在司法技术、司法判例上下功夫,实现社会转型期的司法职能。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
D909
A
1003-4145[2011]03-0152—04
杨兆龙:《法治的评价》,节选自《杨兆龙法学文集》,艾永明、陆锦璧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2011-01-15
张娟,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