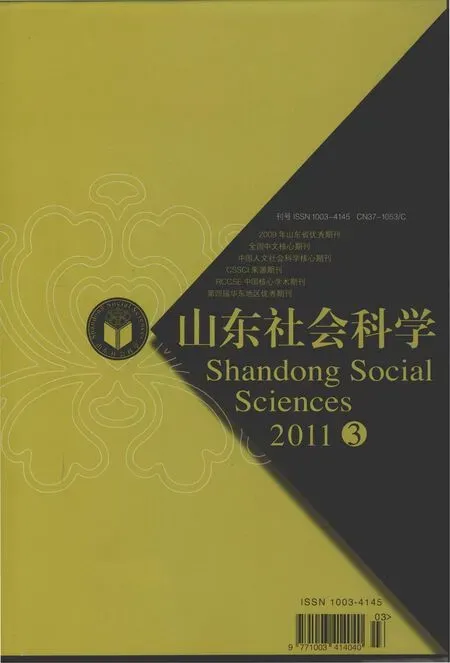环境侵权若干问题之检讨①
2011-04-12徐伟敏
徐伟敏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环境侵权若干问题之检讨①
徐伟敏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环境损害的两种类型。民法中的环境侵权仅指环境污染致人身财产损害。对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免责事项、最高赔偿限额应作出必要限定。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不能任意扩张。环境损害的救济需要综合运用私法、公法手段和社会安全机制。
环境侵权;环境侵害;救济
环境侵权既是《民法通则》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的一种,又是环境法规制的主要对象。由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学界对环境侵权及相关概念的涵义理解不一,对其归责原则、违法性判断、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下面,笔者试图运用民法和环境法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及其上位概念
将人为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区分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学界共识。学界的通说认为,人为活动产生的物质与能量进入环境,引起水、土、大气污染及噪声、振动、电子辐射危害,导致环境的不利改变称为“环境污染”。人类不适当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导致环境功能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称为“环境破坏”。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都是人为活动致环境不利影响的法律事实,是根据环境侵害的原因将人为活动引起的不利环境影响进行的类型化。环境污染强调人为活动产生的物质与能量进入环境,致环境不利改变而间接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环境破坏强调人类开发利用环境要素时,造成环境要素本身及生态功能的损害。台湾学者陈慈阳先生强调,公害(环境污染)之构成,要求人为行为经媒介物影响环境并造成多数人人身、财产损害或环境损害的后果,两者缺一不可。人类非经媒介物直接为开发利用行为、超出环境容许限度造成自然生态的损害,一般不产生公众直接损害的后果,不是公害或环境污染。如滥砍滥伐直接造成生态破坏不属于环境污染或公害。①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这种学理区分对法律适用也有实际意义。首先,从各国环境立法的实际情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实行分别立法的,环境损害的这两种类型分别对应违反这两种类型立法的后果。其次,这种划分对探讨环境民事责任具有重要价值。在各国法律中,环境民事责任都是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手段,但是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和环境破环的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
关于何为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共同的上位概念,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总结起来大致有“环境问题”、“环境损害(环境侵害)”、“环境侵权”诸说。
韩德培、陈汉光先生认为,“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原因和规制的对象,是指人类活动使环境质量下降或生态失调,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及其它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现象,包括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②韩德培、陈汉光:《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陈泉生先生认为,“环境侵害”是因人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污染或破坏,从而侵害相当地区多数居民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及其他权益,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事实。①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汪劲先生认为,“环境侵害”即人类利用环境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继而导致公私财产损失或人体健康损害、环境质量恶化环境功能下降的现象。②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7页。王明远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致使自然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或公共财产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的事实。③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张梓太先生认为,“环境侵权”较之“环境损害”或“环境侵害”更能揭示环境污染、破坏致人损害问题的实质,广义的环境侵权包括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致损害,狭义的环境侵权仅指因生产活动或其它人为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和其它公害,并给他人财产人身等造成损害或损害之虞的事实。④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6页。
笔者以为,明确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共同上位概念是环境法立法和实施的需要,也是环境法体系化的需要,因此,对这一环境法基本范畴的含义应准确界定。通过抽象环境法的基本范畴,界定其准确含义,可以构建学者间对话的基础平台,规范环境法的研究,增强法的安定性。笔者以为,“环境损害(或环境侵害)”作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上位概念,较之“环境问题”、“环境侵权”更为合理。“环境问题”的含义过于宽泛,不宜作为法律术语;而之所以弃“环境侵权”不用,是因为“环境侵权”在民法上有特定含义,随意改变会导致概念混淆。这样“环境侵害”就可界定为人为活动直接、间接导致不利环境影响的事实,其外延涵盖经由环境媒介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环境污染)和人类开发活动直接造成的环境要素本身及生态功能的损害(环境破坏)。
二、《民法通则》中“环境侵权”的含义
在民法体系中,侵权是侵害他人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行为,是行为人基于民法规定应负侵权民事责任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6条是我国关于侵权责任的最基本的规定,它确立了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和特殊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明确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是特殊侵权的一种。而民法中通常所称“环境侵权”,不过是环境污染致害的代名词,仅涉及因环境污染所致人身财产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情形,而不包含环境破坏。关于环境侵权的构成,目前我国民法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归责实行无过失责任,损害事实是污染致人身损害,或者是致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毁损,丧失价值和使用价值。⑤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因此可以说,民法上以“环境侵权”专门指代环境污染致害已属约定俗成。
基于对“环境侵权”含义的探讨,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的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仅适用于环境污染致害;人为活动直接损害生活环境,然后经由环境媒介间接损害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是环境污染致害的实质,这一点在界定是否构成环境侵权时应予强调。正是这种间接侵害之特性,才成就了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原因行为的持续性、反复性;损害的累积性、复合性;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难以直接证明;后果的滞后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等。一般环境破坏行为并不具备这些特点,因而就不是“环境侵权”,不适用《民法通则》第124条,应适用动物、物种保护的特别法或者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纵然学界对环境污染致害民事责任的性质、构成要件尚未完全达成一致,有关侵权责任的探究也应在民法框架内依据民法原理进行,任意解释、改造将导致民法和环境法无法有效沟通。
三、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问题
19世纪以来的侵权行为法主要建立在过错责任基础之上,对填补损害、促进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繁荣起到了推进作用。由于现代工业社会意外事故增多,无过错责任渐次扩张成为与过错责任并驾齐驱的归责原则。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环境侵权采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原因是,特定企业、设备、物品是潜在危险之源,其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因该活动受有利益也应承担风险,损益共担符合正义。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加害人并无道德上的可非难性,其承担责任仅为实现损失的公平分配。然而,无过错责任的必要前提是对损害赔偿数额的限制,且加害人可以通过定价机制和责任保险分散风险。由于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相配套的损害补偿社会化机制,因此无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无过错责任是令加害人负担“道义责任”,代替国家和社会履行社会保障职能,因此应将其从民事侵权法中“卸载”,并转而主要从社会化或社会法的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①赵 红梅、李修棋:《无过错污染受害者补偿救济的理论与制度选择——一种社会法的观察视角》,《环境资源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笔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出现是基于损失合理分配的公共政策考虑。侵权责任中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等多种归责原则并存是必然趋势,不容动摇。但上述学者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提醒我们应重视如何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利益的衡平。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有利于受害人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已经是侵权责任制度适用于环境侵权时最大限度的让步。如果没有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免责事项、最高赔偿限额的必要限定,没有损害补偿的社会化机制,就会抑制对社会有益的产业活动,难以实现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安全的调和。
四、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
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赔偿范围除了包括污染所致人身、财产损害外,还应包括生态价值损失和环境权益损害。②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德国《环境责任法》(1990年)也规定,经水、土、空气传播的物质、振动、噪声、压力、放射物、煤气、蒸汽、热气等排放物在造成物之损害的同时,造成自然和景观破坏的,应当恢复原状,赔偿权人可要求预支恢复原状的费用。
笔者以为,在侵权法中一味扩张赔偿范围是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传统侵权法之环境污染致害的赔偿范围,仅涉及经环境媒介致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不包括恢复环境本身的费用,这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类似。传统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仅及于缺陷产品以外的人身财产损害,而不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适用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同理,恢复环境费用和生态价值损失可以不必在侵权责任中解决,而在专门的自然保护法中解决,以避免侵权责任法不堪重负。至于环境权,笔者以为也不宜列入环境侵权赔偿范围。环境权一般表述为人类在良好、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及利用环境的权利。由于自然生态和环境本质上非专属于某个个人,使环境产生负担的环境利用行为不可能全面禁止,因此通过排除侵害和赔偿损失保护环境权很难操作。笔者赞同叶俊荣先生的观点,即环境权保障或实现的重点不在于私权化,而在于保障民众参与环境决策的程序性权利。公民可以通过参与立法和行政过程,影响与环境利用有关的资源分配和利益调和。③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五、环境侵害的预防与救济
实际上,环境侵害的私法救济并非事实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全部。私法在救济受害人、努力实现损失的公平承担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也具有消极性、个案性、任意性,缺乏在预防环境损害和提升环境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私法手段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须是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受害人提出排除、防止或赔偿的请求,才能通过民事责任机制排除侵害、补偿受害人损失、制裁违法。如果将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张至生态价值损害或公民环境权益损害,一方面由于高度不确定性和涉及复杂利益衡量而难以操作,另一方面可能超出民事责任、私法手段所承载的功能,把民法改造得面目全非。
环境侵害的救济需要综合运用私法、公法手段和社会安全机制。从各国环境立法和环境管理实践来看,污染控制、自然保护等环境行政法规范构成环境法的主体,环境管制和环境规划的公法手段对环境侵害的排除和防止起主导作用。环境保护和环境侵害的预防与救济,从预防与规划、开发利用活动监管到具体危险的应变处理,主要通过命令—控制等公法手段实现。但是公法的反应也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无论多么严密的管制和污染控制都不能完全杜绝污染。因此,环境侵害的救济应当多措并举。于加害人明确之情形,可考虑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解决受害人救济问题,籍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转移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同时辅之以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由所有风险相近的设施经营者、污染者共同负担分散风险,避免因加害人财力不足而无法对受害人全部赔偿。于致害污染源不明或加害人无赔偿能力又没有参加责任保险时,考虑运用特别补偿和整治基金提供受害人补偿和环境整治费用。
(责任编辑:武卫华)
D922.6
A
1003-4145[2011]03-0149—03
2010-12-08
徐伟敏(1967-),女,浙江鄞县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法学、经济法学。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07JJD8201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