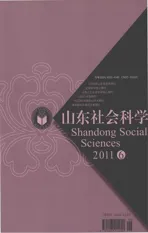文学研究的学科权力:知识转换和嫁接
2011-04-12张荣翼张译丹
张荣翼 张译丹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文学研究的学科权力:知识转换和嫁接
张荣翼 张译丹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文学知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文学知识求知、求真这种面对事实的简单外貌下,可能遮蔽了它作为主体的秩序建构执行者的性质,文学知识说到底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秩序的建构!在文学知识的运作中,它和某种渗透到学科中的权力发生紧密关联。这种权力关系在文学研究的学科策略上有鲜明的体现。另外,在文学的想象框架中,文学知识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文学研究;学科权力;知识;文学想象
或许文学研究有过一个按照研究者兴之所至、凭借兴趣加以言说的阶段,但是这样一个时段我们只能以“或许”来臆测了。在我们有文献可考的研究中,这些文学研究都不是凭借所谓兴趣来支配的。孔子提出诗歌的“兴观群怨”的功能,就是把诗歌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驱逐诗人的主张以及亚里士多德对于诗人存在合法性的辩护,也都是以文学与社会有着重大关联作为前提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兴趣最多只能作为研究行为选择的一种佐料,而核心的还是文学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目的。
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目的性的活动,在求知的理由之下,它包含了意识形态的诉求。也就是说,通过文学研究的表达,能够把所指涉的文学的意义纳入某种符合某一阶层的文化秩序的框架中,在积极的角度上是要为这种秩序的建构增砖添瓦,而在消极的意义上,也要防止文学作品的意义对于该文化秩序造成伤害。在这样一种涉及了权力问题的领域,就有权力关系发挥作用了。文学研究的学科权力就是这样的权力关系的直接体现。
一、学科权力作为知识权力的体现
福柯在对知识谱系的梳理和分析中,始终关注知识权力问题。如果我们也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的话,那么知识的权力关系其实在很古老的年代就已经被掌握了知识权力的人自觉地运用了。
柏拉图创建他的学园这种教学机构,一方面当然有满足人的知识的追求的意图,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未来的社会精英,这些未来精英要充当社会的管理者,就是力图通过掌握相应的知识作为领导的技能,而且对可能威胁到知识的系统性的力量保持一种警惕,基于这一考虑,他才提出了在理想社会下诗人不应该受到赞许的观点。中国的孔子在教导儿子孔鲤的时候说过了“不学诗,毋以言”等,把对诗歌的学习作为立足于社会的最基本的要务,这看起来和柏拉图的主张严重对立,可是孔子的出发点也是要让知识成为未来社会秩序的保障。只不过柏拉图看来感性色彩浓厚的诗歌容易放纵情欲,不利于公民的素质培养;而在孔子看来在经过他自己编删过了的《诗经》中,个人情欲的表达已经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尺度,能够形成一种满足个人需求又不损害社会整体的平衡效果。
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以后的漫长时期,社会和社会的思想也都经过了很多变化,甚至有与前代主张严重冲突的新观点问世的这种激变,可是在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上依然认可古老时代的基本定位,就是这种研究不是一种单纯兴趣,不是简单地对于审美方面的奥秘加以探询,而是涉及对于文学的话语权的占领!
这样一种局面形成之后,已经类似于战争状态。杰姆逊曾经在正面意义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发生在我们人类文明上的最为关键的事情是,我们的文明正逐渐变为各个专家的文明。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被越来越多的锁进他自己的一小块区域,并且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区域。现在,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同时解释一个古代的铭文和一个现代科学的公式。文化和人类的共同财富,已经成为各个专家要掠夺的东西。”③里维特语,转引自[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杰姆逊肯定了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但是这样一个状态显然不是健康的,也因此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派别在的确这样争夺资源的同时,并不明确提出这种状况的存在,仿佛认可了这种状况存在的事实,就会影响到本学科的研究的正当性。
这种学科的权力话语不一定就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意识到的。恩格斯曾经说,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意识不是思想家们都明确意识到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这里可以参照一个事实,学者坎贝尔发现,都市里的妇女们往往会说买杂货是“买东西”(doing the shopping)(与干家务类似),而买衣服是“去购物”(going shopping)(与愉快地“去外面”相似)。④[美]柯林·坎贝尔:《购物、快感和性战争》,载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页。用词的差异不是简单的称谓问题,这里的差别在于,买衣服属于与自己的身体外观相关的,而身体外观在这里成为女性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具体的落实之处。她想象自己是什么样子,她就把自己穿成那种样子,她把自己穿成那个样子,她就认为自己是那样一种身份或者地位。因此男性需要在生活中苦苦拼搏得来的那种职业意义上或者经济条件上的地位,家庭主妇们只需要在购物中就可以达成。对于广大女性来说,生活中的这一“事实”是通过“想象”来达成的。而这种达成至少可以在女性群体的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可以说通过“购物”和“买东西”这不同称谓,女性掌握了自身的利益所在,但是这种掌握在自觉性的程度上还是不够的,她们更多的是一种朦胧的倾向而非自觉地思考。在用词差异的背后,凸显的是权利关系和权力的关系!
应该说,学科的权力关系远比这样一种事物的指称关系复杂。它可以通过对文学现象中的若干事实的聚焦、评价、相互关系的建构、文学现象和文学研究的沟通等达到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还有很关键的方面在于,学科的权力影响不只是在对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评价方面有所体现,它还会对文学现象的选择产生影响,就是说它可以以褒贬的方式来作出评判,也可以通过根本就不置一词的方式来对对象作出冷遇。在当代社会中,是各领域实行分工但是各领域又有联系的状况,文学研究的状况会对文学的创作产生强烈的反馈,因此文学研究的学科权力实际上也就成为影响创作的重要方面。
二、文学的知识转换与嫁接:两种策略
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权力系统,它的作用不只是个人的关系方面得到体现,不只是某一个人因为秉有了比较多的影响力就可以在对文学的言述、评价方面发表更有权威性的见解。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权力系统,它还要和社会的其他话语系统发生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研究领域自身的权力关系也可以得到体现和落实。
这种权力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不同方面。
文学研究借助于文学知识来进行,而文学知识往往是不能证伪的,也即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这种知识的有效性其实是可以质疑的。譬如文学意境、文学典型的美学价值,在各种文学理论的书籍中连篇累牍地加以表述,如果说它的表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应该可以找寻到一条文学创作的成功路径,可是按照文学理论书籍的引导,可能作家还可以进行创作,但是创作中的灵感一类恐怕就所存无几,作家创作也不会有多少乐趣可言了,而工作乐趣是工作干得不够出色的重要条件。文学知识的规定性还体现在对文学的接受方面。“如果有人不具备这种(关于阅读的)知识,从未接触过文学,不熟悉虚构文字该如何阅读的各种程式,叫他读一首诗,他一定会不知所云。他的语言知识或许能使他理解其中的词句,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一定不知道这一奇怪的字串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一定不能把它当做文学来阅读——我们这里指的是把文学作品用于其他目的的人——因为他没有别人所具有的那种综合的‘文学能力’。他还没有将文学的‘语法’内化,使它能把语言序列转变为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①[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事实上,文学之为文学并不在于作品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很大程度上是看你怎么来阅读它。通过相应的阅读规则,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把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灌输给公众,建立起一套关于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的秩序;而在这一规则得到普遍认可之后,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强化了作为背景的话语体系的权威性。
学科权力还需要对外部实施影响。对于文学研究的学科来说,其外部影响主要是该社会的政治、宗教等影响,以及学科之间相互的影响。在这两个方面文学的学科权力可以体现为两种不同的倾向,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套策略。
对于社会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影响,文学理论拿出的一套策略是强调文学学科的相对独立性,认为社会的各个方面要对文学发生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也是通过美学的途径发生作用,不能简单地把文学的事情比附为一般的社会实践。在这种策略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当年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这种思潮从单纯的艺术角度看是强调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其实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各种不同的艺术和美学的流派与理论中都认可艺术美并且往往还宣称自己是真正的艺术美的看守者,这样看来唯美主义的特殊性其实在于强调艺术领域中感性的重要地位,这种强调和此前流行过的理性主义的艺术观完全牴牾。那么我们知道理性主义的艺术观其实是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统治有着密切的共谋关系,而唯美主义对于在个人层次发挥作用的感性作出特殊强调,其实就是要和官方划开一段距离,形成一爿小资趣味的自由化的审美天地。也就是说,当唯美主义者宣称文艺和政治无关时,其实就是把统治者对于文学的强势地位进行屏蔽,这也是一种政治!只是相对于以前统治者对文学提出要求的政治来说,这是一种文学领域要求自治的政治!
对于学科关系问题,文学研究就是另外一种策略。和面对社会的实际统治力量情况相反,文学研究在此时不是强调文学的特殊性以达成文学领域的自治目的,它倒是积极地追求文学研究和其他研究尤其是其他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种沟通尤其在文学研究“向外转”的趋势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②[美]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载[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这里说到的状况是“1979年”作为一个时间的分期标志,也许这一年在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众多现象可以作为佐证,不过在此时间可以有一些上下的波动,譬如在中国其实也就是1979年才刚好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了拨乱反正的转向,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恰好就是力图摆脱以前官方对文学的影响力,但是文学研究领域自身又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主张,于是就采取一种规避政治的路径。在这种主张文学相对自治的观点中,其实不是因为美学的要求而作出的反应,它只是对于此前的文学过度政治化的一种反应!在这一积极寻求文学和文学之外的因素的关联性的研究中,主要体现为两种趋势。
一种是跨学科的研究,即在文学研究中更多地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乃至方法,譬如关于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变化,其中一个方面不是文本就能够说明问题实质的,即文学生产的体制问题,这种体制最直接的出现就在于,古代作者的创作可能更多地属于业余爱好,或者已经有了一官半职,创作可能和所在的职务有一定相关性,多少属于职务行为,如白居易的讽谕诗是作为左拾遗官职的工作报告;还有就是已经衣食无忧者,创作是其精神追求的表现。在近代以来文学和出版行业有了密切联系,这样就有了作者和书商的相互沟通、洽谈,创作可以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直接面对市场的选择了。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基本上都以一种不同于社会上其他职业化的工作的面貌出现,这种复杂性为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种则是专门化研究,突出文学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如20世纪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强调文学的诗性,而文学诗性被聚焦到文学的语汇、修辞、结构方面,这些方面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属于文学形式,它是被作为服务于文学表达的手段这一角度来看待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把它提升到了文学的本体层面。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文化批评,则是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甚至文学表达的修辞手段都可能是隐形的意识形态灌注其中。那么,它们这种鲜明对比并不是非要辨析出其中的对错是非,而是各自扫描了文学的一个侧面。当对于文学的研究采取不同路径时,也就会有不同的学科权力及其表达的东西。
三、文学知识:想象的和事实的
文学知识是作为对于文学的认识的系统而存在的。在这种知识系统中,有些部分是对文学所存在的现象的言说,属于事实陈述的范畴,另外有些部分涉及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属于评价范畴。除此之外,文学知识还有一种就是它不是简单对于事实的陈述,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它不是主观性的价值评判,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可以说是对思想领域建构出来的关系的思考。譬如,在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中的“意境”,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我们并不能指称某一个词语、某一次的修辞是意境所在;同时也不是一种主观评价性的概念,仿佛对作品的“好”的评价,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意境是从更大的文化观念出发来看待文学的结果,意境并不是主观的。在文学的和艺术的观念系统一旦建立了所谓意境的追求之后,它就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存在。
在文学知识的想象关系中,在创作领域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一般人都同意文学属于想象的范畴。这种想象不只是体现在细微的修辞表达层次,而是文学如何来看待社会的层次。譬如同样属于“现实主义”文学,鲁迅笔下的浙东农村是落后的、愚昧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农村,则显得富于诗意,它是纯朴的、宁静的。当我们分别阅读他们各自的作品时,都可以各自体现出它们打动人心的力量。可是,当我们来进行对比思考时就会发现问题。鲁迅的家乡是包括绍兴等地的浙东地区,这里是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要说的话,“绍兴师爷”这种职业可以说明当地智力资源的雄厚。而湘西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属于文化上的落后地区。如果结合到近几百年来,两地各自有多少举人、进士、院士等也会有很大差异。从“现实主义”要从生活的客观角度描写生活的认识出发,应该是沈从文和鲁迅在立场上互换才对,因此在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的立场是错位的。这样可以说明,文学的表达在细节方面可能达到了逼真的层次,其实在更大的视野看,它其实是想象的产物。在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关于中国乡村的想象中,他们把自己的对于乡村的理念灌注到了描写中,因此才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乡村面貌。
在两位作家的乡村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想象不只是一种修辞意义的表达,而且是一种整体化的结构作品的方式。整体化不是限于某一步骤就戛然而止,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也体现在文学的研讨领域。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事例: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受到了日本左翼作家的影响,在文学的观念上,他提倡带有左翼色彩的劳动起源说。但是鲁迅也有另外的想法。他在一次讲座中说:“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鲁迅在这里就是采取了一种骑墙的态度。一方面提倡劳动说,一方面又提倡休闲说。如果文学中的诗歌和小说各自有其产生的渊源的话,那么就需要说明文学是一种集合的概念,即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并不都是同一发生学的对象,只不过它们现在都有我们今天看来的“文学”的特点,就被纳入了同一个序列。但是包括鲁迅在内的说明文学起源的研究者们并没有这样思考,他们还是在寻求一种统一的关于文学的观念,可是在面对具体一些的问题时,则又采取分别对待的态度,于是就有了以上的矛盾!总体来讲,文学研究中往往就是以一种想象的前提来框架文学现实,这样的话,不管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尊重现实的客观性,在认识中其实已经没有了客观性的基质,这就好比戴着有色眼镜来寻求五彩缤纷的色彩,不管如何细致都注定了它是悖谬的。
作为文学理论学者的海登·怀特考察了历史文本的写作问题。他说:“‘历史’不仅是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①[ 美]海登·怀特:《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载[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他是文学理论家,可是在这里却谈论“历史”,这就在于,历史是讲究客观叙述的,可是这种客观性作为一种态度应该提倡,也应该看到当人来叙述历史时,历史作为人的记忆总是会遗漏很多东西的,因此这里就有历史叙述的选择问题。历史必须遵循客观性,可是历史不等于就是过去发生了的事实的复写,选择角度决定了历史学的叙述可以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表述。说“狗咬人”与“人被狗咬”,如果其中一则为真,则另外一则就会同时为真,它们在逻辑上是等值的,可是二者的强调有不同,这种不同在对事实的层面上没有影响,可是对阅读该信息的人在心理上是不完全一致的。再把报道放在稍微复杂的情况看,“一个人因为酗酒导致车祸”和“一个人遭遇了车祸,查明了他在事前酗酒”,可以是对同一事实的描写,可是我们知道酗酒的确是车祸的常见原因,但是并不是酗酒就一定引发车祸,也正因为酗酒并不必然引发车祸,才会有很多人持侥幸心理,这种侥幸心理又大大提高了该种原因车祸的比率。于是在交通安全的宣传上,就会更加强调禁止酗酒,而在另一方面酗酒所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比率仍然是一个大体的常数,譬如每一百次酗酒会有一次中等程度的事故,于是对于那些不循规蹈矩的肇事者起不到警示作用。
学科研究是针对学科所涉及的事实的,可是学科的关注点和事实本身可能并不始终同步。文化学家美因霍夫曾注意到,在非洲有两个相邻的部落,一个是农耕社会,另外一个是游牧社会。在农耕社会方面,耕地和拓荒各是一个词汇,而在游牧社会里则是笼统用一个词。因为在游牧部落看来,耕作是一种没有出息的下贱的工作,根本用不着对它的活动加以细致的区分。实际上,他们没有农耕经验,也可能根本就体察不到扩大农耕而积的拓荒之举与每年都在同一块土地上耕耘之间的差异。卡西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心智曾经创造的东西,它从意识的整体范围内择选出来的东西,只有当口说的语词在其上打下印记,给它以确定的形式时,才不会再次消逝。”②[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4页。这里,学科的语词是学科思考的标记,标记的行为依赖于价值判断的标准。游牧部落所认为的“下贱”的农耕活动,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角度看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也许农耕部落会认为游牧群落不理解开荒是一种愚顽的表现,就像荒地需要开发才能耕作一样,他们需要被启蒙才懂得事理。学科的工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针对客观事物,而是针对看到事物的方式和对其他看待方式的评价方面。
学科工作最初建立的目的是针对所研讨的对象,可是在学科的发展中,有时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人的,这里包括抨击论敌,也包括施加社会影响力。利奥塔关注知识社会学,其实也就是知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科学在起源时便与叙事发生冲突。用科学自身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学不想沦落到仅仅陈述实用规律的地步,只要它还寻求真理,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种话语就被叫做哲学。”③[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载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所谓知识和叙事的冲突,就是叙事不只是针对事件,它还表明了叙事人和事件的关系。如另一位西方学者所总结的:“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够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化。”④[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科学在这里完成了由简单的工具,向着超越了工具的形而上的意义建构系统的转变!
文学知识是文学话语的原发点,通过已有的文学知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更大范围的文学知识。在文学知识的这种生产性中,可以使得相近的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言说框架下显现不同面貌;也可以使得在直观看来不同的文学现象,在框架的组织中获得系统的共同性。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特性,进而再熟练地运用文学知识的特性进行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则还需要通过对这一特性的把握,破解文学知识所带来的困局。
I06
A
1003-4145[2011]06-0125-05
2011-04-20
张荣翼(1956—),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张译丹(1988—),女,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福柯认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①[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这种情况当然也会体现在文学研究这样的人文领域。这种学科权力在伊格尔顿的著作中有过说明,“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教师们,这些人与其说是学说的供应商,不如说是某种话语的保管人。他们的工具是保存这一种话语,他们认为有必要对之加以扩充和发挥,并捍卫它,使它免遭其他话语形成的破坏,以引导新来的学生入门并决定他们是否成功地掌握它”②[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也就是说,掌握学科话语的人通过教育、培养人才的模式,实际上也是寻求对自身学科的接班人的模式,把对某些学科的见解以知识传承的名义灌输下去。在这种灌输过程中,最直接的学业成绩评分的方式,通过这种尺度把合格的人选甄别出来;在进一步的形式中,就还有评选论著的奖项、评审职称,甚至直接声言谁是他的衣钵传人等方式来传达这种权力话语。当然,这种权力话语的确立也包括“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教师们”拥有较多的学科的话语权,他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得本学科的信息、项目、资助等资源。掌握了学科话语权力的人通过这种权力支配关系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而那些希望在权力系统中分一杯羹的人,则是依赖于效忠的方式来获得同情。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