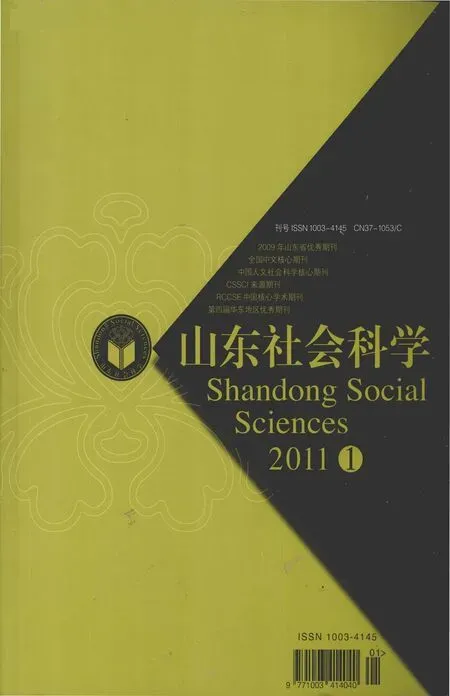中国有狂欢吗?
——狂欢理论的应用与反思
2011-04-12鄢鸣
鄢 鸣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中国有狂欢吗?
——狂欢理论的应用与反思
鄢 鸣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狂欢理论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起我国学界的巨大共鸣。然而,中国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狂欢节,其文化更多地呈现出“非狂欢”的特征。因此,在运用狂欢理论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在对话中实现新的文化形态的构建。
巴赫金;狂欢;语境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对话、杂语、狂欢等现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命题,既扩大了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野,又有力地推动了人文学科诸领域的进步。作为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狂欢理论不仅受到俄苏文学界与理论界的重视,也引起了各国相关领域学者的兴趣和注意。他们纷纷对巴赫金的狂欢思想给予高度评价,并从本民族的研究视阈中对狂欢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再阐释和卓有成效的补充。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也颇有心得,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钟敬文的《文学狂欢化思想与狂欢》、钱中文的《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等等。所有这些阐释对于理解和丰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然而,当前在“狂欢理论热”的背后,也潜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以狂欢视角研究中国文艺现象,成果虽然丰富,可大多数研究者习惯将狂欢理论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加以接受,在涉及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或者干脆一笔带过。当然,在个别研究中也有人对狂欢理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比如,阎真对狂欢理论的质疑①阎真:《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又见阎真:《文化史的虚构——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七大缺失》,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两篇文章均坚持狂欢理论是巴赫金对文化史的虚构。。不过,这样的质疑声音虽然可贵,却缺乏对巴赫金理论的完整与深入的了解,存在着全盘否定狂欢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倾向。客观地讲,狂欢理论是巴赫金在系统研究欧陆狂欢现象时得出的深刻见解,体现出理论家对西方文化源流脉络的清晰把握,决非是一种凭空的想象性的虚构。但是,这并不是在赞同狂欢理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调。研究者在将狂欢理论从俄苏文化语境移植到东方文化语境时,遮蔽了文化间明显的差异,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甚至直接在狂欢理论的独白话语中建立起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应关系。这样做,不仅违背了理论应用的一般原则,造成理论的泛化,也严重扭曲了巴赫金理论“对话”精神的基本内核。本来是要进行文化间的“对话”,结果却变成了理论的“自我论证”、“自说自话”的独白。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颇欠妥当的,也是需要巴赫金理论研究者认真反思的。
如何准确理解中国文学中的狂欢化问题?这里首先必须要清晰地厘定狂欢理论的“中国边界”。研究者必须回答下面三个根植于大前提的问题:一、狂欢理论的内涵性问题;二、狂欢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三、中国语境下狂欢理论的价值性问题。只有对这三个问题作出回应,才有可能触摸到狂欢理论的基本脉络,找到狂欢理论与中国文化现象的切入点,进而推动对狂欢与狂欢化现象的研究和认识。
一、狂欢理论的内涵性问题
狂欢理论是什么?无论承认或者不承认狂欢理论的价值,研究者都认为巴赫金对狂欢的论述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体系。但是,要准确理解“狂欢”的含义,还必须区分出三个有内在联系、相互关联的层面:文化领域的狂欢活动、文学领域的狂欢化现象以及狂欢的生命哲学。
首先,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活动,狂欢节起源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人类节庆活动,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则占有了重要地位:“狂欢节型的庆典,在古希腊罗马广大民众的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古罗马,中心的(但并非唯一的)狂欢型庆典,是农神节。”①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第170页,第173页,第218-219页,第221页,第220页。不过,狂欢节的全面兴盛,却是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之后的事情:“在中世纪,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宗教节日,全有人民在广场上狂欢这个内容……中世纪晚期的各个城市(如罗马、拿波里、威尼斯、巴黎、里昂、纽伦堡、科隆等),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三个月(有时更多些)时间,过着全面的狂欢节生活。”②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第170页,第173页,第218-219页,第221页,第220页。与其他严肃的宗教节日活动相比,狂欢节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它对神圣、严肃的宗教生活的颠覆。从本质上看,中世纪的狂欢节既是民众生命力得以淋漓释放的节日,也是等级社会的“减压阀”、“安全阀”。在巴赫金的研究中,所有狂欢节庆式的庆贺活动的总和被统称为狂欢式。狂欢式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具有全民性、颠覆性、狎昵性等特点。它是狂欢节的重要载体,深刻体现出民间对世界和生命“交替变更”的两重性认识与理解。
当然,狂欢式是狂欢节的仪式现象,属于一种民俗文化存在,却并非是一种文学现象。但是,狂欢式拥有一整套与狂欢相联系、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当狂欢式转化成为文学的语言,成为文学表述内在的一部分的时候,这就出现了巴赫金所说的文学狂欢化。直接生成于狂欢节庆典活动的题材、体裁、话语等,在狂欢化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越到后期,狂欢化的文学越来越显现出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独立的传统:“十七世纪下半期以后,狂欢节几乎已完全不再是狂欢化的直接来源;先已狂欢化了的文学,其影响取代了狂欢节的地位。”③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第170页,第173页,第218-219页,第221页,第220页。于是,本来意义上的狂欢节、狂欢式的其他庆典以及其他形式的民间狂欢化文学等等,虽然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对文学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但其重要性已经逐渐让位给独立的狂欢化的文学传统。然而,无论是直接受到狂欢式影响的文学,还是经过狂欢化文学传统“转述”后的文学创作,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中,都深刻渗透进民间独特的狂欢节世界感受。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巴赫金的狂欢还指一种根源于民间生活的生命哲学和世界观。与官方貌似一本正经的严肃的独白话语意识不同,狂欢意识并不是封闭的自足体,而是具有深刻对话性、包容性和创造力的开放的价值体系。这种开放意识根源于狂欢节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并由狂欢节的功能与性质所决定:“狂欢节总是在庆贺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世界——新年,新春,新王朝——的诞生。”④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在狂欢的笑声中,“这个笑是在更替转变的过程中捕捉和认识现象,在现象中找出不断更替、除旧布新的两极:在死亡中预见到降生,在降生中与见到死亡,在胜利中预见到失败,在失败中预见到胜利,在加冕中预见到脱冕……”⑤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第170页,第173页,第218-219页,第221页,第220页。因此,狂欢的话语展现了危机与嬗变的奇异结合,使得固定的价值立场和严肃的评判标准都被相对地模糊化。它破除了话语的等级藩篱,从而为话语内部创造力的解放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它揭示了世界的丰富的物质开端、形成和交替,新事物的不可战胜及其永远的胜利,人民的不朽”⑥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第318页。1998年版,第478页,第318页。;“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也是没有终结的,同任何的最终结局都扞格不入。因为在这里,任何结局都只能是一个新的开端,狂欢体的形象是不断重生的”⑦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第170页,第173页,第218-219页,第221页,第220页。。
总之,在狂欢理论的三个层次中,狂欢活动是民众确证自身的庆祝方式,文学的狂欢化具有结构体裁的重要力量,构成了强大的狂欢化文学潮流。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巴赫金发现了狂欢化的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立场的影响。这就是:“它排除任何单一的教条主义的严肃性,不让任何一种观点,不让生活和思想的任何一个极端,得以绝对化。任何单一的严肃性(包括生活中和思想中的严肃性),任何单一的情调,都只能属于主人公,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小说的‘大型对话’之中以后,却总不结束这个对话,总不肯打上完结的句号。”⑧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第170页,第173页,第218-219页,第221页,第220页。巴赫金对狂欢化世界观的深刻揭示,应该是狂欢理论最富价值和最富魅力的地方,也是吸引学者关注并运用狂欢理论阐释中国文化文学现象的主要动因。
二、狂欢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狂欢理论是对狂欢现象的抽象与概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狂欢理论进入中国不久,研究者多从同一性的角度来把握狂欢现象,指出狂欢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活动,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狂欢是人类活动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特殊的文化现象。”⑨钟敬文:《文学狂欢化思想与狂欢》,载《光明日报》1999年1月28日。然而,从钟敬文作出这样的论断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光阴。研究者必须要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提上日程,在接近与揭示巴赫金笔下的狂欢活动的本质过程中,重新思考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与现实环境。
从总体上看,狂欢并非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是一种“变态”,其存在与兴盛有着自己的文化语境和内在逻辑。当深入考察狂欢这一现象时,其内部有三种明显的分立倾向,不能不加以充分的考虑。一是人神之分。古老的狂欢节起源于宗教活动,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狂欢虽然颠倒了天国与现世的关系,但是它的兴盛却恰恰是在基督教最为发达的中世纪。对于宗教来说,人是神的仆人,在万能的主面前每个人都有原罪。只有不停地忏悔原罪,人才能被主引导,得到最终的拯救与解脱。在重大的宗教责任面前,中世纪的教士们认为哭泣是一种功德,以致不少人哭得非常辛苦,眼帘都脱落了。⑩[挪威]吉尔胡斯著,陈文庆译:《发笑的神灵,哭泣的贞女:宗教史中的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不过,对普通大众来讲,这种宗教责任非常沉重。他们只能在中途稍作休息,从沉重的宗教义务中解脱出来,在尘世建立一个“颠倒世界”,暂时嘲笑一下天国/地狱的混乱。这是狂欢的宗教性。二是人群之分。从表面上看,在狂欢节中普通群众可以嘲笑王公贵族,乃至出现了“小丑国王”的形象,一切与等级相关的事物都被降格处理,狂欢有突破严肃的等级制度的一面。然而吊诡的是,欧洲大陆的中世纪恰恰是等级制度最严格、各阶级间壁垒最森严、阶级的分化最严重的时期。表面上差异较大的事物,也许在深层次中正是同一因果链条上的两端。在等级秩序沉重的压迫下,民众的生命力在狂欢节上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迸发出惊人的爆发力和创作火花。如此说来,狂欢节应是等级社会的“减压阀”、“安全阀”。这是狂欢的阶级性。三是人自身之分。“死生亦大矣”,对个体生命而言,最大的对立莫过于生死之分。在对于生死问题的态度上,形成了两种趋向。一种是建立于对彼岸、对神圣事物、对死亡恐惧的基础上的世界观。官方文化有意利用这种世界观培育恐惧,达到贬低和压迫人的目的。根植于这种世界观之上的,是权力、人世间的皇帝、人世间的社会上层以及压迫人和限制人的一切恐惧的因素。另一种是狂欢的世界观。它反映的是民众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与理解。它并不建立在个体对死亡的恐惧上,而是建立在大众对新生的愉悦的基础上。这种世界观集中体现在狂欢的两重性形象上:“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的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①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第170页。与官方世界观不同,死亡不再被认为是生命的终结,而成为蕴涵无限生命嬗变的进程的开端,是人类群体生命的一环。在价值评判标准相对模糊的狂欢节里,民众完成了对“大写的人”的书写,实现了对自身生命力量的确认。可以说,人神之分、人群之分以及人自身的分立,不仅是狂欢活动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文化语境,也是狂欢活动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人神之分、人群之分以及人自身分立的视野下,中世纪的欧洲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②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第170页。狂欢也如同神话传说中的双面雅努斯一样,在其所颠覆的对象背后,总能显现出西方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
然而,具体到东方语境,又出现了复杂的新情况。因为东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在东方文化语境的内部,造成狂欢的三种分立倾向可以说是缺失的。首先,如果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点简要概括成为“两个世界”的模式,那么中国文化的关键精神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域(宗教)。”③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页。李泽厚总结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和“情感本体”的特点。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中国文化就显现出对“实用理性”的极强关注。由于缺乏追求超越此世间的彼岸的动力,中国文化的宗教情怀缺失,显现出非宗教性的存在特点。其次,与西方严格的等级社会相比,中国一直是以家族为中心结构的伦理本位社会。梁漱溟甚至否认中国是阶级社会:“假如西洋可以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当然,如果从经济、政治角度来划分,中国是有阶级的。不过,如果从作为自觉的阶级意识方面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却可以说是缺乏的,以至于进入20世纪以后,革命党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和“诉苦”形式,重新唤起人们的阶级意识。这可以归结为中国文化的非阶级性。最后,就人自身之分而言,虽然中西方对生与死问题普遍关注与重视,但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性和阶级性,也造成了中西方的生命意识有很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偏重于讲究中庸,侧重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人与天地的交融感应,而非分裂对立。中国虽然也有地狱天国的神话,但是只作为一般的传说与寄托,并不刻意追求宗教上的目的,更谈不上通过严格的修行生活达成宗教的圆满。由是观之,与巴赫金的欧陆文化传统,特别是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散发出其自身强烈的非宗教性、非阶级性的气息,具有交融而非分裂的趋向。以中国比较具有狂欢气息的民族节日端午节为例,它最初的产生可能与原始民族的庆祝方式有关,反映了原始民族的神话思维特点。但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一节日逐渐与纪念诗人屈原结合起来,被纳入儒家的节日表述体系中,真正成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本来的目的倒不是很明显了。因此,在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分类中,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拒绝“酒神”,属于一种“非酒神型”的文化:“很明显,即使不说‘礼乐’传统是日神型,但至少它不是酒神型的……中国上古是一种非酒神型的原始文化。”⑤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非狂欢”型的。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中国文化中的狂欢因素。在有些地方、有些民族以及部分的民俗活动中,这种狂欢的因素还是表现得很突出、引人注目。比如湖南的迎傩送傩仪式,以及钟敬文指出的华北地区“骂社火”、“闹春官”等。但是,这些活动与类似于“第二种生活”的中世纪狂欢节相比,无论是在强度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中国文学源流中,即使存在着狂欢因素,在文化与历史表述中也不占据主要地位。至少在20世纪以前,在“五四”民俗意识被唤醒之前,它们是被表述、被遮蔽的。那么,在一个“非酒神”、“非狂欢”的文化语境中极力挖掘狂欢因素,片面强调狂欢因素的作用与意义,其价值可能就不如预先设想的那样重要了。
三、中国语境下狂欢理论的价值性问题
当前,有不少学者从事狂欢理论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多有开拓。在纷纭繁杂的研究中,产生了两种倾向。一是在文学领域,将狂欢理论应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发掘古典文学的狂欢因素。比如寻找先秦两汉诗歌中的狂欢因素、《水浒传》语言中的狂欢化色彩等。二是在文化领域,将狂欢作为一种主要是负面的概念加以应用,并予以批判。这两种倾向都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对于前者而言,一方面如前所述,中西方文化语境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古代文学已经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当然,从古代文学中发掘狂欢因素,从而证明狂欢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在古代文学体系中,只能占据次要而非主要的地位。就后者来说,只看到民间狂欢活动低俗、消极的一面,忽视了狂欢具有全民性、创造性的精神内核,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狂欢意识与不同意识结合形成的多层次的狂欢形态。
上面的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出来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它们同样都犯了过高或过低估计民间狂欢价值的错误。狂欢理论是一种关于文化转型时期的理论。巴赫金对狂欢活动的梳理与研究,其重点并非放在民间狂欢领域,而是侧重于对文化转型时期的狂欢化的意识形态进行发掘和重评。在这一点上,它与巴赫金对“对话”、“杂语”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或者毋宁说,狂欢是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超出以往的特殊“对话”。只有在涉及文化转型时期的研究与论述时,狂欢理论才能找到体现其价值的土壤,显现出特别的意义。那么,这种适宜狂欢理论应用并能对当下研究产生借鉴意义的领域,在中国则只能在20世纪中寻找。因为20世纪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时段,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文化转型期。
现代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它与古代文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具有丰富的对话性。这是因为,现代话语的建立过程并非是一条通天坦途。它不断地遭受来自本土语境内部话语的排斥与质疑。在现实中,现代话语与本土话语处于无休止的对峙与冲突中。这种矛盾冲突,割裂了统一而完整的价值体系,为新的价值建构和审美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乃至革命文学对民间戏曲等的改造,都从自己的视野中对民间的神话、传说或者戏曲进行了再创造。这是现代文学中的狂欢化潮流。可以说,正是现代文学的这种话语存在特点,塑造了现代文学的姿态与审美品格。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与狂欢性的二重属性。对于现代文学的狂欢属性,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曾以“众声喧哗”命名之。但是,“众声喧哗”只是反映出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复杂与价值立场的多元,无法涵盖现代文学内部的嬗变力量与生命价值。
现代文学的狂欢性问题,确实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地方。然而,这一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现代文学视野下的狂欢化文学潮流,在表现形态上与民间的狂欢活动有根本的不同。民间的狂欢与现代文学的不同意识相化合,产生了不同层次的文学狂欢形态,比如有鲁迅式的狂欢,有沈从文式的狂欢,有革命文学的狂欢,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狂欢理论擅长的是处理转型期的文化问题,研究者也应对现代文学的狂欢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逐渐建立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相区别的学科内质,这也许是将狂欢理论引入中国并进行中国化阐释的主要价值所在。
四、结论
在狂欢理论的运用中,必须要回应与对象语境相衔接的问题。既不能一概否认巴赫金对狂欢现象研究的主要价值,抹煞其理论的深刻性;也不能出于某种偏爱,任意地扩大狂欢理论的论阈。通过对上面三个问题的回应,可以初步总结,狂欢活动的发生是有其条件的,狂欢理论的应用是有其边界的,狂欢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引导人们关注文化转型期丰富的对话性与杂语性,从而建构起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文学结构。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把握住狂欢理论的内核,在与巴赫金乃至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实现新的文化形态的建构。
(责任编辑:陆晓芳)
I022
A
1003—4145[2011]01—0159—04
2010-10-10
鄢 鸣(1983-),男,山东青岛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