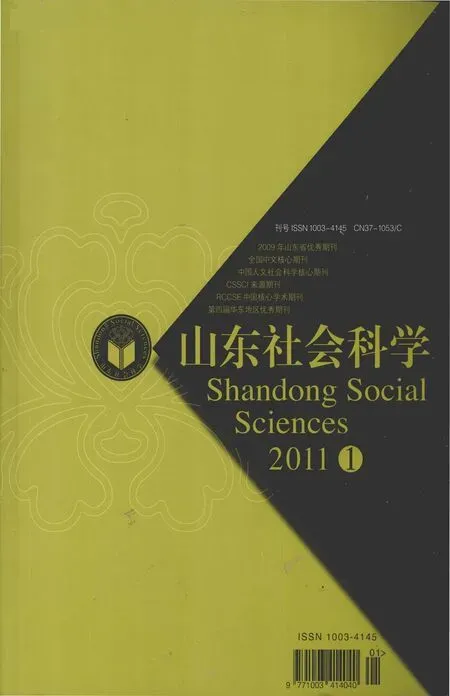《风筝》:寻找精神家园*
2011-04-12李玉明
李玉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风筝》:寻找精神家园*
李玉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风筝》所揭示的并非一般研究者认为的“负疚感”。它是鲁迅在一种悔恨和自责的情绪的支配之下对自己所坚守的某种人生价值的一次检验,是对已失的精神家园的一次顾盼,显现的是先觉者沉郁复杂的心灵世界。
负疚感;人生价值;精神家园
在《风筝》中,鲁迅以动人的语调抒写了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色,以及与这温和的春日相映照相衬托、荡漾于明净春光里的孩子们的世界:显示着春之融融的早发的杨柳、吐蕾的山桃、孩子们无限神往并给他们带来欢乐与惊异的斑斓着的七彩风筝,以及源自于幼小心灵深处的金红色的梦。这一切在鲁迅的笔下构成了一个令人神迷的意境。——然而这于鲁迅能有几多迷醉?!由于突然回忆起二十年前对小弟弟粗暴的“行为”,“我”感到了深深的内疚与悔恨。对早春的故乡的回忆带来的并非释然与恬静之感,而是伴随着一幕“精神的虐杀”的沉滞而郁闷的情怀,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这几乎是在原罪式的自责与反省的情感支配下进行的,它给诗人以凝重的压抑感,使其陷入自我内心的交并与搏斗而难于自拔了:
……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在这里,由于意识到自我的难以甩掉的罪恶感而引起的负疚心理,显示出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罕有的反省精神,以及鲁迅肩负着历史与现实重荷的深刻心理特征。在这种沉重的愧疚与自省的心境中,分明揭示出鲁迅对封建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的痛恨,推而及之,是对一切扼制人性、种种精神虐杀行为的抗议,它从一个侧面显现着鲁迅勇于自我反省、敢于自我解剖的襟怀,以及一个感受着五四新文化思潮而觉醒的先驱者的内心世界与品格。这是《风筝》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也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对《风筝》论述较多、止步于此的一层蕴涵。
实质上,对负疚感这种难以自制的心理倾斜的剖析,在《风筝》中还潜存着另一方面更为内在的含义。自责与悔恨,仅仅是《风筝》的表面心理层次;它还有更潜在的心理内涵。《风筝》的抒情方式是“回忆”,在处理“记忆”和“事实”的态度上,可以发现这是一首深具符号学所指和能指的意义的散文诗。我们可以相信二十年前“精神的虐杀”的一幕是事实,但是回忆者对这一事实的语调,却使人觉得二十年前的事实如何是无所谓的。事实不过是被追忆所借用。如此,二十年后“我”与“他”的会面,是否有这么一回事,也是可疑的,虚构的成分居多。所以,只剩下了追忆本身,只剩下了我“现在”的情感,只剩下了我对回忆的态度,而追忆本身却是真实的,因而被着力渲染的情感和态度更是真实的、主要的。鲁迅在突出或寻找什么呢?他在寻找附丽于回忆本身的意义,由回忆者所暗示的那个东西。所以它的意义,已经离开了回忆和事实本身。但是,他不能像虚构过去那样来说明现在的心境,甚至回避作出说明,至少没在话语上作出说明。“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在此变成了应该去追忆的东西,鲁迅以此获得的自觉是什么?
《风筝》中所暗示的鲁迅的情感和态度,或所谓更潜在的心理内涵,是珍藏于鲁迅心底的对过去纯真时光的眷爱,对充满着梦幻和痴情的童稚天性,以及人们最正当的追求行为与合理发展的肯定,扩而大之,是对一切真正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的肯定。《风筝》的后半部,就是鲁迅这种深层意识的坦露与测试:一方面,凭借着一种极难挣脱的悔疚心绪,“表白”源自于自我心灵深处的人生追求的心迹,——“重责”本身不是证明他对人类天性与人间一切美好愿望的珍惜和弘扬吗?!另一方面,又怀着一种急不可耐的试探心理,企冀在人世间看到至少是与自己有着一样人生感受、人生追求的心灵闪现,哪怕是极其微弱的闪现。换言之,鲁迅力图借助于一种赎罪的方式,在外在于自我的现实人生中,寻求对深埋于自我心灵底层的这种人生价值的呼应与赞同,或者体察一种心灵上的感同身受。追究到底,鲁迅力图在现实人生中寻找一种支撑自我求索和自我奋斗的肯定力量。
出于这样一种感情上的焦渴,鲁迅特地设置了一个讨得宽恕的会面场景,在“我”与“他”(小弟弟——“他”,这时候已具有类的象征意义)的对比中揭示出这一潜在的寓意。鲁迅希望在“他”身上看到同样的对久经诀别的故乡的留恋,同样的对那最令人企盼的梦幻时期的怜惜,并希冀在“他”心灵的底色上映照出对那最闪光不可复还的年华的珍慕;更重要的是,由此而生出的孜孜不息的人生探求。——要知道,这一切正是支撑鲁迅不倦于探索和战斗的一种人生力量,它构成了鲁迅最基本的、饱含有强烈现实内容的人生目标,也是鲁迅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上下求索的最本真的人生实在。鲁迅曾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①《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 2卷,第 236页。又说:“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②《〈十二个 〉后记 》,《鲁迅全集 》第 7卷,第 312页。。驱迫鲁迅时时反顾的正是在灵魂深处对某一种人生价值的刻意探求,它密切联结着鲁迅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同时又与鲁迅长期地独特地对历史审视考辨,对现实静观默察的认识成为一体,因而带有他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极强的历史纵深感。
然而鲁迅彻底绝望了。被现实的重轭所困迫,丧失了人生追求,脸上添刻了许多“生”的条纹的“他”,已经冷然麻木,不能给“我”会意的回答。鲁迅在自我之外寻求人生支撑的努力彻底失败: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全然忘却,多么沉重的回答和打击!鲁迅本已难以自制的心理倾斜再也无法补偿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揪心的孤独,难耐的寂寞,一种朦胧而巨大的绝望之情,这时候又如无法挣脱的大毒蛇层层缠住了鲁迅,使其本来就缺少暖意的心怀顿生冰透骨髓之感: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四面正是肃杀的严冬,凛冽,冰冷,它以其沉重的威压,几乎是残酷地把鲁迅那种急挠挠地试图在现实人生中得到回应、渴求内心的温暖并进而达到自我肯定的愿望揉得粉碎。这是多么惨痛的事实:怀抱着热,内藏着火,然而却被深不可测的巨大冰谷封住、包裹。鲁迅感到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横亘着一种强大异己力量的阻遏,因此陷入苦闷绝望之中,咀嚼着内心所感得的悲哀孤独。其结果是,更深刻的痛心疾首般的对自我奋斗和自我力量的怀疑情绪紧紧攫住了鲁迅:严冬般肃杀的现实正以强大的冷威劈头盖脸地砸向了他,使他极难招架支撑。这又是多么惨然的人生!
可惊异的是,鲁迅并未被这既成的事实所压垮,他仍然怀抱着这热,深藏着这火,仍然怀抱着虽虚幻渺远却韧性如磐的人生信念,勃勃然以源自于灵魂深处的热力驱除心中的寒冷与一切对自我力量的动摇情绪,不仅急切地寻求着一切促使自己站立和充实的外在人生内容,而且艰难地掘发着自我内心的支撑力量,“肉搏”这“严冬的肃杀”。——《风筝》的表层话语并未提供这样的意义。因此,当我这样解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风筝》更隐秘的内涵——第三层心理内涵。陷入“严冬的肃杀”的人,却抱着这样热的、火的追忆,在这样的追忆中的儿时的“故乡”又是这样的使人身心摇荡,一切都指向:诗人究竟在寻找什么?是这样,他试图借助于对已逝的故乡的儿时时光的追忆,唤回久违了的、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感和人生信念,他在暗示:他在追求什么,尤其是他在坚守什么。但也可以转换一个角度追问:“现在”的“我”丢失了什么?这是更令人揪心的一问,它又导向:“我”从哪里来?又怎么了?在《风筝》中,抒情主人公对过去的追忆,也即对人生信念和生命意义的追求和坚守,却因为“他”的忘却而遭到否定,否定的是自我的希望和人生信念,于是“我”彻底地陷入虚无和绝望之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人生,和同样令人绝望的现在的自我状态,激起了鲁迅对童年故乡的追忆,我们发现这一追忆,从一开始便被一种依恋的情感所包裹着,成为“我”意念中的对抗因“严冬的肃杀”而引起的绝望的热流和源泉。然而这是一个“骗局”:儿时和故乡已被“我”疏离,现在它也不能附丽于“我”什么,现实的家园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精神的家园的丧失,意味着“精神的虐杀”。失去家园、回眸家园、寻找家园,是构成《风筝》抒情方式的一个内在张力。“这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体现的正是现代知识者在中国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他们疏离了自己的‘故乡’,却又对自身的归宿感到忧虑。他们与乡土中国的关系可归结为‘在’而不‘属于’”。“在心理和现实的两相映照之下,作家笔下的时间一点点地吞噬人的生命,使蓬勃的青春变得枯萎,而叙述者则在叙述对象的生命流逝中感到自己的生命也慢慢失去了魅力。然而恰恰是在生命的流逝的悲哀中,叙述者不再去追索逝去的生命,再现过去的存在,而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现在性’,从而在虚无的过去与虚无的将来之间,用现实的生命活动 (‘走’)筑成了‘现在’的长堤,从而使自己成为生命和时间的主宰,诞生出‘反抗绝望’的哲学主题”①汪晖:《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 1卷),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版,第 415-416页。。不管怎样,回眸和寻找就意味着意义、抵抗和行动,意味着生命感觉,因而希望和绝望就不再是对立的,在一种特殊的心灵沉思当中它们已经连为一体,并转化为一种真正的人生选择:反抗绝望!——这一切所显现的是一个灵魂的生命活动,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摧折不倒的灵魂,更是一个“活在人间”、充满血与铁的“人之子”的灵魂!
I210.97
A
1003—4145[2011]01—0150—03
2010-11-08
李玉明 (1961-),男,山东省牟平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人之子的绝叫”(课题编号:06FZ W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