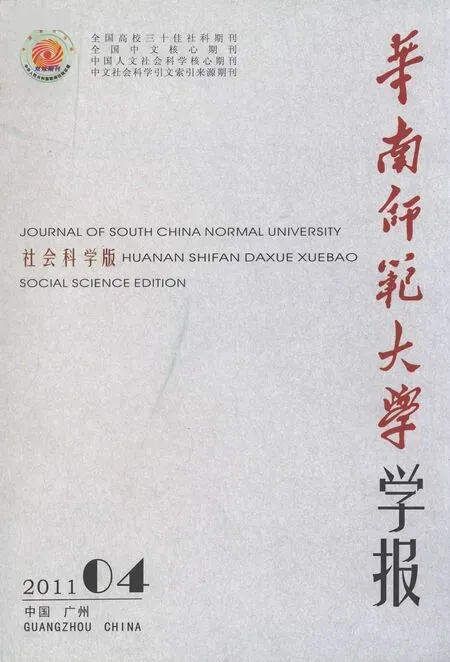现代著作权法公共领域的危机和出路
2011-04-10冯心明丘云卿
冯心明,丘云卿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现代著作权法公共领域的危机和出路
冯心明,丘云卿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公共领域在著作权法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公共领域已处于危机之中。这些危机体现在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非理性延长、数据库对公共领域的冲击、技术保护措施对公共领域的封锁等。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缓解公共领域的危机,包括:重构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采取针对著作权扩张的缓和性立法措施及倡导知识共享的理念。
公共领域 著作权扩张 著作权法全球化 危机 知识共享
一、引 言
著作权法上的公共领域是从著作专有权中剥离出的可以为公众自由利用的部分,它由思想、事实等素材组成,包括著作权保护期满的作品;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作品;实际上无法赋予确定著作权的作品;作者明确表示永久放弃权利的作品以及在法定的合理使用、强制许可情况下,作品的某些方面也处于公共领域。以此推出,公共领域是一个公众得以对其对象进行利用而阻却违法性的制度场域。
长期以来,公共领域被看作是著作权法在界定了著作权人权利之后所留下来的一个无主的自然区域,而不受人们的重视。直到上世纪末美国杜克大学著作权法学者大卫·兰吉(David Lange)才开创性地将研究的注意力投向了公共领域。他首次指出:“近些年来对于公共领域的关注越来越少,而对权利的扩张则持放任态度,以致到了不能容允的程度。”①David Lange.Recognizing the Public Domain.Law and Contemp.Probs.,1981(44):147.该说法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此后,杜克大学成立公共领域研究中心。近几年,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从表面看,公共领域纯属自然领域,法律是不该涉足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从直觉上看,公共领域似乎与公共政策或法律原则相联系”②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3期。,实际上公共领域是充满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要素的。这种法律的规范意义表现在:一方面,公众在公共领域中享有广泛的接触权与使用权,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表现在不得侵害作品的著作人身权以及不可以干涉其他公众对作品的接触和利用;另一方面,作者在公共领域中也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公共领域中,作者依然享有著作权人身权,在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场合,作者也享有除法定的限制外的所有著作权,但作者在享有著作专有权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一定的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通过公共领域分享作品的需求,不能以著作专有权干涉公众对公共领域的合法接触和利用。因此,我们应重新认识公共领域,重视公共领域在保障公众文化权利以及推动社会文化进步中的价值作用,使这个承载了公众重要权益的领域在推动社会文化进步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公共领域危机的表现:全球范围的解析
在社会进步、传播技术发达的今天,理论上公共领域应当比史上任何时期更具繁荣状态,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20世纪晚近以来的著作权法发展,使得著作权不断扩张,以至于公共领域处于学界称之为“第二次圈地运动”③James Boyle.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Law and Contemp.Probs.,2003(66):33-74.的危机之中,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著作权保护期间的非理性延长
保护期限届满是作品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最重要的途径。公共领域危机的最首要体现即是各国立法不断地延长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如美国1790年第一部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保护期限为14年,而1998年的版权期间延长法案(CTEA),对作品的保护期限已延长至作者终身及其死后70年,或自作品首次发行起95年,甚至自创作完成起的120年!①CTEA的签署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不少人斥之违反了宪法第1条第8款。但在2003年的Eldred v.Ashcroft上诉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七票对二票维持原告(主张CTEA违宪)败诉的判决,判定CTEA合宪。参见Eldred v.Ashcroft 537 U.S.2003(186).德国也如此,著作权保护期限历经数次延长至现在的作者终身及其死后70年。中国的著作权立法虽然短暂,但保护期限仍呈扩张之势,从1910年清末的《大清著作权律》规定的著作权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3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死后50年。保护期限的延长使得本应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重新回归于私人领域,从而构成公众的接触与使用障碍,相应也导致公共领域消极缩减。
显而易见,对著作权设定保护期限的最原始动机是给予作者有限期内的专有权,以激励他们持续创作,以促进文化事业的进步。问题是,不断地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是否具有合理性?
答案是否定的。兰德斯和波斯纳这两位美国著名学者提供的数据表明,保护期限的扩张不一定能给作者带来额外的收益,“在1883年至1964年间,尽管当时进行续展的成本相当小,但也只有不到11%的已登记著作权在其28年保护期结束时进行了续展。……1930年在美国出版的10 027册图书中,到2001年只有174册还在印刷——只占1.7%。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著作权迅速贬值了”②[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第271-274、274、272页,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可见,即使在最初保护期为28年的时候,权利届满之时著作权的经济利益已基本消耗殆尽,以至于绝大多数的著作权人都不屑于哪怕花费廉价的续展费用来获得作品的更新保护期限,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并不能给作者带来额外的收益。
作为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两位扛鼎人物,兰德斯和波斯纳对著作权的保护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法经济学分析,他们研究的其中一个结论,则充分说明了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非理性:在作品上的增量性激励在该期限超过25年左右就可能变得非常小,即使给予著作权以永久性保护,其产生的现值与25年著作权的现值相差只有2.5%!④[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第271-274、274、272页,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正如兰德斯和波斯纳所指出的,任何对著作权保护的扩大都将使公共领域的数量减少。⑤[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第271-274、274、272页,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保护期届满的作品是公共领域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著作权保护期限非理性并不断地延长,严重延缓了作品进入公共领域的时间,使得许多公众无法在有生之年等到作品进入公共领域,导致了公共领域萎缩——公众的接触权与使用权的客体减少。
(二)数据库对公共领域的“蚕食”
据WIPO统计,目前全世界至少有130多个国家为数据库提供著作权保护,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四条也将数据纳入“汇编作品”类型给予保护。根据汇编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特点,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与数据库内部所收录的数据并非同一。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根据“额头滴汗”的原则,数据库制作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数据采集和收集,应给予法律保护。但笔者认为对数据库给予版权保护将对公共领域造成重大影响。
首先,数据库圈存了公共领域的大量要素。以单纯信息、新闻或者法规等公共领域素材为收集对象的数据库,其库内元素本身乃属于不受著作权保护之客体,公众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些材料被数据库所收编后,通常被私人“包围”起来——由于数据库本身的著作权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公众不得对数据库的内容进行自由利用,这无异于在事实上导致了本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材料受到了著作权的控制(虽然此时这些材料本身依然没有著作权)。
其次,对于数据库内的著作权作品,数据库著作权的存在给社会公众对这些作品行使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造成了障碍。对于著作权作品,公众要对其进行公共领域上的合理利用与法定许可之时,并不用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当然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支付报酬),但著作权作品一旦进入数据库,受数据库著作权的影响,公众在对其合理使用之时遭到了阻拦,或者出于合理使用的目的使用作品而被迫支付不合理的费用。
最后,数据库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有可能在事实上进一步延长了作品归入公共领域的期限,即对于数据库中属于公共领域的作品,数据库著作权的存在,无异于在一个公共的宝藏外围修建围墙,然后告诉公众:这些宝藏是大家共同所有的,但是这堵围墙是我的——公众只能望宝兴叹。
(三)技术保护措施对公共领域的“封锁”
一般而言,技术保护措施是指著作权利人为控制其作品可否被接触、复制、使用或传播,而以有效的科技方法所采取之保护措施。技术保护措施是20世纪晚近应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成为保障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著作权法新内容,发端于美国、欧盟,后被规定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随着WCT的生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技术保护措施写入著作权法。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确立了著作权人可对作品实施技术措施。在本文看来,出于保障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技术措施已经明显地超出了公共领域容忍的限度。
技术保护措施的存在,实质上已经极大地加强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有效地阻挡了公众对作品的接触,导致公众难以对作品进行公共领域意义上的使用。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曾指出:“技术的设计可以使一个文件剪贴到另一个文件成为不可能。”①Lawrence Lessig.Law Regulating Code Regulating Law.LOY.U.CHI.L.J.,2003(35):7.刘铁光博士进一步论述道:“技术保护措施使作品完全被权利人包裹起来,这使合理使用保护公众创作自由的功能大受限制”,“不仅如此,出版商可以将已经属于公共领域的作品通过技术保护措施锁上,在公共财产周围安上归私人所有的技术措施‘栅栏’”。②刘铁光:《著作权正当性的危机与出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公众一旦避开技术保护措施,就极有可能被斥之为侵权,公众的心理被笼罩在“寒蝉效应”阴影之下,从而使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的实现遭遇了严重的阻碍。因而,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是公共领域的重要规范内容。
三、公共领域危机的出路:中国的可能性选择
造成公共领域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大陆法系自然权利论的影响。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文直译就是“作者权”,著作权立法以作者权利为中心。我国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也不例外,实质上也偏向于以保护作者的权利为中心,作者的权利被狂热地无限放大,而公众的利益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所谓的权利保护期限以及公共领域成为了令人憎恨的枷锁,这是导致公共领域危机的内因;二是在著作权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际利益集团意图通过著作权扩张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大量的利益,由此产生的公共领域的萎缩危机也被推向了世界,这是导致公共领域危机的外因。
在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公共领域的危机已在全球蔓延。但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公共领域的危机是不现实的,本文主要立足于中国,探讨在公共领域危机语境下的我国著作权立法问题及其相关措施,试图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寻求避免国内公共领域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对策。
(一)重构我国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可否认,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在形式上考虑了作者和公众的利益,但实质上我国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在实际立法的权利设置中还是偏向于作者的权利保护(体现为不断扩张著作权的立法),而不是这里所说的“着眼于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正如有位学者在分析知识产权扩张原因时指出的:“《著作权法》着眼于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其宗旨均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认为,“功利论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的立法中具有主导地位,影响力极其广泛”③饶明辉:《当代西方知识产权理论的哲学反思》,第20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事实似乎可以印证上述判断。为了加入WTO,我国迅速修改《著作权法》以符合TRIPS协议要求。④参见2000年12月22日在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国家新闻出版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石宗源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而学术界的表现则提供了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专家学者们的论调都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如何加强作者权利的保护上。①饶明辉博士曾指出:“倘若搜索有关知识产权的中国文献,保护知识产权的主题文献就可能占据了绝大多数。可以说,知识产权的不断强化与扩张,至少部分地归功于学界的倡导。”参见饶明辉:《当代西方知识产权理论的哲学反思》,第213页。笔者就此在中国期刊网进行搜索,结果恰如饶博士所言。当然,专家学者们经常扮演的角色就是作者,而对于著作权的公共领域关注甚少,甚至对于著作权法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言之甚少,使得公共领域的命运堪忧。要解决公共领域危机,应以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理论对著作权法价值取向进行重构,以协调作者权利和公共领域的紧张关系。
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规划理论是晚近西方学界对于知识产权正当性论证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②关于社会规划理论源流,参见饶明辉:《当代西方知识产权理论的哲学反思》,第90-104页。其核心关注点是:我们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法来实现一个怎样的社会?哈佛大学费歇尔教授在知识产权社会规划理论中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知识文化蓝图:知识产权法规则能够在鼓励创造和鼓励传播、使用之间保持最佳平衡以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信息和思想丰富,公民能获得广泛的信息、思想和娱乐形式的文化;具有丰富的艺术传统;符合分配正义,所有人都有权获得信息和艺术资源;人们尊重他人的作品……③[美]威廉·费歇尔:《知识产权的理论》,黄海峰译,见刘春田:《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第34-3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社会规划论融合了人类社会进步和合理的思想,勾画出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作者的创作激情得到了足够的激励,作品的传播和使用也得到鼓励,思想文化素材异常丰富,公众能广泛获取思想文化和艺术。一言蔽之,社会规划论着眼于构建著作权与公共领域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据此,笔者主张,我国著作权法在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应以此为主导价值取向,在立法与司法中要协调著作权保护和公共领域公众接触和利用权的关系,即要保护作者的专有权,也要注意创造一个具有人类文化丰富遗产的公共领域。
第一,修改《著作权法》第一条,将其修改为:“根据宪法,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依本法受到保护”。调整后的条文在内容上实质与原文不变,只是在语序上进行了调整,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放在首句,因其内涵包含有丰富和繁荣公共领域之意,凸显重要地位,而将保护作者权利放在最后,避免了著作权法原第一条以作者权利保护为首要任务的误读。对《著作权法》第一条的调整有助于引导学界和社会公众对著作权法立法目的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扼制学界不断鼓吹著作权扩张的趋势,也有助于唤醒公众的公共领域权利意识。另外,《著作权法》第一条作如此调整并不会与我国所加入的任何著作权国际条约产生任何冲突,因而是可行的。
第二,将“公共领域”写入著作权法。在《著作权法》第三节“权利的保护期”下增设一条:“著作权保护期满,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任何人可以自由利用,但本法另有规定除外。”虽然《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已对权利的保护期限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并且对于作品创作完50年未发表的明确表示“本法不再保护”,事实上在权利期限届满时作品已进入公共领域,增设此条似乎会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是,考虑到法律不仅仅有规范功能,还有教育功能,将“公共领域”写入《著作权法》,虽在规范功能上没有增益,但是对指引学界研究和民间了解公共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唤醒公众的权利意识,以及增强公共领域的话语力量,对实现著作权法价值取向的良好愿景大有裨益。此外,在著作权法中设立类似条文其他地区已有先例。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43条即规定:著作财产权消灭之著作,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而实质上,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本身最初制定于大陆,且两岸同根,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完全可以借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条但书所指“本法另有规定除外”,主要是指《著作权法》第二十条关于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也不得侵害。
(二)采取针对著作权扩张的缓和性立法措施
在著作权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可能置国际公约于不顾,一意孤行地缩短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并限制著作权的客体与内容的扩张。要正面消除著作权扩张带来的公共领域危机是极其困难的。一条可能的途径是,从扩大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范围的角度入手,通过扩大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权利来达到缓和著作权扩张带来的危机,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应采取如下的立法措施。
第一,设立合理使用一般条款。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以有限列举的方式列举了12种合理使用的情形,而且没有设置兜底条款。对于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而言,有限的合理使用方式已不能丰富和繁荣公共领域的需要。因此应当改变我国对合理使用进行有限列举的立法方式,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以“具体列举加一般条款”的方式对合理使用进行规定。
具体可作以下修改:一是在《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列举中增加一项:“(十三)属于合理使用的其他情形”。此举目的是使合理制度的情形从封闭走向开放,为更多合理使用情形设置对应的规范依据。二是在二十二条下增设一款:“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当考虑如下因素:(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这种使用是否为商业性质或者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2)被使用作品的性质;(3)所使用的内容占整个作品质与量上的比重;(4)这种使用对该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合理使用的四个因素的具体判定判准,应以不得损害作者的著作财产权且不得妨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为指导性原则。
对合理使用条款的上述修增,主要参考了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例,也未超出国际公约所赋予的自由度——伯尔尼公约与TRIPS协议以及WCT对合理使用(即权利的限制与例外,包括法定许可)的一般规范。伯尔尼公约第九条①伯尔尼公约第九条:本联盟成员国法律有权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致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危害作者的合作利益。、TRIPS协议第十三条②TRIPS协议第十三条:各成员对专有权作出的任何限制或例外规定仅限于某些特殊情况,且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得无理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WCT第十条(含关于第十条的议定声明)③WCT第十条:(1)缔约各方在某些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作者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在其国内立法中对依本条约授予文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规定限制或例外。不言而喻,第十条的规定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中依《伯尔尼公约》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同样,这些规定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均承认各国在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至于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作出权利限制的例外规定。而且,这样的修增在我国著作权法体系内部也不会造成任何的规范冲突,公众又可以在著作权急速扩张的情况下获得对著作权作品更多方式的接触与使用,在公共领域消极缩减的情况下,可以一定程度缓解著作权对公众在利用作品上的束缚。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对合理使用做广义解释,这样就有助于在无限的续展的制度之下保持一个足够丰富的公共领域。”④[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第278页。
第二,新增网络转载摘编法定许可。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与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的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并未包括网络刊登与转载、摘编的情形,且《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至第九条也未将网络发表后的转载与摘编列为合理使用,故实际上在网上的转载行为都涉嫌侵权,这样实际上限制了作品和信息的传播,有损于公共领域,不利于网络时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有鉴于此,应当扩大法定许可的范围,建议在《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增加一款:“首次发表于网络的作品,网站可以转载、摘编,但应注明出处,并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但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除外”。本款的设置,将为网络上的转载与摘编扫除法律障碍,极大丰富公共领域的公众可接触的作品数量,与著作权法原有条文相协调,与国际条约也没有冲突。
第三,合理限制技术保护措施。前文已指出,技术保护措施的存在,将在事实上使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变得困难,使得公共领域公众的接触权与使用权难以实现。为了维护公众合法使用和接触作品的权利,在著作权人与公众的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对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进行合理限制是有必要的。故笔者主张,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⑤《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的但书修改为:“但是,属于本条例及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情形除外,但使用人对此负举证责任;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另有特别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即公众在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情形下,可以避开技术保护措施。这种避开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但为了防止公众滥用此豁免行为,一旦发生涉及故意避开或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的诉讼,行为人即需对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负举证责任。此规定可以较恰当地平衡著作权人与公众的利益。
第四,缓解数据库保护对公共领域的冲击。由于数据库对作品的“内容的选取和编排”是一项具有高度商业性,以及需要强大信息技术的支撑的活动,因此决定了它的权利人不会轻易地免费授权给公众使用。而公众如果出于对数据库内部作品合理使用的目的进入数据库获取该作品,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数据库的著作权客体“内容的选取或编排”进行使用。这种使用很难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所以数据库的保护与公共领域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关系。
为了解决该矛盾,笔者建议,在进行著作权法修改涉及有关数据库立法条文时,可规定一条:“数据库内部数据或作品保护期届满后,公众可以自由获取并利用,数据库权利人不得对此进行妨碍”。设立此条可以和前文所述的“著作权保护期满,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任何人可以自由利用,但是本法以及其他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相呼应,共同保障公众在公共领域的权利,以免保护期届满的作品被数据库权利人实际上控制而不能进入公共领域。此条文符合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也可以缓解数据库保护对公共领域的冲击。
(三)倡导知识共享的理念
缓解公共领域危机的另一种重要的途径是倡导作者建立知识共享的理念,向公共领域释放全部或部分权利。
知识共享发端于美国,源于美国国内民众对国会通过CETA延长版权保护期限的不满。知识共享是通过设计一套简明的著作权许可条款及其组合许可协议(简称CC许可协议)①由于各国著作权法具体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故CC协议在不同国家需要根据本国法律进行本地化方能适用于该地区。,免费提供给公众使用,鼓励著作权人在某些条件下自愿选择某种许可协议,与他人分享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或者进一步将作品奉献给公共领域,由此促进文化传播,营造公众得以特定方式自由使用作品的公共领域空间,同时又可以保护作者的作品、不至于侵害著作权人的权利。在著作权日益扩张并且“所有权利保留”(all rights reserved)的情况下,通过鼓励作者“保留部分权利”(some rights reserved)的方式向公众释放权利,乃至宣布放弃作品的任何权利,以挽救公共领域于危机之中。这种知识共享的理念现正被引入中国。在“著作权丛林”日益膨胀的今天,知识共享营造了一个人为的公共领域空间,为解决公共领域危机提供了重要途径。
四、结 语
我国自1990年制定《著作权法》之时就已经有意识地考虑与世界接轨,体现为其规范内容基本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随着加入WTO,我国于2001年根据TRIPS协议的要求修改了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系列知识产权法,“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程”。②曹新明、梁志文:《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三十年(1978-2008)》,2010-06-01,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网,http://www.rucipr.com/ArticleView.aspx?id=844。所以我国在著作权法诞生之时就隐含了先天的公共领域危机基因。
从公共领域的危机角度审视我国的著作权立法,可以发现,我国对著作权保护的标准已经极高。西方国家通过系列国际公约与协议,将其国内已经遭致严重侵害公共领域批评的著作权扩张运动推向了全球,我国也被卷入其中。对于著作权法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公共领域危机,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在对著作权法进行必要的修改时,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我国的著作权保护标准不能盲目追随西方国家的超高标准保护,而是要在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保护的标准,以缓和著作权扩张所带来的对公共领域的冲击。
冯心明(1956—),女,海南海口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1-03-17
DF523.1
A
1000-5455(2011)04-0094-06
【责任编辑:于尚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