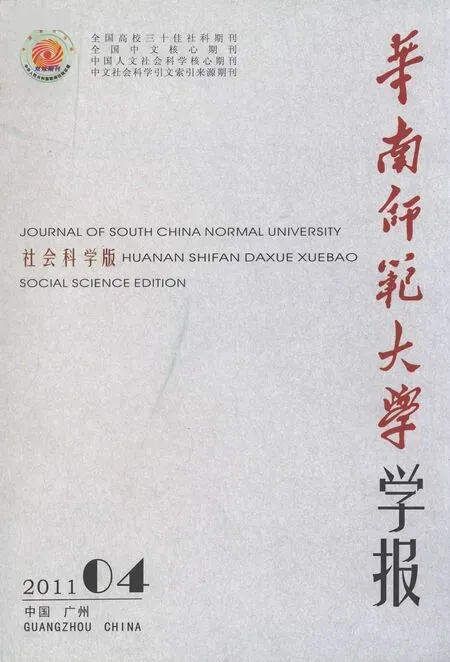多维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2011-04-10谢放
谢放
(华南师范大学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多维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谢放
(华南师范大学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应该以多维的视野来研究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进程、结局和影响,总结其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 立宪运动 清末新政
武昌起义后不久即问世的苏生《中国革命史》(辛亥九月出版)可以说是关于辛亥革命史的最早著述,而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辛亥革命始末记》则是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的史书。所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不可否认,辛亥革命史长期以来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作为研究主线。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并给予了新的审视和评价;但正如朱育和教授所指出,由于受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较大影响,仍然形成了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①朱育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如果从多维视野来审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实际上应该包括三个“运动”,即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立宪派发动的立宪运动和清政府推行的新政。②最近出版的张海鹏、李细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论述1901-1912这段历史时,虽然总的叙述框架还受以往的辛亥革命史体例的影响,但是已经开始用较多的篇幅来关注和研究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后两者之所以长期以来不被列入革命的范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革命的理解比较狭义,认为只有流血的武装斗争才算是革命。其实,1902年梁启超发表《释革》一文,就对革命的涵义作了较恰当的阐释,认为革命的涵义有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话语中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指以武力推翻前朝的改朝换代,“皆指王朝易姓而言”;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则包含英语的reform和revolution之义,前者如1832年的英国国会改革运动,后者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③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68-3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从革命的“内容”而不仅从“形式”来讲,只要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都可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清末立宪运动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清末新政就推行者的主观愿望来说,自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但其客观效果却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出现和成长,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发生变革作了铺垫和积累。
一、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原动力
辛亥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长期坚持不懈的结果,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和民主革命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于1895年发动了广州起义,1900年又发动了惠州起义。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国人对革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孙中山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而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①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郊区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军事学校,训练革命军事骨干,让学生入学时填写的盟书首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1904年4月26日在上海发行的《警钟日报》通过发表孙中山的一封信,首次在国内公开介绍了十六字誓词,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可以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此时,孙中山作为革命运动领袖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日益倾向革命的仁人志士的认同。章士钊在1903年译述《孙逸仙》一书(原为日人宫崎寅藏记载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三十三年之梦》)的序言中说:“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②黄中黄(章士钊):《孙逸仙》,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1册,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04年4月20日《警钟日报》也指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民主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作为政纲,其机关报《民报》发刊词将这一政纲明确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政纲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相结合,表明不仅要推翻清朝政府,还要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孙中山还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念,“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以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英雄革命”,并宣布:“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③孙中山:《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具有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离不开革命思想的广泛宣传。1903年发生的“拒俄运动”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的转折点,这一年出现了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高潮。据统计,1903年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夕,革命党人创办或主持的报纸有12种,期刊有20种,影响大的革命书籍有19种。④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册,第192-19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出现了三位最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及其代表作,即邹容及其《革命军》、陈天华及其《警世钟》和《猛回头》、章太炎及其《驳康有为论及革命书》。尤以《革命军》影响最大,发行逾百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第一位。《革命军》庄严宣布:“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明确提出效法美国建立“中华共和国”,高呼“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将武装斗争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手段。同盟会成立之后至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十多次著名的武装起义,即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复会浙皖起义,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反映了革命党人具有脱离民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后人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但革命党人为了救国救民,不顾自身力量的弱小,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清起义,希望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继续抗争,这又是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革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气节和献身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垂千古。黄花岗烈士方声洞在起义前夕给父亲的绝命书中写道:“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死,亦义所应尔也。”林觉民奔赴前线时,给爱妻陈意映留下绝笔书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⑤方声洞《赴义前别父书》与林觉民《与妻书》皆见萧平:《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第167-168,17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喻培伦就义前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⑥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革命志士为祖国的独立和民主、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为主义的彰显和实现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成为了推动反清革命继续进行的巨大动力!正如孙中山评价黄花岗起义的重大意义所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页。
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除了湖北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聚集点这一重要客观因素外,更是与革命党人在新军和学生中长期坚持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分不开的。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着重在学界和军界发展革命力量而不轻易发难;二是革命团体屡受摧残而不垮,革命活动屡遭镇压而不息。从1904年成立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到1906年成立日知会,再到起义前夕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武汉地区先后出现约三十个革命团体。而自孙中山于1906年4月派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湖北发展同盟会员之后,武汉革命党人在组织上便与同盟会发生了联系,在政治上接受了孙中山的领导。正是由于长期深入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因官方的搜捕或牺牲或出走的危急关头,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仍然按原订计划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虽然远在欧美从事筹款和外交活动,但国内舆论视他为新生共和国的元首。武昌起义后第四天(10月14日)《纽约时报》刊载芝加哥13日来电称:“孙博士是大清国革命党的领袖,并且,如果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他即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②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39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1911年10月31日,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安抚人心,在其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上,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③陈旭麓、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第541-5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虽然因欧美列强为维护其在华权益而属意袁世凯,使孙中山的外交努力成效有限,但革命党人仍对孙中山欧美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1911年12月20日《民立报》发表马君武所撰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指出:“国人日望孙文之归”,“外人之敬重孙君,非为具为革命党首领之故也,以为有孙君之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而复可以为革命党首领。孙君今日之受欧美人崇拜,以视意大利之加利波的(按:今译加里波第,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匈牙利之噶苏特(按:今译科苏特,19世纪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有过之无不及”。孙中山一回国即被选举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这不仅反映了南方独立各省代表的共同意愿,也是历史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充分肯定。
二、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的助推手
长期以来,学术界十分强调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政治分野和对立。当年的革命派和立宪派也同样如此表述。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就宣布“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232页。梁启超也曾声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同盟会成立后,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所进行的大论战,更使这种政治对立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报》第三号以“号外”的形式发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论纲》,列举出双方有重大原则分歧的12个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报》是站在国民的立场,以政府恶劣,主张国民革命以实现共和立宪;《新民丛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以国民恶劣,主张政府实行开明专制。论战涉及的问题虽然广泛,但双方都一致承认“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所以论战归根结底的问题,是选择暴力革命还是渐进改革的途径来救亡图存,以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平心而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虽然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两条道路之争,并在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但是,不论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还是采取激进的革命,其最终达到的目标,都是要仿效欧美或日本在中国建立近代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在建立民主政治、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双方虽有异见亦有共识。或许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一种深切关注,都是对如何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一种真诚探索,也都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选择。武昌起义的爆发,证明了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但在起义爆发之前,这场论战却为人们提供了选择救国道路的思维空间,尤其为选择革命道路作了有力铺垫。而不同的政治派别的思想论战之所以能够发生,不同的政治理念之所以能够交锋,恰恰又是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普及,而且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也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
其实,立宪派与革命派并非一开始即处于对立地位。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2,6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并一度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谋求与兴中会合作,计划共同组织革命团体。②冯自 由:《革 命逸史 》,初集 ,第72,64页,中 华书局1981年版。1900年康有为、唐才常等人策划的自立军起义也是改良派以武力开辟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1902年具有强烈反满倾向的梁启超写下了《拟讨专制政体檄文》,宣称:“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③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0,369-370页。并发表《释革》一文,鼓吹革命为“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理”,“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④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0,369-370页。,大力提倡“破坏主义”,呼吁“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⑤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244页。。梁启超作为20世纪初“言论界之骄子”所进行的启蒙宣传,在《新民说》长文中提出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新民”即“人的现代化”的命题更是影响深远。当年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曾称梁氏“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当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和文字的洗礼”⑥郭沫若:《我的童年》,见《沫若文集》,第6卷,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梁启超的民主观念和革命主张实际上成为了20世纪初不少仁人志士倾心民主、走向革命的思想资源,邹容的《革命军》便借鉴和汲取了梁启超的这些思想。
立宪派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希望清政府通过实行君主立宪来避免和阻止革命的发生,但立宪运动的客观效果却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可以说立宪运动成为瓦解清政府统治基础的另一条战线,或者说成为了革命运动的助推手。1910年立宪派连续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所动员的各阶层人士十分广泛而影响深远。参与国会请愿的社会群体涉及绅商学警报军各界人士以及八旗士民和海外华侨,参与人数之众多,请愿声势之浩大,皆前所未有。仅据直隶留下的不完整的请愿签名册统计,即包括该省72州县绅民25 051人。至10月中旬,仅奉天一省即有二十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请愿签名者多达三十余万人。⑦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84,311、469 -470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革命党人创办的《神州日报》、《民立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对国会请愿运动“为民请命”的行动给予声援和支持。⑧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84,311、469 -470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与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相呼应,由云贵总督李经羲主笔拟稿,会同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十八省督抚、将军、都统联衔电奏朝廷,吁请“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明年开设国会”⑨《各省督抚合词请设内阁国会奏稿》,载《国风报》第1年(1910年)第26期。,也壮大了立宪运动的声势。而清政府对立宪运动的横加压制,终于导致原来倾向于改良的人们相继转向了革命。据《铁庵笔记》记载,国会请愿者“相率痛哭流涕,斫腕沥血,上书请愿早开国会,以定邦基”;清政府则“漫然拒绝,甚至饬步军衙门驱逐请愿诸代表,遂使天下志士灰心疾首,一瞑不顾,势迫形驱,相率入于革命”⑩转引自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475页。。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也是由立宪运动转向革命运动的典型事件。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商办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转让给四国银行团。在立宪派的领导下,掀起了波及全川的保路运动。立宪派无情揭露了清政府破坏宪政的行径,指责清政府“借款收路”,“为宪政前途的根本上之破坏”⑪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2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号召民众奋起“抗官”以争取“立宪国民的自由权”⑫《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停办捐输歌》,见四川省档案馆:《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171-17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版。,实际上是为推翻清政府制造了舆论。同盟会员则因势利导,“组织民军,共同革命”⑬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见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380页。。以9月7日川督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制造“成都血案”为转折点,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最终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的催化剂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的新政,在某种意义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和扩大。维新运动虽然被慈禧太后所镇压,但镇压者依旧成了被镇压者遗嘱的执行者。于是有了清末十年所推行的新政,其改革举措远比戊戌变法范围广泛而更有力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政”的尝试。在政治制度层面,从改革官制到彷行宪政;在司法制度层面,从革除一些酷刑到试图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经济制度层面,从奖励农工商业到试图确立近代产权制度;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式陆军到确立近代军制;在文教制度层面,从设立学堂、改革科举到停废科举、建立近代学制。就广义的涵义而言,清末新政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革命。研究新政的美国学者任达即直接称之为“新政革命”(The Xinzheng Revolution),并认为:“晚清革命本身便足以使人惊叹不已。那已经发生的转变,无论在速度、范围和持久性方面,在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①[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219页,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的评价可能过高。新政的不少“成就”或停留于章程条文,或局限于有始无终。正如1909年御史赵炳麟所指出:“恐纸片上之政治与事实上政治全不相符,从纸片上观之,则百废具举,从事实上核之,则百举具废。”②赵炳麟:《请确定行政经费疏》,见《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卷6,第3,4页,民国11年全州赵氏印。可见新政的实际成效,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新政的推行至少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结果:一是新兴社会群体(绅商学军)的出现和队伍壮大,二是北洋集团的崛起和势力膨胀。
新政固然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但不能忽视新兴社会群体所做的种种努力,其昭示的前景,正是力图使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摆脱政治的强行干预而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新兴社会群体所争取的最主要权利,就是财产权和参政权。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商业法规和奖励实业章程。这些法规的颁布对于促进工商业法人社团的兴起、维护商人的权利、提高商人的地位都起了积极作用。1907年预备立宪公会发起参与制订商法的活动,提出新兴商人要求财产权的强烈诉求,“我商人之在国内者,顾无一定之法律足以保其财产之安全,不可谓非吾国民之大耻矣”,呼吁“以本国之惯习,参各国之法典,成一中国商法”,以保护商人的利益。③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8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为新兴社会群体争取参政权的活动提供了合法阵地;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和1910年资政院开议,都表明新兴社会群体的参政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新政的推行也造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崛起和势力膨胀,也可以说北洋集团是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新政最重要的举措是练兵筹饷,至1911年,编成的新军共14镇,18个混成协,总兵力约十五六万人,而拥有最精良装备的北洋六镇即有7万余人,这成为袁世凯日后攫取革命果实的最大政治资本。
新政的推行还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积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举办新政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这对于背负着巨额赔款和外债的清政府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1910年清政府试编下一年财政预算,支出达33 865万两,收入仅29 696万两,赤字4 169万两,加上地方赤字共7 939万两。④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第4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版。于是,滥铸铜元、苛征捐税便成为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从1904年至1908年,全国所铸铜元已达120亿枚以上;至1910年,国内流通的铜元多达140亿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904年每一银元换铜元88枚,而1909年末则换180枚。“盖视四年前之价不及其半,几于与所含铜价相接近。政府虽欲更藉以牟利,而亦有所不能矣。”⑤沧江:《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载《国风报》第1年(1910年)第5期。沉重的捐税导致民生的凋敝,“近年度支所入,岁逾一万万两,练兵之经费,新政之诛求,铜圆之损失,何一非取给于民,八口之家,不聊其生者,比比皆是”⑥赵炳麟:《请确定行政经费疏》,见《赵柏岩集·谏院奏事录》卷6,第3,4页,民国11年全州赵氏印。。连慈禧太后的懿旨也不得不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深宫惓怀民瘼,常切疚心。闻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吾民有限之脂膏,岂能堪此剥削?”⑦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25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清朝官吏的贪污腐败也十分惊人。洞悉官场内幕的辜鸿铭当时即指出:“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⑧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官官商商》,见黄兴涛:《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31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结果清末十年间各地民怨沸腾而民变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城乡民变1905年为103次,1906年为199次,1907年为188次,1908年为112次,1909年149次,1910年266次。①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第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其中以莱阳抗捐民变和长沙抢米风潮规模最大。是年8月5日出版的《国风报》第18期所刊《论莱阳民变事》评论说:“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火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新政的推行不但没有缓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反而成了革命的催化剂。
当立宪派一再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督抚纷纷奏请成立责任内阁之际,清政府却对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横加压制,又欲以中央集权的名义削夺督抚之权。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笼,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来面目,将原来拥戴清政府的立宪派和汉族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武昌起义能够及时得到各省响应,清王朝的统治能够迅速分崩离析,与立宪派和汉族官僚纷纷转向革命不无关系。一方面,因军制和教育改革所产生的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军和学生、因社会矛盾激化而积聚的会党和民众、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对清政府极度失望的官绅商民,实际上都成为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另一方面,因推行新政而权势膨胀的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则又成为独裁政治的继承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似乎都表明:这场革命正是革命、立宪和新政的“合力”所孕育和造成的。
四、结语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modernity)带来稳定,现代化(modernize)引起动乱。”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4页,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清王朝不能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革命的发生便成为了必然。而革命的发生从来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果仅仅以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主线来研究辛亥革命史,必然妨碍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因素来揭示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进程、结局和影响以及总结这场革命的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
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史在继续深入研究革命运动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强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研究,尤其应该深入探讨三者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影响。过多地强调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改良”性质和责难革命的“破坏”作用,都不利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辛亥革命既然已经发生,历史便不可能假设。研究者不宜仅仅申述自己的“后见之明”,而是需要深入探讨这场革命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特殊的、深层的各种因素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和深远影响,以有利于更好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谢放(1950—),男,四川成都人,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09JDXM77002)
2011-05-25
K257
A
1000-5455(2011)04-0068-06
【责任编辑: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