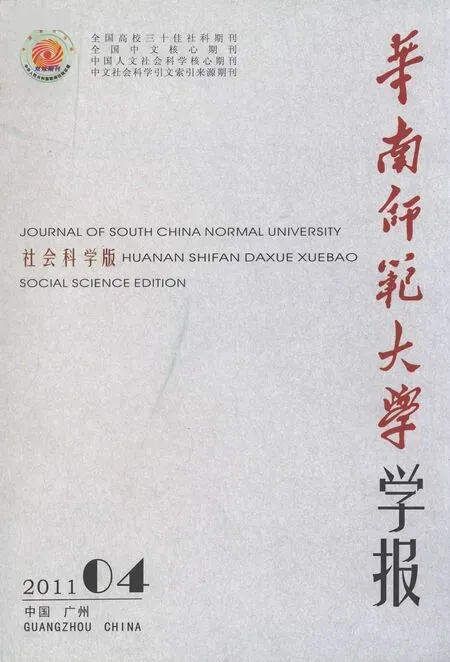世纪回望:辛亥百年遗产解析
2011-04-10汪炜伟
侯 杰,汪炜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世纪回望:辛亥百年遗产解析
侯 杰,汪炜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20世纪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辛亥革命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通过对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宋教仁、赵凤昌等人的思想、言论、遗言、遗电、书札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结合对他们实践层面上的考察,不难发现“和平统一,利国福民”堪称其孜孜以求的革命志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愿望,是爱国襟怀的抒发和理想、愿望的表达,可谓这场革命的重要遗产之一。百年之后,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机遇下,对于该遗产的整理与阐发,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而且有益于发现其现代意义,可视为中国人百年理想实现的关键所在。
和平统一 利国福民 辛亥革命 遗产
一
以“辛亥”命名的这场“革命”,其目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影响,曾引发海内外学者的诸多深入思考,并且发表过很多高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历史新转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刻,重新认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既要充分肯定其打破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中华民国等历史功绩,同时更要进一步探讨这场“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革命者们如何在“革命救国”的理想与现实中进行思考、抉择等问题。
1925年3月11日夜,处于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已不能有系统的发言,仅以英语或粤语”断断续续地向守护在病榻旁的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何香凝、李烈钧、于右任、林森等亲友、同志们说了七个字:“和平、奋斗、救中国”。①《中山饰终典礼之昨闻》,载《大公报》,1925-03-15。孙中山临终前所奋力说出的这几个字,不仅是他一生追求的自我言说,也是他对辛亥革命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度概括。对此,近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梁启超给予高度关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汪精卫说:“此数语实抵中山一部之著作,足予全国人民一极深之印象。”②《中山饰终典礼之昨闻》,载《大公报》,1925-03-15。显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最后绝唱,梁启超既看到这是孙中山用生命写就的革命箴言,也意识到它对国人认识和了解辛亥革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代学者曾经提出,对孙中山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应该百倍珍视,并牢牢记取。这句话虽然是孙中山的遗言,但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致力于振兴中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力量源泉。总之,今天我们致力于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也是孙中山未竟事业的继续和发展。③葛培林:《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晚年北上纪实》,见《中山文史》,总第32辑,第329页,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4年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28年6月3日深夜,曾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被时人与孙中山、黄兴并称为“首义三杰”的黎元洪逝世,其遗嘱以通电的方式公开发表。④侯杰、姜海龙:《百年家族黎元洪》,第2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这封长达千言的遗电中,黎元洪对自己投身革命以来的经历进行了总结。他明确提出:“首义之初,主张罢战言和,军民分治,驯致裁兵废督,身为之倡。一切措施,虽不能尽满人意,要无非力求和平统一,利国福民。”⑤沈云龙:《黎元洪评传》,第18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版。这不仅是黎元洪对自己革命实践的谦逊剖白,而且揭示出这位辛亥首义元勋所不懈追求的主要目标及其核心内涵——和平统一,利国福民。
遗言、遗嘱、遗电,往往是历史人物在生命最后时刻对某些自己牵挂于心、不能释怀之事的一种特殊表达。虽然不能排除某些历史人物,在生死面前怀有某种祈求别人理解、掩盖历史真相的想法,或有不惜颠倒是非,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做法;也不能无视人们在阅读、体味这些遗言、遗嘱、遗电时,存在某种宽容、谅解的心理,并进而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评判。但是问题在于,孙中山、黎元洪等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所言显然并非为澄清某些具体事实,而是着眼于革命襟怀的抒发和理想的表达,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考诸史实,“和平统一,利国福民”思想也并非仅在这些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的遗嘱、遗电得到阐述,而是弥散于他们各种公开或未公开文献,贯穿于他们各种思想言论中,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他们对辛亥革命之目的的基本概括。他们一方面以和平方式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追求;另一方面以服务国家和造福人民作为革命的主要目的。
二
众所周知,自清末以来,兵端一起,战祸频临,直至今日中华民族都未实现完全意义的统一。毋庸置疑,统一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之一。当然,由于时势不同,中国的统一议题在每个时期也存在差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统一议题基本上围绕着南北问题展开。尽管暴力的战争,一直是辛亥革命的基本面相,但不应忽视,革命激情之下的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求与为实现和平统一所付出的努力。
实现统一是孙中山一生的追求。他曾从历史角度展开分析:中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3、37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统一是中国的历史大趋势。面对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存在的割裂状态,孙中山多次深刻阐明这样的道理:“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3、37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国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的,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尽管在其一生中,孙中山多次发起革命,以武力推翻帝制、捍卫共和,但终未放弃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内统一之夙愿,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他尝言:“予素来主张中国南北和平统一”,“愿尽力于和平统一之事”④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16、4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平一直为孙中山实现国家统一的首要选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革命暴力之后,更重要的是“于内”造就“统一之机关”,“于外”形成“对待之主体”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3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而其让位于袁世凯,便是此良苦用心之表现。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孙中山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暴力并非中国的最佳选择,不流血的革命更是此时迫切之需。因此,他并不反对南北议和。1912年1月2日,在回复袁世凯的电文中,孙中山表明自己的态度:“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如果袁世凯能使中国“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将总统之位让予他,也“自是公论”。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3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后在致社会各界人士的电文中,他多次强调必须坚持这一原则。1912年1月23日,在给南北议和会议南方代表伍廷芳的通电中,孙中山更直言不讳地指出:“盖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3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即使是1913年宋教仁案真相大白之后,孙中山仍在《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中明确表示,其让位袁世凯乃是以维护国内和平为初衷,“余自共和告成以来,竭力从事于调和意见,维持安宁,故推袁世凯为总统,原冀全国从此统一,人民得早享安居乐业之幸福耳。”为此,他殚精竭虑于弥合社会各界人士的不同政见,以期建立一个“能维持全国治安”的“善良政府”。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1912年5月2日,孙中山在致其师英人康德黎的电文中,向英国政府、议会及欧洲各国政府宣称:“自民国诞生之日起”,他“便致力于谋求和平、和谐和繁荣”,之所以推举袁世凯出任总统,也是因为“似乎有理由相信,国家的统一、和平与繁荣时代的黎明,或将由此而加速。”因此,“从那时以来,我已尽我之力所能及,促使革命所造成的混乱演化为和平与秩序”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 58、91、333、377 -378页。。故而,孙中山退位于袁世凯,不能仅仅视为革命领袖软弱之举措,更应该从他致力于和平、避免内战的善良愿望及高尚的政治操守等方面进行审视。这样便会得出与以往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而且还可以理解当袁世凯破坏共和,违反了人民“息兵安民,以事建设”的愿望,渐渐走向帝制自为之时,他屹然举起反袁大旗,要求“爱国之豪俊”急起共击的举措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 58、91、333、377 -378页。。而当1916年袁世凯因帝制败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孙中山仍抱定“破坏既终,建设方始”的和平统一,利国福民愿望,急令革命党人停止军事行动。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 58、91、333、377 -378页。他认为,“自袁逆自毙,黄陂继任,约法恢复,国会再集,吾党不得不宣布罢兵,以示吾党革命志在护法,而非为利。”他号召革命党人投入国家建设之中,“现在时局阽危,民国基础,危如覆卵,欲谋奠定,非弟一手一足所能为力,不得不仗诸同志之协助”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 58、91、333、377 -378页。。
在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中,黎元洪向称“善容嘉言”,乃为“不失自处之士”⑤楚伧:《人物闲评一·元洪》,载《民国日报》,1917-07-07。。武昌起义之初,他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决心转向革命后,便一直成为民主共和的忠心支持者。由于以革命派为正统的历史观念造成认识上的偏失,学界一直低估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事实上,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黎元洪转向革命对于当时局势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⑥冯天瑜:《黎元洪出任辛亥革命鄂军都督始末》,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与孙中山一样,武昌起义后黎元洪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南北的和平统一。在一则给伍廷芳、温宗尧、汪精卫等人的覆电中,黎元洪写道:“自议和以来,往复商榷,将近两月,千回百折,颇费经营”。他之所以“如此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主要也是为了能“顾惜无数生命,保全无数财产”。他充满期待地指出:“卒能和平解决,造成共和民国,其待无涯,其功无量。”⑦黎元洪:《覆伍佚庸、温宗尧、汪兆铭三君》,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5页,广益书局1931年版。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后的国家组织和建设更为重要,“此后组织中央,一统南北,及一切建设方法,大大皆重要问题”,如果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稍一失着,即足以启内讧,遭外侮”。⑧黎元洪:《致孙总统论除意见》,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5页。他寄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于“此时大局初定百废待举,仍乞大力维持,建设完全共和民国,则不独颂缔造之功,即万国亦莫不庆平和之福”⑨黎元洪:《覆伍佚庸、温宗尧、汪兆铭三君》,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5页,广益书局1931年版。。
黎元洪对武昌起义后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现象非常不满。在《通告各省就任临时副总统》中,黎元洪告诫各省政要:“现在和议未定,战争方棘,尚望诸君子坚矢初心,共襄盛业,勿争权利而越范围,勿怀意见而分门户,勿轻敌而有骄心,勿畏难而萌退志,岂惟我中国父兄子群相讬命,环球万国,将于是观听随之,元洪有厚望焉”。⑩黎元洪:《通告各省就任临时副总统》,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1页。他认为,民国初肇,“虽稍具热忱者,尤当于一息尚存之时,力图统一”。然而事与愿违,令他感到忧愤的是,“而滚滚诸公,乃或猜心藏忌,苦志鸣高,瓦解棋分,夷然弗恤”。他感叹道:“哀我生之不造,痛大命之将倾,瞻仰昊天,曷其有极!”在他看来:“夫共和宣布,南北一家,虽稍抱野心,断不容于千夫交指之世。我当轴诸公,正宜沥胆披肝,和衷共济,纵万一所如不合,权见相乘,亦可藉议会为中坚,持人民为后盾,福民利国。”⑪黎元洪:《致唐总理各部总长敦促临时政府成立》,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26页。为此,他四处奔走,“弥缝其间”⑫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见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卷五,第2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于山东、安徽的都督之争,黎元洪毫不留情地痛斥道:“共和成立,胡越一家,况同隶省域,尤当共策进行,力图补救。乃竟以各戴都督之故,藉武力为后援”。他认为,“杀机一开,龙蛇起陆,牵一发而动全身,合九州而铸大错。各省效尤,列强乘寡。虽有圣智,亦无所施,设大陆神州,竟从此酿瓜分。”⑬黎元洪:《致袁总统请改任山东都督》,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12页。他呼吁各方为大局着想,“同心救国,有何猜嫌,且派员协商……加以绅民代表,重以总统之委员,更不难樽俎之间,立蕲修辑”。⑭黎元洪:《致袁总统及各团体解决皖事》,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14页。针对民初由于各种原因而引致中央政府不断更迭的现象,黎元洪也常常感到痛心疾首、“五内俱焚”。他认为,“国家兴亡,视乎政治,政治隆替,视乎官制”①黎元洪:《致袁总统各部总长劝规政府诸公》,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19页。,实现国内和平统一首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组织一统一的、稳定的、负责任的政府,“夫有政府,然后有国家,有部员,然后政府”②黎元洪《致各省团体痛陈时局》,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9页。。因此,他先后通电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等,催促各方“无拘党派,无拘常德,但以民福国利为前提”,只要各方“知识互换,意见消融,不隶党籍,但谋福利”,便能达到“共促国基之巩固,勿滋他族之狡谋”。③黎元洪:《致大总统参议院论时局》,见汤寿铭:《黎大总统文牍汇编》,第38页,会文堂新记书局1929年版。黎元洪认为,维护国内和平,共同建设国家,才是起义之初志。在《致各省都督各会党》中,他指出:“破坏匪易,建设良难”,在“方今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的时局中,各方应泯除矛盾,“共持初志,合五大族人民之众,廿二省四部土地之广,同心戮力,一致进行”,这样才能“有对诸先烈在天之灵,达诸志士倡义之首功”。④黎元洪:《致各省都督各党会》,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10页。
在黎元洪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一方面为实现和平统一的理想,另一方面因自己的政治位势——仍不断地在南北各方之间竭力弥和。1919年,他隐居天津时,仍不忘通过各种方式调和南北对峙双方。在一封写给岑春煊的信中,他谈道:“纷争不息,徒苦吾民,南北睽违,同深感慨。比者障疑渐除,足觇天道。倘能发扬民意,急起直追,未始非解决时局之良好机会。”⑤黎元洪:《关于议和问题复岑春煊函稿》,见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2卷,第1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1923年5月6日,他在给王景春的电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国人厌乱已极,何堪再事兵戎”,要求国内各派“不宜轻启内争,予外人以口实”,只有“解除误会,当可泯萧墙之私源,为和平之保障也”。⑥黎元洪:《就保持国内和平消除各派误会覆王景春电》,见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3卷,第80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时人曾十分形象地描述了黎元洪对于和平统一之热盼,及其所付出的努力:“黄陂因急盼南北统一,屡次电致南方各要人,推重之辞,谦撝之语,满于字里行间。又复迭遣专使南下,与南方要人,如孙文、陈炯明、唐绍仪、孙洪伊、唐继尧、李烈钧接洽。因有人言于黄陂曰:‘公不辞劳怨,以通好于南方,独不虑有力者方面之疑虑,而虞公有别结强援深心耶?’黄陂闻之,不觉笑曰:‘予视政治如苦海,方将求去之不遑,宁愿与此辈营营扰扰耶!如人或疑予有他,则在予但求此心之坦白,更不管身外之是是非非。’闻者欢为名言”⑦李定夷:《黎黄陂轶事》,第123-124页,上海国华书局1922年版。。可见,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一直是黎元洪执着的政治追求。
孙、黎以外,黄兴也主和平统一。黄兴曾指出:“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为急,无逾于此日。”⑧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第149、262、25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希望革命党人“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第149、262、25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将“统一精神”作为“第一要义”,化除党派之间的政见之争,达到“南北一家,兄弟一堂”的和平统一局面。⑩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第149、262、25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后世历史学家常常指出,无论是孙中山、黎元洪还是黄兴等,对于和平统一的呼吁,不免显得有点一厢情愿;并且在客观上还有为袁世凯所利用,从而方便其以和平统一为幌子消磨革命于无形之中的嫌疑。然而,百年之后,当我们回眸这段历史,揭开政治权力争斗的层层面纱,认真清点辛亥百年遗产时,显然不能完全以此种后见之明去解释和评判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的和平统一主张。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主张蕴涵了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们的救国热诚,及他们所确立的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
三
实际上,孙中山等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的“和平统一”言论无论在当日抑或以现在标准衡量之,绝非单纯的政治妥协可以概括。这些主张凝聚着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们对于革命的认识,渗透着他们革命非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利国福民的基本共识。
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利国福民”自不待言。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起草的《建国方略》等历史文献,均蕴含着救亡图存的殷切期望。孙中山曾集中阐述了辛亥革命之目的,并非权势之争,“须知民国以专制为敌,而权位非所争”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目的在于“利民福国”。因此,他在《临时大总统誓词》中明确提出:“倾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1、20、84、44 页。。这番言论基本概述了孙中山对于革命目的的深刻认识。1912年1月4日,在给直豫谘议局的通电中,他又指出:“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解职之条件”。对他来说,无论是受任还是解职都是“示为民服务之本心也”。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1、20、84、44 页。2月3日,他在给《咨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文》中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1、20、84、44 页。。孙中山之所以力主和平统一,缘于其深刻地认识到“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暴力革命乃万不得已之举措。“夫破坏云者,仁人志士,任侠勇夫,苦心焦虑于隐奥之中,而丧元断脰于危难之际,此其艰难困苦之状,诚有人所不及知者。及一旦事机成熟,倏然而发,若洪波之决危堤,一泻千里,虽欲御而不可得,然后知其事似难而实易也。”但“建设之事则不然。建设,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部所议者国家无穷根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1、20、84、44 页。革命也只是一时的选择,起到的“乃暂时之作用,建设乃永久的事业”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页。。
怀揣着现代化的梦想,退职后孙中山立即转入国家建设之中,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四处演讲劝说人们发展实业,并致力于铁路建设。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具体领导和策划,描绘了具有完整体系的三大铁路干线蓝图,提出修建20万里铁路计划,还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并自任总理,等等。⑥[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士未酬的爱国者》,第30-31页,杨慎之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孙中山在其一生的言论和实践中,充分表达了致力于和平统一,利国福民的意愿,使之成为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黎元洪也曾多次指出“武昌起义,原谋国利民福,毫无自私自利之念,参杂此中”⑦黎元洪:《致中央各省消除私念》,见汤寿铭:《黎大总统文牍汇编》,第28页。。他认为,起义中的革命者之所以“出生入死,万祸不辞”,也在于“但为同胞谋幸福,非为个人营利”。⑧黎元洪:《致各省各团体痛陈时局》,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9页。与孙中山革命理念和精神相同,黎元洪也对破坏与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明确提出:“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修养生息,恢复元气。”⑨沈云龙:《黎元洪评传》,第18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版。为此,他批评了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利国福民”之初衷的现象,“乃不意专制政治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⑩黎元洪:《致中央各省消除私念》,见汤寿铭:《黎大总统文牍汇编》,第28页。他期待着中国的有识之士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关键时刻,“正宜明目达聪,与民更始。我民国士夫,亦应清操自励,劲节不阿,树后学之楷模,作中流之砥柱”。⑪黎元洪:《致袁总统各部总长劝规政府诸公》。也就是说,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投入到“利国福民”的建设运动中,成为建设共和新国家的中坚力量。
黎元洪还将“利国福民”作为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改革的前提。如在对政体功能的认识上,黎元洪从达到国家“治”与“安”的目标来评判专制与共和。他透过国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阐明自己的想法:“天地生人,由图腾而部落而国家,递演进化,无非以保全治安为主旨。无论为君主民主共主,为专制立宪共和,要不外合人群之心理,应世界之趋势,俾国家成一健康强固之机体,以为保全治安之方法而已”,国家机器的根本目的,是使社会达到“治”与“安”。他认为,“三代以前,号称极治”,主要是因为“上古时期,虽属君主国体,而民贵君轻,公理早着。举凡逊位迁都,国疑国危,用贤刑罪诸要政,无一不取决于国人,视听同民,好恶同民,无共和立宪之名称而无一非共和立宪之元本”。然而,自秦实行愚民政策后,专制横行,每下愈况。到了武昌起义之时专制制度达到极点,“君权愈尊,官常愈替,内之则陵民族,苛捐滥杀,专利攫权。外之则开寡邻邦,败盟丧师,失地赔款,使我华夏神明胄胤,成一至愚至贫至弱病莫能兴之国,人民土地之濒死垂亡者,不绝如缕焉,有不可终日之势”。此种臻于极致的专制之害,使得“民气沸腾,举国震惊”,有识之士们“兴言改革,历经燕、豫、皖、滇、桂、粤等处,凡十六次举义不就,而于去秋假手于武昌”。①黎元洪:《国庆日演说辞》,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2页。从根本上讲“民主共和”对黎元洪来说,主要在于其能使国家达到“治”与“安”;而专制愚民,则使国家沦为“至愚至贫至弱病”之地,人民“濒死垂亡”。在此“利国福民”观念之下,黎元洪走上了以实现民主共和为职志的政治道路。1915年,当袁世凯力谋称帝,对其拉拢,册封其为武义亲王时,他“拒其册”,“却其禄”,并对来贺者说:“辛亥倡义,踣军民无算,非为一人求官禄也,诸君如相迫,即触柱死矣”②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章太炎全集》卷五,第204页。,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维护共和的决心。
“利国福民”也是黎元洪判断其他政治问题的重要标准。如在对待政党问题上,黎元洪认为,“窃维群法进化,政党攸关”,然各种政党“虽异帜纷张,众言淆杂”,总的来看“其归宿未有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③黎元洪:《致中央及各省忠告政党》,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三,第1页,广益书局1931年版。又如民初各报有称当道者“以志士自命”,许多人渐“染骄奢淫佚之习,与满清当道故态,有过之无不及”的现象。黎元洪对此“不胜骇异”,遂在《致参议院力崇节俭》一文中指出:“我国民膏血,自满清□削二百余年,即无此次战争,亦当力崇节俭,以恢复元气,况当干戈未已,偏地嗷鸿,即尝胆卧薪,尚恐不能造国民之福。果如该报所云,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他希望“大总统速下崇节俭抑奢侈之命令,凡军民人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挽颓风,而免外人讪笑”。④黎元洪:《致参议院力崇节俭》,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36页。黎元洪还极力赞成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禁烟行动,在《致各省都督议会赞成禁烟》中痛陈鸦片之害,指出:“民国为鸦片进口终止之日,救国救民”。⑤黎元洪:《致各省都督议会赞成禁烟》,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第7页,广益书局1931年版。
通过军民分权而达“利国福民”是黎元洪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民国初年,军人柄政,祸患无穷,黎元洪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推动军民分权,阐明“军民分权为当今正本清源之策”⑥黎元洪:《致各报馆论军民分权》,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30页。。在《致袁总统及各省痛陈时弊》中,他从赋税、外债、司法、经济等十个方面,说明“军民不分”的流弊,并进一步指出军界存在“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的现象。⑦黎元洪:《致袁总统及各省痛陈时弊》,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20-23页。惟有“将军务民政划分为二”⑧黎元洪:《致袁总统及各省痛陈时弊》,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20-23页。,才可以起到“远惩联邦会长之政,近鉴督抚专权之弊”⑨黎元洪:《致中央及各省论军民分治》,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第11页。。如若“优游不断”则“贻患滋深”⑩黎元洪:《致各报馆论军民分权》,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30页。,“已足亡国灭种而有余”⑪黎元洪:《致袁总统及各省痛陈时弊》,见朱瑞:《黎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一,第20-23页。。
为了早日实现“利国福民”的愿望,黎元洪也热心参与实业。他广泛投资金融、矿产、森林、造纸、食品、面粉、贸易、证券、保险等经济领域;且投资的地域也相当宽阔,从黑龙江到香港,全国不少地方都有黎氏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黎元洪先后参与投资、创办或协办的银行、厂矿70余家,其中包括20余家银行;投资金融业不低于300万元。8个大型煤矿;8个矿产公司;3个森林公司;6个纺织企业;5个生产食品、物品的公司等。⑫侯杰、姜海龙:《百年家族黎元洪》,第256-258页。对于与民生关系极为密切的行业,他都热情参与,并且想方设法苦心经营。而所有这一切,都与黎元洪“利国福民”的理想有一定的联系。
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领袖,也纷纷以利国福民为奋斗目标。黄兴先是在1912年10月26日黎元洪于武汉都督府为其举办的宴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舟共济,以国利民福为前提”;⑬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87、12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又批评政党利益至上:“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乃为民国之福”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87、12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字里行间充满一位革命者的期待。需要指出的是,利国福民不仅是黄兴等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们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检验革命思想与实践是否取得成效的指标,甚至被视为革命的旨归。宋教仁在1913年曾提出假如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设想可以变成现实的话,“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⑮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5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遇刺受伤后,宋教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然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文,明确表示:“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⑯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5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可见,“国基未固,民福不增”,成为宋教仁深感“死有余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通过梳理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的各种思想与实践,不难发现,“和平统一、利国福民”并非他们人生的最后绝响,而是他们参与革命、为官执政的态度和目标之一。事实上,“和平统一、利国福民”不仅是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们的共识,也为彼时中国仁人志士的普遍诉求。
透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类似的言论与行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南阳路10号惜阴堂由“布衣”赵凤昌等人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早在南北议和以前,以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人为首的12省代表便联合发表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要求各省仿照美国第一次大陆会议,“为保疆土之统一,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沪集议”。①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赵凤昌藏札》卷十,第449-451、433-4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尽管这些行动与言论,长期以来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但是可以看出,赵凤昌等人的言论和行为,实际上正是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之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结晶。首先,清王朝的垮台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离不开以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们的共同努力。其次,以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人为首的12省代表,在政局未稳的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发表政见。他们在《国土辽阔种族不一与共和政体之问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提出:“且保全领土尤为今日南北所当同心协力,唯一无二之问题”。这是关系到新建立的国家能否得以继续存在,以及能否得到各国承认等一系列问题。“列邦对我条约,皆以‘保全领土地,机会均等’为公认前提”,因此,国家能否统一,关系到此后避免列强借端介入,使中国面临“死生存亡”的大问题。再次,他们还明确提出北方各省赞成共和的要求,只有南北一致赞成共和,才能达到保存国家与民族的目的。“中国近二十年来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赞成于西北。昔之推行新政,请求立宪,现已南北响应一致而无疑。今若南主共和,而北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此真全国汉满蒙回藏五族死生存亡之机。”为了实现共和统一的目标,他们拟定了五条政治主张:“一、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之地位;二、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四、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五、联络全国军民以促进共和之实行。”②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赵凤昌藏札》卷十,第449-451、433-4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同样是“和平统一,利国福民”的善良愿望。
总而言之,“和平统一、利国福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出千万人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革命”真谛,凝聚了仁人志士的心血和智慧,成为辛亥革命经由大破、大乱走向大立、大治之伟大目标的基本概括。虽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和平统一,利国福民”难免会被某个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这更能进一步锻炼和提升辛亥革命领袖、首义元勋的政治智慧,也并不妨碍其作为辛亥革命重要遗产之一的重要历史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百年后的今天,以此重新认识辛亥革命,既符合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又是中国人百年梦想的关键所在,还是所有中国人都要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
侯杰(1962—),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03-12
K257
A
1000-5455(2011)04-0061-07
【责任编辑: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