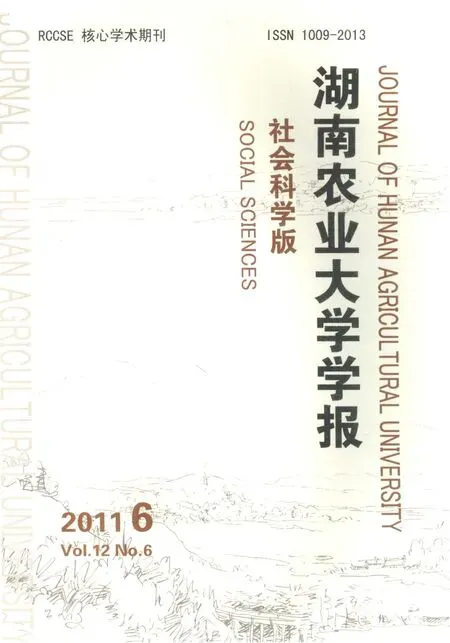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2011-04-08路培炎陈运雄
路培炎,陈运雄
(湖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
——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路培炎,陈运雄
(湖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建立“法律信仰”作为很多学者为实现中国法治的愿景已有多年,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驳斥虽非学界主流却也从未间断。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信仰的唯一性否定了“法律信仰”命题的合理性;“礼治”以及“法即刑”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民众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也令法律信仰的建构缺乏社会基础。为此,惟有通过价值重建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
法律信仰;合理性;权威性工具;自然法;实在法
针对当前中国法治社会建设面临的许多困难,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困难是由“法律信仰”的缺乏所导致的,建立起“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实现法治。学者纷纷对培养法律信仰提出建议,希求以此促进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法学界关于“法律信仰”问题发表的论文不下百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法律信仰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剖析,充分表明了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重视。
尽管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此,但仍有学者对“法律信仰”命题持批判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永和教授以及范愉教授等。如张永和教授认为“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将一个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哪怕就是在西方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操作性的理念引进中国并希望在中国得以生根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和不理智的表现。”其理由主要有四点:一是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中国;二是法律不具被信仰的超然品质;三是法律至上不等于“法律信仰”;四是“法律信仰”会导致误区并造成严重危害,会转移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混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1]范愉教授认为“中国法学家创造的‘法律信仰’命题实际上是对伯尔曼思想的误读,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2]王启梁教授的观点是“法律不会成为人们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不能妄图成为一种信仰,因为法律如果要成为一种信仰,意味着他要改变和重塑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对生活意义的认同。”[3]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质疑“法律信仰”的命题,但总体来讲“法律信仰”依然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所认同。鉴于质疑“法律信仰”命题的学者大都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去论证法律不能被信仰,笔者希望通过考量中国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等各种因素对所提命题产生的综合影响,从自然法与实在法两个角度,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证明“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的缺乏。
一、“法律信仰”及其逻辑前提
在中国,梁治平译文版的伯尔曼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常常被中国绝大部分法律信仰研究者引用。其实在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中,这句话的原文是“Law has to be believe in,or it will not work”。“believe in”可以是“信任”、“相信”、“信念”,也可以是“信仰”,而词源学上谈及纯粹的信仰,必然要使用“faith”。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们也大都认为这里的“believe in”应作“信赖”、“信任”解释。[4]对“信仰”具有代表性的界定主要有三种。一是康德的“非理性论”,二是中国正统或主流观点似乎认同的伯尔曼的“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论”,三是难以界定论。笔者基本上认同陈会林先生的观点:“信仰是对教理、主义、正义等事物虔诚信服和尊重,并以其为行动的准则的心灵状态”,“具有神圣性、不可侵犯性和永恒性。”[5]至于法律信仰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学界存在各种看法。例如陈会林认为,“就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强制性行为规则”[6];于文静、夏宏强则认为是“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7]。这些观点讨论或指涉的无非是人类的两大类法律:自然法与实在法。
需要明确的是,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在西方的确具有深刻的自然法背景。诉诸于西方的法律传统,则主要表现为伴随着自然法思想演变中信仰的本质的逐渐凸现。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经历了古典自然法、经院自然法和现代自然法的转变;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传统自然法世俗化的转变,即本质——神谕——理性的转变。在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法律信仰的实现需要神谕的支撑,这使法律信仰类似于宗教信仰,在宗教法的法文化中,法律信仰等同于法信仰;但是,对着自然法思想的更新,自然法提出理性概念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这使法律信仰的概念发生了转化和更新,法律信仰成为人们对良法的信任与遵从,法律信仰的对象成为法律中所蕴含的良善价值。所以,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就是价值,这可以是宗教价值或者是世俗价值。法律信仰不能脱离价值这一逻辑前提,脱离价值的法律信仰必然会发生异化。但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发展并非如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不同价值的演变,中国本土资源中缺乏宗教根基,人们无法从宗教中挖掘法律信仰的文化因子。当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主要是在立法层面的法律移植,这就需要在法律移植中确立良法之治,以实现中国对于法律价值的重建。[8]
二、“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的缺失
1.基于自然法视角的分析
人们对自然法的宣扬是在表明关于法的正义性、正当性的主张和立场。如上所述,法律信仰不能脱离良善价值的逻辑前提,否则必然发生异化。分析法学派在二战以前占据了西方法学的统治地位,提出“恶法亦法”的理论。纳粹期间的德国便是以“恶法”为手段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暴行,此间的暴政实质上就是“法治国”观念的异化。于是在自然法背景之下,对良法的信任与遵从为“法律信仰”命题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法律中所蕴含的良善价值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
如果说自然法角度的“法律信仰”是指对良善价值的信仰,是否就意味着“法律信仰”命题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得以成立呢?那么此时就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或者说良善价值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笔者认为,基于信仰的自身特性,虽然社会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存在各自信仰的差异性,但是如果将社会主体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信仰主体进行培养,那么此种信仰的对象应该并且只能是一元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中国,显而易见,这个信仰就是社会主义,其本质内容“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具体说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要实现自然的社会化——全面的公有制,在交往关系上要实现世界的社会化——人类解放,在政治上要实现权力的社会化——社会收回国家的政治权力,在文化上要实现社会化的个性自由发展模式——‘自由劳动’的生存方式”。[10]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和国家终将消失,法律也将随之消失。那么公平、正义将撑破“法治精神”的胞衣,冲出法律文化的范畴,自然而必然地直接被社会主义信仰内容所涵盖。也就是说,自然法角度的“法律信仰”与社会主义信仰内容的一部分是重合的。因此,即便现在中国学界经常提及的“法律信仰”是基于自然法的角度,此命题在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进程中的中国,在主体信仰培植一元化的前提下,也缺乏合理性。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语境下,法律无须被信仰。
2.基于实在法视角的分析
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乃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而得出的产物,这种制度移植的背后隐含着文化传统的巨大冲突。正如梁治平所言:“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11]笔者尤其赞同张永和的如下观点:“中国现阶段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新规范制度的不适应和对待法律的传统态度不能扭转”[12]。这是试图在中国树立法律信仰必然遭遇的障碍,也是为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文化决定的。
一是“礼治”传统的影响。儒家正统思想对“礼治”情有独钟,道德受到特别重视,导致后来泛道德主义盛行,最终造成中国法治的缺失。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对社会关系调整在各个方面都有着相对于法的显著优势,基于此产生的价值判断使中国民众内心的价值天平倾向于“礼”而不是“法”。法外因素对诉讼的大量介入导致的大众误解,更加重了这种社会价值倾向。因此,中国可以很早提出“法治”观念,可以大量移植先进法律制度,但法律却始终无法渗透到最大范围的社会生活。
二是“法即刑”观念的影响。中国法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认识之一即是“法即刑”——法的内容就是刑、刑法,把法视为仅以刑罚手段调整社会关系的强制规范。这种观念导致两种效应:一是将法律恐怖化,二是将法律工具化。基于这两种效应,中国民众“贱讼、惧讼、避讼”,认为诉讼意味着对和谐秩序的破坏和背叛,所以古代“中国拥有精致的律令制度,拥有以皇帝为顶点的官僚制度,但人民有了纠纷,大部分不向官府起诉,而是通过地缘、血缘和同行业等关系中的头面人物的调解而获得解决。”[13]
由此可以看到,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民众几千年来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与把实在法角度的法律作为信仰对象的思路恰恰是相对立的。二者是一种竞合关系,此长则彼消,实在法角度的“法律信仰”得以树立就必然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部分消解。这其中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及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效率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毕竟,文化乃是一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核心因子。正如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契丹族,其血缘角度的血脉不曾也不可能真正消失,但自其文化血脉既断,这一民族永远成为历史。面对实在法角度的“法律信仰”与我民族文化的巨大冲突,如果仍逆流为此“法律信仰”勉强堆砌文化土壤,笔者不能否认其实现的可能性,但考虑为之付出的文化代价以及由此引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灵魂所受之炮烙,未免要用“得不偿失”四字概括。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中国数千年民族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现今以及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进行审视,无论是从自然法还是实在法的层面进行意指,“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在中国语境之下都缺乏合理性。
三、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对“法律信仰”命题进行争论,其指向其实是法律权威问题,即民众观念和行动中对法律的认同和尊重。提倡“法律信仰”的本来出发点是追求中国法治的精神意蕴,以建立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笔者认为,此愿望无望倚靠“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而达成,但或可通过确认法律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
一提到“工具”二字,必然令人联想到广受学界批判的“法律工具主义”。其实,学者们所攻讦的对象是政府将法律视为阶级统治工具随意玩弄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律权威的倒塌,而并非法律本身具有的工具品格。如今,中国的现实进程早已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我们在思维层面上也早该由“革命思维”转到“建设思维”。如果民众对法律的工具价值加以重新认识和利用,这非但不会妨碍法律权威的树立,反而可以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坚实心理基础。
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4],法治既是一种制度上的完备,又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根据马克斯·韦伯对人类行动合理性的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在民众心中确认法律的权威性工具地位可从两个维度切入。
1.价值理性维度:价值重建
法治常被视为一种制度安排,但精神的缺失无法造就法治。对法律本身的价值评价是法律第一权威能否在民众心中得以树立的首要因素。在中国社会追求西方移植型的法律制度完美运行,有必要而且可以从东西方文化的交集中寻求支持。
一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有着通过长期的历史文化形成的、默默支配法律运行的精神力量,法律的精神只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于一国总体文化覆盖之下的法律文化,在实践中必然染有本民族的特色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它影响着法律的有效实施并指引着法律的发展路向。主观的立法活动不可能全然改变传统的社会精神本身,而只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更新。唯此,法律才可能具有社会生命力。冲动地将西方法律文化引作中国法律精神基础的结果只能是法律精神和社会精神的脱节。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宗教信仰得到广泛承认的事实,实际上这一现实的另一角度是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稍显太早的时期就跨进了“民本”同时也是“人本”的文化阶段。这正如孟子所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正确的制度方向来自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古代法家的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人莫不然”。每个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共通之处。诚如库朗热在评价早期特权的古希腊罗马社会所言:“但凡人所构想和建立的社会组织,没有不变的道理。这种组织本身就有致死的疾病,那就是巨大的不平等,对于自己丝毫没有益处的社会,人们只想摧毁而后快。”[15]当法律对人们实现利益最大化具有工具价值时,法律就自然成为人们追求、信赖、尊崇的对象。对私人利益的关心也是西方国家公民对法律尊重和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法治应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行为。“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6]只有当人们真正从法律或法治中得到好处、利益、方便时,法律本身的价值才能真正契合于民众的价值评价标准,建立在人们真正信服、依赖基础之上的法律才获得真正的权威。
2.工具理性维度:合法性维护
法律制定和运行程序的正当性、合法性,是树立法律第一权威的另一决定性因素。而现实中我们却恰恰缺乏能够反映这种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制度环境和生活经验。立法缺乏稳定性,主体行动难以对可能得到的法律评价进行预期;部分立法因显著缺乏立法技术导致有法难依;“抢滩圈地”使立法扭曲成部门利益保护工具;类似“钓鱼执法”的违法式执法使民众权益受到粗暴践踏;悖法徇私、权钱交易等等。现行政治制度所追求的目标无疑是合理的,但具体制度设计上依赖更多监督而非制衡导致监督成本提高且并发监督者的监督问题。权威的树立需要制度环境的先行,制度环境的缺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众对法律的感受,也就导致了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生活经验的缺失。因此,可从两方面来维护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工具的合法性。
一是完善立法体制以促进良法生成。托克维尔曾经提到:“不管一项法律如何叫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容易服从,这不仅是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作品,而且是因为这项立法也是本人的作品。他们把这项立法看成是一份契约,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加者。”[17]因此,立法者或可参考国内学者提出的“立法听证”等建议,改进立法监督与立法审查、切实提高民众的立法参与度。况当代中国之政府是人民之政府,立法也即人民之立法,诸般字眼本身已然代表合法性及正当性。二是推动公正实施以确保良法良治。司法公正是解决社会纠纷、救济公民权利的最可靠保障。沈家本先生有言:“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18]。培根也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破坏了”[19]。运行程序正当化、合法化方可强化法律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从而使法律获得民众的认同与信赖。因此,实现审判独立、完善审判监督机制以维护司法公正可能是当下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性步骤。
诚然,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制上可以从西方发达法律体系进行借鉴甚至移植,但对法律文化进行移植却并非明智之举。如若追求文化新枝的顺利萌发以及稳定生长,必须将其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使其顺应合理的成长方向。而文化中的评价标准产生自社会生活的现实土壤,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必然要求社会规范工具的多样性。作为社会规范工具的法律、道德、舆论等等各自存在自身的功能特性,不同的社会形态选择决定着各种社会规范工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权重和序列。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既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取向,自然要求法律在社会关系调整及社会利益协调过程中的首发序位及至重威严,从法律自身的角度来讲也即赋予其权威性工具地位。在“依法治国”的宏声中,始终应清醒认识到的是人民的主体地位。“信仰”是作为“人”的社会中的存在,“工具”也因“民”的使用而伟大。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创造始终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服务,“人民的参与,就是法治。这样,法治也就意味着人民的参与或人民的最终统治。”[20]。“人民”之词汇应从典籍进入头脑并贯彻入实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中国学者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理性思考与广大学者的热情、激情同样不可缺少。
[1]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3):55.
[2]范 愉.法律信仰批判[J].现代法学,2008(1):12.
[3]王启梁.信仰与权威:诅咒(赌咒)、发誓与法律之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2.
[4]张永和.信仰与权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81-183.
[5]陈会林.现代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传统根源[J].中西法律传统,2006(1):392.
[6]陈会林.现代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传统根源[J].中西法律传统,2006(1):393.
[7]于文静,夏宏强.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的再认识[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6):36.
[8]崔雪丽.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0-6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10]胡 建.社会主义信仰及其存在合理性探讨[J].云南社会科学,2010(5):6-7.
[1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6.
[12]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5):54-55.
[13]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M].何勤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3.
[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991.
[15]库朗热.古代城邦— —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M].谭立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7.
[1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5.
[1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2752.
[18]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
[19]培 根.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4-185.
[2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91.
Query on the proposition of “belief in law” in Chinese Context: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uthoritative tool position for law
LU Pei-yan,CHEN Yun-xi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Establishing “belief in law”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many years as a will of many scholars to realize China's rule of law,and the refuting on the proposition of "belief in law" has never stopped though it is not the academic mainstream.Generally speaking ,the logical premise of “belief in law” is value,however,the uniqueness of belief in socialism neg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 belief in law ".In addition,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 of “rule by ceremony” and“law equals to punishment” causes the public to alienate the law and thus the construction of “belief in law” lacks social foundation.Hence,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belief in law" and the veneration position of law can be realized by reconstructing value and setting law as an authoritative tool for social norm.
“belief in law”; feasibility; authoritative tool; natural law; positive law
D920.1
A
1009-2013(2011)06-0074-05
2011-11-15
路培炎(1985—),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
陈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