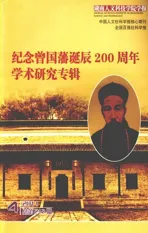我的父亲和《曾文正公家书》的故事
——纪念曾文正公诞辰2 0 0周年
2011-04-07曾光
曾 光
我的父亲和《曾文正公家书》的故事
——纪念曾文正公诞辰2 0 0周年
曾 光
孩提时代的记忆中,看到父亲书房桌上的笔架和砚台旁,总是摆放着一本米黄色硬封皮的书。正在上初小的我已经能够读出封面上印的“曾文正公家书”那几个楷体字了。不过我既不知道这书名的意思,更不懂里面的内容。稍大一点时,只听外祖母(她一直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对我们说过,“那是你们曾家老祖宗写的书,你们别去动它啊。”
解放了,我已进入高小。父亲作为起义人员留用在人民政府机关工作,因为工作学习忙就住到单位里去了,只有周末才回家。父亲的书房已成为我和弟妹们的学习室。那本《曾文正公家书》也就放到了书架上面。记得到了初中,在语文课中学到唐代诗人杜甫的五律《春望》,其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句子,才知道“家书”就是写给亲人的书信。好奇心使我想起了书架上的那本老祖宗的《家书》,回家便从书架上拿出那书,随手翻了几页,由于是文言文,许多地方还看不懂,读着感到别扭,也就随即放了回去。不过这段时间当母亲批评我和弟妹有时学习懈怠,或与邻居孩子吵架,或偷懒不愿做家务时,常指着书架上的那本书说,“你们那是不对的,做人不应该那样,老祖宗在书上都说了的。”
1950年代中期,我和弟妹逐渐长大。中学的历史课中已告诉我曾国藩是近代镇压农民革命的一个最反动的人物,这对我少年成长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偶尔想起了那本《家书》,回家到书架上一看,那书还在,但放在架子的最下面,而且包了一层棕色牛皮纸,外面已看不出是什么书了。然而那时对自己家族历史的自卑心理和负罪感已使我对这本《家书》毫无兴趣,也不愿再去动它了。
1957年反右运动,父亲蒙冤遭难,1958年被开除了公职,交由街道管制。迫于经济压力,我们家的房子也仅留下两间,父亲的书架只能放到后面房间的角落里。好在那年我已考上了师范学院(万幸),在我周末或假日回家时,偶尔发现“那本书”早已不在书架上了。过了些年,在家中衣柜下面的抽屉里我又见到了“那本书”,还用报纸包着。我打开看,封皮已很陈旧,书脊也已开裂,我当然知道这已是一本“禁书“,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放到抽屉的最底层,上面是一些破旧手电筒,灯头、五金工具等杂物。
1966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父亲是1957年划的右派“死老虎“,倒也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和迫害。最多是去参加“陪斗”或是接受街道干部的训话。我当时已经在外地教书,1969年暑假我回长沙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有时和父亲聊天,谈到曾国藩和我们的先祖曾国荃等历史时,我提到了那本《家书》,父亲说,“那本书其实并没有什么反动的内容,只不过讲一些处世做人的道理,大到读书明理、戒免骄奢,小到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虽然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但有许多就是以无产阶级观点看也是正确有理的。”他还告诉我那本书还在,他已把书偷偷藏到后面厕所的墙上面。我拿了凳子去看,那书果然在杂屋和厕所的间墙上,用一块灰色的布包着,上面再压上了一块砖,不仔细一点是看不出来的。
1970年代后,经过林彪事件,社会下层的政治压力明显放松,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谈论时世和历史也不那么紧张和害怕了。这时母亲也退了休,早已成为街道居民的父亲也显得开朗多了。当我回家时,在父亲的书架上又看到了那本《家书》。虽然封面仍然用纸包了,但纸很薄,能隐约看到书脊上的书名。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右派冤案得到改正,恢复了干籍。1980年代还享受离休待遇。那本《家书》又回到了父亲的书桌上,仍旧放在笔架和砚台旁,虽然有些破旧,但封面仍然完整。
198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钟叔河先生整理校点的《曾国藩家书》。1990年代父亲来株洲看我时,曾特意买了一本带来送我,虽然当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它,但我知道这书是老祖宗的教诲和父亲的心意,在我心中弥足珍贵。
1994年10月7日父亲走完了风雨坎坷的一生,两年后母亲也去世了,而人到中年的我们都正缠身于工作和家庭。直到世纪末我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去整理父亲的遗物,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父亲珍藏的那本《曾文正公家书》。好在父亲送了我一本1989年新版的,它现在放在我新置的玻璃书柜里。闲暇时看到它我总要取出来翻一翻,读上一两篇。抚摸着这本书,想起父亲的一生和那本《曾文正公家书》的境遇,我心中真有无限的感慨。
注:父亲曾宪枢1911年12月22日出生于北京,忠襄公(曾国荃)五世嫡孙。1935年国立湖南大学商学系学士,终身从事财经会计工作。解放前在湖南省会计处任职,1949年后作为起义人员留用,先后在湖南省财经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任科长、处长。1980年代享受离休待遇。1994年10月7日在长沙逝世,葬于长沙潇湘陵园。
2011-07-06.
曾光(1939—),男,湖南双峰人,曾国荃六世嫡孙。
(责任编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