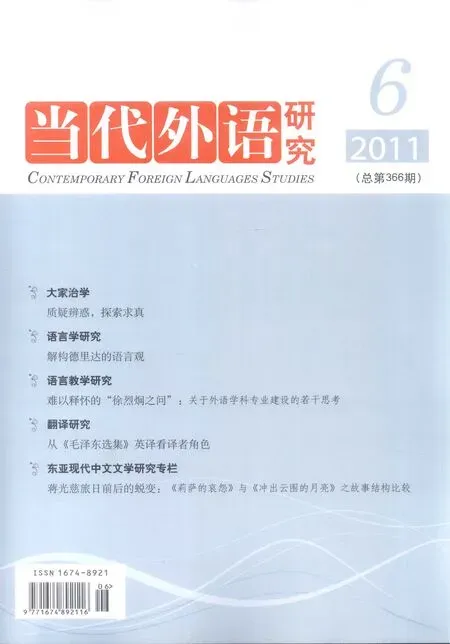“流亡”在上海——重读梁京(张爱玲)的《十八春》与《小艾》
2011-04-03陈建忠
陈建忠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新竹,30013)
“流亡”在上海
——重读梁京(张爱玲)的《十八春》与《小艾》
陈建忠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新竹,30013)
1949年后的张爱玲人生行程发生变化,她体验了典型流亡作家的心路历程,成为东亚流亡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以“境内流亡”的视角探讨张爱玲以笔名“梁京”所写的《十八春》及《小艾》,通过分析两作的不同版本,可以厘清张爱玲藉修改来响应时代变化的心路历程。研究发现,张爱玲在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追求上逸离主导性的时代潮流,表面看似无可奈何地屈从了时代,但实际依然不合时宜,因此她的人与作品都具有流亡的意味。
流亡文学,梁京,《十八春》,《小艾》,亦报
1.前言:流亡者张爱玲
作家柯灵是张爱玲旧识,他对张爱玲崛起于文坛、以及无法被同时代的中国读者所认识,曾有过精到的观察。那是由于张爱玲崛起于一个“新文学传统”被切断的沦陷区之故,她便不受限于正统的启蒙与救亡文学传统的要求:
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
幸与不幸,难说得很。(柯灵 1985:101)
惟其如此的张爱玲,似乎才颠倒了文学必须是救亡图存的伟大工具这样伟大的包袱。但不幸的是,张爱玲活在一个如果不是为了救亡图存就绝无完全创作自由的时代里。流亡,成为她保持自由创作必须付出的代价。
张爱玲(1920-1995)个案的特殊意义,在于从身处沦陷区到生存于解放后的上海,再南下至香港,转而进入美国,及至作品被“中介”至台湾,她经历了在中国内战与世界冷战体制的背景下,典型流亡作家的心路历程,应该可以成为一个东亚流亡文学(Exile Literature in EastAsia)的重要案例,表现了二战后中文作家如何漂泊离散在不同的土地与政权之间。藉此历程,又可串连起台湾、香港、中国、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学/文化与政治关系,从而深化中国文学或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
在沦陷区文坛出场的张爱玲,心灵流亡与身体离散成全了文学,创造了一生传奇。张爱玲出生于上海,1939年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香港沦陷,来年返回上海。1943年于上海发表第一篇文章《沉香屑:第一香炉》后声名大噪。1945年抗战结束、内战继起,她颇沉寂一时。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于来年开始以笔名“梁京”于《亦报》发表连载小说《十八春》及《小艾》,但由于数次修订、改写,以至于到今天为止版本依旧残缺不全,处处显示出她的流亡心理与命运。笔者因而认为,张爱玲在上海解放后的处境与心境,以及她流亡至香港和美国这段期间的作品,无论属于境内流亡 (exile in the country),还是海外流亡 (exile out of the country),都无疑可以从“流亡文学”的角度对 50年代的张爱玲文学予以重新解读和定位。
本文旨在考察张爱玲在创作必须处处与统治者妥协或合作的情况下,流亡于中国境内的书写意义。本文强调,张爱玲的流亡境遇不仅始于她流亡香港。事实上,在 1945年至 1951年间,她就已倍尝“准流亡”的经验。先是耳边时不时传来“汉奸”、“文奸”的骂声,解放后则是跟着一起下乡体验土改。
迄今,台湾没有《十八春》(1951)的任何版本,只见其在流亡期间改写的版本《半生缘》(1969),即令皇冠出版社多次再版的全集里亦然。在“张学”香火鼎盛的此间,这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出版现象。但有趣的是,中国境内的数个张爱玲全集、文集或单行本,全都收录了《十八春》,而未必只重视《半生缘》,至少如安徽文艺、浙江文艺、海南、哈尔滨等出版社都出版过《十八春》。
无论如何,当今学界与书界无疑需要重新正视《十八春》缺席的现象。然而,《十八春》与《小艾》之创作、修订与出版,连带其日后在海外与中国被接受的经验,都显示出这两部张爱玲 1950年代沪上创作末期的小说,已置身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内战与冷战的历史情境当中,且已开启她“言不由衷”或“勉与配合”的创作形态。这些状况之所以产生,其实是她即将或已然成为一名“流亡者”的身份使然。
本文试图从“境内流亡”的角度,重读《十八春》与《小艾》(其中涉及以张爱玲本人删修、以及台湾香港两地之各种版本的演绎过程),藉以凸显其作品即使在今日,仍未能完全免于以不同版本“流亡”各地的状态。
2.“梁京”:一个国境内的“亡名之徒”
1950年 7月,张爱玲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联主席夏衍的提名下,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她使用的名字正是解放后才开始使用的新笔名“梁京”,它在 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是一个人人猜测的名字。直至 1970年代初,张爱玲才首次对研究者水晶承认,梁京乃其笔名(参见水晶 2000:26)。无论刊行与出版作品,还是出席公开场合,张爱玲都以“梁京”之名来签署。这已非寻常的化名行世,简直是想要隐姓埋名。不能现身来领受更多的掌声,对于坚信“成名要趁早”的张爱玲而言,当非所愿,实属无法而为。据此,笔者认为,“梁京”作为一个新名字,便是张爱玲开始其境内流亡的先兆。她不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局势之不利,也藉由新笔名预示了她将步上“亡名之途”的命运。
关于张爱玲被指为汉奸的问题,当年她就曾予以辩解,这当然可视为中日战争的后遗症之一,直接促成她必须要取新笔名。当年,战争刚结束,国民党接收上海,批评的压力马上涌现。因此,1946年 11月,张爱玲在增订版的小说集《传奇》里,以“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代序,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辩诬。文章一开头她就说到: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张爱玲 2010a:294)
在上海沦陷区,张爱玲还能够以辞函婉拒,不去参与日本帝国的大东亚作家会议,但受邀本身已足以为她招来“汉奸文人”的骂名。这种经验可堪对照台湾作家如张文环、龙瑛宗、杨逵等身在日本殖民地的经验,这些台湾作家不仅为“[日]帝国”效命的经验丰富,犹有甚者,他们甚至没有婉拒的空间,只能去为“帝国战争”宣传。
新中国时期,张爱玲受邀复出,1950年 3月至1951年 2月间,于《亦报》连载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1951年 11月则在同一小报发表《小艾》。不过,1951年 11月,文艺整风运动开始,夏衍、蔡楚生、史东山等权威人士都遭到批判 (沈鹏年 2009:246),这时虽然张尚在连载《小艾》,但此事是否让她明白中国的言论尺度,而有出走之举,值得再加考证。不过在行动上,张爱玲于 1952年 7月,以恢复因战事中断之学业为由,申请离境到香港。
此后,张爱玲再没有回到中国,直至老死异乡。张爱玲流亡海外长达四十年,无论对于喜之者还是恶之者,她作为海外中国文学、乃至于海外流亡文学的代表当无疑异。本文进一步认为,张爱玲仓促出走的原因其实可逆推至其自上海光复至解放期间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因此 1950年代初期,在逗留于上海的最后时光里,张爱玲应已进入一种“准流亡”(quasi-exile)的心理状态,一如她以“梁京”之名行世所表现出的意涵。因此,“流亡”在上海,意味着张爱玲已是主流话语的局外人。在这样的脉络下重读她的《十八春》与《小艾》,兴许能带给我们更多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与国家权力,乃至于张爱玲与东亚冷战结构间更多的反思空间,从而重新定位她在1950年代创作的意义。
3.为人民服务:重读《十八春》的连载、修订与改写
1950年 3月 25日《十八春》开始在《亦报》连载,至次年的 2月 11日结束,时间将近一年,分 317回载完,此为“亦报连载版”。1951年 11月,亦报社出版了修订后的单行本,初版两千五百册,此为“亦报修订版”。以上两种版本作者均署名“梁京”。
《十八春》主要以回忆方式讲述了世钧与曼桢相恋十八年却无缘结合的故事。其间,曼桢遭姊姊曼璐陷害,失身于姊夫祝鸿才。而世钧误信曼璐,以为曼桢和仰慕者慕瑾成婚,遂在万分痛苦下与世家小姐翠芝结褵。此后,曼桢历经产子、逃家、姊死、下嫁姊夫并离婚等事。解放后,众人在巧合下重遇,一同相约到东北去为人民服务。
在美国時期,张爱玲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1969),其中最重大的改变是将叙事时间缩短为十四年,只讲到 1945年抗战胜利,不再触及全国解放这一历史背景。删去国民党迫害豫瑾(原著名慕瑾)太太受酷刑拷打致死的情节;另一人物叔惠也未曾到西北解放区去加入共产党,而是留学美国,娶了富家女,后离婚回到上海。曼桢与世钧重逢时,只演绎了“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这样“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凄美结局①,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壮志已然让位于儿女情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亦报修订版”的《十八春》之外,实另有“亦报连载版”的问题必须厘清。这点迄今并未受到重视。对比过《十八春》亦报连载版与亦报修订版的学者杜英表示,当年《十八春》的修订主要表现为:1951年 11月,外在的艺术要求其实更加政治化,“张爱玲却在修订本中大面积地删除关于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描写”(杜英 2008:354),其中部分细节如下:
内容的修订主要表现为曼桢等人政治思想的淡化和诸多人物阴暗面的隐去。修订本中,浓墨重彩的舞会和具有政治意味的对话均被删除。如此,解放前的世钧和曼桢并无意去边区工作,而叔惠去西北解放区也是受同事的影响。张爱玲不仅彻底改写了三人解放前政党认同的明确性,还抹平了这种认同的主体自觉性(359)。据此,有论者 (金宏达 1994:391)认为:“《十八春》删去后半部变成了《半生缘》,张爱玲还是张爱玲”,这恐怕还描述得比较简单。至少在《十八春》删修为《半生缘》之前,尚有连载版与修订版的《十八春》之别。换言之,张爱玲在小说发表后当年,就在一年内做了某种程度的故事“复原”工作,而在真正流亡后才又更大幅度地舍弃了有关上海解放初期的描写。不过,重读《亦报》上的首发版本,并对照张爱玲修订后出版的版本之后,可以发现她的思考其实颇有“悬崖勒马”的意味。从连载、修订到改写,当被视为一次作家回归创作本意的修正行动,因为这种修订其实是修去了与爱情故事不合拍的部分,同时也具备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危险性”。
亦报连载版《十八春》的描述中,解放前的叔惠、世钧和曼桢在学生时代都是共产党员,立志去边区服务,叔惠还实践了这种志向,但这些对话在修订版中已被删去。例如连载版第十三章中,叔惠向世钧表明要去兰州:
世钧呆了一呆,道:“那边好像有战事吧?现在西北成了解放区了。”叔惠笑道:“我想去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世钧望着他微笑。叔惠笑道:“你怎么好像很诧异似的。从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都是共产主义者?”世钧笑道:“那……就像出疹子一样,是每一个年青人都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叔惠微笑道:“你说这个话,倒好像你跟年青之间已经有距离了,我觉得非常可悲”。(梁京 1950)②
也就是说,连载版有“从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都是共产主义者”等政党认同的话语;修订版则改为叔惠去解放区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选择,而不是意识形态认同。当然,这段情节也多出了“我觉得中国要是还有希望的话,希望就在那边”这样的话,以符合叔惠的心理动机;可是修订版《十八春》上的叔惠如此说道:
我也不是共产党员,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梁京 1951:261)③
这些段落的删去与修改正说明了连载时积极与主流共产主义话语呼应的写法。如果当时的某种表态明显有别于张爱玲以往对于政治活动的态度;那么,修订版则显示了张爱玲试图找回较为忠于原始创作意图的思考。虽然解放以来“三反”、“五反”活动的持续展开使思想改造的压力有增无减,张爱玲仍然选择了淡化政党认同与政治思想的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十八春》连载期间,张爱玲不仅参加了上海文代会,也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 (魏绍昌 2002:142)④。此次的土改经验成为她日后写《秧歌》的素材之一。但笔者更想指出的是,如果张爱玲在苏北体验土改时依然持续创作连载《十八春》,⑤那么可以推断,亲眼得见土改状况应已埋下她对于新中国的某种疑虑,以至于她在修订时大幅修改了表态过度的话语。
同时,如同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半生缘》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长篇小说,那是因为它改写自《十八春》。除去局部的政治性描写外,《十八春》本身已具足一个爱情故事的完整要素,其美学表现较诸张爱玲此前的短篇更为沉稳、细腻。虽然张爱玲也曾把《十八春》形容成是“Potboiler”(“为糊口而写的”)⑥,但它其实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爱”:“与大部分作品侧重于表现男女之爱可笑或悲哀背后的‘空虚’和‘苍凉’不同,《十八春》尝试着描写和表现理想的男女之爱”(陈晖 2010:5)。换言之,张爱玲并非完全以政治为考虑来写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而是在既有题材上,将背景的设定随着政体而稍加变动,实际上无损于原本的艺术构思。试看随手摘录的《十八春》第五节中的一段情话:
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表示他爱她。他所爱的人刚巧也爱他,这也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他太快乐了。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 --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他只能够在寒夜的街沿上踯躅着,听听音乐 (梁京1951:95)。
这样的基调虽然随着剧情历经多次压抑与改写,但仍能看出张爱玲对理想之爱的渴求,以及某种难以言明的哀感。这种理想之爱的描写实与任何政治无关;甚至与之完全相反,它与任何政治都可能有关(“政治要找上你”),但这无损于小说基本的人性关怀——向往爱情。
解放可能振奋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心,但政治之于张爱玲仍是不够熟悉的领域,只能“半强迫”着她的主角们在儿女私情之外还要一同去为人民服务。旨在走向读者群、去寻找读者所喜欢的“趣味”的张爱玲,之所以在自己的通俗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政治议题,恐怕也是人们对一个但爱成名、不问国运的作者某种“隐然”或“自然”的排斥所致。
4.梁京的“另类”阶级想象:重读《小艾》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经学者关注,几乎篇篇小说都不乏充分探讨,已然成就“张学”之名。而本文所举的两部作品可以显示“张学”在未来还大有讨论空间。《十八春》因为有《半生缘》对照,且题材更具有政治敏感度,颇能搏取某些研究者的关注;而研究者对《小艾》的关注,显然是少得可怜,其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小说因政治问题不断删修,导致出现了多种不完整版本。
中篇小说《小艾》讲述的主要是小艾的丈夫金槐去香港谋生,留下小艾在孤岛侍奉姑婆。为挣钱她去当女佣,并辛苦劳作养活婆婆与丈夫兄弟一家。根据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并不喜欢《小艾》,并且是“非常不喜欢《小艾》,有人说缺少故事性,说得很对”(张爱玲 2010b:210)。她说另有原来的故事,比如小艾曾一度对比自己大七八岁的、主人家的私生子怀有情愫;婚后的小艾努力想发财,但解放让她怅然:“现在没指望了”。可见,《小艾》中的故事原该更加曲折,人性也还是向往有钱的生活,这才是张爱玲式的市民小说。
根据将此作重新“出土”并重刊的陈子善 (2004: 131)考据,《小艾》最初于 1951年 11月 4日至 1952年 1月 24日在上海《亦报》第三版连载,后来它与修订后的《十八春》一起在 1951年 11月正式面世;被发掘后,《小艾》1987年 1月在香港《明报月刊》重刊,其时章节做了调整;1986年 12月 27日至 1987年 1月 18日在台湾《联合报》副刊重刊时又作了删节,收入 1987年 5月皇冠出版社出版《余韵》的《小艾》则是新的删节本。1992年另有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参见高全之 2008:124)。真正以《亦报》的连载版本为准、未经删修的版本在出土二十年后,方得以“首次以本来面目与读者见面”。它收录在陈子善主编的《郁金香》中,共分 81节,与连载时正相符合(陈子善 2006:469)。2010年再次重新出版的《小艾》皇冠版,依然不是完整版,只收录了净化后的 70节的内容,这显然无法当作发表时的“善本”来研究;且整篇小说的背景交代亦因删修而完全难以掌握。读者终究还是不免于被“规定”如何接受张爱玲,而不是自由“选择”是否接受张爱玲。
皇冠版《小艾》只 70节,并且未有证据显示为作者亲自删修。但自其 1987年出版后,一直未见张爱玲提出异议,因而不妨视之为作者极不喜欢的状态下的一种妥协或默许。皇冠版《小艾》由于具有作者授权出版的优势,应当是目前流通最广的版本;但对照亦报连载版的原文,会发现最大的修改差异当是删去了对国民党与蒋家政权的有关批评。
“亦报连载版”原文显然极为符合当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氛围。例如,连载中描述金槐自重庆回来后,发现在内地尽是贪污腐败、投机囤积的行径,而且“由上面领着头”,根本没在抗战:
……到内地去了这几年,看见许多事情都是使他灰心的,贪污腐败,由上面领着头投机囤积,哪里有一点“抗战建国”的气象,根本没在那里抗战。现在糊里胡涂的算是胜利了,倒又打起内战来了,真觉得前途茫茫,不堪设想 (张爱玲 2006:311-2)。⑦
此外,“连载版”上还有关于“蒋匪帮”的批评:
那是蒋匪帮在上海最后一个春天了,五月里就解放了。楼底下孙家上了国民党的当,以为他们在上海可以守三个月,买了许多咸鱼来囤着。在解放后,孙家连吃了几个月的咸鱼,吃得怨极了(318)。⑧
而从蒋匪帮被赶出上海到上海获得解放,这两段情节紧接在一起,转换速度极快,表明金槐与小艾的生活一下子由地狱到了天堂,过程全省略了。解放后,大家都积极融入新社会,这一大段在皇冠版中也全被删去:
解放后,金槐非常热心的学习,又像从前小艾刚认识他那时候一样,总拿着本书,到印刷所去也带来带去,在电车上看。在家里也常常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史讲她们听。小艾虽然很喜欢听他发议论,她彷佛有一种观念,认为理论是男子的一种装饰品,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得意的微笑静静听着,却不求甚解。她最切身地感到的还是现在物价平稳,生活安定,但是人是健忘的动物,几天好日子一过,把从前那种噩梦似的经历也就淡忘了(318)。⑨
这里,我们仍不难看到张爱玲的机智。虽然是附和主流话语,但对金槐的社会主义议论,小艾认为是“装饰品”;怎至于过了几天好日子,就忘了过去的噩梦,全知的叙事者也彷佛意在言外地透露着,好日子真的会就此永远延续吗?显然,张爱玲在唱和声中,仍对新时代的影响力保持高度警戒。若依上述推论,面对小说的写法与情节的走向,我们是否该把这一篇小说视为张爱玲迎向新政权的主动表态?亦或是言不由衷?又或者,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妥协之外的“另类”阶级想象?
陈子善《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一文便正面肯定,张爱玲在小说中真切展现了小艾被卖到景藩家后蒙受的种种欺凌和屈辱,更以细致的笔触抒写小艾的痛苦到挣扎等心理状态:“……从而对社会的不平透出了张爱玲式的人道主义的呼声。作者对小艾充满同情和爱怜,为她终于获得新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陈子善 2004:135)。这样的解读似乎表达了张爱玲对于某个阶层的关怀,特别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等于是呼应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基调。
其实,张爱玲老早在 1944年的《写什么》一文里说过,她不会写无产阶级故事,但对比她解放后创作《小艾》,她终究还是写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故事。当年会提起这话头,想必与左翼作家对她的批评有关,而她则刻意暴露了连谁是无产阶级都无法分辨的能力,读来不免有些微讽刺的意味: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张爱玲 2010a: 161)。⑩
如今她真写了无产阶级,是否就违背的理念,纯然只是迎合新政权?笔者认为,《小艾》如果按照原有的故事写,那该是一个无产阶级女性努力想挣钱改善生活的版本,此事已由张爱玲自己言明。即令最后发表的《小艾》,不为张爱玲所喜,恐怕也不为多数评者所喜,笔者仍想强调,张爱玲式的“翻身故事”,与共产党式的“翻身故事”,其差别当在“人性论”与“斗争论”的不同。除高全之 (2008)由“人性倾轧”对小说中妻妾争权的诠释极为到位外,《小艾》当中对蒋帮的批评与对社会主义之为“装饰品”的反讽,显然是张爱玲从无产阶级“女性”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另类”的阶级观察。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小艾这样平凡的女性,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联系着爱情的想望,而这正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在第 64节中,一段小艾要回复金槐来信的情节,就写到小艾听金福念出金槐信中描述在香港工作受苦的状况时,“两行热泪直流下来”。可她却不让金福为她写信,彷佛不愿让亲人看出她心里的秘密,刻意去找个非亲非故的测字先生写,其实信里无非是些问候之语。然而以下这段细腻的描写,方能看出追求“现世安稳”的张爱玲,是如何让一对无产阶级夫妻(ㄚ头与排字工人)也拥有了属于他们那种世界的爱情:
她现在也略微认识几个字了,信写好了,自己拿着看看,不是自己写的,总觉得隔着一层。她忽然想起来从前他给她的“冯玉珍”三颗铅字,可以当作一个图章盖一个在信尾。他看见了一定要微笑,他根本不知道那东西她一直还留着(张爱玲 2006:303-4)。
笔者认为,张爱玲的《小艾》正是她发展得并不完全的“另类”阶级想象的产物。一方面是由于不够熟悉题材,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政治妥协的缘故。倘若能够在作品中窥见张爱玲的另类阶级观,则正可尝试从新的解读视角重读《小艾》。
基本上,张爱玲的文学并非没有政治性格,甚至也可以说,张爱玲是很有“智慧”地与现实政治进行对话后,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政治叙事来呈现。但如果不欲刻意地扭曲历史事实,仅因个人自私的人生态度而选择不写或写政治,那终究还是一种“不够爱国”的坦诚;因为她并没有写出完全合格的无产阶级小说与土改小说,只是流亡在政治体制规训的罗网边缘,写她所能知道的“人性政治”,这又岂是“善变”、“自私”等字眼可以穷尽的状态?
当年的政治压力诚如上述,张爱玲不免会自愿或非自愿地向主流话语靠拢,但在现世的评论者眼中,这种靠拢都是刻意而非真诚的表态。问题是我们如何要求一个小说家要真诚讴歌统治者,才算拥有被论者肯定的识别证?这完全是以政权中心思考出发的判断,而不是以“个人”的角度为其设想的评断。换言之,这样的“动机论”评论,恰好让我们照见张爱玲不讴歌则无法离境、讴歌则被视为伪装、不断变更讴歌对象则被视为变节这种只有“境内流亡者”才能拥有的特殊待遇。
5.代结语:作品尚在流亡
虽然有论者认为,张爱玲在沦陷区时期,曾写下《自己的文章》表明心志,那种“不妨苟且性命于乱世、但求个人现世安稳的乱世偷生之道”虽没有政治妥协色彩,但妥协的人性迷思却消解了“人的文学”的人学与文学尊严(解志熙 2009:395)。换言之,妥协于日本侵略的状态下而不思保留被侵略者的尊严。随后,她又在战后初期,甚至解放后,以文字呼应了新开启的时代,写下《十八春》与《小艾》诸作。但这究竟是一个文人的“人间失格”,导致“时穷节不见”,还是一种饱受帝国主义侵扰与国家内部争斗的中国人难以自我掌握生命走向,而终于流亡飘零的精神状态?
诚然,面对各个当权者,张爱玲不够勇于抵抗,也太过易于妥协。强调“现世安稳”的她,对读者所造成的有意无意的“影响”,都有被检讨的空间。但要强调的是,若舍去道德与文学的成见,张爱玲可以是一个中国境内流亡文学的案例。她让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语境下,一个文人将如何失去心灵的坐标;在共产主义环境中,一个个人主义者将如何袭用别人的话语以求一夕安稳。当然,如果再注目于张爱玲的海外流亡经验,则将看到反共主义与资本主义又将如何驱使一个孤身流亡的女作家必须写作一些“委托创作”(commissioned)的作品。流亡,始终是张爱玲的创作语境;甚至,她也流亡于自己的亲人家族之间。她的一枝笔,在她生存的任何时空,显然有爱之者;但她为生存所写的作品,较诸其它作家,显然领受了更多不够忠诚与投机的质疑。
已经被政治染色的作品,不需也无法恢复创作前的样貌,但后世的读者却不应只是接受出版者(为商业考虑)或政治人物 (为忠心爱国考虑)允许的张爱玲形象,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张爱玲的各种可能面貌。梁京(张爱玲)的《十八春》与《小艾》当年在《亦报》上连载的最初版本,迄今未在台湾的皇冠版全集中出现。那么,半个世纪过去,如今张爱玲看似已重返她在当代中国文学史该有的位置上,但她的某些作品却依然处于流亡的状态。我们理当呼吁出版更完整的张爱玲全集,如此“张学”的建构才算有真正完备的基础。
附注:
①该书 1967年 2月至 7月在台湾《皇冠》月刊连载修订版时就先取名《惘然记》,后于1969年3月,以《半生缘》为名出版。
②引自全文连载第 189回。初次连载的《十八春》原见于1950-51年之《亦报》,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承虎尾科技大学河尻和也教授提供复印本,特此志谢。
③此亦报社出版之修订版《十八春》,现藏上海图书馆。承北京市社科院张泉教授提供复本,特此志谢。
④沈鹏年还曾提及,文代会后,张爱玲被夏衍吸收入“剧本创作所”工作,这点尚待核实。出处请参见沈鹏年 (2009: 246)。
⑤此作本是随写随刊,而非先有完稿。
⑥Potboiler之说见张爱玲 1966年 10月 2日致夏志清的信,而“为糊口而写的”则为夏志清之译语。请参见夏志清(1997).
⑦亦可参见《明报月刊》1987年 1月号第 112页。
⑧亦可参见《明报月刊》1987年 1月号第 114页。
⑨亦可参见《明报月刊》1987年 1月号第 115页。
⑩原刊上海《杂志》1944年第 13期第 5-8页。
陈晖.2010.《十八春》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P].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办“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陈子善.2004.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陈子善.2006.编后记[A].张爱玲.郁金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468-469.
杜英.2008.离沪前的张爱玲和她的新上海文化界:从《十八春》的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A].陈子善.重读张爱玲[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351-377.
高全之.2008.张爱玲学 (二版)[M].台北:麦田出版.
金宏达.1994.论《十八春》[A].于青.张爱玲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389-402.
柯灵.1985.遥寄张爱玲[J].读书(4):95-102.
梁京.1950.十八春 (第十三章-九)[N].亦报 30-9.
梁京.1951.十八春[M],上海:亦报社.
沈鹏年.2009.行云流水记往 (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水晶.2000.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台北:大地出版社.
魏绍昌.2002.在上海的最后几年[A].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38-144..
夏志清.1997.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J].联合文学 151(5): 59-60.
解志熙.2009.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
张爱玲.2006.郁金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2010a.华丽缘(张爱玲典藏 11)[M].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张爱玲.2010b.惘然记(张爱玲典藏 12)[M].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O n Exile”in Shanghai:Re-reading Liang Gin(Eileen Chang)’s Eighteen Springs and Xiao I,
by CHEN Jianzhong,
I206.7
A
1674-8921-(2011)06-0052-05
陈建忠,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子邮箱:chicchen@m x.nthu.edu.tw
(责任编辑 林玉珍)
Ever since 1949,Eileen Chang experienced a typical mental course of writers on exile,thus being an important case for the study of exile literature in East A sia. Intending to explore Zhang’s mental course of adapting to the times by revising her works,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exile in the country”, analyzes different versions ofEighteen SpringsandX iao Iwritten by Zhangwith the penname Liang Gin. It is found that though she had resigned herself to the status quo superficially,she was still out of accord with the times as both her spiritualworld and literary pursuit deviated from the leading trend of the times,giving her works as well as herself a tinge of ex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