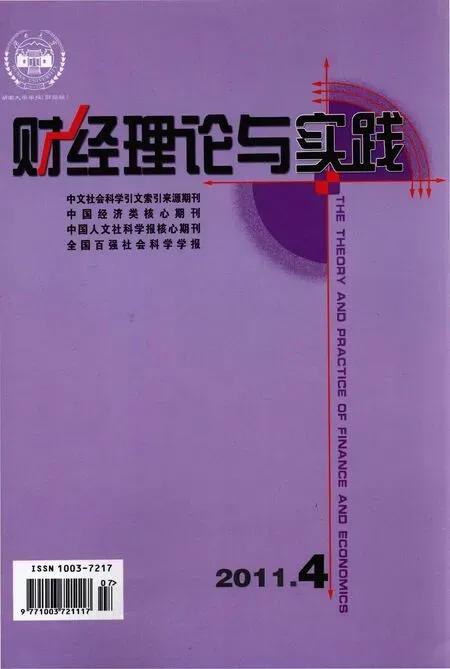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代际交换失衡的影响分析
2011-04-02聂焱
聂 焱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外出农民工主要是青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35岁以下民工占全部民工的约80%[1]。对流出地而言,外出务工人员的这种人口学特征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年龄结构,对具体的家庭而言,外出务工人员的这种人口学特征则影响到家庭的代际交换,甚至加速了家庭代际交换的失衡。其严重后果就是使农村老年人“老无所养”,这会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力是增加经济收入,外出务工后对老人照料的缺失将用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来补偿。姚远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可能造成家庭照料资源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可能增强家庭的经济支持力度[2]。即劳动力外流只是改变了代际交换的方式,而不会改变代际交换的强度,更不会导致代际交换的失衡。笔者通过在劳动力流出地的考察发现,外出务工人员的确把自己打工的部分收入带回农村老家。但是,通常只有未婚的外出务工者才会把钱带给父母。在农村,通常只认可已婚子女的赡养义务,如果子女没有结婚,即使父母已经年老体衰,也会认为是父母没有完成责任,而不认可未婚子女有养老的义务。而已婚的具有养老义务的外出务工者一般都把钱交给留守在农村的妻子,夫妻子女都外出的家庭则很少寄钱回来,并没有给老人提供更多经济支持的迹象。因此,笔者提出相反的假说,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不仅改变了代际交换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代际交换的强度,加速了家庭代际交换的失衡。
二、家庭代际交换模式及其演变
(一)抚养—赡养模式
家庭代际交换主要是发生在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交换关系,亲子关系又被称为“抚养—赡养”关系。“抚养—赡养”模式由费孝通提出,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属于“抚养—赡养型”,即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赡养乙代,费孝通将其概括为“反馈模式”[3]。这种“抚养—赡养”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代际交换关系,交换的内容包括财产、照料、情感三部分,即父母养育未成年子女,给子女提供财产、照料、情感三方面的支持,父母老了以后,资源的流向发生逆向变化,由已成年的子女来赡养他们的父母,同样给老年父母提供财产、照料、情感三方面的支持。由于时间的跨度太长,这种代际交换与一般的交换关系不同,正如费孝通把子女成年的这一刻作为时点把这个交换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抚养阶段和赡养阶段,抚养阶段就是父母单方面付出的不公平交换,赡养阶段则是子女单方面付出的不公平交换。在每一个阶段对资源的提供者来说更像一种义务而不是交换。因此,要想保证这种交换关系顺利进行,就需要以下条件:第一,相互提供的资源量大致对等,即抚养成本和赡养成本大致相当。第二,资源的提供者有能力和意愿提供资源,即年轻父母有能力和意愿抚养子女,成年子女有能力和意愿赡养父母。
在传统社会,对大部分的家庭来说,抚养和赡养的成本都不高。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孩子们很小就参加了劳动。费孝通就指出:“孩子在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时候,很早就参加了家庭的共同工作,成了分工结构中的一分子。……在一个家庭中,除了在襁褓间的婴孩,孩子们时常有一定的职役。他们喂猪,放牛,割草,采柴;稍长一些就参加重要的生产劳动”[4]。另外,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就意味着对孩子的教育成本也低。抚养孩子对大部分的家庭都容易承担。在当时,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很低,1936年,中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为33.34年,女性为33.10年[5](P76),绝大多数老年人在刚刚步入老年的时候死亡,减少了子女赡养的成本。另外,家庭的子女数普遍很多。夏业良就提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在5个以上的家庭相当普遍,不少家庭子女数量达到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之多[6]。众多的子女也分担了赡养压力,赡养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在抚养和赡养的成本都不高的情况下,代际之间相互提供的资源量大致对等,资源的提供者也有能力提供资源。另外,为了保证资源的提供者有意愿提供资源,传统社会的道德舆论作了严格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传统社会的代际交换关系得以顺利进行。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正处于从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进入以市场经济为表征的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结构性的变动破坏了代际交换的条件。就抚养来说,成本仍然很低,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仍具有传统社会特征,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孩子们很小就参加了劳动。由于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加上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不高,通过加入现代教育体系而获得体制内就业的机会下降,农村孩子的辍学率很高。2005年,贵州省在校小学生人数为473.76万人,而在校初中生则只有209.09万人[7],近似地可估算在初中阶段流失了264.67万学生,这些流失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学生。不进入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农村孩子的教育成本就不高。可见,对农村父母而言,抚养孩子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就赡养来说,由于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增加(我国男性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由 1936年的33.34岁上升到2000年的69.63岁)和孩子数减少(我国乡村总和生育率从 1950年的 5.96下降到 1992年 1.81)[5](P40),赡养成本大大地上升了。对家庭来说,由于交换的资源量不对称,抚养成本低,赡养成本高,这种成本的变化影响到了代际交换行为。也就是说,由于子女提供的资源量大大超过了父母提供的资源量,子女提供资源的能力和意愿受到了影响,许多家庭只愿意抚养子女,而不愿意赡养老人。代际交换的资源主要包括时间和物质财富,而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了赡养者的缺位,不能保证时间的跨期提供,另外,由于在外务工收入低,不能保证物质财富的提供,再加上频繁的流动弱化了人们的赡养意愿,加剧了代际交换的中断。
(二)子女赡养意愿由自律转化为他律
劳动力外流削弱了子女给老人提供资源的意愿,即赡养意愿。子女的赡养意愿由群体的价值观决定,而价值观是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不仅约束着人们的养老行为,也支配着人们的赡养意愿。在中国,与赡养有关的道德观念被称为孝道,孝道是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的有力工具。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受到劳动力外流的影响,传统的孝道观遭受到了来自城市的现代文化的冲击,同时也改变了子女的赡养意愿。
群体的稳定是维护传统孝道观念的基础,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恰恰破坏了这一基础。第一,劳动力外流从群体外部带来了孝道观的革新力量。外出务工人员来到城市,潜移默化地受到城市所包含的独立、自由等现代观念的影响。外出务工人员作为媒介,又把这些现代观念带到乡村,这些现代观念形成了改变甚至瓦解孝道观的力量。第二,劳动力外流从群体内部削弱了孝道观的力量。孝道观念对个体的约束是通过初级群体来发挥作用的,因为个体的位置被牢牢地嵌在群体中,成员之间形成有效的监督。如果流动变得容易,初级群体的控制能力就会因成员的大量离去而削弱。此外,群体成员有了逃离初级群体的机会,初级群体的软控制对他们就不再有效。孝道观念及保证孝道观念被实行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以后,受到利益的驱使,子女们的赡养意愿也同样会弱化。
流动削弱了初级群体的自律性控制力量,从而弱化了子女们的赡养意愿。另外,流动还通过空间距离拉大、亲子互动频率减少来直接弱化子女的赡养意愿。再加上年轻一代人的家庭关系因为城市的示范效应而具有现代特征,即年轻一代的婚姻关系取代亲子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家庭结构核心化,个体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发生了变化。对老年人来说,亲子关系是维系家庭的基础,因此,老年人在主观上认可的家庭成员包括自己、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子女、子女的配偶及孙子女。而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在主观上认可的家庭成员只包括自己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父母被剔除出来。这就直接从内部导致了子女的赡养意愿减弱。
另外,农村劳动力外流促进农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社会控制的手段就随之从道德的自律控制为主转变为法律的他律控制为主。但是,法律的控制有着固有的缺陷。首先,法律无力控制生活的隐秘部分,而在赡养中出现的许多越轨行为都属于个人的隐秘空间。其次,法律的制裁只能触及人们的外部行为,而很难通过制裁改变被制裁者的价值观[8]。由于法律具有这些固有的缺陷,对赡养行为的控制就应该既适用法律也适用道德,当道德规范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而削弱,对赡养行为的监控就会变得无力。同时,道德的削弱不仅使赡养行为失去监督,还使赡养行为失去了可供参考的制度框架,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不孝变得模糊,老有所养就难以得到保障。
三、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子女提供资源的能力
1.子女提供时间资源的能力。外出务工主要有三种形式:丈夫单独外出型、夫妻共同外出型、妻子单独外出型。(1)丈夫单独外出型的,一旦丈夫外出,过去由丈夫承担的事务就由妻子承担,妻子照料老人的时间势必要减少。在外的丈夫受到空间距离的限制,其所提供的时间资源只能通过打电话或写信等方式给老人提供情感慰籍。但事实上,外出者打电话或写信给老人的很少。据调查发现,贵州省麻江县贤昌乡甲耳村全村劳动力外流率高达72%,大部分老人反映子女不常与家里联系,仅有重要事情告知时才往家里打电话,甚至有几户家庭反映外出人员从不与家庭联系,更谈不上给老人提供情感慰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出务工者从事的都是很辛苦的工作,没有精力与家庭联系。一项针对贵州农民工生存状况所做的调查发现,贵州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10.34小时,工作12小时以上的占19%,10~12小时的占43%,8~10小时的占26%,8小时及其以下的仅占12%。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劳动强度大,外出者根本就没有精力给老人提供情感慰籍。(2)夫妻共同外出型的,却没有能力把老人接到身边,就住房来说,农民工自己租房子住的占48.2%,住集体宿舍的占42.2%,自己有住房或住亲戚朋友家的占9.6%……调查对象中,41%的人把孩子带在身边读书;49%的把孩子留在家中[9]。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自己的住房,老人甚至孩子都只能留在家里,老人不仅完全失去了照料者,而且有时候还要帮助照顾留守老家的孙子孙女。(3)妻子单独外出型从表面上看与丈夫单独外出型很类似,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分工的差异,男性普遍没有受过做家务的训练,妻子在家里承担的事务不是由丈夫承担,而是由老人承担,老人不仅没有人照顾,还要在生活上照顾儿子及孙子女。另外,男性由于生理的原因通常都不擅长表达感情,由他们给老人提供情感慰籍是不现实的,外出的妻子一方面没有精力给老人提供情感慰籍,一方面由于与老人没有血缘关系及与老人成长环境的不一致而不能给老人提供情感慰籍。可见,劳动力外流削弱了子女给老人提供时间资源的能力。
2.子女提供物质财富的能力。因为赡养不仅需要人力更需要财力,如果子女的经济条件较好,完全可以通过给老人雇用照料者的方式来提供照顾。换言之,财富是通用性资源,可以用来购买时间。所以,第二个因素即物质财富的提供才是决定代际交换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外出务工使农村老年人子女的收入增加了,但增加的收入必须达到一定的阈限值,才有可能会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阈限值由经济状况决定。经济状况的测量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经济状况是把过去的收入与现在的收入进行比较,按照这种测量方式,外出务工者的经济状况的确有了提高。相对经济状况是一个结构指标,是把务工者的收入与他的需求或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作比较,按照这一指标进行测算,外出务工者的经济状况就不一定有了提高[10]。
对个体的生活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是相对经济状况。因为对利益的追逐是流动的动力,务工者的收入虽然比他自己务农时高,但流动也同时改变了流动者的需求和他生活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在当地与其他村民相比是比较高的,收入与需求相比或与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是很高的。然而,来到城市后,受到一系列有歧视倾向的制度的制约,他们并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工作机会、收入及其他待遇相对城市人来说都很低。根据《2007贵州统计年鉴》、《2007广东统计年鉴》、《2007上海统计年鉴》、《2007浙江统计年鉴》和贵州财经学院所做的贵州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提供的数据计算,虽然贵州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是在家务农收入的近5倍,但其平均月收入仅为贵州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84.26%,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更低,只有广东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62.17%,上海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63.44%,浙江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56.91%[11,12]。这说明,农民工的相对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收入的增加远远没有达到增加老人的经济支持的阈限值,结果导致外出务工者给老人提供物质财富的能力的下降,老人没有享受到外出务工的好处。
四、结 论
代际交换是亲子双方通过“抚养—赡养”来进行资源交换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交换关系,“抚养—赡养”关系就应该具有互惠互利的特征。在我国农村,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增加和家庭生育孩子数减少,抚养成本变化不大,而赡养成本则上升了,“抚养—赡养”的平衡关系逐渐被打破,赡养阶段出现了难以为继的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在三个方面加速了“抚养—赡养”关系的失衡:一是赡养意愿的弱化,二是提供时间资源即提供日常照料和精神慰籍能力的下降,三是提供财富资源即提供经济支持能力的下降。许多家庭只愿意抚养子女,而不愿意赡养老人。这种情况对老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养老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社会养老必须充分发挥作用,以解决赡养者赡养意愿弱化和赡养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次,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来强化年轻人的赡养意愿;第三,改善农民和外出务工者的相对经济状况来提高年轻人的赡养能力。
[1]章铮,杜峥鸣,乔晓春.论农民工就业与城市化[J].中国人口科学,2008,(6):149.
[2]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149.
[3]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A].费孝通社会学文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86.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67.
[5]胡伟略.人口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夏业良.家庭规模与社会分工[N].北京青年报,2002-10-14.
[7]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贵州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8][美]E·A·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6.
[9]赵勇军.贵州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EB/O L].http://www.gz.xinhuanet.com,2007-06-12.
[10]聂焱.从经济的角度考察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3):73-79.
[11]白万平.农民工流入地劳动市场均衡工资与价格歧视实证研究——基于贵州农民工调查数据 [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3):75-81.
[12]侯风云,伊淑彪.行政垄断与行业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1):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