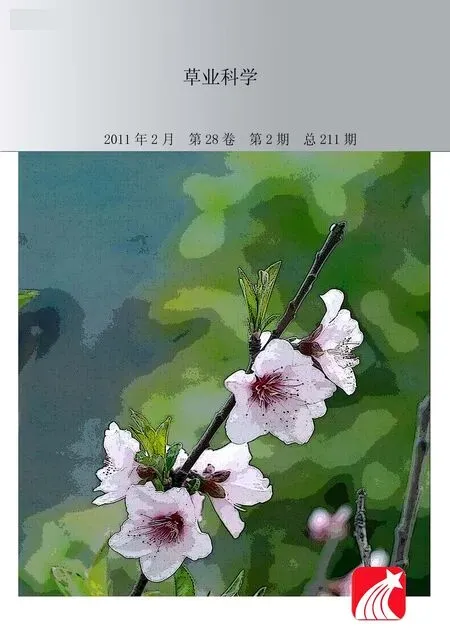草地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与生态阈值研究进展
2011-04-01张泽华王广军
刘 艳,张泽华,王广军
(1.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2.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北京 100081)
我国拥有近4亿hm2草地,占国土面积的41.7%,是我国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及超载过牧等原因造成了沙化、退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导致蝗虫等生物灾害的不断发生。1999年以来我国北方草原连年发生大面积蝗灾等生物灾害,草地生态系统步入草场退化-害虫猖獗-草场进一步退化的恶性循环[1]。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1999-2006年,该区连续暴发蝗灾,累积草原蝗虫发生危害面积达0.622亿hm2,虫口密度均在50头/m2以上,最高可达650头/m2[2]。蝗灾不但给畜牧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威胁着我国北方草原生态安全。因此,开展草地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economic threshold)与生态阈值(ecological threshold)研究,对于有效指导蝗虫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害虫防治经济阈值的研究进展
害虫防治的经济阈值问题是现代害虫管理系统中进行优化决策的基本依据,也是使害虫治理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与生产措施相联系的唯一纽带。1959年Stern等[3]最早提出了经济阈值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害虫的某一密度,在此密度时应采取控制措施,以防种群达到经济危害水平”。此后,经济阈值的概念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与深入探讨。Edwards[4]将经济阈值定义为“可以引起与控制措施等价的损失的害虫种群大小”。Headley[5]提出的定义是“使产品价值增量等于控制代价增量的种群密度”。Norgaard[6]提出损害阈值(damage threshold),定义为“引起经济损失的最低种群密度”。在我国,盛承发先生[7-8]曾在该领域进行过全面的综述与讨论,他给经济阈值的定义表达为“害虫的某一密度,达此密度时应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否则,害虫将引起等于这一措施期望代价的期望损失”。缪勇和许维谨[9]在对经济阈值定义的讨论中,认为经济阈值应是“针对某一密度(含预测)的害虫种群,边际成本函数等于边际产值函数时的种群密度。超过此密度时,应适时采取控制措施,将种群密度压制至该密度水平,可以获得最大净收益”。实际上,经济阈值不同于产量损失阈值和经济损害水平,因为经济阈值作为害虫防治的决策依据,要综合考虑到防治成本、产品价格、生态效益、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是一个经济生态学参数,是进行防治决策的依据,是生产者关注的焦点[10]。
国内外在农业害虫防治经济阈值领域的研究较为广泛。Naranjo等[11]对棉花上烟粉虱[Bemisiatabaci(Gennadius)]的防治经济阈值开展了研究;Szatmari[12]研究了鳞翅目昆虫对树莓(Rubusidaeus)损害的经济阈值;Singh[13]对印度西部一种有斑点的螟蛉(Eariasspp.)的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Diaz[14]研究了烟草(Nicotianatabacum)上蚜虫(Myzuspersicae)的经济阈值;Bharpoda[15]在印度研究了棉铃虫(Helicoverpaarnigera)防治的经济阈值;Ukey等[16]对辣椒(Capsicumfrutescens)螨类的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Afzal等[17]对大米蛀虫(Scirpophagaspp.)的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经济阈值研究的报道也较多。盛承发[18-19]、高宗仁等[20]对棉铃虫的经济阈值均进行了探讨;曹莹等[21]对危害水稻(Oryzasativa)的中华稻蝗(Oxyachinensis)、稻螟蛉(Narangaaenescens)和粘虫(Mythimnaseparata)的经济阈值进行研究,并提出水稻孕穗期是进行化学防治的最佳时期;赵利敏和张海莲[22]报道了灰翅麦茎蜂(Cephusfumipennis)的经济危害水平和经济阈值,为麦田生产提供了防治的参考依据;此外,牟少敏等[23]对苹果黄蚜(Aphiscitricala),蒋杰贤等[24]对菜青虫(Pierisrapae),姜鼎煌等[25]对苦瓜(Momordicacharantia)地的瓜实蝇(Bactroceracucurbitae),卢巧英等[26]对韭菜迟眼蕈蚊(Bradysiaodoriphage)等害虫的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探讨。这些研究基于挽回损失等于防治成本的原则,为害虫适时防治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指标,为农业管理者进行害虫有效控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2 害虫防治生态阈值的研究进展
相对于经济阈值,生态阈值的定义和研究是近些年才受到重视的。1977年May[27]最早提出了生态阈值的概念,指出生态系统的特性、功能等具有多个稳定态,稳定态之间存在的阈值和断点(thresholds and breakpoints)就是生态阈值。此后,生态阈值的概念受到生态学和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展开了学术探讨。Friedel[28]认为生态阈值是生态系统两种不同的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boundaries);Muradian[29]定义生态阈值为独立生态变量的关键值,在此关键值前后生态系统发生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Wiens等[30]认为生态阈值是生态系统的转变带(region or zone),而非一系列的离散点。Bennett和Radford[31]等提出生态阈值是生态系统从一种状态快速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某个点或一段区间,推动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某个或多个关键生态因子微弱的附加改变,如从破碎程度很高的景观中消除一小块残留的原生植被,将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总的来说,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生态阈值有两种类型,即生态阈值点(ecological threshold point)和生态阈值带(ecological threshold zone),在生态阈值点前后,生态系统的特性、功能或过程发生迅速的改变,生态阈值带暗含了生态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稳定状态逐渐转换的过程,而不像生态阈值点那样发生突然的转变,生态阈值带在自然界中可能更为普遍[32]。
目前,基于生态阈值理论的相关研究较少。Noy-Meir[33]研究指出,在放牧草地生态系统中,家畜利用面积的5%是其供应牲畜取食的阈值,这为人类活动干预下草原退化与恢复演替的研究,特别为确定天然草原放牧强度的生态阈值提供了依据[34]。韩崇选等[35]以人工林生态系统中的啮齿动物群落和主要造林树种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人工林群落生态阈值概念,并指出林区啮齿动物管理中的群落生态阈值是单个林木过渡到森林群落的预测指标,考虑的是啮齿动物群落与林木的相互影响,其目的是保证成林。骆有庆等[36]研究表明,森林生态系统中杨树天牛(Anoplophoraglabripennis)的防治生态阈值为4.8个羽化孔,并指出对于以生态防护效益为主的防护林来说经济阈值具有局限性,而应以生态阈值作为害虫防治的参考依据。可见,生态阈值在有害生物防治中不同于经济阈值,这一指标是以生态系统平衡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出发点,对于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探讨害虫的防治阈值具有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3 我国草地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与生态阈值研究动态
前已述及,草地生态系统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在我国也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蝗虫作为一种危害性较大的食草害虫,自古至今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危害屡有记载。据统计从公元前707年至1907年间我国共发生蝗灾739次,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地方志均有蝗灾的详细记载[37]。21世纪以来,我国西部主要草原区蝗灾时有发生,2004年内蒙古草原蝗虫发生面积达529万hm2,2006年新疆草原蝗虫危害面积为203万hm2,甘肃省草原蝗虫高峰期危害面积达197万hm2[38-40]。草地蝗虫防治也因此成为草地植保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开展蝗虫防治阈值(包括经济阈值和生态阈值)的研究与制定,对于控制蝗虫暴发,减少经济损失和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3.1草地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少数学者开始从事草地蝗虫防治经济阈值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某一草原类型区的优势蝗种开展区域性研究,为所研究地区的蝗虫控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防治阈值。1998年,李新华等[41]选择新疆天山北坡蒿子(Artemisiaspp.)+苔草(Carexliparocarpos)+羊茅(Festucavalesiaca)草地植被类型,探讨了意大利蝗(Calliptamusitalicus)防治的经济阈值,得出采用马拉硫磷和敌敌畏控制该区意大利蝗,3龄前的最低防治密度为69头/m2。同样是意大利蝗,张泉等[42]在新疆玛纳斯县南山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区研究后,得到3龄前防治的经济阈值为8头/m2。同一蝗种在两个不同试验区防治的经济阈值相差高达8.6倍,这主要是由于草地群落植被组成、初级生产力等具有较大的差异造成的。因此,不同地区蝗虫种类和草地类型不同,需要根据不同地域的蝗虫危害和防治措施,制定不同的防治经济阈值[43]。西伯利亚蝗(Gomphocerussibiricus)是新疆山地草原的主要危害种,乔璋等[44]采用田间罩笼试验首先计算了虫口密度与牧草损失量的关系式,然后通过测算确定3龄前化学防治西伯利亚蝗的经济阈值为26.8头/m2。乌麻尔别克等[45]采用相同研究方法,对新疆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区主要危害种红胫戟纹蝗(Dociostauruskraussi)的防治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提出化学防治的最低经济阈值为8头/m2。邱星辉等[43]测定了内蒙古典型草原5种优势蝗虫的防治经济阈值,亚洲小车蝗(Oedaleusasiaticu)防治的经济阈值最小,为16.9头/m2,小蛛蝗(Aeropedellusvariegatesminut)最大,为37.4头/m2,分析指出经济阈值与蝗虫的个体大小呈负相关,即个体大者因造成的牧草损失大,其经济阈值小。以上研究主要是结合特定区域的优势蝗种,对单一种群的防治阈值进行探讨,但是草地蝗虫的发生往往比较复杂,常常是多个种群的混合暴发。廉振民和苏晓红[46]对甘肃省祁连山东段草地蝗虫复合防治指标(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指出牧草的损失量取决于受损害量,而蝗虫只是起执行损害过程的作用,因此无论几种蝗虫为害,只在牧草的受损量达到28头/m2时才进行防治,这是关于混合种群蝗虫防治经济阈值的一个新观点。总的来说,我国在草地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领域已经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但是与农业害虫的研究相比仍十分薄弱,且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难以有效指导草地上复杂的蝗虫灾变形势,因此蝗虫经济阈值研究仍将是今后的重点研究课题。
3.2草地蝗虫防治的生态阈值研究 目前,关于草地蝗虫防治生态阈值方面的研究少见报道,本领域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草地蝗虫暴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草地初级生产力和次级生产力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从生态层面上引起的草地退化,在蝗虫防治时单纯考虑经济阈值,不制定以生态效益为主导的生态阈值显然是不利于草地的可持续发展。周寿荣[47]结合草地生态系统,提出草地生态系统在不断降低和破坏其自动调节能力的前提下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的外界压力(临界值),称为生态阈值。当蝗虫的为害超过草地生态系统的耐受范围时,就有可能引起草地退化的发生和加剧,因此,草地蝗虫防治生态阈值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卢辉[48]根据经济阈值的基本概念,挽回损失=防治成本的原则,将补偿作用和盖度的指数引入模型,初步建立了亚洲小车蝗为害草地的生态阈值模型,这个模型把草地植被盖度作为草地生态系统变化的参数,提出随着盖度增加,也是草地类型从荒漠草原-半荒漠草原-典型草原的过渡,亚洲小车蝗防治生态阈值也在增加,例如,盖度值为0.2时,防治指标为3.4头/m2; 0.4时,防治指标为6.0头/m2;0.7时,防治指标为15.3头/m2。 余鸣[49]在研究蝗虫防治生态阈值时,将干旱因子引入了模型中,理论上提高了经济阈值的可用性,但是在他的阈值模型中对于蝗虫与草地平衡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衡量指标模糊,需要进一步的田间试验研究验证。这两篇关于草地蝗虫防治生态阈值的学术论文,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与方向。笔者在文献查阅时未找到更多关于蝗虫防治生态阈值的资料,因此在草地植保领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课题。
3.3经济阈值与生态阈值在蝗虫防治应用中的思考 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与生态阈值之间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二者作为蝗虫防治决策的参考依据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在蝗虫危害达到经济阈值指示的防治指标时,并未危及草地生态平衡,即生态系统尚有一定的耐受能力,这时经济阈值小于生态阈值,在防治时则应以最大限度的挽回经济损失为目的,以经济阈值作为防治指标;另外一种情况是,蝗虫的种群暴发造成的经济损失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草地物种多样性等生态指标遭到破坏,致使草地生态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当以生态阈值作为防治的指标。
4 蝗虫防治阈值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4.1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草地蝗虫发生数量急剧上升,蝗虫灾害频繁暴发,严重影响了天然草地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削弱了草地生态功能作用的发挥,加剧了牧区人民经济负担,威胁到草地畜牧业和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50]。但是,由于我国草原面积大,草地蝗虫种类多,在蝗虫防治阈值的研究方面存在较多问题:1)参考防治指标陈旧,存在“一刀切”的问题,难以适应当前日趋复杂化的草原保护形势;2)不同草原区优势蝗种的生态学研究匮乏,限制了经济阈值与生态阈值的研究;3)偏重于经济损失方面的经济阈值研究,对反映生态平衡的生态阈值缺乏深入研究与探讨;4)国家对草地蝗虫防治及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与投入经费不足,限制了本领域的发展。
4.2建议 当前,我国草原退化形势仍十分严峻,造成了草原退化-蝗虫发生-草原进一步退化的恶性循环。因此,开展蝗虫防治阈值方面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与重要。今后,在本领域应组建包括昆虫学、生态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跨学科团队,对我国草地蝗虫防治的经济阈值与生态阈值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加大对草地蝗虫生态阈值的研究,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提供有力指导。对不同草地类型区和各区优势蝗种开展有重点的研究与探讨,为各区的蝗虫防治提出科学的防治阈值。此外,应进一步争取国家对蝗虫防治研究的投入,以保障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 潘建梅.内蒙古草原蝗虫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J].中国草地,2002,24(6):66-69.
[2] 哈斯巴特尔,高娃,斯琴,等.内蒙古草原蝗虫成灾原因与防治对策[J].内蒙古草业,2007,19(4):52-55.
[3] Stern V M,Smith R F,van den Bosch R.The integ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ontrol of the spotted alfalfa aphid[J].Hilgardia,1959,29(2):81-101.
[4] Edwards C A.The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entomology[M].London:Chapman and Hall,1964.
[5] Headley J C.Defining the Econontic the Threshold[A].In:Metcalf R.Pest Control Strategy for the Future[C].Washington D 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972:100-108.
[6] Norgaard R B.The economics of improving pesticide use[J].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1976,21:45-60.
[7] 盛承发.经济阈值定义的商榷[J].生态学杂志,1984(3):52-54.
[8] 盛承发.防治棉铃虫的新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9] 缪勇,许维谨.经济阈值定义等的讨论[J].安徽农学院学报,1990(2):137-142.
[10] 郝树广,张孝羲.对害虫经济阈值理论的再思考[J].生态学杂志,1998,17(2):71-77.
[11] Naranjo S E,Chu C C,Henneberry T J.Economic injury levels forBemisiatabaci(Homoptera:Aleyrodidae)in cotton impact of crop price,control costs,and efficacy of control[J].Crop Protection,1996,15(8):779-788.
[12] Szatmari S.Lepidoptera living on raspberry in North Hungary,Integrated plant protection in orchards,soft fruits[J].Bulletin OILB-SROP,1998,21(10):35-38.
[13] Singh J.Economic threshold for spotted bollworms,Eariasspp.in cotton,GossypiumarboreumL[J].Journal of Insect Science,1998,11(1):66-68.
[14] Diaz F P.Economic threshold of Heliothis virescens in three tobacco varieties from Cuba[J].Revista Colombiana de Entomologia,1999,25:1-2,33-36.
[15] Bharpoda T M.Evaluation of economic threshold levels forHelicoverpaarmigeraon ‘H 6’ cotton (Gossypiumhirsutum) in central Gujarat region[J].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69(4):304-305.
[16] Ukey S P,Naitam N,Patil M J.Determination of economic threshold level of mites on chilli crop[J].Journal of Soils and Crops,1999,9(2):268-270.
[17] Afzal M,Yasin M,Sherawat S M.Evalu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economic threshold level (ETL) for chemical control of rice stem borers,ScirpophagaincertulusWlk.andS.innotataWl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y,2002,4(3):323-325.
[18] 盛承发.华北棉区第二代棉铃虫的经济阈值[J].昆虫学报,1985,28(4):382-389.
[19] 盛承发,杨辅安.棉铃虫经济阈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生态学报,1999,19(9):720-723.
[20] 高宗仁,赵洪义,秦田丰.河南棉铃虫再猖獗的生态学特点及经济阈值研究[J].棉花学报,1994,6(1):57-60.
[21] 曹莹,曹志强,肖红.3种水稻食叶性害虫对辽粳454为害经济阈值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2,33(1):35-39.
[22] 赵利敏,张海莲.灰翅麦茎蜂(Cephusfumipennis)的经济危害水平和经济阈值(膜翅目:茎蜂科)[J].西北农业学报,2008,17(1):65-69.
[23] 牟少敏,刘忠德,孔繁华,等.苹果黄蚜危害苹果经济损失和经济阈值的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2,33(1):87-88.
[24] 蒋杰贤,王奎武,陈永年.菜青虫为害春甘蓝不同生育期对产量的影响及经济阈值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20(4):312-316.
[25] 姜鼎煌,艾洪木,赵士熙,等.瓜实蝇经济阈值的研究[J].福建农业学报,2006,21(3):207-210.
[26] 卢巧英,张文学,郭威龙,等.韭菜迟眼蕈蚊防治阈值研究[J].西北农业大学学报,2008,17(2):279-284.
[27] May R M.Thresholds and breakpoints in ecosystems with a multiplicity of stable states[J].Nature,1977,269:471-477.
[28] Friedel M H.Range condition assessment and the concept of thresholds a view point[J].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1991,44:422-426.
[29] Muradian R.Ecological thresholds a survey[J].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8:7-24.
[30] Wiens J A,VanHorne B,Noon B R.Integrating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scale in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A].In: Liu J,Taylor W W.Integrating Landscape Ecology in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3-67.
[31] Bennett A F,Radford J Q.Know your ecological thresholds[J].Thinking Bush,2003(2):1-3.
[32] 赵慧霞,吴绍洪,姜鲁光.生态阈值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7,27(1):338-345.
[33] Noy-Meir I.Stability of grazing systems:an application of predator-prey graphs[J].Journal of Ecology,1975,63(2):459-481.
[34] Lv D R,Chen Z Z.Climate-ecology interaction in Inner Mongolia semi-arid grassland[J].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02,9(2):307-320.
[35] 韩崇选,杨学军,王明春.林区啮齿动物群落管理中的生态阈值研究[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5,20(1):156-161.
[36] 骆有庆,宋广巍,刘荣光.杨树天牛生态阈值的初步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9,21(6):45-51.
[37] 游修龄.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94-100.
[38] 陈素华,乌兰巴特尔,曹艳芳.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草原蝗虫消长的影响[J].草业科学,2006,23(8):78-82.
[39] 傅玮东,姚艳丽,李新建,等.新疆草原蝗虫发生面积与大气环流特征量指数模型的研究[J].草业科学,2009,26(12):124-130.
[40] 方毅才.甘肃草原蝗虫现状与防治对策[J].草业科学,2009,26(11):157-160.
[41] 李新华,赵智刚,牛永绮.草场蝗虫的种群密度与受害程度及经济阈值的探讨[J].干旱环境监测,1998,12(3):158-160.
[42] 张泉,乌麻尔别克,乔璋,等.意大利蝗造成牧草损失研究及防治指标的评定[J].新疆农业科学,2001,38(6):328-331.
[43] 邱星辉,康乐,李鸿昌.内蒙古草原主要蝗虫的防治经济阈值[J].昆虫学报,2004,47(5):595-598.
[44] 乔璋,乌麻尔别克,熊玲,等.西伯利亚蝗对草原的危害及其防治指标的研究[J].草地学报,1996,4(1):39-48.
[45] 乌麻尔别克,张泉,乔璋,等.红胫戟纹蝗损害牧草及其防治指标的评定[J].草地学报,2000,2(8):120-125.
[46] 廉振民,苏晓红.牧场蝗虫复合防治指标的研究[J].植物保护学报,1995,22(2):171-175.
[47] 周寿荣.草地生态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39-40,187-188.
[48] 卢辉.内蒙古典型草原亚洲小车蝗防治经济阈值和生态阈值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2005.
[49] 余鸣.蝗虫生态阈值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2006:328-331.
[50] 孙涛,赵景学.草地蝗虫发生原因及可持续管理对策[J].草业学报,2010,3(19):2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