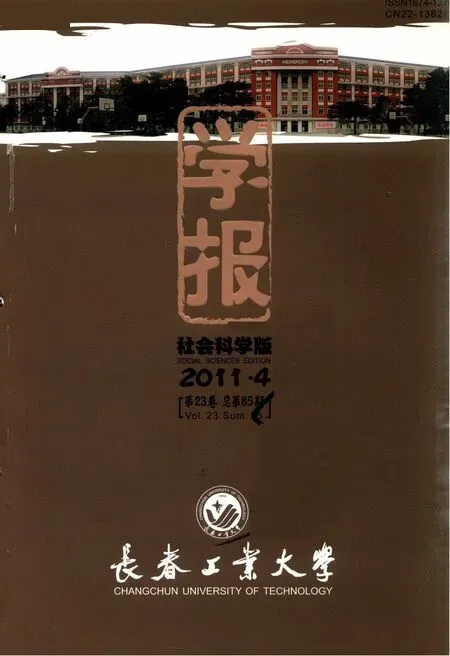地理景观、位置感与身份建构
——《爱药》的生态视角解读
2011-03-31张明兰
张明兰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223003)
地理景观、位置感与身份建构
——《爱药》的生态视角解读
张明兰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223003)
厄德里克在《爱药》中描写了印第安人与大地互为一体的地理景观,揭示了印第安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命运,同时关注印第安人的精神生态,展现了位置感与身份建构的血脉关系,为处于文化边缘状态的印第安人寻得一条出路。这体现了当代生态文学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
《爱药》;地理景观;位置感;身份建构;精神生态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印第安本土作家作品中独特的生态情怀和生态智慧开始得到关注和研究。在西方学界,2001年以后出版的一些重要生态文学文集,如《文学和环境:自然和文化读本》、《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判》以及《文学和自然,1600一2000:生态文学四百年》,都收录了以斯科特·莫马迪 (N.Scott Momaday)、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和路易斯·厄德里克 (Louise Erdrich)等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当代美国本土作家的作品,并对印第安人的自然观十分推崇。①Loraine Anderson,Scott Slovic and John P.O’Grady eds.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New-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1999);Laurence Coupe.ed.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riticism (London& New York:Rouledge,2000);Bridget Keegan and James C.Mckusick eds.Literature and Nature,1600-2000:Four Centuries of Nature Writing (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2001)
崇尚自然于印第安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通过对莫马迪、西尔科和厄德里克作品的细读,我们会发现由于印第安人在白人世界里处于边缘化的生存境况,印第安作家的自然书写中浸透着深重的历史、种族、政治和文化因素,几乎都涉及到土地、地理景观、位置感、身份认同等问题。这些土著作家力求从地域环境、部族文化和传统中寻得一条重建身份的途径,为文化迷失中的印第安人找回自我。从生态视角看,他们的作品蕴含着更丰富的生态内涵,不仅关注自然生态,更加关注印第安人的精神生态。
厄德里克的《爱药》就是这样一部思想意蕴丰富的杰作,该作品曾获得1984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与《洛杉矶时报》评选的1985年度最佳小说奖,与后来的《甜菜女王》(1956)、《轨迹》(1988)、《宾戈宫》(1994)一起构成了印第安小说四部曲。下面笔者尝试从生态视角对这一小说进行解读。
二、人与大地互为一体的地理景观
关注自然、书写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关系是印第安作家写作的一个常见主题,因为大自然早已根植于印第安部落的传统里。在堪称生态整体观宣言的《西雅图宣言》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姊妹,驯鹿、骏马和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河里泛起的水花,草原上的露珠,小马的汗水和族人的汗水,全都属于一个整体,全都属于一个种族,我们的种族。”[1](P198)西尔科也饱含深情地描绘族裔的土地,“大地是你的母亲”,“天空是你的父亲”,“彩虹是你的姊妹”,“风儿是你的弟兄。”[2](P51)艾伦则更明确了印第安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是大地,大地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这是印第安人生活的核心理念。”[3](P127)
印第安人的世界有着自己的道德和生态伦理,他们与大自然结合为一体,与自然界的万物交流感情、平等相处。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和森林里,靠捕鱼和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简单质朴的生活。近两百年来,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新的土地政策的实施,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印第安人离开生养他们的保留地,进入白人的大城市,为了谋得一条生路,他们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抛置脑后。然而,即便如此,厄德里克在《爱药》中仍然刻画了几个坚守部落传统的老印第安人形象,凸显了传统土著人与大地互为一体的生态情怀。例如,喀什帕家族中第一代女主人玛格丽特曾赤手空拳扑向一头熊,因此得名拉什斯·贝尔(印第安意思为奔跑的熊)。她坚守在北达科他州的土地上,有着内心的坚定和信仰,当大儿子尼科特被送进白人的学校读书后,她悄悄把另一个儿子伊莱藏在房间下面的地窖里。伊莱没有读过书,却熟知大自然,成为居留地上唯一还会下套捕鹿的土著人。到了老年,尼科特早已糊涂,丧失大部分记忆时,伊莱仍然头脑敏锐,传授年轻人雕刻、捕猎、吟唱等印第安技艺,“是这片土地上最了不起的渔夫”。[4](P34)
另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老印第安人是玛丽和露露——尼科特的妻子和情人。玛丽是喀什帕家族的精神支柱,她勤劳、坚韧、宽厚、仁爱。从小遭受基督教修女的非人折磨,但她没有对人类失去信心,她留在保留地上,坚守着对爱药的信仰,帮助丈夫成为酋长,还独立抚养了自己和别人的众多的孩子。
如果说玛丽体现了土著人大地母亲般的情怀,露露体现的则是土著人大自然般的坦荡。露露是由传统的土著代表人物纳娜普什抚养长大的,深受纳娜普什的影响,露露形成了自己发乎自然、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上学时,露露厌恶白人语言的矫饰和虚伪,她怀念母亲口中古老的本族语言,毅然回到了居留地。在居留地上露露找到了归属感,活得快乐自在,“我热爱世界,热爱世界上用雨露滋养的所有生灵。有时,我望着外面的院子,那儿郁郁葱葱,看见黑羽椋鸟的翅膀油亮油亮的,听见风像远处的瀑布一样奔泻翻滚。然后我会张大嘴,竖起耳朵,敞开心扉,让一切都进入我的体内”。[4](P277)尽管和别的男人的来往招致人们对她放荡生活方式的指责,她从不为自己辩解,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坦诚、自然地对待他人。露露不仅顺应着自然法则生活,还深知人与自然万物的关联。在看到野牛的照片时她提醒年轻一代记住,“这些四条腿的,它们以前帮助过我们这些两条腿的”,“…以前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4](P209)
厄德里克在这些老印第安人的故事中再现了传统土著人与土地互为一体的地理景观。《爱药》中这些老印第安人位数不多,却是部族的核心和精神所在。面对白人文化的侵蚀和消费社会的冲击,他们没有迷失,依然遵循传统道德伦理,坚守部族与大地、自然融为一体的信仰。他们深知部族和自然的血脉关联,顺应着自然,把自然法则和部族文化传承给子孙后代,维系着部族的存在和延续。他们对部族传统和土地自然的信仰,使得他们能够引导后辈走出文化迷失的窘境。
值得注意的是,厄德里克在描写保留地地理景观时,特别关注在白人土地和文化蚕食政策下印第安人和大地休戚与共的命运。1887年通过的《土地分配案》,即《道斯法案》,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为由,强制实行土地私有化,把分配给印第安人后余下的土地向非印第安人开放。这一法案的实施使印第安人丧失了大量的土地,也给保留地及大自然带来毁灭性打击。白人砍伐运走了“坚实苍翠的树木”,留给印第安人的是“树木的阵阵呻吟和每一颗大树倒下时大地的震颤”。[5](P9)在厄德里克笔下,印第安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命运何其相似。
在《爱药》开头,也有一段对居留地景象的描写:“干涸的沟渠,毫无生气的庄稼……居留地就在巨大的农场和微风吹过的田地的尽头。……你远远地就可以通过与小山截然相反的东西——地上的坑洞,干涸的泥沼,沟渠里的香蒲花,沼穴——来感受那些小山。……公路越来越窄,七拐和八弯之后驶上了满是车辙、坑坑洼洼的沙砾路。路边沟渠里长着一丛丛的蓝苜蓿。……空气中满是灰尘。”[4](P11)居留地破败的景象,糟糕的交通状况和印第安人生活的窘境可见一斑。
《爱药》中厄德里克也花大量篇幅揭示传统印第安人捍卫土地和自然的英勇精神。小说的露露不仅自己坚持奉行印第安生活方式,坚持部族信仰和传统,而且承担起保护土地的责任。她憎恶白人来到居留地上对土地和自然进行测量切割,并大胆痛斥和揭露,“什么数字啊,时间啊、英寸啊、英尺啊。这一切不过是用来切割大自然的手段罢了。我知道,大自然是无法测量的。”[4](P282)她抗击白人政府,拒绝人口普查员进家门,斥责土地测量员,“如果要测量的话,那就索性量量清楚。你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哪怕是摩天大楼的顶上,都是印第安人的。”[4](P283)她抗拒政府制定的搬迁要求,拒绝搬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坚守在保留地上,就是为了让她那些远离家园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有家可归”。[4](P296)
当白人政府通过酋长尼科特下令印第安人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腾出地方办工厂时,她怒斥尼科特等人:“美国政府扔了几个小钱在地上,你们就迫不及待地跪下,把钱舔起来,甚至不惜把同胞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4](P285)。更有意思的是,在尼科特死后,玛丽和露露这对往昔的情敌结成联盟,带领印第安人抵制白人在保留地上开办工厂,最终以恶作剧方式把工厂砸成一片废墟。露露与玛丽与企图扭曲印第安文化的功利人物对抗时,表现出了传统土著人的勇气和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些传统土著人的自律和对土地的信仰才使北美大陆几千年来保持着自然生态的和谐。
一个地方的景观就是一部历史,记载着区域内世世代代的人们与自然协调、摩擦和融和的过程。对印第安人来说,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部落土地就是他们的位置所在和精神归属。厄德里克对居留地景观和环境的描写倾注了她对居留地的强烈情感。在她看来,部落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岩石、泥土、古树不仅仅是物质实体,而是信息的载体和部落文化的表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印第安作家常常批判白人殖民者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印第安作家的生态情怀和生态意识等同于“环保主义”。在《爱药》中厄德里克把剥夺印第安人与破坏环境并置,凸显了土著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共同命运,目的是希望激发人们对印第安人历史和命运的深思,共同关心印第安人的处境和自然环境的恶化。
三、位置感与身份建构
位置感是生态地域主义的核心概念。20世纪的生态学强调人类与生态共存,因此格外重视位置感。生态学家认为真正的人需要栖身于某个环境中,需要一个居住地,一个进行价值创造的基地,人们不可能脱离环境而获得自由,而只能在环境中获得自由。[6]美国散文作家罗克韦尔·格雷认为:“所有的经历都带有地方色彩;也就是说,所有人类的经历,实际上都是在特定地点发生的”。[7](P493)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玛丽·奥斯汀则认为:“地理环境形成了人的意识及文学,因为地理环境比共同的语言及政治关系具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7](P493-494)加里·斯奈德认为:“位置感,根的感觉,并不仅仅指在某个小村庄定居,然后有一个邮箱,因为处于一特定位置,我们获得最大群落感。群落有利于个人健康和精神,持续的工作关系和共享的关注。音乐、诗歌、故事进化成共享价值、观念和探索。这实为精神道路之根本”[8](P141)。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位置感成为人类生活中最自然最普遍的概念。位置感意味着了解和融入为某地方的一部分,并对这个居住地承担起责任,这种人与某一环境相依附的关系既是生态的,也是精神的。斯奈德等深层生态学家强调人类居住必须要有位置感,应该忠实生态地域以及在居住中所形成的文化,而并非忠实于政府,并指出现代人之所以精神痛苦、身份迷失,就是因为失去了位置感。
位置感和身份认同的关系是美国印第安作家十分青睐的主题。西尔科认为地理景观之于印第安人意义非凡,“好比一种熟悉感,仿佛某些地方就跟父母或亲戚一样”,或者“人以一种熟悉的方式跟土地联系在一起”[9](P2)。在小说《爱药》里,厄德里克也将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爱药》中所描述,保留地的生活是窘迫和艰苦的,也有酗酒、暴力等不尽人意之处,但不管怎样,这是属于印第安人自己的,而走出保留地之后的印第安人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那就是身份迷失。在白人社会里,印第安人无异于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笔下的“透明人”,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无法定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身份问题困扰着这些走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令他们精神迷茫,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无非是地理环境变了,他们失去了位置感,弄不清自己的真实身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因为白人世界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
厄德里克花了大部分的篇幅描写现代印第安人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位置感迷失的精神困境。《爱药》中的老亨利和小亨利都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白人社会获得认可,然而他们收获的却是理想的幻灭和心灵深处的累累创伤。他们被绝望摧毁,生活失去了意义,老亨利把卡车停在铁轨上,撞车自杀;小亨利则沉入河中,自溺身亡。高迪整天沉醉在酒中以此抚慰内心的痛楚,儿子金也是一回到居留地就乱发酒疯。其他如莱曼和贝弗利等人受白人消费文化的影响,变得冷漠和唯利是图,为了利益,甚至出卖自己的同胞。他们在白人的大都市,以扭曲内心和人格为代价爬上中产阶层,但由于他们既切断了与印第安部族的联系,又得不到白人的认同,因而陷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成为红皮白心、无所归属的苹果人。
《爱药》中,厄德里克不仅渲染印第安人在文化冲击下的精神窘境,更着重为印第安人探索一条出路。地理景观、位置感、部族文化传统成为引导印第安人身份回归,医治心灵创伤的有效途径。尼科特是第一批走出印第安文化圈,接受白人文化的齐佩瓦人。他也努力想融入白人社会,做过演员,做过白人的模特,却发现白人“只对印第安人的死亡感兴趣”[4](P127),最终他回到保留地娶妻生子,当上了酋长,相信也只有在自留地他才会获得成功。开篇故事中的琼也是走出去寻找新生活的一位,她长相迷人,被誉为“美国印第安小姐”。外边精彩的世界吸引着她,她曾到大城市当过招待员、美容师,但在那里她处处受到歧视,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期待的生活。她幡然醒悟,明白只有居留地才是她的归属时,却在回家途中迷失了方向,被大风雪埋没。
小说中位置感、传统文化成为引导印第安人身份回归的途径更明显地体现在利普夏这个人物身上。利普夏从小在保留地上长大,是当代印第安药师,他身上有一种神奇的触摸能力,能预知和减轻病人的痛楚。这种触摸神力给了利普夏部族归属感。然而由于受白人文化长期侵袭的影响,利普夏同样也流露出本土居民经历的困境,陷入了信仰危机。他既不认同基督教文化,也对印第安部族传统模糊不清,缺乏坚定的信念。这在《爱药》这个故事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在这个故事中,利普夏试图求助于齐佩瓦部落传统中的爱药来让尼科特回心转意和外婆玛丽重新修好,在苦于找不到爱药时,他用了超市的鸡心冒充爱药,结果把尼科特给噎死了。通过这个故事,厄德里克揭示了年轻一代印第安人渴望回归传统但又无法回归的两难处境。尼科特的死让利普夏感到回归传统的无望,于是他离开了居留地,试图去白人世界寻找归属。在白人世界的游荡生活使得利普夏进一步了解了白人文化,也加深了对部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最后在露露和玛丽的引导下,他踏上了回归的路。露露告诉他:“没有哪个监狱能困住皮拉杰老头的儿子,纳娜普什的男人。你应该为自己是纳娜普什的一员而自豪”[4](P338)。利普夏从露露的讲述中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从外婆玛丽的故事中意识到自己的神力是与部落息息相关的,“现在我认为,我的某些力量可能是从皮拉杰那儿遗传下来的,后来我发现自己又从露露那里继承了她的洞察力,还从喀什帕外婆那儿学会了用一块锡纸就能预知未来的本事。”[4](P343)利普夏从家庭和传统的关联中汲取营养,意识到部落之内的关爱是人与人之间纽带的真正力量。最后他向外婆坦言,爱之药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药物,而是你对它的信任。自身的经历以及长辈的教诲使得利普夏逐渐走上了精神复兴的正途。在部族的土地上,他逐渐找到了位置和认同感,一度失去的神奇触摸能力又恢复了。在印第安文化中,神力是自然的一个部分,神力和一些精神关联被视为奇迹,只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利普夏触摸能力的恢复象征他印第安身份的重新回归。
《生态批评:环境文学和美国印第安文学中创造自我和地点》一书的作者多尼尔·德里斯(Donelle Dreese)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深受印第安人环境哲学的影响,大多数印第安部族文化都敬畏大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处,地理环境对印第安人的意义非凡,是他们确立自己身份的重要媒介,因为“部族身份的根基是口述传统里的创世起源故事”[10](P8),这些故事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与自然景观紧紧联系。对大自然的信仰,使印第安人相信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与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通。因而在印第安作家的作品中,保留地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场所,还引导着故事中的人物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新获取身份认同。深受印第安自然观影响的斯奈德强调人类生活的地理位置,认为没有地理上的支撑点就没有精神上的支撑。对于处于文化边缘境地的印第安人来说,只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立足于群落,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和谐。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成为生态学发展的一个趋向。生态学家认为人类的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并指出现代人精神生态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位置感和家园的迷失,因而呼吁建立一种强调位置感的新型文化。位置感是对人们最古老最根本身份的探询,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归属地和位置,最大限度实现自己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从《爱药》可以看出,印第安作家的生态情怀是有别于白人主流文学中的怀旧和牧歌情结。他们在展示印第安人独特的地理景观时,更加关注部族的精神状况,他们对地理景观和回归传统的强调,对印第安族群的关怀,与现代生态学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不谋而合,也为当今文化多元社会中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王诺.欧美生态批评[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Silko,Leslie Marmon.Storyteller[M].New York:Seaver Books,1981.
[3]Allen,Paula Gunn.Grandmothers of the Light:A Medicine Woman’s Sourcebook[M].Boston:Beacon Press,1991.
[4]〔美〕路易斯·厄德里克.爱药[M].张廷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5]Erdrich,Louise.Tracks[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88.
[6]张明兰.绿色之思——析20世纪美国生态诗歌的主题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1,(2).
[7]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8]Snyder,Gary.The Real Work:Interviews and Talks 1964-1979[M].New York:New Directions Book ,1980.
[9]Silko,Leslie Marmon.Conversations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M].Ellen L.Arnold,ed.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0.
[10]Dreese,Dorelle N.Ecocriticism:Creating Self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an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M].New York:Peter Lang,2002.
张明兰(1967-),女,硕士,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