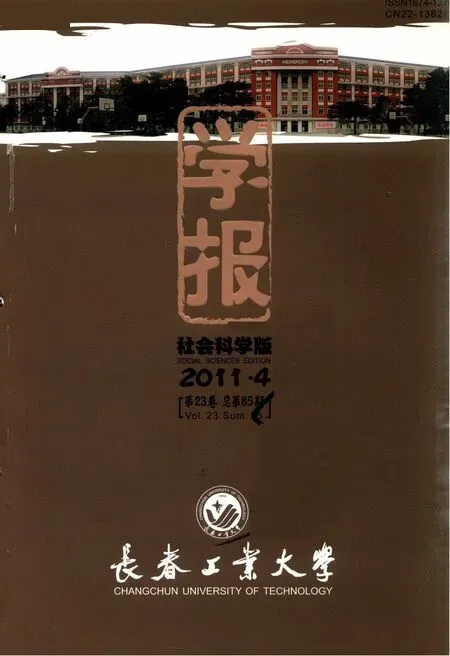《爱泼斯坦》“逾越”叙事探究
2011-03-31金万锋
金万锋
(长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爱泼斯坦》“逾越”叙事探究
金万锋
(长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菲利普·罗斯《爱泼斯坦》尝试以戏谑、反讽的手法描写了一位因突发激情而陷入道德困境的美国犹太老人的故事,令人捧腹的同时亦不禁为其叹惋。本文探讨了促成爱泼斯坦逾越常规行为发生的诸种原因,揭示出爱泼斯坦逾越行为并非表象所示的对犹太传统的颠覆,反而佐证了犹太传统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了罗斯对传统的肯定与坚持。
菲利普·罗斯;《爱泼斯坦》;逾越;叙事
对于菲利普·罗斯的短篇小说《爱泼斯坦》,《纽约时代书评》如是评价:“一位老人在追寻爱情时所引发的令人感觉既可笑又可悲”的故事,并因其“展现了美国犹太人的负面形象,给罗斯带来了‘反犹主义者’的指控”。[1](P27)《美国作家增刊III》则认为爱泼斯坦是“孤独的个体又一次被置于与民族道德感(而非意识形态)发生激烈冲突的境地”。[2](P406)对爱泼斯坦这个形象,罗斯自己则坚持:“他是不是犹太人并不重要;正是由于他的困境变得越发清晰,才激发了我极大地乐趣。”[3](P71)对于罗斯而言,人物塑造的过程就是“表现一种人生经历,展现道德问题所带来的困惑与危机。……我的小说所关注的是那些深陷困境中的人们。”[4](P2)
对于《爱泼斯坦》的诸多解读,大多集中凸显了主人公爱泼斯坦试图突破传统、摆脱束缚的一面,描绘其徒劳挣扎而不可得的尴尬境地,但也仅止于此,并未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本文则通过对逾越叙事的分析来说明爱泼斯坦意欲冲破犹太传统是不可实现的梦幻,他的行为无意识中反而增强了犹太文化加诸于社区成员的影响力,以希帮助读者更好理解罗斯对所处时代的独特体认与感知。
一、“逾越”探源
逾越,顾名思义,即为“超脱戒令、法律和传统所设置的规诫与限定”,但其内涵却不止于此。逾越亦可以被看成“一种对否定和肯定行动都深有所指的行为”,因此逾越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宣传甚至褒扬那些戒令、法律和传统”,[5](P2)其表面的悖论实则蕴含着思辨的理性光辉。
逾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着漫长的形迹。由于中国儒家思想提倡“中庸之道”并奉之为圭臬,导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视锐意革新、试图超越的思想内容为洪水猛兽,无情地给予限制和打压。如此行事使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结构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人为地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及至清王朝末年,中国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导致梁启超发出了“少年中国”的呼号。基于此,对于逾越的研究中国不是一个很好的话语场,而典型“海洋性”大陆―欧洲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在西方文化典籍中,最早具有逾越特征的形象是柏拉图笔下那个看到阳光的“洞中人”,在其返回洞中向乡党“传授”光明的时候却被愤怒的人群撕成了碎片,这个洞中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发现违背并威胁到洞中人长久以来的信念,因而为社会所不容,他的死亡则巩固了“洞中人”的集体信念。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中的“三段论”思想则使逾越概念的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因为界定逾越是否发生的一个根本标准是该现象是否背离了传统或广为接受的事实,而“三段论”非此即彼的推论方式促成了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无情地抹杀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使更多的事物被打入另册。[5](P9-10)启蒙时代的人们坚信理性的升华能够帮助人类到达最终的完善状态,这种对工具理性的坚持与强调致使人们混淆了社会进步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区别,导致他们坚决反对有悖理性的做法,从而使逾越社会常规成为无法容忍的行为。尼采的逻辑思辨对现存社会形态合理性提出质疑,最终宣告“上帝死了”,从而拉开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反传统帷幕。人们千百年来信奉的确定性幻境被粉碎,肇始了20世纪对逾越概念的探究。[5](P4-5)
20世纪文艺理论界对于逾越概念的阐述始于心理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弗氏在很多著作中都对逾越做过阐释,尤其以《图腾与禁忌》最为直接、最具代表性。在这部作品中,弗氏论及禁忌难以界定时指出,“它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对我们而言,它在意味着‘神圣’、‘圣洁’的同时,也呈现出‘怪异’、‘危险’、‘禁止’、‘不洁’的特征”。[6](P18)而在弗洛伊德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对禁忌问题的深入思考为文学批评增加了“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两个术语;这组术语正是通过潜意识中对伦理观念的逾越而实现的,反过来这两个命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潜意识中乱伦冲动的了解,并试图在理性世界中避免如是情况的发生。另一位对逾越概念进行阐释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批评家是巴赫金,他从“狂欢化”视角对逾越进行了揭示。巴赫金坚持语言的对话性特征,肯定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多声部对话的复调特征。这样,巴赫金就消解了语言的高低贵贱之分。正是由于意识到语言的这种性质,巴赫金才在阅读拉伯雷作品后描绘了一幅不同于日常交流的图景:“狂欢节期间等级观念的暂时休眠会产生一种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交流方式。这会导致一种奇特的自由而坦率的市井话语和身势语的出现,使交流中的人没有任何间离感,从而帮助他们摆脱平时礼仪原则的限制”。[5](P165)这样,“狂欢化”就作为对立于日常生活规范的概念呈现出来,但人人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的狂欢过后,意即短暂的宣泄结束后,一切社会等级秩序依旧,甚至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实现了新一轮的循环,所以说逾越的结束标志着新的逾越行为的开始。弗洛伊德、巴赫金等人的文学思想启迪着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帮助他们逐渐意识到逾越现象在(后)现代生活“再现”方面的重要意义,并自觉地把其纳入到自己批评或创作视野中。
二、爱泼斯坦的“逾越”之旅
菲利普·罗斯正是这样一位自觉对逾越叙事孜孜不倦进行探究的大家,并藉此使自己的创作获得了“真实性与艺术权威”。[7](P487)综观罗斯的创作轨迹,其早期作品《爱泼斯坦》已经把逾越叙事作为探讨当代美国人生存困境的重要手段来运用,而这一手法的使用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促使他们思考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体命运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小说中的爱泼斯坦是一位典型的犹太移民,7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到达新大陆后,他们初次接受的“洗礼”竟是从头而降、用来去除头发中虱子的汽油,这成为他记忆中永远的噩梦。凭借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亲力亲为的辛劳,他最终在美国站稳了脚跟,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但即将退休的爱泼斯坦却陷入困境:由于没有合适子女来继承家业,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恐将落入他人之手。对公司命运的忧虑成为他生活的重心,影响着对他人的态度,并最终促成了爱泼斯坦生命中所不能承受的逾越之旅。而这一切都要从访客米歇尔说起。
米歇尔是爱泼斯坦多年未见的侄子,这次遵从父亲的嘱托来看望爱泼斯坦一家。彬彬有礼而又活力四射的米歇尔与爱泼斯坦的女儿希拉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使爱泼斯坦进一步意识自己家里那个美丽的婴孩已经变成一个热衷于政治的妇女,白天参与政治游行,夜晚则回到家里狼吞虎咽,全无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应有的气质。
不但希拉的政治热情令爱泼斯坦难以接受,她所选择的未婚夫民歌手更让爱泼斯坦难以认可。在爱泼斯坦眼中,民歌手背离了犹太尊重学识、扎实肯干的优良传统,是一个靠酒吧卖唱谋生的懒鬼,换言之,一个不务正业的登徒子。而且,民歌手对于历史的看客态度也令爱泼斯坦反感不已。他甚至问爱泼斯坦是否对三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对“社会动荡”有切身体会的爱泼斯坦,无法认同这种轻狂而肤浅的处世态度,并深恶痛绝其置身事外、做远观状的姿态。对爱泼斯坦而言,民歌手无力继承并发展自己的产业,也无法保持并发扬几千年来的犹太传统。此外,民歌手与希拉在性方面也恣意妄为,毫无顾忌,使爱泼斯坦不堪其苦。
而米歇尔的到来表明,并非仅有希拉和民歌手受到了性解放思潮的冲击。米歇尔与临街女孩琳达的“拉链”表演使爱泼斯坦不胜其烦,起身欲痛斥之,却目睹了两个年轻人的激情,心头为之一震,无法挪开自己的脚步,爱泼斯坦深埋心底的对肉体的渴望被唤醒了。
在爱泼斯坦心中,琳达赤裸裸、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肉体与妻子戈尔蒂臃肿而松弛的肉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戈尔蒂更衣就寝时,映入爱泼斯坦眼帘的是她那下垂的乳房、多肉的腰身,此时,他惟有紧闭双目,凭借对昔日美好形象的回忆来打发时光。但琳达与马歇尔激情一幕使爱泼斯坦燃起了对生活的向往与冲动,把对琳达青春活力的渴望投射到她的母亲艾达身上,并最终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爱泼斯坦认识艾达,知道她新近丧夫,但由于自己每日都在为纸袋公司奔波,所以从未仔细注意过她。琳达对爱泼斯坦造成的视觉冲击却使他对艾达的身体进行了再审视,透过衣袖,他仿佛看见了那晚琳达赤裸裸的胴体。潜意识支配下的爱泼斯坦不自觉地把车子停下来请艾达搭乘,启动时却把加速器踩得过猛而使车子猛然向前冲去,这一不经意间的动作一方面表现出爱泼斯坦在和艾达单独相处时的紧张、无措和渴望等复杂的心情,同时也预示着从此爱泼斯坦的生活将和这辆车的启动方式一样不同于往日,开启一段全新并失控了的人生旅程。
真正促使爱泼斯坦把对身体的潜意识渴望付诸实践的是罗斯在创作中所着力表现的一种特殊话语方式,即“犹太玩笑”(Jewish joke)。罗斯认为这种话语方式可以用来展现“一个彻底去神圣化的世界,在这里已无神秘感可言,非浪漫化特征明显,因而人们能够猛然警醒”。[8](P7)爱泼斯坦与艾达间的对话正是这种话语的绝好体现。几句看似平常的开场白把爱泼斯坦因偷窥而产生的窘迫感逼得无处遁形,但随后艾达的玩笑却使爱泼斯坦轻松起来。一句米歇尔真象你的评论,使爱泼斯坦想起了“你的孩子像冰铺老板”的玩笑,联想到身材严重走形的弟妹,他不禁莞尔。面对如此大胆的玩笑,爱泼斯坦也打趣回应,问琳达像谁,不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无所谓的耸耸肩,像是在说谁在乎呢。面对幽默感如此丰富的女人,爱泼斯坦不禁放声大笑,多年来与奉自己的话为“金科玉律”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所导致的压抑心情好像一瞬间得到了宣泄。笑是很好的粘合剂,使两个人的心贴近,所以他们的目的地不再是市场街,而是变成了艾达在巴纳加特的别墅。
这一日的旅途中,并非仅有欢声笑语,还有警察开出的三张传票。第一张是由于开玩笑没有看到红灯,所以警察给了爱泼斯坦一张传票;第二张是去巴纳加特的路上被开出的;而第三张是由于为了赶回家吃晚饭而在公路上超速行驶时而被开据的。三张传票的出现不但促成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而且它们也是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对逾越行为所持立场的象征,是对爱泼斯坦逾越行径的监控与否定,预示着爱泼斯坦将不得不为自己的逾越行为负责任,受到应有的惩戒。
惩戒首先以“疹子”的形式出现在爱泼斯坦的私处,成为家庭伦理法庭的导火索。妻子戈尔蒂一面作势要把床单烧掉,一面对爱泼斯坦高叫,不许他走近,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其他家庭成员与访客相继登场,行使着道德纠察员的职权。希拉坚定地站在母亲的立场,像肩负着使命一样坚守在门口,把意欲赶自己离开的父亲推了回去;米歇尔双腿也像生了根一样,立在那里关注着事情的进展;而那位有强烈“窥视欲”的民歌手上窜下跳,把爱泼斯坦的“疹子”定性为梅毒,引发冲突向高潮发展。赤裸裸暴露于晚辈面前的爱泼斯坦,尊严尽失,下意识地解释着“疹子”的来源,他的内心困窘可见一斑。但家庭伦理审查并未止于此。
当晚,爱泼斯坦不得不和侄子米歇尔共处一室,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想从米歇尔处获得一点理解与同情作为慰藉。爱泼斯坦谈到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谈到了移民美国时受到的羞辱,但深埋在他心底的却是对戈尔蒂深深的失望,是对“美女”变成“清洗机”的抱怨,是对往日生活情趣的无限留恋。而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米歇尔没有给爱泼斯坦任何喘息之机,坚称有些事就是不可为。无奈之下,爱泼斯坦只好自我解嘲,“什么对啦错啦,只有天知道!只要你眼中掉点泪水,还有谁能分得清对与错,是与非!”[9](P57)
翌日天明,冷战成为爱泼斯坦家庭伦理剧场的主旋律。爱泼斯坦发现民歌手已经履行了他每个星期天的传统职责,并在那里如“小丑般”地拨动着琴弦,哼着临时起意、充满讽刺意味的调子;戈尔蒂也对其尽嘲讽之能事,几乎句句不离梅毒带来的后果;而希拉更是坚决,声称爱泼斯坦没有资格做自己的父亲。忍无可忍的爱泼斯坦来到便餐馆,恰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充满生气的窈窕少女弯腰系鞋带,不禁瞧着她出神,手中的咖啡竟溢出并洒落在衬衫的前襟上,象征性地惩罚了这不伦的关注,也使爱泼斯坦猛然意识到自己道德上的失范,发出我到底是怎么了的哀鸣。但此时的幡然悔悟已然有些迟了,走到街上的爱泼斯坦颇有走投无路的感觉,而此时艾达的适时出现成为了爱泼斯坦的救命稻草,虽然有些迟疑、有些顾忌,但最终他还是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向艾达的房子走去。
惩戒又一次发生了,并且来得更加猛烈。当整个街区的人们还都沉浸在周末清晨的闲适时,一辆救护车的呼啸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把人们的注意力带到了街上。车子停在艾达的家门口,一名年轻的医生和他的助手平稳地抬出一个担架,当人们都在猜测可怜的艾达母女又发生了什么不幸时,戈尔蒂却看出躺在担架上的人原来竟是自己的丈夫,她大喊着丈夫的名字,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这样,爱泼斯坦超越婚姻界限的逾越行为完全暴露在整个社区成员的面前,成为人们的谈资,接受人们的道德评判,并被作为反面教材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选择道德的生活。
社会道德舆论惩戒的同时,肉体上的惩戒也是几近致命的。公司后继乏人的烦恼、肉体的愉悦、做贼心虚的羞耻感、对家人的失望等因素导致爱泼斯坦心脏病突发,为自己的逾越行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面对戈尔蒂的询问,医生建议爱泼斯坦只有过正常人的生活,身体才能逐渐才能好起来。一向对爱泼斯坦惟命是从的戈尔蒂,竟自作主张,决定把希拉嫁给民歌手,由他来接管公司的经营,并决定爱泼斯坦退休后,两个人去旅游。听到戈尔蒂的话,爱泼斯坦张口欲表达意见,但他的舌头却无力地垂在牙齿的外面,已经暂时丧失了表达的能力,在语言上被阉割了,最终只能翻了翻白眼,无力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作为婚姻越界罪证的“疹子”在戈尔蒂的请求下,最终也将被医生彻底的医好,至此一个完整的逾越过程已经完成。但事情并未仅仅止于爱泼斯坦因超越婚姻的界限有了婚外情而受到惩罚那么简单,因为这一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强势的男主人爱泼斯坦已经丧失了在家庭中、社区中的传统地位与权威,取而代之的是其妻子戈尔蒂,一句“有我你就放心吧”包含了太多的意蕴在里面。由此可见,爱泼斯坦的逾越行为造成的后果反而是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回归与认可,是犹太传统的胜利,使人们对家庭生活有了新的体会与认识。
三、结语
《爱泼斯坦》等作品“不仅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且现在读来仍有新意,并帮助人们从后现代的身份理论、族群特性、消费主义以及美国梦等角度进行新的阅读”,[10](P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逾越叙事为切入点对爱泼斯坦的越轨行为进行了分析与阐释,认为罗斯在进行创作时,并未仅把注意力放在越轨行为本身,而在于探论它的意义与影响,意在说明逾越行为在否定的同时,往往更注重对传统与被逾越内容的肯定与坚守,意在揭示犹太传统与当代美国犹太人视角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逾越叙事贯穿罗斯创作始终,具有了某种“母题”地位,已然成为从事罗斯研究的学者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之一。
[1]Jones,J.P.,Nance,G.A.Philip Roth[M].NY: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1.
[2]Baechler L.Litz A.W.American Writers Supplement III,Part 2[M].N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
[3]Roth,Philip.“Second Dialogue in Israel.”[J].Congress Bi-Weekly.16Sept.1963.
[4]Searles,G.J.ed.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M].Jackson & London:UP of Mississippi,1992.
[5]Jenks,Chris.Transgression[M].London:Routledge,2003.
[6]Freud,S. Totem and Taboo[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0.
[7]Greenberg,Robert M.“Transgression in 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997)4.
[8]Roth,Philip.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M].NY:Farrar,Straus,and Giroux,1975.
[9]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M].俞理明,甘兴发,朱涌鑫,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Royal,D.Parker,ed.Philip Roth: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M].Westport:Greenwood-Praeger,2005.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逾越之旅—菲利普·罗斯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1]第51号)。
金万锋(1978-),男,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犹太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