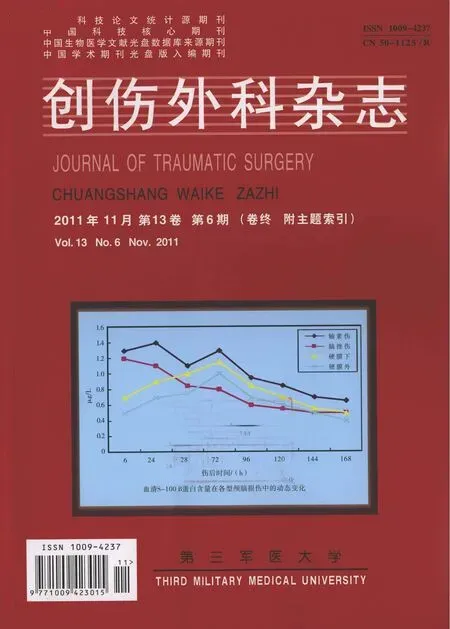浅谈转化医学在脓毒症治疗研究中的作用
2011-03-31李磊
李 磊
所谓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指将基础医学研究中发现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向临床实践中的转化应用,而所谓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来源于临床实践活动中一些未知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实验研究,综合归纳,从而推导出来的对疾病临床治疗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验证的过程。从疾病的命名,分类,以及相关致病机制和各项治疗措施不断发展的历史沿革看,朴素的转化医学思想贯穿了整个临床医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当前,随着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的日益更新,人类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转化医学的不断深入。笔者以脓毒症概念的变迁及其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浅谈对转化医学的管陋之见。
“Sepsis”,目前中文多译为脓毒症。其最原始的称谓来自2700年前的荷马史诗中,随后由希腊学者Hippocrates用于描述战争中发生感染的伤员。sepsis来源于希腊单词“sipsi”,意思为“make rotten”(变腐),强调的是因各种损伤后导致血液的腐败。直到19世纪后叶巴斯德发现细菌,人们才认识到,导致血液“腐败”的病因是致病微生物。1914年Schottmueller将“微生物从人体的门户侵入血液引起疾病征象的状态”称之为septicemia,也即是中文的“败血症”。无论是原始的“sepsis”或是“septicemia”,都是指细菌进入体内产生毒素,引起发热为代表的临床表现。从中文字面上看,败血症,也是指血液发生了“败坏”,为进一步明确,人们又提出了“菌血症”的概念,进一步强调在血液中检测到了细菌(相应病毒血症、寄生虫血症、真菌血症等与此类同)。上述这些概念,强调的是病原微生物对机体的侵袭造成的感染征象,而忽略了机体对入侵病原体的反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炎症和炎症介质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sepsis的发生发展并非只依赖于细菌和细菌毒素,大量炎症介质的释放,同样可以造成类似病原微生物感染的临床表现。为此,1991年8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CCP)和危重病学会(SCCM)联席会,首次提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的概念,认为 SIRS 应包括由感染导致的脓毒症,和非感染因素导致的炎症反应综合征两部分。相应,败血症、菌血症等概念由于不能很好地诠释机体在遭受病原微生物感染时的病理生理状态,也到了该摒弃的时候。
SIRS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首次明确的指出,由感染或非感染因素(包括严重创伤、无菌性胰腺炎等)导致的炎症反应才是导致患者病情危重及死亡的真正原因。虽然炎症概念的提出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明确宿主对致病因素的反应是导致疾病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无疑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后在2000年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免疫炎症休克大会上,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混合型炎症反应综合征(mixed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MARS)等概念相继提出,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炎症和炎症反应的认识和理解。创伤也被认为是一种炎症性疾病。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创伤脓毒症时,机体处于一种免疫功能紊乱状态,在过度炎症反应的同时,机体免疫防御功能处于明显的受抑状态[1]。因此,针对脓毒症的治疗,不仅需要抗炎,同时还需要提高机体免疫防御功能,因此利用乌司他丁抑制过度炎症反应,同时结合α-胸腺肽提高机体的免疫防御功能和抗原提呈功能,使得脓毒症患者预后得到有效改善。最近研究证实,由于创伤脓毒症状态下,机体胸腺功能进行性衰竭,因此辅以leptin治疗可收到较好的疗效[2]。
显然,脓毒症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血液中存在着有害物质;巴斯德发现细菌并创立的巴斯消毒法,大大降低了外科感染发生率,促进了现代外科学的进步;败血症、菌血症概念的提出,推动了抗感染技术和抗生素的发展;而SIRS和sepsis新概念的定义,使人们对感染的关注点转移到宿主对病原微生物反应造成的炎症性损害上,从而使危重病人的监护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对脓毒症和SIRS的深入了解,使我们对感染的概念有进一步的理解。但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机体所面对的外部世界非常复杂,病原微生物的种类繁多,且每一种病菌又存在众多的血清类型,机体怎样对这些微生物进行识别,识别的机制又是怎样。
Medzhitov和Janeway1998年提出在哺乳类动物天然免疫系统存在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s),可识别从病毒、细菌直到寄生虫等病原体保守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而其相应的受体则是存在于天然免疫细胞上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recognitionreceptor,PRR)。TLRs是广泛存在于天然免疫细胞膜上的最具代表性的PRR,现已发现其识别的配体分别为:来自革兰阴性菌内毒素的脂多糖(LPS,TLR4配体);细菌脂蛋白、脂磷壁酸、酵母多糖(TLR1、TLR2、TLR6配体);细菌鞭毛蛋白(TLR5配体);弓形虫profilin样分子(TLR11配体);细菌DNA非甲基化的CpG基序(TLR9配体),病毒双链RNA(TLR3配体),病毒单链RNA(TLR7和TLR8配体)等。
新近研究发现[3],PRR 不仅可识别 PAMP,更重要的是识别各种可对机体造成损害的“危险信号”,也即是Matzinger等所提出“危险相关分子模式”(danger-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s)的概念。当机体受到创伤、感染,以及其它危险因素刺激时,由于组织的损伤以及细胞的裂解,藏匿于机体细胞内的这些危险信号可被释放,并由相应的PRR识别。PRR不仅存在于天然免疫细胞的膜上,在细胞质中,同样存在类似于TLRs的模式识别受体,被称为 NLRs(NOD-like receptor,或 nucleotide-binding domainleucine-rich repeat containing)。NLRs的功能也与TLRs类似,当受到刺激后NLR同样可以通过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kinase,MAPK),活化核转录因子 NF-κB,诱导炎症反应,但更为重要的是,NLRs可通过对炎症复合体(inflammasome)的激活,诱导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的活化,促进IL-1、IL-18和IL-33前体的剪切成熟,从而引发炎症介质的级联释放,参与脓毒性损害的发生和发展[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通常诱导TLRs活化的配体多为存在于细胞外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保守基序,而NLRs不仅可识别细胞内与机体细胞共栖共生的病菌,如结核杆菌、李斯特菌、军团菌等,还可识别因感染、损伤、低氧、应激等引起的多种细胞产物,如热休克蛋白、染色质及核酸裂解片段、纤维连结蛋白、层黏蛋白、纤维蛋白原、尿酸结晶、高迁移率蛋白族1(HMGB1)等,甚至过量的ATP刺激,以及钾离子外流形成的细胞内低钾状态均可被 NLRs识别[5]。
上述研究进展提示,在创伤诱发的SIRS和脓毒症过程中,病理生理过程极为复杂,更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深入研究。然而,无需讳言的是,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同样存在终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法则。医学领域分支日益增多,虽然能为我们对疾病的理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系统和整体的忽略,标本不能兼顾、顾此失彼而加重对伤病员损害的病例逐年增多。疾病的发生是人体这个大系统面对体内外各种压力与刺激下的平衡失调,近年来注重系统、注重整体治疗的呼声日益升高。有害模式识别理论、损害控制理论,个性化治疗理论,以及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炎症组学及医学社会心理学等概念的诞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6]。
当今世界,创新(innovation),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ity),和整合(integration)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三I”大趋势。现代外科学已进入四R时代[去除病原(resection),修复组织(reconstruction),替代治疗(replacement),再生医学(regeneration)]。与之相应的信息化、显微化、个体化,以及转化医学已成为当今外科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四化”特征。
临床医学是一个以经验性为主的学科,如何借鉴当今众多的理论知识和架构,去指导临床救治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因而转化医学近年来备受关注[7]。从脓毒症概念及含义的变迁可以看出,转化医学的思想已贯穿始终,如何更有效地从病床旁(bedside)发现问题,置于试验台上(bench)研究,再返回病床旁(bedside)实践验证成为转化医学最核心的问题。
从Hipporates将Sepsis应用于临床到巴斯德发现病原菌,人类走过了千年的历史;从败血症、菌血症概念的提出到SIRS概念的诞生,花费了近百年,但从病原相关分子模式到危险刺激信号系统的建立仅用了10年,表明当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医学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朴素的转化医学思想也需适应当前科学发展的现状,发挥其前所未有的作用。
笔者以为当前转化医学的运行模式应该为:在组织机构上,应建立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紧密性医疗单元,貌合神离的松散组织于事无补。在组织形式上,应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双向学术交流制度,促使科研人员主动参与临床危重、疑难病例的讨论,鞭策临床学家积极介入基础研究项目;在学术思想上,科研人员应面向临床寻找科研课题,临床工作者应将临床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主动与科研人员交流;在项目管理上,应积极鼓励和大力扶持针对临床实践中存在或发现的问题所设置的研究课题;在项目实施上,应由临床人员和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完成;在成果共享上,应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意识,提倡科研人员和临床人员互为主配角意识。相信随着脓毒症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学家与基础医学家之间建立良好的3B运行模式(bedside-bench-bedside model),无疑是彻底改善脓毒症最有效的发展策略。
[1] WynnJ,Cornell TT,Hector R,et al.The host response to sepsis and developmental impact[J].Pediatrics,2010,125(5):1031-1041.
[2] Tschöp J,Dattilo JR,Prakash PS,et al.The leptinsystem:a potential target for sepsis induced immune suppression[J].Endocr Metab Immune Disord Drug Targets,2010,10(4):336-347.
[3] Joao HF,Pedra J,Casse SL,et al.Sensing pathogens and danger signals by the inflammasome[J].Curr OpinImmunol,2009,21(1):10-16.
[4] MartinonF,Mayor A,Tschopp J.The inflammasomes Guardians of the body[J].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2009,27:229-265.
[5] Ting JP,Lovering RC,Alnemri ES,et al.The NLR gene family:a standard nomenclature[J].Immunity,2008,28(3):285-287.
[6]李磊,王正国.炎症组学-应运而生的新概念[J].中华创伤杂志,2010,26(1):3-5.
[7] Proudfoot AG,McAuley DF,Hind M,et al.Translational research:what does it mean,what has it delivered and what might it deliver[J].Curr OpinCrit Care,2011,Epub ahead of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