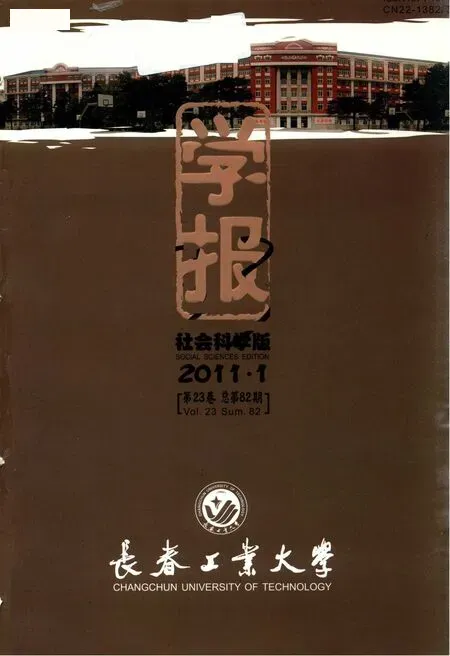大革命时期汪精卫急剧走向叛变的原由探讨
2011-03-31王鹏程张运洪
王鹏程张运洪
(1.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武汉 430022;2.防空兵指挥学院政治部,河南郑州 450052)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急剧走向叛变的原由探讨
王鹏程1张运洪2
(1.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武汉 430022;2.防空兵指挥学院政治部,河南郑州 450052)
大革命后期汪精卫的叛变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叛变的根本原因,是其资产阶级属性使然。然而,“迎汪复职”、“拥汪反蒋”中对汪精卫的过分迁就,导致了他随后的巨大心理反差,使其认为共产党不可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不可依靠,国共迟早要分家;工农运动中的过激行动,造成社会秩序动荡,军心不稳,对汪精卫急速右转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莫斯科五月来信及罗易的“泄密”,更是在客观上加速了汪精卫“分共”的步伐。
大革命;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汪精卫;叛变
蒋介石于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曾一度采取“联共反蒋”政策。但从5月底到6月初,汪精卫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转变,并最终决定“七·一五”“分共”,背叛了国民革命。汪精卫叛变的根本原因是其资产阶级阶级属性使然。除此之外,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等,也对汪精卫的叛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谨就这个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迎汪复职”“拥汪反蒋”中对汪精卫迁就,导致了其后来巨大的心理落差
1926年底,随着北伐战争顺利进行,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用心日渐显露,政治态度日益右转。在这种情况下,为遏制蒋介石专权,国民党左派掀起了“迎汪复职”运动,希望通过汪精卫回国掌握党权来抑制蒋介石的军权。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也很欣赏汪精卫,根据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精神,1926年12月中旬,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等七项挽救危局的措施。[1](P565-567)会议经过争论,通过了这个报告。于是,“迎汪回国”、“拥汪反蒋”,便成为当时中共的重要策略。中共中央认为,只要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中心,就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同样,苏联顾问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对汪精卫十分看好。苏联顾问鲍罗廷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出,迎汪复职“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于是提出让汪精卫回国、建立军事委员会等措施以与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相抗衡。[2](P261)汪精卫在归国途中曾经路过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得到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都将给予全力支持的允诺。[3](P116)由于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都过于轻率地信任汪精卫,一直视他为“左派的唯一首领”,幻想依靠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来挽救危机,所以基本上对汪不设防。
中共中央期望与汪精卫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立场,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得到了确认和强调。“五大”还破天荒地邀请汪精卫列席了一天会议,并允许他旁听罗易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报告。罗易作报告时,汪精卫“非常注意倾听”,并发表了演说。他宣称,虽然他一般也同意提纲中谈到的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未必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4](P274)并且他向参加大会的代表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共产国际是否认为小资产阶级能够跟从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罗易发表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罗易说,在现阶段共产党将同国民党合作,但必须以共产党不仅分担责任而且也要共同有权为条件。然而,三个阶级(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纲领将不可避免地引向社会主义,在这一发展中,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队,将决定通往社会主义方向的进程。[3](P83)这个讲话被某些代表批评为“不策略的攻击”。它使汪精卫明白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策略中,他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联合的对象,而不是像“迎汪复职”时讲的请他出来领导;明白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力争领导权的。因而他认为共产党不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不可依靠,国共迟早要分家。在革命的危机关头,汪精卫一方面在口头上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
二、工农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对其思想转变也有一定影响
其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不足和指导思想上的偏颇,两湖一带的工农运动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发生了若干过激行为。如工人动辄罢工,“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提出“使企业倒闭”、“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等种种“过度”的要求;[5](P576)农会随意行使权力,捕人、罚款、毁庙、分浮财,提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口号,甚至没收普通士兵寄回家的饷钱。这些“左”倾错误的蔓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动荡,军心不稳。这种情况,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基础,对汪精卫的权力和地位也构成了严重威胁,使汪精卫对共产党产生了强烈不满。对于武汉政府的危机,汪精卫把主要罪责归结于共产党,认为工农运动过火是武汉政府财政困难和军人政变的直接原因,深感自己既受到蒋介石的封锁和压迫,又受到共产党的“威胁”,处于“夹攻中”,要摆脱困境,必须分共。汪精卫的这一态度可以从如下材料中看出。中共五大后,陈独秀与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在谈话中汪精卫提出以下四点:(1)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2)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3)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4)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最后,“汪精卫总结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对人民群众来说会更糟糕。”[2](P248-249)由此可见,此时汪精卫心中已深深埋下了对苏联和中共不满的种子。
三、莫斯科的《五月指示》与罗易“泄密”,加速了汪精卫“分共”的步伐
中共“五大”结束后,国内政治形势又发生急剧变化。夏斗寅叛乱、“马日事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赣等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国民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国共合作到了最后关头,破裂已是在所难免。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仍把汪精卫等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当作国民党左派、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团结汪精卫作为“全部政策的中心”,害怕他们被大资产阶级拉走。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会,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为了贯彻这一“中心”,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放弃建立、掌握自己武装的机会;放弃湖南暴动反抗许克祥叛变的计划;放弃江西暴动讨伐朱培德的计划;放弃土地革命的原则。
但是,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及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即“五月指示”。“五月指示”的要点是:中共应厉行土地革命;要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袖去充实国民党中央;要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建新军;要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等。[2](P298-300)“五月指示”反映了莫斯科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举棋不定,朝令夕改。“五月指示”一改过去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激烈的手段来对付国民党右派和改造国民党,由此挽救中国革命。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指示是不切实际的,很难执行。中共中央最终也没有执行,但“五月指示”仍给中共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五月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它促使汪精卫思想进一步右转。罗易出于“想在那个紧急关头进行最后的努力,去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的考虑,“于是,就把莫斯科来电送给他”。[3](P117)当汪精卫从“五月指示”得知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新态度”的实质时,他“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在汪精卫看来,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利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7]“天真”的罗易的鲁莽言行使汪精卫觉得“共产党在策划政变”,[3](P119)使他进一步感到了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的威胁,认为国共合作同坐的船,已经到了终点,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遂决心加速反共。
汪精卫在得到“五月指示”信息后不久,立即动身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郑州会议,冯玉祥政治态度的转变加深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促使汪精卫进一步右转。1927年6月13日,汪精卫等自郑州回到武汉。15日,武汉各界召开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凯旋大会,议决讨伐蒋介石,恳请中央拿办许克祥,抗议江西驱逐农工领袖等。会后,各团体向武汉政府请愿,湖北总工会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同意,散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喊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等口号。汪精卫由此更加怀疑共产党人联络军队反对他,流泪切齿地对鲍罗廷、陈独秀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指总工会)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6](P86)此后,汪精卫集团议论的中心就是如何“分共”的问题。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作者注)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8](P510)这时,中共主要负责人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且企图以进一步的退让来争取汪精卫等人继续革命。7月3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继续主张妥协退让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只是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参加,为减少政局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等等。[9](P726)但是种种让步都未能阻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对汪精卫叛变革命原因的分析,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俄罗斯新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全面地历史地进行分析,既要看到他叛变革命的主观原因,也要分析客观因素对其叛变革命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Z].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M].王淇,杨云若,朱菊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六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册补编(1919—1927)[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汪精卫.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N].汉口民国日报,1927-07-18.
[8]刘继增.武汉国民政府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9]魏宏远.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2)[Z].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王鹏程(1970-),男,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